20世纪电影巨星的自传、笔记、访谈录甚至日记,无疑是近年来国内出版业的热点。
像路易斯·布努埃尔(1900-1983),费德里科·费里尼(1920-1993),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1996),英格玛·伯格曼(1918-2007)和米凯莱洛·伯格曼(Michelelogni),1912-2007自传,对Rainer Werner Fassbender(1945-1982)的采访,Anders(Wim Wenders,1945-)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笔记和日记(1932-1986),亨利耶 - 布列松的散文和散文(1908-2004)是它的本质。
它们的受欢迎程度显然是中国家庭影院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性,使得电影史上的杰作,只属于专门机构的数据室(甚至不一定),非常简单,成为粉丝的私人收藏。如果有毅力,有心情,仅仅两三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就列出了近1万部(主要是西方)艺术电影,这似乎并不难。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从电影发行之初以及后来从作品本身的成功中出现的专家视角?
严格来说,上述真正有意义的读物很少,更何况它们提供了更多的作者自己的思想,他们在创作作品前后的思想变化,情绪波动和世俗的征兆,而且,似乎是基于某种游戏规则,它们似乎刻意回避了对他人作品的批评, 而说到自己的作品,他们似乎更愿意谈论怪癖的幕后制作(这恰好是大多数读者的兴趣所在)。
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而暂时的现象,我们积累了很多关于艺术电影的介绍和信息文本,但个性化评论的真正含义,即回答为什么一部电影好,好的地方这些基本问题的文字,用来判断和解释有价值的文字,还是很少见的, 而各种电影史教科书中的批判文本,要么是一字论证,要么是泛泛而谈的语言。
总之,一个真诚的、独特的见解,涉及范围广泛、有据可查的价值,最好是从电影大师手中的影评收藏,应该呈现给有一定视野的影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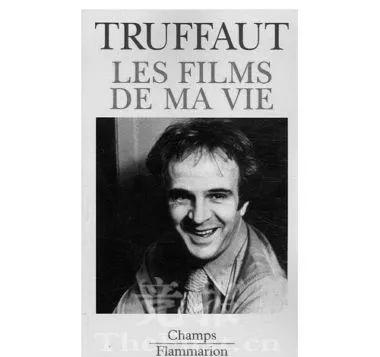
52岁的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1932-1984)中国大陆 在1980年代中期首次接受了电影界的新浪潮大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表演了他的热门歌曲《最后的地铁》(The Last Subway),被认为是对商业的妥协。
今天,从粉丝的角度来审视他的作品,你无法习惯他的编剧《筋疲力尽》(导演戈达尔),不喜欢《昼夜的黑暗》中关于琐碎导演生活的启示,不接受他模仿希区柯克的电影,但你不能拒绝他的自传《四百下》、《七和吉姆》,它探讨了三人关系的可能性, 和"阿黛尔·雨果"作为一个奇怪的心理成长备忘录。
他的演艺生涯同样具有传奇色彩,他的成长经历是他在14岁时辍学,在巴黎的电影院及其周边地区工作,直到七年后他遇到了巴赞,并开始为着名的电影手册撰写评论,当时他完成了3000多部电影收藏,开始了他前往学院的旅程。
《特雷弗:我一生的电影》中的文字可以通过《四百人》(1958年)的时代来区分,特雷弗作为影评人写的,然后是特雷弗作为导演写的,共同点是对电影的热爱,其真诚,直觉和灵感的时刻构成了这些词的基础。
这本书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献给默片时代,在有声时代继续大放异彩,这些知道"他们过去没有浪费电影"(Jean Renoir)名字的人,包括卓别林和特雷弗一生的偶像希区柯克,以及Abel Guns,Jean Vigo, 德雷尔和约翰·福特。
第二部分,"有声电影时代:美国人",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1958年对库布里克的"荣耀之路"的影评,也许是第一份有价值的文件,肯定了库克鲁姆的才华并预见了其未来的成就。
这就像另一部关于吕美特处女作《十二个愤怒的人》(1957)的不遗余力的广受好评的作品,而今年,俄罗斯导演米哈尔科夫(Mikhalkov)刚刚对这部电影进行了一次好评如潮的翻拍。
在《法国人》的第三部分,我欣喜若狂地读到了作者对雅克·贝克(Jacques Baker)的越狱电影《洞》(The Hole)的精彩评论,这是我以前从未在国内出版物上读过的。
在关于布列松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他前辈的无限尊重,但遗憾的是,我看不到对《扒手》和《巴尔特扎尔历险记》等杰作的评价,也遗憾的是,梅尔维尔只有一部对他早期作品《可怕的孩子》的影评,并不能代表他的成就。
这一部分的另一个精彩阅读体验来自作者对拉莫里斯《红气球》的冷静评论与我自己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之间的对比。
第四部分题为"庆祝日本电影",只涵盖了四部不是一流的电影(其中最有价值的可能是川久保的"缅甸的竖琴"),不到七页长。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笔者并没有给黑泽明、小津宏、宋浩留留有余地,无论如何,要理解作者的序言《评论家的梦想是什么》对其他章节有一般性的评论,而只是对日本电影, 那么,"掌声"说了什么呢?
在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中,作者评论了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同行,重要的是要注意,他在这里表达了他对奥森·威尔斯"强烈的欧洲态度"的认可,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公民凯恩的见解,罗西里尼的立场,"更喜欢现实生活",詹姆斯·迪恩,"无端的反叛者",以及新浪潮的同事艾伦·雷恩, 瓦尔达、路易·马勒、莱维特等人走上了各自的道路。
归根结底,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电影中一生都在做梦的人——那个在梦中长大、发现、相爱的逃学男孩,他真实理性地感人,他爱心驱动的艺术触角,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印记。
如果我们同意特雷弗的名言:"导演的电影是他一生的编年史。"嗯,我生命中的这部电影是一本关于电影的珍贵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