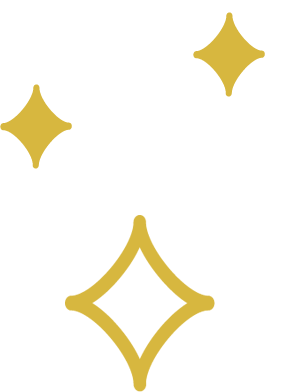
导 读
本文摘自《湘水》(第六辑),原标题为《屈原:楚中诗儒》,作者欧丽娟,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
《湘水》杂志创刊于2013年,以“发掘湖南人文历史、阐扬湖南人文精神”为宗旨,兼具思想性、可读性和鉴赏性。
“湖南人文丛刊”《湘水》(第六辑),聚焦蓝墨水的上游——汨罗江,重点介绍屈原、《楚辞》以及汨罗江流域的文脉,邀请韩少功、张炜、王跃文、李元洛、梁振华、赵逵夫、吴广平等知名学者和作家撰文,展现汨罗江作为文化之江的古今风貌。
《湘水》(第六辑),岳麓书社出版
屈原:楚中诗儒
文 | 欧丽娟
现代诗人郑愁予曾以激昂的青春情怀,满心孺慕地呼告:
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在遥想幻设的这幅图像里,诗人是黑夜即将笼罩下来时,伸手点起火焰的提灯人,他们无惧阴暗,不怕混沌,自有一心如星月,为世界指出真相与方向。而对于这两句现代诗人的提问,若论中国文学史上传下诗人行业的第一先行者,答案应该是:屈原。
同样是民族的“根文学”,成为文化血脉的源起,《诗经》是集体的创作,而《楚辞》从开创、奠定、拓展,则都端赖于屈原一人之手,倾其所有心力全幅灌注、滋养此一脉脉不息的渊泉,既承续了《诗经》的诗灵,又进一步打开诗歌的国度。这般高才大能,被刘勰《文心雕龙》颂赞道:“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来者无可比肩,只能与《诗经》并论,从此风、骚与共,就一人而言,堪称力可扛鼎。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楚辞》,岳麓书社出版
若问此何人也?又孰以致之?而其惊采之绝艳,又是何等风貌,能否仅以“浪漫”名之?
巨灵的诞生
任何一个人的孕育养成,除无可探究的先天禀赋外,成长环境构成了另一关键性的影响,堪称第二天性。屈原这个独一无二的巨灵,亦如同所有的生命体一样,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再如何优异秀出,仍有赖于环境的塑模始能成形,好比创作《红楼梦》的曹雪芹,便慧眼洞察到只有在“公侯富贵之家”,天赋“正邪二气”者才能成为贾宝玉之类的“情痴情种”,完全符合现代人格理论对人性的研究成果。
《红楼梦》(名家演播阅读无障碍版),岳麓书社出版
正是置身于具体而特定的成长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还有种种莫以名状的人际互动、物我相接,诸多意识或不自觉的复杂因素交织互渗,在每一个心灵的小宇宙中神秘运作,缺一不可,始能构成特定的个人,以致无法复制,伟大的灵魂更是如此。单单以自然环境而言,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刘勰,于《文心雕龙·物色》即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至于江山究竟何助?首先可以设想一幅拼图:倘若在水深土厚的黄土高原、黄淮平原上嵌入屈原的形象,诚然有点格格不入而难以协调,如同《诗经》的韵采是以整齐的四言诗展现出均衡、平稳、朴实和温柔敦厚,屈原的跌宕起伏、幽渺腾跃也只能是在江南的楚风里延展挥洒。
借由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对此地的描述,所谓:“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一方水土一方人,生长于此的族类自成一格,形成鲜明的文化印记,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便扼要指出屈原的作品特色是:“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而楚地所化育的兰、茝、荃、药、蕙、若、芷、蘅等,即楚物也。山川风物寓目即是,随处可见,于日常生活里点点滴滴渗入生命里,岂能不在呼吸目视之间潜移默化,渗透到心里深处而化为骨血?
《船山全书》,岳麓书社出版
那树梢闪耀的点点露珠,藤萝飘动的斑驳阴影,香草散发的隐隐芬芳,山坳传来的神秘声响,天空风云变幻的灵动莫测,岂不会在幼小的心灵上烙下奇丽的宇宙情思?超现实与现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随时随处可以穿越、飞翔,不只是观注日常生活,还可以凝视无限!配合“些、只、羌、谇、蹇、纷、侘傺”的楚语,以及“顿挫悲壮,或韵或否”的楚声,也因此在笔端流泻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磅礴,是为《离骚》等篇最令人心魂迷醉的魅力。
贵族的素质
当然,虽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却并非这一方人都会变成屈原。屈原之所以为屈原,更端赖其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与际遇。很明显的,屈原学识渊博,襟怀宏大,高瞻远瞩,迥然超乎一般文士,这也与他的身份或职业密切相关。
《离骚》开篇即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段历数家世,把自我置放在宗族传承中的定位,并不仅只是一般重视血统的观念反映而已,其中实在更有一种阶级归属与贵胄世系的珍重自豪。
根据学者的研究,屈原担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应该具有巫师、祭司之类的特殊身份,现代人往往误以为那是一种宗教迷信的怪胎乃至骗徒,但其实,如同宋兆麟所指出的,巫师不仅是巫教和巫术活动的主持者,也是当时科学文化知识的保存、传播和整理者,特别是在天文学、医学、文字、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可以说是当时解释世界的精神领袖,是史前时代的智者或知识分子。那么,这一类的文化掌舵者要如何养成呢?西方学者Arthur Waley对《九歌》的研究指出,从殷代巫咸与巫贤父子的例子,略可推知家世相传或是一个重要的方式。这就难怪屈原会如此重视家族谱系,天命般精神文化的遗传最为关键。
而这一类带有神职功能的人,除掌握庞大深奥的专业知识之外,甚至也具备特殊的通灵体质,能够出神入幻,与鬼神灵怪沟通无碍,更且在祭祀仪式中扮演沟通两界、天人合一的角色,因此,屈原笔下人神之恋的旖旎款款应该也是宗教性的反映。再说,屈原渲染远游的种种奇幻经历,恐怕并不只是想象力的发挥而已,亦为灵魂出窍离体飞升的如实描绘,这些都可以推测出屈原的神职身份属于萨满教(Shamanism)。根据Mircea Eliade的研究,萨满的通神能力(shamanic powers)有多种来源,包括上帝特赐、家世相传、梦中神授、老辈导引、精神狂昂(“ecstasy”or “trance”)的经验等等。
如此描述,岂非与屈原丝丝入扣?他之所以一开始即郑重铺陈自己的家族世系、命名取义,正是交代自己的特殊身份。“字余曰灵均”的“灵”字,即隐隐对应于超自然的灵界属性,至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的“内美”,或即与生俱来的上帝特赐,以及家世相继的血缘遗传;而“又重之以修能”的“修能”,应该就是后天成长过程中相关知识技术的专业训练了。他之所以能远游、能招魂,都是肇因于此,当远游、招魂时所展现的精神狂昂,岂不正是其篇章中迷幻魅力的来源?
当然,屈原并不只是一个优秀称职的巫师,他的“内美”与“修能”更包含了高度的道德素质,所谓“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好修”即一种对人格修炼的爱好,这是他赖以建构自我的内在基调。苏雪林《楚辞新诂》统计过,单单《离骚》一篇便使用了五次“好修”,此外还有与“修”字复合的词语,诸如修能、修名、前修、信修、修姱、宜修、修初服,以及新铸的语词“灵修”,凡十一见,此外还出现于其他的篇章中。可见屈原更是一位洁身自好、修德自励的煌煌君子,那卓越的人格堪任整个国族真正的精神导师,引领前进的步伐,因而《离骚》里便殷殷呼吁:“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正是这般高标崇举的理想取向,才是《离骚》等作品之所以诞生的关键。
灵魂的肖像
诚然屈原是自爱的,也是自信的,他清清楚楚了解自己的珍贵,因此坚持不愿打折扣:当受到压抑排挤的时候,便激起强烈的义愤不平,往往控诉世间俗众的平庸污浊。所谓: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如此之洁净不染、美丽无瑕、贤德良能,集众善于一身,以至《离骚》一篇中,单单“美”字即出现了十二次,还未包括不言美而美在其中的诸般描写。屈原对这样的自己也百般呵护,以致峭然孤出,东汉的班固便称之为“露才扬己”,一旦与世相忤,横遭挫磨,又岂能不怨悲愤,故明朝袁宏道指他“劲直而多怼,峭急而多露”,都客观看到屈原的一面。
确实,《离骚》全诗多达三百七十七句,淋漓尽致地抒发个人情思,据王海龙所见,其中使用了六个不同的自称代词,包括予、我、朕、之(自谓以第三人称)、余、吾等,共反复出现了八十八次,单单“余”字即出现五十次,“吾”字二十六次,自我张扬的现象是极其鲜明的。可以说,这些篇章都是屈原的个人倾诉,因此字里行间处处有我。很多人把《离骚》视为中国抒情诗的开端,将屈原当作浪漫派的代表,便是因为看到专属其个人的鲜明印记。
然而,屈原的自我却是无比纯净的,没有一般人的自私自利,甚至没有个体存在必有的社会依傍,屈原横空出世,似这般足不点地,与尘世毫无瓜葛,在他的笔下,完全没有人间事、烟火气,只有一片纯净的冰心。精确地说,我们看到的不是屈原这个人,而是他的心灵活动,其作品中折射的纯然是精神的光辉,而一无生活尘嚣的氛埃。
诸如屈原只谈到过父亲,但那与其说是家族伦理的传记呈现,不如说是精神事业的传承谱系。除此之外,屈原是否结婚生子?他和朋友的往来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一片空白,除了他所遇到的君王与小人之外。但君王是遥不可及的虚像,实质上是千山万水阻隔之下的悬空思念;虽然小人处处作梗,却也只是一些抽象的负面基点,若非要用来突显他的高洁,屈原也实在不屑一顾,是故完全缺乏有影有迹的恶形恶状。
至于家庭亲友呢?姑且不论孔子有妻有子,绵延至今已七十多代,身边还围绕着七十二个弟子继承衣钵,师生之间的相处、对话丰富而精彩,有温暖,有严峻,有共享春水闲适的怡然和乐,也有生死交关的凛然扶持,在《论语》里,万世师表刻画出熠熠生辉的伦理版图。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论语》,岳麓书社出版
即使以同时代、同故乡的庄子来看,他有“鼓盆而歌”一段所透露的妻子,她“与人居,长子老身”,是一起养儿育女的生活伴侣,夫妻白头偕老;还有濠梁之上对辩鱼之乐的友人惠施,这位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交流的朋友,不但去吊唁庄子的妻丧,还曾经发动军队去搜捕庄子呢。可见这个逍遥超脱的思想家,往往透露出从人间世挣脱的痕迹,让人瞥见那隐藏在蜻蜓点水之下的斧凿:原来在达到“逍遥游”之前,庄子首先是多么深陷于“人间世”里!甚至在依违往返之际,他还通过“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的亲子寓言,表达自己对盲昧无明的悚然与悲悯。
但屈原却纯乎独与精神往来,渺无生活层次的雪泥鸿爪,甚至连他穿在身上的衣装,都是“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哪里是“人”的造型?血肉之躯被涵融于一片晶莹芬芳的春花香草里,只剩下纯粹的美感形象,以及纯净的神圣空间。
不只如此,从屈原的作品里,我们也看不到年龄,甚至看不出性别!当他殷殷对君王发出声声呼唤时,那般深情款款、缱绻难舍,犹如月光下守望夫君的思妇,日日年年,难怪有学者把屈原怀才不遇的郁郁寡欢比喻为“政治失恋”。而这个终身处在失恋状态的贵裔男子,时时刻刻承受着椎心蚀骨的痛苦,却总是倾力奋斗,不肯妥协,不愿放弃,只有在最终选择远离人间的前夕,才显露出疲惫的痕迹。《渔父》一篇中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即使到了此时此刻,他仍然感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愿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终究选择以百分之百的洁净为生命画下句点,死亡成就了彻底的晶莹。
难怪司马迁以其史家的眼光,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盖棺定论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正是一片光明,比大鹏鸟飞得更高,超越了九万里的垂天之云,从人间的角度只能仰望到一片空灵。
“全本全注全译”《史记》(全九册),岳麓书社出版
浪漫外衣下的儒家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首度被比拟为日月恒光者,即是屈原。相较之下,孔子固然更是文化正统的总源,后来也因此被比诸天日,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一前一后,屈原闪耀在先,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冠冕。必须说,司马迁的日月之喻,正显示他身为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卓越判断力,精确掌握到屈原的灵魂根柢其实来自于儒家血统。
的确,“无限”可以说是屈原的内在世界的基本核心,再加上其所焕发出来的种种奇思幻想,从表面上看,很容易被类同于浪漫精神的发挥。例如英国文学批评家休姆(T. E. Hulme)在描述浪漫主义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时,曾说道:“浪漫主义者以为人是无可限量的,故必然时时吟咏无限的事物。”这岂非切中屈原笔下无尽的时空,可以绵延到宇宙开端而发出天问,或远游于现实边界之外?而美国文学批评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声言:“浪漫的想象,即是不以伦理中心为归宿的想象,亦即是在荒诞领域中疯狂驰骤的想象。”这似乎也很符合屈原笔下超越伦理禁忌的人神之恋,以及飞天入地超现实的灵界经历,充满神话国度不受拘束的奇诡幽渺。至于英国批评家佩特(W. Pater)简单总结所云:“浪漫精神的要素,就是好奇之念与爱美之心”,更一语道中《离骚》等篇章的基本风格。这么一来,楚文化的特征诚彰明可见。
只不过,单就楚地的浪漫风格而言,一般都将庄、屈并称,但其实两人的性格特质截然不同。缪钺曾以此二人为代表,区辨中国古人两种不同的基本性格特质,一曰“入而能出”,一曰“往而不返”,庄子正是深于情而超乎情,故成就其带着深沉重量的逍遥,是谓“入而能出”;而屈原却是一往投入,不肯自拔,终究以身相殉,故云“往而不返”。此种“往而不返”的执着,一般又容易理解为李商隐式的浪漫,所谓“深知身在情长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乍看之下,那裹挟一生无时放下的执着确实若有相合。
然而失之毫厘便差之千里,《文心雕龙》说屈原“绮靡以伤情”的情实则全非李商隐式的个人私恋,既一无得失荣枯的计较,也迥异于自我的情绪好恶。质言之,屈原的情并不是小我的延伸,而是以大我为丈量,所以其“往而不返”者并非无力解脱的陷溺,或激情驱使之下的难以自制,本质上更接近儒家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姑且不论《离骚》中已经一再树立价值标竿,声称: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
这样的道德判准与儒家思想完全一致,至于《离骚》所说: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又与孔子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相去几希!可见“浪漫”只是外在包装的表象,真正构成屈原的内在根柢者,实乃源自孔子对理想追求的执着。而这样的个性注定只能坚持不懈,根本与庄子的“坐忘”无缘。
这就是司马迁之所以将屈原比诸孔子的慧眼所在。太史公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将两人比肩,在独尊儒术又楚风流衍的汉代,不可不谓灵巧,不可不谓奇妙。试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篇末的一段“太史公曰”,那是司马迁以史家的身份对屈原所下的历史论断: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值得注意的是,于《孔子世家》最后的篇末赞语竟然差相仿佛: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这两段简直如出一辙!其一,司马迁身在后代,都通过阅读两人之著作而引发无限的向往之情,启动进一步的心灵相接。其二,意欲“究天人之际”的大史家也都亲赴其地凭吊,进入两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神圣场所,接受其精神的无形洗礼,一处是让屈原获得绝对净化的长沙,一处是孔子弘扬礼乐钟鼓的鲁国。其三,既读其书,复履其地,最终也都激发出“想见其为人”的钦慕神往。唯一的不同是:他对屈原多了“悲其志”与“未尝不垂涕”的强烈动情,对孔子则多了“祗回留之不能去”的沉浸流连,深度更有过之。
就此,文学家与思想家道路不同却殊途同归,一并受到史家的极力赞扬而相提并论,岂非双方共有品格高洁的同一核心所致?那令人崇敬之心不禁油然而生的人格,正是一种让人可以维持一定的心灵高度,不会越来越坠落的伟大力量!可见司马迁以其史家的洞察力,早已对屈原骨子里的儒家血统作出盖棺定论。因此确切地说,屈原其实是个浪漫的儒家信徒,与孔子同一高度更是屈原得以在黄昏里挂起一盏灯的关键。
然而,明亮高悬如日月者虽足以辉耀古今,但当其燃放光亮的同时,却注定要承受拒斥、排挤甚至放逐的待遇。庄子已经锐利地洞察到孔子的悲剧,乃如《达生篇》所指出:
今汝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激起愚污者之反扑逆袭者,难道不正是那令人无法直视的极端光亮?它让愚昧无法匿迹,污秽无法隐遁,以致更加哓哓张舞,吊诡地在日月周边造出黑洞,反过来吞噬了光源!这是庄子的洞见,也是庄子的怜悯,更是庄子对孔子的尊敬。同具日月之光的屈原又岂其不然?孔子行走人间,坚持了一生,却终身落拓无依,不也预告了屈原的命运?屈原这个巨灵毕竟装载于凡人之躯中,无法避免在人群里遭遇人性的阴暗纠葛,复以深情难遣,更容易被是非所伤害,所谓蛾眉见嫉之叹,莫非如此。
踽踽独行的屈原当下既无法安顿,于是退一步以飞天想象作为现实的解脱,他毕竟是优秀的巫灵,通过家传的专业技艺展开灵魂飞升的远游,那是一种心灵大开的飞跃,即使受困于此时此地,也依然可以遨翔宇宙。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便曾概括了“游”字在早期文献中的各种含义:“游”可指到山间的旅行,还意指萨满巫师式的天际飞行,以及道士换身置于神秘的高空所取得的一种自由感。
这便是屈原唯一的出路所在,也是他重获尊严的方式!
只可惜,毕竟任何形躯都深受地心引力的牵制,不能永恒高飞,必须复归回落尘土,然后再继续腾空奋斗;而上穷碧落下黄泉之际固然汲取了自我解脱的自由,同时却又隐含着茫然无着的巨大彷徨。在更辽阔的世界里遭受更彻底的失落下,屈原更加没有皈依,其中的艰苦与庄严,又何尝稍减于孔子?
孔子遭到麒麟折足的打击,终于哭泣哀叹“胡为乎来哉”的苍凉,以致《春秋》停笔的绝望,生命之火乃随之熄灭。同样的,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之余,屈原也终于憔悴枯槁,徘徊于江边泽畔咄咄问天,苦苦追讨没有回应的答案,再一步即投江葬身鱼腹中,这岂不与孔子的“绝笔于获麟”异曲同工?
“国学经典文库”《春秋左传》,岳麓书社出版
其实,任谁都能感受到放弃世俗的一切,包括权位、财富,甚至尊严,当一个彻底的失败者,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屈原迥非一味偏执之辈,何尝不知一旦踏上这样的道路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在历经种种严酷的考验之后,屈原终于确定自己的道路并不是选择得来,而是无法逃脱的命中注定,对于降格以求、步入歧途以转向康庄大道,实在不是不为,而是不能。相较于世人轻易地“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屈原却办不到就是办不到,于是他说:“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那等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宿命了。
屈原在天赋秉性与后天的“好修”下全力扛起这个宿命,从来不曾犹疑。只不过在长途跋涉之下,屈原劳苦倦极、疾痛惨怛,实在太累、太绝望了,即使遇到渔父这样一位庄子般的智者,提供给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此一与世推移的因应之道,但也只是让他将生命献祭于理想的决定更加明确而坚定。或者我们可以采用象征的角度,把《渔父》这一篇视为屈原的自我诘辩乃至自我挣扎,借由分裂出来的两个人物彼此对话,以厘清激荡纷扰的思绪,一个通脱的屈原想要说服另一个执着的屈原,对比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和处世方式。
终于,屈原更看清了自己,他终究不是同一方水土所产生的庄子,而遥契远方的孔子。虽然他写起对君王的眷顾难舍,简直如同缠绵悱恻的恋人絮语,但其实骨子里是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儒家君子,完全没有同乡庄子的豁达与超脱。所以说,屈原自楚文化的母胎孕育而出,但又不限于楚文化,日月的比喻更道出屈原的超越性与永恒性。
魂兮归来:现代的招魂
青山不老,为谁白头?
两千多年前,屈原诞生了,在活着的一生中,他一片赤诚,两袖清风,四顾无人,伫立于八方天地殷殷呼唤,却像面对黑洞般毫无回声,只在湘水边憔悴徘徊,于茫茫虚空里刻画出没有答案的问号。幸而英灵不死,那余音袅袅终究在后世许多纯净的心灵里不断重现,屈原因此而获得永生。
但造成屈原以及孔子之悲剧的那个世界并没有消失,顽强地代代相传,“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颠倒依然,清朝诗人黄仲则不也感叹:“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可伤时至如今,是否连书生也不复存在?湘水悠悠,屈子能否魂兮归来,难道不是决定于吾辈的招魂之心?即使英灵复返,是否有“乐莫乐兮新相知”的故乡可以安顿,还是再一次遭受“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失落,甚至重蹈麒麟折足的覆辙,徒增“胡为乎来哉”的苍凉叹息?
湘江来自一方水土,却脉脉流入长江,汇入更盛大的澜潮,再奔入浩瀚无涯的海洋,与世界合而为一,同样的,屈原在战国时期荆楚之地孕育而生,却又超越了这里,成为整个民族精神的典范,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悠悠苍天,证明崇高的品格与深厚的文化才是人类的尊严、文明的成就,唯有尽量超越人性与本能的地心引力,才得以接近永恒的北极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