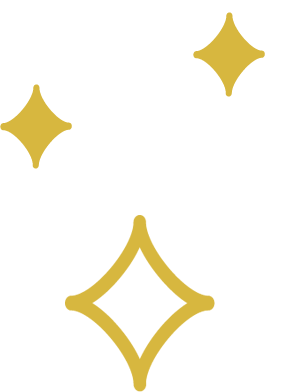
導 讀
本文摘自《湘水》(第六輯),原标題為《屈原:楚中詩儒》,作者歐麗娟,系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湘水》雜志創刊于2013年,以“發掘湖南人文曆史、闡揚湖南人文精神”為宗旨,兼具思想性、可讀性和鑒賞性。
“湖南人文叢刊”《湘水》(第六輯),聚焦藍墨水的上遊——汨羅江,重點介紹屈原、《楚辭》以及汨羅江流域的文脈,邀請韓少功、張炜、王躍文、李元洛、梁振華、趙逵夫、吳廣平等知名學者和作家撰文,展現汨羅江作為文化之江的古今風貌。
《湘水》(第六輯),嶽麓書社出版
屈原:楚中詩儒
文 | 歐麗娟
現代詩人鄭愁予曾以激昂的青春情懷,滿心孺慕地呼告: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黃昏裡挂起一盞燈?
在遙想幻設的這幅圖像裡,詩人是黑夜即将籠罩下來時,伸手點起火焰的提燈人,他們無懼陰暗,不怕混沌,自有一心如星月,為世界指出真相與方向。而對于這兩句現代詩人的提問,若論中國文學史上傳下詩人行業的第一先行者,答案應該是:屈原。
同樣是民族的“根文學”,成為文化血脈的源起,《詩經》是集體的創作,而《楚辭》從開創、奠定、拓展,則都端賴于屈原一人之手,傾其所有心力全幅灌注、滋養此一脈脈不息的淵泉,既承續了《詩經》的詩靈,又進一步打開詩歌的國度。這般高才大能,被劉勰《文心雕龍》頌贊道:“氣往轹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并能矣。”來者無可比肩,隻能與《詩經》并論,從此風、騷與共,就一人而言,堪稱力可扛鼎。
“古典名著普及文庫”《楚辭》,嶽麓書社出版
若問此何人也?又孰以緻之?而其驚采之絕豔,又是何等風貌,能否僅以“浪漫”名之?
巨靈的誕生
任何一個人的孕育養成,除無可探究的先天禀賦外,成長環境構成了另一關鍵性的影響,堪稱第二天性。屈原這個獨一無二的巨靈,亦如同所有的生命體一樣,與生俱來的遺傳基因再如何優異秀出,仍有賴于環境的塑模始能成形,好比創作《紅樓夢》的曹雪芹,便慧眼洞察到隻有在“公侯富貴之家”,天賦“正邪二氣”者才能成為賈寶玉之類的“情癡情種”,完全符合現代人格理論對人性的研究成果。
《紅樓夢》(名家演播閱讀無障礙版),嶽麓書社出版
正是置身于具體而特定的成長環境裡,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還有種種莫以名狀的人際互動、物我相接,諸多意識或不自覺的複雜因素交織互滲,在每一個心靈的小宇宙中神秘運作,缺一不可,始能構成特定的個人,以緻無法複制,偉大的靈魂更是如此。單單以自然環境而言,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文學批評家劉勰,于《文心雕龍·物色》即指出:“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然屈平是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至于江山究竟何助?首先可以設想一幅拼圖:倘若在水深土厚的黃土高原、黃淮平原上嵌入屈原的形象,誠然有點格格不入而難以協調,如同《詩經》的韻采是以整齊的四言詩展現出均衡、平穩、樸實和溫柔敦厚,屈原的跌宕起伏、幽渺騰躍也隻能是在江南的楚風裡延展揮灑。
借由王夫之《楚辭通釋·序例》對此地的描述,所謂:“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一方水土一方人,生長于此的族類自成一格,形成鮮明的文化印記,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便扼要指出屈原的作品特色是:“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而楚地所化育的蘭、茝、荃、藥、蕙、若、芷、蘅等,即楚物也。山川風物寓目即是,随處可見,于日常生活裡點點滴滴滲入生命裡,豈能不在呼吸目視之間潛移默化,滲透到心裡深處而化為骨血?
《船山全書》,嶽麓書社出版
那樹梢閃耀的點點露珠,藤蘿飄動的斑駁陰影,香草散發的隐隐芬芳,山坳傳來的神秘聲響,天空風雲變幻的靈動莫測,豈不會在幼小的心靈上烙下奇麗的宇宙情思?超現實與現實之間并沒有明确的界線,随時随處可以穿越、飛翔,不隻是觀注日常生活,還可以凝視無限!配合“些、隻、羌、谇、蹇、紛、侘傺”的楚語,以及“頓挫悲壯,或韻或否”的楚聲,也是以在筆端流瀉出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磅礴,是為《離騷》等篇最令人心魂迷醉的魅力。
貴族的素質
當然,雖說一方水土一方人,卻并非這一方人都會變成屈原。屈原之是以為屈原,更端賴其與衆不同的個人特質與際遇。很明顯的,屈原學識淵博,襟懷宏大,高瞻遠矚,迥然超乎一般文士,這也與他的身份或職業密切相關。
《離騷》開篇即雲:“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這段曆數家世,把自我置放在宗族傳承中的定位,并不僅隻是一般重視血統的觀念反映而已,其中實在更有一種階級歸屬與貴胄世系的珍重自豪。
根據學者的研究,屈原擔任楚國的三闾大夫,應該具有巫師、祭司之類的特殊身份,現代人往往誤以為那是一種宗教迷信的怪胎乃至騙徒,但其實,如同宋兆麟所指出的,巫師不僅是巫教和巫術活動的主持者,也是當時科學文化知識的儲存、傳播和整理者,特别是在天文學、醫學、文字、文學、曆史、音樂、舞蹈、繪畫等方面,可以說是當時解釋世界的精神領袖,是史前時代的智者或知識分子。那麼,這一類的文化掌舵者要如何養成呢?西方學者Arthur Waley對《九歌》的研究指出,從殷代巫鹹與巫賢父子的例子,略可推知家世相傳或是一個重要的方式。這就難怪屈原會如此重視家族譜系,天命般精神文化的遺傳最為關鍵。
而這一類帶有神職功能的人,除掌握龐大深奧的專業知識之外,甚至也具備特殊的通靈體質,能夠出神入幻,與鬼神靈怪溝通無礙,更且在祭祀儀式中扮演溝通兩界、天人合一的角色,是以,屈原筆下人神之戀的旖旎款款應該也是宗教性的反映。再說,屈原渲染遠遊的種種奇幻經曆,恐怕并不隻是想象力的發揮而已,亦為靈魂出竅離體飛升的如實描繪,這些都可以推測出屈原的神職身份屬于薩滿教(Shamanism)。根據Mircea Eliade的研究,薩滿的通神能力(shamanic powers)有多種來源,包括上帝特賜、家世相傳、夢中神授、老輩導引、精神狂昂(“ecstasy”or “trance”)的經驗等等。
如此描述,豈非與屈原絲絲入扣?他之是以一開始即鄭重鋪陳自己的家族世系、命名取義,正是交代自己的特殊身份。“字餘曰靈均”的“靈”字,即隐隐對應于超自然的靈界屬性,至于“紛吾既有此内美兮”的“内美”,或即與生俱來的上帝特賜,以及家世相繼的血緣遺傳;而“又重之以修能”的“修能”,應該就是後天成長過程中相關知識技術的專業訓練了。他之是以能遠遊、能招魂,都是肇因于此,當遠遊、招魂時所展現的精神狂昂,豈不正是其篇章中迷幻魅力的來源?
當然,屈原并不隻是一個優秀稱職的巫師,他的“内美”與“修能”更包含了高度的道德素質,所謂“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修以為常”,“好修”即一種對人格修煉的愛好,這是他賴以建構自我的内在基調。蘇雪林《楚辭新诂》統計過,單單《離騷》一篇便使用了五次“好修”,此外還有與“修”字複合的詞語,諸如修能、修名、前修、信修、修姱、宜修、修初服,以及新鑄的語詞“靈修”,凡十一見,此外還出現于其他的篇章中。可見屈原更是一位潔身自好、修德自勵的煌煌君子,那卓越的人格堪任整個國族真正的精神導師,引領前進的步伐,因而《離騷》裡便殷殷呼籲:“乘骐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正是這般高标崇舉的理想取向,才是《離騷》等作品之是以誕生的關鍵。
靈魂的肖像
誠然屈原是自愛的,也是自信的,他清清楚楚了解自己的珍貴,是以堅持不願打折扣:當受到壓抑排擠的時候,便激起強烈的義憤不平,往往控訴世間俗衆的平庸污濁。所謂:
衆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诼謂餘以善淫。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如此之潔淨不染、美麗無瑕、賢德良能,集衆善于一身,以至《離騷》一篇中,單單“美”字即出現了十二次,還未包括不言美而美在其中的諸般描寫。屈原對這樣的自己也百般呵護,以緻峭然孤出,東漢的班固便稱之為“露才揚己”,一旦與世相忤,橫遭挫磨,又豈能不怨悲憤,故明朝袁宏道指他“勁直而多怼,峭急而多露”,都客觀看到屈原的一面。
确實,《離騷》全詩多達三百七十七句,淋漓盡緻地抒發個人情思,據王海龍所見,其中使用了六個不同的自稱代詞,包括予、我、朕、之(自謂以第三人稱)、餘、吾等,共反複出現了八十八次,單單“餘”字即出現五十次,“吾”字二十六次,自我張揚的現象是極其鮮明的。可以說,這些篇章都是屈原的個人傾訴,是以字裡行間處處有我。很多人把《離騷》視為中國抒情詩的開端,将屈原當作浪漫派的代表,便是因為看到專屬其個人的鮮明印記。
然而,屈原的自我卻是無比純淨的,沒有一般人的自私自利,甚至沒有個體存在必有的社會依傍,屈原橫空出世,似這般足不點地,與塵世毫無瓜葛,在他的筆下,完全沒有人間事、煙火氣,隻有一片純淨的冰心。精确地說,我們看到的不是屈原這個人,而是他的心靈活動,其作品中折射的純然是精神的光輝,而一無生活塵嚣的氛埃。
諸如屈原隻談到過父親,但那與其說是家族倫理的傳記呈現,不如說是精神事業的傳承譜系。除此之外,屈原是否結婚生子?他和朋友的往來如何?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一片空白,除了他所遇到的君王與小人之外。但君王是遙不可及的虛像,實質上是千山萬水阻隔之下的懸空思念;雖然小人處處作梗,卻也隻是一些抽象的負面基點,若非要用來突顯他的高潔,屈原也實在不屑一顧,是故完全缺乏有影有迹的惡形惡狀。
至于家庭親友呢?姑且不論孔子有妻有子,綿延至今已七十多代,身邊還圍繞着七十二個弟子繼承衣缽,師生之間的相處、對話豐富而精彩,有溫暖,有嚴峻,有共享春水閑适的怡然和樂,也有生死交關的凜然扶持,在《論語》裡,萬世師表刻畫出熠熠生輝的倫理版圖。
“古典名著普及文庫”《論語》,嶽麓書社出版
即使以同時代、同故鄉的莊子來看,他有“鼓盆而歌”一段所透露的妻子,她“與人居,長子老身”,是一起養兒育女的生活伴侶,夫妻白頭偕老;還有濠梁之上對辯魚之樂的友人惠施,這位既是競争的對手又是交流的朋友,不但去吊唁莊子的妻喪,還曾經發動軍隊去搜捕莊子呢。可見這個逍遙超脫的思想家,往往透露出從人間世掙脫的痕迹,讓人瞥見那隐藏在蜻蜓點水之下的斧鑿:原來在達到“逍遙遊”之前,莊子首先是多麼深陷于“人間世”裡!甚至在依違往返之際,他還通過“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的親子寓言,表達自己對盲昧無明的悚然與悲憫。
但屈原卻純乎獨與精神往來,渺無生活層次的雪泥鴻爪,甚至連他穿在身上的衣裝,都是“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這哪裡是“人”的造型?血肉之軀被涵融于一片晶瑩芬芳的春花香草裡,隻剩下純粹的美感形象,以及純淨的神聖空間。
不隻如此,從屈原的作品裡,我們也看不到年齡,甚至看不出性别!當他殷殷對君王發出聲聲呼喚時,那般深情款款、缱绻難舍,猶如月光下守望夫君的思婦,日日年年,難怪有學者把屈原懷才不遇的郁郁寡歡比喻為“政治失戀”。而這個終身處在失戀狀态的貴裔男子,時時刻刻承受着椎心蝕骨的痛苦,卻總是傾力奮鬥,不肯妥協,不願放棄,隻有在最終選擇遠離人間的前夕,才顯露出疲憊的痕迹。《漁父》一篇中說:“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但即使到了此時此刻,他仍然感慨“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不願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終究選擇以百分之百的潔淨為生命畫下句點,死亡成就了徹底的晶瑩。
難怪司馬遷以其史家的眼光,于《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蓋棺定論道:“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屈原正是一片光明,比大鵬鳥飛得更高,超越了九萬裡的垂天之雲,從人間的角度隻能仰望到一片空靈。
“全本全注全譯”《史記》(全九冊),嶽麓書社出版
浪漫外衣下的儒家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曆史上首度被比拟為日月恒光者,即是屈原。相較之下,孔子固然更是文化正統的總源,後來也是以被比諸天日,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而一前一後,屈原閃耀在先,不能不說是莫大的冠冕。必須說,司馬遷的日月之喻,正顯示他身為最偉大的曆史學家的卓越判斷力,精确掌握到屈原的靈魂根柢其實來自于儒家血統。
的确,“無限”可以說是屈原的内在世界的基本核心,再加上其所煥發出來的種種奇思幻想,從表面上看,很容易被類同于浪漫精神的發揮。例如英國文學批評家休姆(T. E. Hulme)在描述浪漫主義者對宇宙人生的态度時,曾說道:“浪漫主義者以為人是無可限量的,故必然時時吟詠無限的事物。”這豈非切中屈原筆下無盡的時空,可以綿延到宇宙開端而發出天問,或遠遊于現實邊界之外?而美國文學批評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聲言:“浪漫的想象,即是不以倫理中心為歸宿的想象,亦即是在荒誕領域中瘋狂馳驟的想象。”這似乎也很符合屈原筆下超越倫理禁忌的人神之戀,以及飛天入地超現實的靈界經曆,充滿神話國度不受拘束的奇詭幽渺。至于英國批評家佩特(W. Pater)簡單總結所雲:“浪漫精神的要素,就是好奇之念與愛美之心”,更一語道中《離騷》等篇章的基本風格。這麼一來,楚文化的特征誠彰明可見。
隻不過,單就楚地的浪漫風格而言,一般都将莊、屈并稱,但其實兩人的性格特質截然不同。缪钺曾以此二人為代表,區辨中國古人兩種不同的基本性格特質,一曰“入而能出”,一曰“往而不返”,莊子正是深于情而超乎情,故成就其帶着深沉重量的逍遙,是謂“入而能出”;而屈原卻是一往投入,不肯自拔,終究以身相殉,故雲“往而不返”。此種“往而不返”的執着,一般又容易了解為李商隐式的浪漫,所謂“深知身在情長在”“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乍看之下,那裹挾一生無時放下的執着确實若有相合。
然而失之毫厘便差之千裡,《文心雕龍》說屈原“绮靡以傷情”的情實則全非李商隐式的個人私戀,既一無得失榮枯的計較,也迥異于自我的情緒好惡。質言之,屈原的情并不是小我的延伸,而是以大我為丈量,是以其“往而不返”者并非無力解脫的陷溺,或激情驅使之下的難以自制,本質上更接近儒家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姑且不論《離騷》中已經一再樹立價值标竿,聲稱: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這樣的道德判準與儒家思想完全一緻,至于《離騷》所說: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又與孔子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相去幾希!可見“浪漫”隻是外在包裝的表象,真正構成屈原的内在根柢者,實乃源自孔子對理想追求的執着。而這樣的個性注定隻能堅持不懈,根本與莊子的“坐忘”無緣。
這就是司馬遷之是以将屈原比諸孔子的慧眼所在。太史公以一種十分獨特的方式将兩人比肩,在獨尊儒術又楚風流衍的漢代,不可不謂靈巧,不可不謂奇妙。試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篇末的一段“太史公曰”,那是司馬遷以史家的身份對屈原所下的曆史論斷:
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值得注意的是,于《孔子世家》最後的篇末贊語竟然差相仿佛:
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适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回留之不能去雲。
這兩段簡直如出一轍!其一,司馬遷身在後代,都通過閱讀兩人之著作而引發無限的向往之情,啟動進一步的心靈相接。其二,意欲“究天人之際”的大史家也都親赴其地憑吊,進入兩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神聖場所,接受其精神的無形洗禮,一處是讓屈原獲得絕對淨化的長沙,一處是孔子弘揚禮樂鐘鼓的魯國。其三,既讀其書,複履其地,最終也都激發出“想見其為人”的欽慕神往。唯一的不同是:他對屈原多了“悲其志”與“未嘗不垂涕”的強烈動情,對孔子則多了“祗回留之不能去”的沉浸流連,深度更有過之。
就此,文學家與思想家道路不同卻殊途同歸,一并受到史家的極力贊揚而相提并論,豈非雙方共有品格高潔的同一核心所緻?那令人崇敬之心不禁油然而生的人格,正是一種讓人可以維持一定的心靈高度,不會越來越墜落的偉大力量!可見司馬遷以其史家的洞察力,早已對屈原骨子裡的儒家血統作出蓋棺定論。是以确切地說,屈原其實是個浪漫的儒家信徒,與孔子同一高度更是屈原得以在黃昏裡挂起一盞燈的關鍵。
然而,明亮高懸如日月者雖足以輝耀古今,但當其燃放光亮的同時,卻注定要承受拒斥、排擠甚至放逐的待遇。莊子已經銳利地洞察到孔子的悲劇,乃如《達生篇》所指出: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激起愚污者之反撲逆襲者,難道不正是那令人無法直視的極端光亮?它讓愚昧無法匿迹,污穢無法隐遁,以緻更加哓哓張舞,吊詭地在日月周邊造出黑洞,反過來吞噬了光源!這是莊子的洞見,也是莊子的憐憫,更是莊子對孔子的尊敬。同具日月之光的屈原又豈其不然?孔子行走人間,堅持了一生,卻終身落拓無依,不也預告了屈原的命運?屈原這個巨靈畢竟裝載于凡人之軀中,無法避免在人群裡遭遇人性的陰暗糾葛,複以深情難遣,更容易被是非所傷害,所謂蛾眉見嫉之歎,莫非如此。
踽踽獨行的屈原當下既無法安頓,于是退一步以飛天想象作為現實的解脫,他畢竟是優秀的巫靈,通過家傳的專業技藝展開靈魂飛升的遠遊,那是一種心靈大開的飛躍,即使受困于此時此地,也依然可以遨翔宇宙。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便曾概括了“遊”字在早期文獻中的各種含義:“遊”可指到山間的旅行,還意指薩滿巫師式的天際飛行,以及道士換身置于神秘的高空所取得的一種自由感。
這便是屈原唯一的出路所在,也是他重獲尊嚴的方式!
隻可惜,畢竟任何形軀都深受地心引力的牽制,不能永恒高飛,必須複歸回落塵土,然後再繼續騰空奮鬥;而上窮碧落下黃泉之際固然汲取了自我解脫的自由,同時卻又隐含着茫然無着的巨大彷徨。在更遼闊的世界裡遭受更徹底的失落下,屈原更加沒有皈依,其中的艱苦與莊嚴,又何嘗稍減于孔子?
孔子遭到麒麟折足的打擊,終于哭泣哀歎“胡為乎來哉”的蒼涼,以緻《春秋》停筆的絕望,生命之火乃随之熄滅。同樣的,飽經滄桑、曆盡憂患之餘,屈原也終于憔悴枯槁,徘徊于江邊澤畔咄咄問天,苦苦追讨沒有回應的答案,再一步即投江葬身魚腹中,這豈不與孔子的“絕筆于獲麟”異曲同工?
“國學經典文庫”《春秋左傳》,嶽麓書社出版
其實,任誰都能感受到放棄世俗的一切,包括權位、财富,甚至尊嚴,當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那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屈原迥非一味偏執之輩,何嘗不知一旦踏上這樣的道路後所要付出的代價?隻不過在曆經種種嚴酷的考驗之後,屈原終于确定自己的道路并不是選擇得來,而是無法逃脫的命中注定,對于降格以求、步入歧途以轉向康莊大道,實在不是不為,而是不能。相較于世人輕易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屈原卻辦不到就是辦不到,于是他說:“鸷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那等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宿命了。
屈原在天賦秉性與後天的“好修”下全力扛起這個宿命,從來不曾猶疑。隻不過在長途跋涉之下,屈原勞苦倦極、疾痛慘怛,實在太累、太絕望了,即使遇到漁父這樣一位莊子般的智者,提供給他“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此一與世推移的因應之道,但也隻是讓他将生命獻祭于理想的決定更加明确而堅定。或者我們可以采用象征的角度,把《漁父》這一篇視為屈原的自我诘辯乃至自我掙紮,借由分裂出來的兩個人物彼此對話,以厘清激蕩紛擾的思緒,一個通脫的屈原想要說服另一個執着的屈原,對比出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質和處世方式。
終于,屈原更看清了自己,他終究不是同一方水土所産生的莊子,而遙契遠方的孔子。雖然他寫起對君王的眷顧難舍,簡直如同纏綿悱恻的戀人絮語,但其實骨子裡是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儒家君子,完全沒有同鄉莊子的豁達與超脫。是以說,屈原自楚文化的母胎孕育而出,但又不限于楚文化,日月的比喻更道出屈原的超越性與永恒性。
魂兮歸來:現代的招魂
青山不老,為誰白頭?
兩千多年前,屈原誕生了,在活着的一生中,他一片赤誠,兩袖清風,四顧無人,伫立于八方天地殷殷呼喚,卻像面對黑洞般毫無回聲,隻在湘水邊憔悴徘徊,于茫茫虛空裡刻畫出沒有答案的問号。幸而英靈不死,那餘音袅袅終究在後世許多純淨的心靈裡不斷重制,屈原是以而獲得永生。
但造成屈原以及孔子之悲劇的那個世界并沒有消失,頑強地代代相傳,“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颠倒依然,清朝詩人黃仲則不也感歎:“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可傷時至如今,是否連書生也不複存在?湘水悠悠,屈子能否魂兮歸來,難道不是決定于吾輩的招魂之心?即使英靈複返,是否有“樂莫樂兮新相知”的故鄉可以安頓,還是再一次遭受“悲莫悲兮生别離”的失落,甚至重蹈麒麟折足的覆轍,徒增“胡為乎來哉”的蒼涼歎息?
湘江來自一方水土,卻脈脈流入長江,彙入更盛大的瀾潮,再奔入浩瀚無涯的海洋,與世界合而為一,同樣的,屈原在戰國時期荊楚之地孕育而生,卻又超越了這裡,成為整個民族精神的典範,甚至是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産。悠悠蒼天,證明崇高的品格與深厚的文化才是人類的尊嚴、文明的成就,唯有盡量超越人性與本能的地心引力,才得以接近永恒的北極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