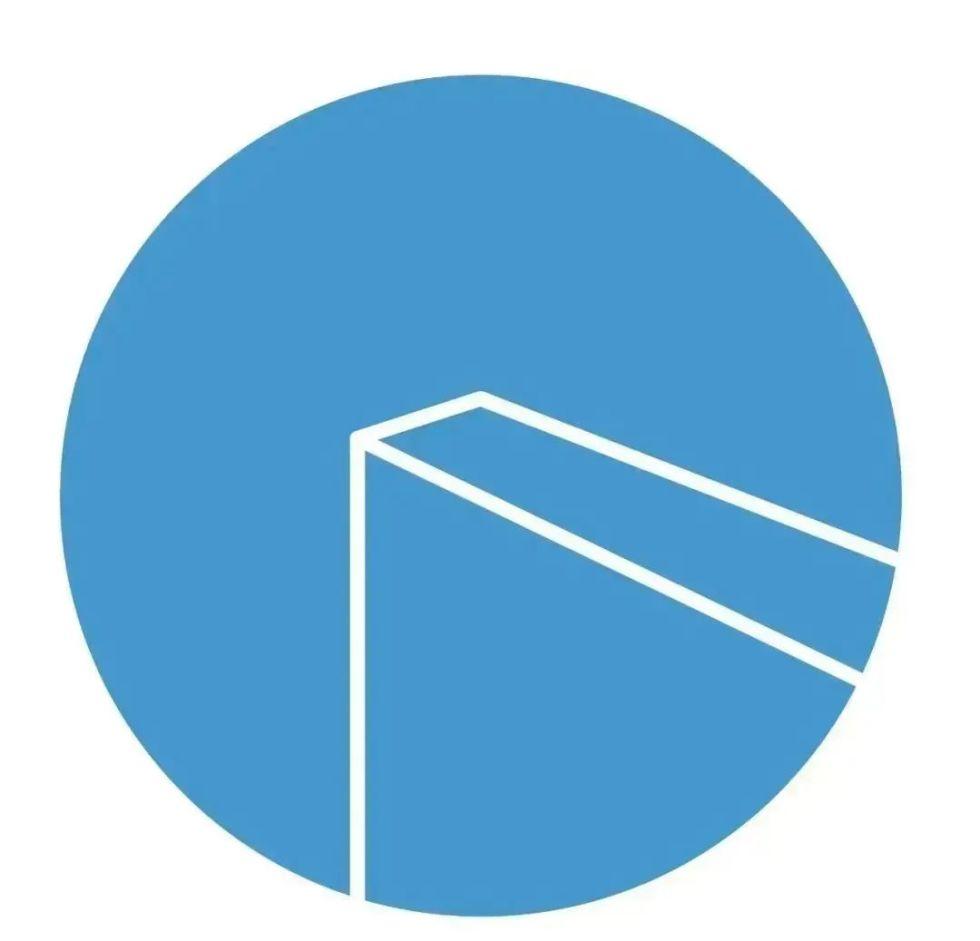
微信公众号推送规则变更
请将“探照灯好书”设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期好书推送
《琢玉成器——考古艺术史中的玉文化》是美国早期中国艺术史研究专家苏芳淑(Jenny F. So)教授首部中文译作。全书自新石器时代以降,就中国历代出土与传世的玉器中的十个学术性问题进行深度探讨,涉及牛河梁、红山、良渚、三星堆等多个文化聚落,带我们了解古人采玉、治玉、用玉的具体方式,以及玉器在不同时代礼制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玉器的装饰与其他器物门类的关系,也借玉器延伸出华夏文明与周边文化交流的文化细节。
下文选自书中《三星堆的玉与石》一章,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从略。
文/苏芳淑
20世纪以来,三星堆古城附近经常发现玉、石器。最早的出自古城北部。1929年当地一个地主在自家院子旁修筑灌溉渠,从底部掘出了数百件璧、戈和其他器物。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前身)的考古学家于1933年对该地点进行调查,此时大多数遗物已被出售,剩余部分被四川省博物馆以及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古城内又多次发现作坊遗存,出土工具、未加工的石料以及半成品,说明这里曾经有过繁荣的石器加工。1986年从两个惊世的祭祀坑中出土了十分丰富的遗物,其中有逾两百件玉器和石器。目前我们对三星堆玉、石器的认识已可窥见其特征,有别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玉石器加工业。
材料和工艺
根据考古报告,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近二百件“玉器”中,真正属于软玉的不足百分之六,其他大多数是各种硬度相对较低的大理石或石灰岩,既可以用解玉砂琢磨,亦可用金属工具直接加工(图1)。报告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玉器统计表共罗列105件“玉器”,但只有4件注明是软玉;二号祭祀坑统计表罗列81件“玉器”,只有6件是软玉。那些用较软的材料制成的器物,从形制来看应是当地产品。软玉制品包括少数珠饰、环形饰物(图2)、戈以及抛光工具,其中戈和璧/环类饰物可能是外地输入品。即使并非外来,其材质的珍贵也会令它们在三星堆文化中拥有特殊意义。
图1 长椭圆形宽边器,白云石灰岩,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至中期
图2 2.宽边镯,软玉,公元前十三世纪或公元前十二世纪
其余许多利用硬度不等石材制作的器物应不是外来的。例如Y形器(forked blade)(图 3),其形制和两侧镂雕勾卷状齿形饰的特征表明它是本地产品。出自一号坑的一件超大刀形器,残长162厘米,亦同属当地生产(图4)。两者均采用硬度很高的类似石英岩的材料加工而成Y形器柄部复杂的勾卷状齿形饰,若在石英岩上加工,难度很高。假如三星堆玉石工匠已经有能力锯、钻、琢、磨此般坚硬的石材,那么他们大量采用较软石材为制作材料,应非由于工具或技术落后,而更可能是补充原材料的不足。该遗址出土的抛光工具硬度较高,有一些是软玉,其余主要是石英云母类(硬度7)材质(图 5)。数量有限的坚硬石材可能优先用于制造工具而非成品。
图3 Y形器,石英岩,公元前十二世纪
图4 Y形器,涂朱石灰岩。三星堆遗址出土,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期
图5 抛光工具
三星堆出土的大多数是扁平的片状器,其年代均属青铜时代。在发明使用金属工具之前,任何石材都只能靠研磨来加工;金属工具出现以后,三星堆石器工业分化为二。坚硬不宜用金属直接切割的石料,必然继续磨制(当然金属工具可以使研磨更加高效)。对于像石灰岩般较软的石材,则可以用金属工具直接整形,使加工速度和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许多器物的边缘或表面,均见呈直线的锯痕,表明采用了金属锯类的工具。齿饰内混合型戈(图6)表面的刻划线条纤细笔直,与两侧齿饰整齐相对,说明采用了尖锐的金属工具沿尺类工具进行加工。另一方面,这些器物上的穿孔均为单面钻,孔壁倾斜较甚,表明所用钻头由木、骨类较软材料制成,随着钻头磨钻穿孔时的缺损而直径逐渐减小。直径大的穿孔一般采用中空的竹类管钻,但同样从单面钻,留下倾斜的孔壁(图7)。传统上称为“有领璧”和“有领环”(在这里根据其用途改称为“宽边玉镯”)的器物则不同,其穿孔明显是两面对钻而成。这是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下游玉工最常用的标准操作方式,因此成为我们推测三星堆出土此类器物是外来产品的依据之一。
图6 齿饰内混合型戈,大理石,公元前十三世纪或公元前十二世纪
图7 璧和璧芯,石质不明。广汉真武村1987年出土
形制、尺寸和功能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绝大多数都是用于某拜祭仪式而专门制作的礼器。此外,有少数宽边玉镯、环、珠等是装饰品。礼器中有三类器形较为特殊。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戈形器,外形模仿中国青铜时代的兵器,即在木柄上横装具有双刃的青铜戈。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石戈(图8)显示了黄河流域典型玉石戈的所有特征。这样的戈在两个祭祀坑中都有出土。另一方面,二号坑出土的石戈(图9)器身拉长,这是三星堆的特有样式,可能是标准的地方形态变体。
图8 戈,大理石,公元前十三世纪或公元前十二世纪
图9 戈,白云石灰岩,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二世纪
第二类器物最受研究者关注,其柄部呈长方形,其上两侧凸出镂雕勾卷状齿形饰,器身逐渐外扩,顶端或平斜,或略微内凹,或分叉(图10、图11)。这类器物一般被称为“璋”。然而,“璋”字最早只见于战国时代古籍,它们的编者可能从没有见过这类器形,因此用“璋”来指这种器形不大正确。为了避免因沿用后世文本的名词而引发关联错植,本文概称这类器物为Y形器(forked blade)。
图10 Y形器,石质不明,公元前第二千纪早、中期
图11 Y型器,玄武岩,公元前十二世纪
Y形器由于造型奇特,亦无实用工具或武器可明确视为其原型,长久以来在古玉研究者心中是一个谜。苏蒙尼(Alfred Salmony)认为可以作为清理动物皮毛或去除鱼鳞的刮刀。稍后有学者推测该器形的原型可能是骨耜,并把其玉制品与太阳崇拜联系起来。三星堆出土的标本虽然未对讨论原型带来新线索,但却为认识其功能提供了新的信息。据刻纹刀型器(图12)上刻划的场景,可以考虑至少在三星堆文化范围里,这些Y形器是某种祭祀仪式上手执之器,使用时,内凹或分叉的一端朝上。
图12 刻纹刀形器,石质不明,公元前十二世纪
齿饰内混合型戈(图13)为第三类器物,目前仅见于三星堆。考古报告未将其与前述Y形器区分,统称为“璋”。但是,这类器形明显具有自身特色——其顶端不分叉或平斜,而是有像戈一样尖锐的锋——应单独区分为另一类。实际上,该器形结合了Y形器饰齿的柄部,和戈的逐渐收窄且不对称的援部轮廓,是二者的混合体。虽然这两种器形都起源和分布于其他地区,但是它们的混合器形目前仅见于三星堆。图6是这类器形中最特殊的一例,尖端镂雕一鸟,器身两面分别刻划一Y形器,图像比出土的实物更加繁缛精致。有意思的是,两个祭祀坑中都出有戈(一号坑出土45件,二号坑出土31件)。
图13 齿饰内混合型戈,白云石灰岩,公元前十三世纪或公元前十二世纪
通常在祭祀遗存中比较少见个人装饰品,因为它们本就不是用于祭祀的典型器物。三星堆的祭祀坑中有少量器物可能是装饰品,但与其推测它们具有特殊的礼仪功能,不如说它们因珍贵而被埋藏。其中绝大多数是环形器、有的带宽边,可能当手镯佩戴(图2)。不少这样的手镯出土时与贝壳、玉珠一起盛放在青铜容器中。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中宽边手镯(图14)只占很少数,但它们的青铜仿品却数量惊人:一号祭祀坑出土74件,二号坑出土56件,而且这些青铜仿品不见于其他地方。青铜仿品大量存在,说明其玉质原型由于材质优良和制作费力而价值高。而且倘若它们是舶来品的话,其珍贵性也会大大增加。宽边手镯可能起源于东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区,那里大量流行陶、石和玉质的镯、钏,但玉制品主要出土于青铜时代的安阳、江西新干和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出土青铜、玉石质环形器数量总计超过一百件,表明该器形在这里具有特殊的意义或地位,或者是特别流行。越南北部和马来西亚出土标本反映了该器形从四川一路向南传播。
图14 宽边镯,石质不明,公元前十三世纪或公元前十二世纪
三星堆出土的各类石器还有一项独有之特色,那就是尺寸多样。前述残石刀为目前所见最大者,即使长度残缺依然达162厘米。1929年曾出土一件石璧,直径69厘米,重50千克。Y形器尺寸从长达90厘米,到仅长三四厘米。不仅玉石器中有尺寸微小的标本,金箔中亦然(原本可能包裹在木器表面)。有些尺寸的标本很适宜在仪式过程中持用,而有一些则更适合静态展示,比如那些握在小型青铜人像手中的微型器物。
除了出土时盛装在青铜容器中的标本外,两个祭祀坑中绝大多数玉石器在埋藏前均经火烧。这令器物表面呈现白垩色、手感干燥以及有细龟裂纹或呈灰黑色(图12)。还有不少石器表面涂抹着一层红色物质,可能是朱砂(据发掘报告推测,无检测分析),完全掩盖了石材本身的颜色和纹理(图4)。这种处理方式常见于石灰岩质器物和璧,或是改善差劣材料的有意行为,抑或出于某种礼仪程序而涂彩。中原墓葬中常见朱砂,然而那里的具体做法是在尸体上或整个墓葬中撒满朱砂,而不是涂抹在个别的器物上。二里头遗址出土两件、郑州采集到一件的Y形器,表面涂有一层红色,这在中原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图15)。鉴于它们的材质是石灰岩而非软玉,齿饰轮廓和穿孔均与三星堆以北的中兴乡出土标本一致,因而推测它们可能是三星堆制作,通过某种情况流传到中原黄河流域。
图15 Y形器,涂朱石灰岩。河南偃师二里头三号墓出土
三星堆与周边文化
三星堆玉石加工业无疑十分独特,但却并未与其他地区玉石工业完全隔绝。戈以及宽边手镯等都是从黄河流域传入的器形;其他的器形则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容器大都源自长江中游文化;异型的玉石戈,可与湖北盘龙城二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标本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1997年至1998年在古城西郊一个墓地中出土了一件锥形饰,器形与长江三角洲良渚文化相类似,同时出土的灰白陶又与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2200—前1800年)石家河文化陶器相似。因此,在三星堆祭祀坑年代更早的阶段已经窥见到四川与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关系。
另外,要考虑带镂雕勾卷状齿形饰的Y形器的起源,视野却应要转向四川以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陕北神木遗址是唯一大量出土这类Y形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数量最接近三星堆,其形式虽稍简,但如出一辙。但由于在黄河流域的二里头和郑州也出土了少量Y形器,一般学者以为Y形器首先从神木东传到二里头,然后再从二里头传入三星堆。其实Y形器更可能是沿着黄河,自发源于秦岭的支流向南或东南传入四川。齐家文化不出Y形器,说明不经甘肃南传。安阳亦缺Y形器,更说明这器形在西北与西南地区的独特意义。所以,二里头和郑州发现的Y形器实际应是来自三星堆,经过长江中游北上到达黄河流域的遗址。此外,三星堆文化独特的Y形器更清楚地沿着另一个方向输出,南至中国香港、越南北部冯原(Phung Nguyen),乃至马来西亚。
就加工技术来说,三星堆玉石器显示出与陕北、甘南联系紧密。这些地区的石器制造有许多相同的特征:使用金属锯,在器表面留下直线锯痕;使用桯钻从单向钻孔,留下明显倾斜的孔壁;以及保留璧芯进行再加工等不见于其他玉石作坊的做法。三星堆和齐家玉石工匠利用的石材品种亦相似,材质包括软玉、各种石灰石和大理石。
三星堆文化的独特面貌,透过青铜器表现得十分突出。通过研究青铜器的来源、联系及影响,我们了解了该文化与外界的联系,经过以上玉石器的研究亦为此增添了更进一步的信息。因玉石器往往可能比入葬时间更早,可以带出比青铜器更深远的历史发展点滴,表现出长江上游与黄河流域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存在或许短暂的接触交流,而与周边西北和西南区域持续地保持联系。
(本文节选自《琢玉成器——考古艺术史中的玉文化》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授权发布)
非虚构 | 翻译好书 | 艺术史
《琢玉成器:考古艺术史中的玉文化》
苏芳淑 著
禇馨、代丽鹃、许晓东译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社
2021年9月
苏芳淑(Jenny F. So)出生于香港,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在罗樾(Max Loehr)教授的指导下,专攻新石器时期至青铜时代的早期中国艺术史研究。1990年至 2000年任史密森学会佛利尔 - 赛克勒美术馆中国古代艺术部高级策展研究员。2001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讲座教授及系主任,2002年起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201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2015年荣休后定居美国。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兼职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代表性著作有 Early Chinese Jades in the Harvard Art Museums (2019),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1995),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1980).
值班编辑 |小仙女
值班主编 |海 蓝
Contact us
主编
张英
执行主编
刘羿含
微信:happysueve
文化是国家的灯塔,阅读是文化的精神的象征。
我们仍然相信文化的力量,相信阅读的力量。
请您关注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我们会为您推荐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