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
启蒙,来自法文lumiéres,意思是光明。光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倘若一个人木讷,两眼一抹黑,脑子是空的,别人说什么他都信,什么指令都执行,不敢想,久而久之,就不会想,这就是一个蒙昧的人。
所谓启蒙,就是教人学会独立思考,从黑到明,有了光,不仅要感谢思想的导师,还要批评自己的导师,对今天的思想者而言,过河可以拆桥;而即将过时的曾经启蒙他人的人,也要有这样的胸怀,不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自己——否则,思想史就无法前进。我们不要怕批评自己的民族,不要怕批评自己的文化传统。越是批评,就越有光明的未来,以至于使如此的启蒙成为一个新传统。
西方哲学史,就是一个不断批评西方传统思想的历史,它在批评时并不直呼“造反有理”,而是以商量的口吻,说您说的这个意思我已经懂了,但是您说的这个意思,还可以像我这样说。而我说着说着,就说出来自己独自想出来的新东西,使传统在潜移默化中,被消解掉。这就比较爽,因为它符合内心的真实,没有把精气神用在与外面的某种“高大尚”的思想对照,而且并不像某些人事先所认为的那样,很费脑子。
不费脑子的,只需要略微任性一点,这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的必然结果,它并非一定来自思想家,可能出自一个小说家。现代法国作家纪德写了一部小说《伪币制造者》,书中主角爱德华想写一部小说,书名叫做《伪币制造者》。为了写好这本小说,他每天写创作笔记。结果呢?小说没写成,如何写这本小说的创作笔记却写的很好,甚至可以当成小说发表。
爱德华将《伪币制造者》这部小说,写成了如何写这部小说的小说,——这很符合人的真实思考过程。也就是说,人真正的思考——我是说在人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我们的教育糟蹋得几乎成为一个整天被疯狂灌输的机器人之前——人真正的思考过程,从来就不走直线。现在的教育是由一整套“你应该”组成的,你不能问“为什么应该”,你要认定“为什么”的问题,已经有人事先给你指定好了正确的方向,你的义务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走,你没有权利问为什么是这个方向?别的方向不行吗?这就不是一个好机器人的态度。但使人成为只知道服从指令的机器人,是违背启蒙精神的。
上世纪80年代,学生们回答政治考卷,会出这样的题目:“什么是‘五讲四美三热爱’?”我相信当时出这个题目的人,他自己现在也不知道答案了,因为它都算不上知识,它可能是某个大领导的的某个秘书,某天胡思乱想出来的,然后非常庄重地由某大领导,在正式场合宣读,就成为了不得的东西了,杜尚感到很厌倦,于是就对一个日常用品做了一次“异位移植”( hétérotopies,又译成“异托邦”),在博物馆这个非常正经的地方,展出了一件原本是正经的物件(一个小便池)却由于出现的场合不对头,就变成了在正经的地方展出了一件不正经的东西。不曾想,这暴力行为竟然成为艺术史上的创举,它开创了现成品艺术的先河,但它首先是行为艺术。它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品,并不在于杜尚对小便池做了什么艺术改装,他只是动了动心眼。于是,小便池就不再是现成的了,而是它如何成为一件艺术品的问题,这有点像爱德华把《伪币制造者》这部小说,写成了如何写这本小说的小说,呵呵,又相当于把艺术写成了艺术评论。
A“什么是启蒙”和B“什么是‘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两个题目中都有“什么是”,句式似乎一样,但就像只知道命题或者表达式的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并不意味着会造句。会造句或者会写作,并不意味着只会使用华丽辞藻,而要会思想。会思想在写作上的标志,在于句子的含义是开放的。以上的A就是这样的“活句”,究竟什么是启蒙,其意思不明,有待于思考与重新思考,而B是一个死句子,因为它的含义已经在打哈欠中完成了,它堵塞了任何一种突破与发展的空间。
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就区分了以上的A和B。B属于“已经有所见解而提出的主题”,对此,我们已经说不出任何新东西了,而A属于“尚无办法解释的”,它会逼着作者独立思考与创作。例如,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与杜尚创作的艺术史上第一件现成品艺术,它其实就是一个小便池。但是此刻,我们已经不再想对着它尿尿的感觉,全然丧失了这种欲望,它燃起我们别一种感觉、别一个方向的欲望,这就是启蒙,既是康德的也是福柯的启蒙,但杜尚不是在读了这两篇著名的《什么是启蒙》之后,才诞生了如此创作的灵感——这个问题,就属于“尚无办法解释的”,我也不想解释。
福柯说,“尚无办法解释的”问题,才更吸引人。他说的有道理,杜尚的小便池可以显露这一点,但不必证明。显露就已经是证明,这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其实是立刻爱上的,但为了解决这样会显得不正经的问题,你慢慢瞎编理由,因此,杜尚从来不在意他这件艺术品成功之后来自他人的排山倒海般的评论,因为这些评论属于模仿与伪造,而将小便池拿到博物馆展出的这个行为本身,就像love at first sight,但这还不够浪漫,它同时意味着不够诗意、不够哲学。在这里,诗意与哲学的味道浓郁,都在于它不仅停留在这个表达式本身,这感觉本身与其说是一种德行,远不如说是一种突袭过后,所造成的精神创伤。
因此,波德莱尔以一位现代诗人的敏锐指出,loveat first sight其实是love at last sight,“一见”就是“最后”,生就是死,这里没有功夫缠绵,因为我们在讨论启蒙的大问题——在这里,从黑暗到光明的转折点,就在于当我们意识到“一见”就是“最后”的时候,明白了艺术与哲学的创造性就来自这样的瞬间。此刻,我们纯粹思想感情关注的目光,发生了一次扭转,它不是其原来所是的东西,而是别的东西。
福柯正是用这样的眼光,重新理解康德说的“启蒙”:启蒙不是一个现在已经存在着的任何现成的东西,不是似乎有某种标准答案等着我们去背诵。启蒙意味着去发现差异,发现别一种思考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开放的,要有思考的勇气。这就是启蒙的箴言。所谓发现差异,就是出现了一些不曾有过的生活与思想事件。习惯的生活被打断了,这些作为事件的现象,无法用从前的解释加以解释,因为它们并不隶属从前的解释,它们意味着别的什么,而对于这些新鲜的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难以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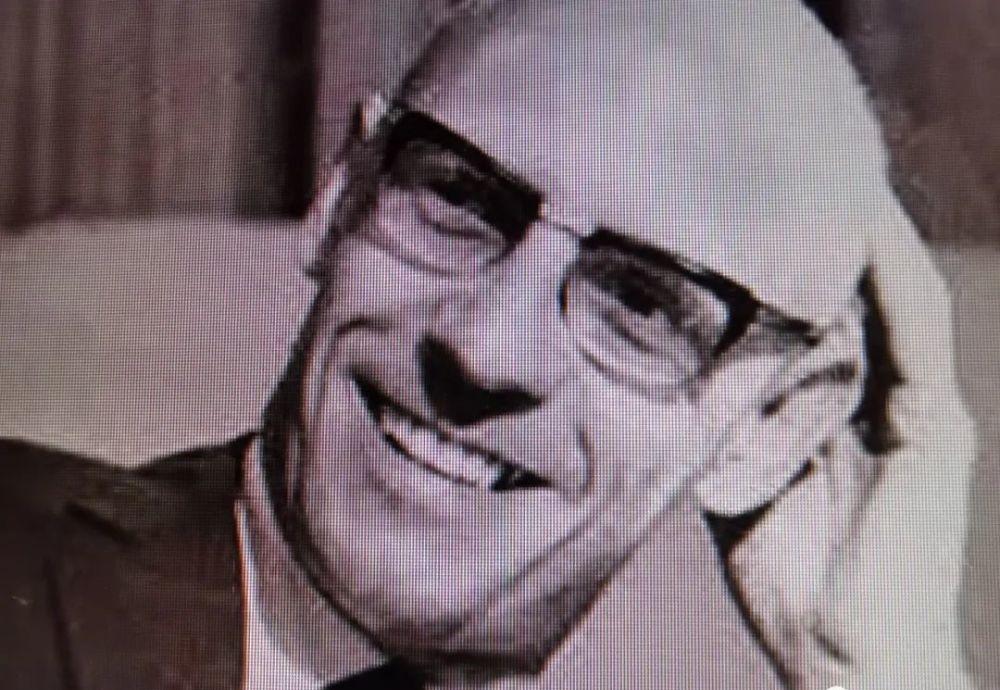
米歇尔-福柯(1926-1984)
不要迷信现有的知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如果一个人的心智只相信权威(专家、别人,有资格代表某领域说话的人),就等于把自己的理解力交了出去,这样的人,是心智不成熟的人。比如,某本权威的书或者文章,代替了我们的理解,我们读什么就信什么(为了尖锐,我们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这本书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福柯的《词与物》,或者是他俩的同名文章《什么是启蒙》)。或者,一位牧师代替了我们的良心……总之,在福柯看来,“康德是把启蒙描述为一个历史转折点(moment),在这一点上,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参见福柯《什么是启蒙》)
乍听起来,我们倾向于完全赞同康德以上的观点,但可疑之处,在于康德在这里只说出来某种一般情况,他默认了自己的哲学就走在启蒙之路上——我们承认这一点——但就像德里达所说,启蒙的光从来都不是一个样子的,还有来自不同方向的光。我们来看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对于康德式启蒙的质疑:康德认为,理性要恰当地合理运用,他用自己的《三大批判》解决了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应该希望什么?最后回答了人是什么?于是,康德自己,现在成为了权威。一个挑战思想权威的人,结果自己成为了权威,成了“圣康德”。依照我的理解,福柯批评康德式启蒙,问题的关键,在于“我认为,如果这样来看待这篇文章,我们就会从中认识到一种出发点:它的概貌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态度。”(同上文)。
福柯同意这样的说法:所谓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是态度或者模式的问题,而不是时间断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用理解的模式,来划分思想史。康德的理解模式属于18世纪,那种启蒙模式,是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说话的,相信科学思维的确定性,试图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目的式思维,试图建立一揽子解决人类全部困境的总体方案。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多塞的《人类进步史表纲要》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都打着“为了人类”或者“解放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号。问题不在于这些口号不是正确的,而在于它们固执地认为只有走自己指出的“正确”方向,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这是使用大字眼,进行宏大叙事。它是怎么发生的?让我们具体来看:
如果我们不用大字眼,那么所谓现代或者当代,其实是一个意思,就像“现在”和“当下”是同样意思,都指此刻此情景——这时发生了两种情景,一种是在我们的脑际诞生了某种纯粹的计划、想法、方案、理想,某种志向,然后我们将这些念头写出来。于是,就有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共产党宣言》——作者此刻的理想是,由于有了自己的书,“时间开始了”。但这种开始,相当于时间被冻结了,因为它建立起某种解释历史的模式,一切杂多的生龙活虎的经验都要被套进这个模式里筛选,从而我们说,思想史从此再无真实的时间,这是在反动的意义上把“一见钟情”凝固为“最后一瞥之恋”,因为之后的日子缺乏真正的新思想了,感情被困在某一个无形的笼子里,只是在重复“柴米油盐”的乏味日子而已,这等于杀死了真正的生活。
那么,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换句话说,此刻,全世界有精彩纷呈的不一样的此情此景,它不遵循某一个所谓正确的思想路线前进,而是上演同一个时刻的不同内容,或者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或者福柯前面说到的“异位移植”或者“异托邦”的情景,这就像在康德(1724年出生)与马克思(1818年出生)之间,还有叔本华(1788年出生),而从思想史来划分,尼采属于叔本华连带着叔本华属于后现代,而马克思更属于康德连带着马克思属于传统启蒙思想家,这就是按照思想态度或者模式来划分思想的时代,而不可能按照钟表时间的真实顺序。
如果我们把现代或者当代的大字眼因素去掉,那么等于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如果这里会发生某种模式的话,那它完全取决于临时性(为了证明这一点,此刻我放弃打字,我抬起了胳膊,它取决于两点:第一,我对这个姿势,有某种兴趣。第二,我有体力能抬起胳膊),我胳膊在空中划了一条弧线,然后打电话叫外卖,然后继续打字。于是,在短短的一分钟内,我的手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姿势,这姿势讲述了此时此刻关于我的手的真实故事。这里发生的时间与空间都是真实的,它们被我的手占据着。
我的当代性,此刻就是我的手与手所做的事情之间的关联方式,一会它就变成别的方式了,而这些不同的方式之间,是断裂的关系,因为萨特曾经说,人的手是肮脏的,而德勒兹在一次访谈中认为,萨特说的是对的,因为同一只手,什么东西都摸,而不仅仅只是摸那些高尚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事先给手制定一个“5年计划”,从此以后,手就只能按照这个计划摸东西,这似乎是开玩笑,但我们人世间真的曾经上演过这样的玩笑,不仅是在半个世纪前搞过后来实在搞不下去了的“计划经济”,还包括“计划思想”,它现在还在上演。比如,如果我们生造出一个专业,然后全国指定一本教科书,往18岁的孩子的大脑里灌输,这就相当于我以上说的给手的活动方式,制定一个5年计划,不把手烦死,决不罢休。
那么好了,我的手现在可以与任何东西发生关联,这是关于手的潜在可能性,手因此而兴奋不已。比如,我可以只用一个手指头敲字,也可以闭着眼睛练习盲打。总之,在每个不同的人那里,关于自己手的故事都是片断的、破碎的。
在以上的语境下(不是指“手的故事”),福柯笔锋一转,出乎所有读者的意料。原本是在讨论康德的现代启蒙模式问题,福柯却用一种思想突袭的手法,这样写道:“勾勒这种现代性的态度,因为人们广泛认为,他对现代性的自觉意识,是19世纪最为敏锐的意识之一。他,就是波德莱尔。”福柯在这里首先冒犯了哲学史,因为哲学史不会给诗人波德莱尔留出一个章节。于是,我想到了和福柯是一伙的思想家德勒兹,他说哲学史行使某种镇压的职能,相当于对思想的鸡奸,也就是不生育(参见德勒兹访谈录《哲学与权力的谈判》中译本)。在此,福柯和德勒兹、德里达一样,求助于艺术家,以获取新启蒙的灵感。
在写《什么是启蒙》时,福柯只是把康德的同名文章匆匆带过,却用更大的篇幅讨论波德莱尔诗歌中的思想。他这样写道:“人们经常把现代性概括为对时间的非连续性的自觉意识:与传统的决裂,对新颖的情感,在不断逝去的时刻前的眩晕。当波德莱尔将现代性界定为过渡、短暂、偶然的时候,想表达的似乎正是这个意思。但是在他看来,要成为现代的,并不在于认识并接受这种无休止的运动,而是在于针对这一运动采取某种特定态度。存在某种永恒的东西,它既不是在现在时刻之外,也不是在现在之后,而是在现在之中。正是在对这永恒之物的重新捕捉之中,体现出审慎从容、不易屈服的态度。现代性不同于时尚,后者只限于对时间的流逝念念不忘;现代性是这样一种态度,它促成人们把握现时中“英雄”的一面。现代性并不是对于短暂飞逝的现在的敏感,而是将现在“英雄化”的意志。”
筛出以上引语的关键词:非连续性、决裂、新颖、眩晕、短暂、偶然、现在之中(=永远的现在==正在发生=悖谬的)、重新捕捉。最后,就像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赞誉:抓住灵光即将消逝的瞬间——那么,现代性与时间的断裂(成为瞬间)有关系。这瞬间呈现为当下在场——空间、构成有情节的事件、事件之间的连接是不能连接的连接,因为如上所述,在于同时发生的不是同时发生的、目光是不对称的,破坏同一性。例如,语言没有能力表达眼睛看见的。这些,都显露出有限性。
福柯模仿波德莱尔的说法:“你们无权藐视现在”。什么是现代人呢?现代人是大城市的人,是由陌生人组成的人,是人群中的人,是繁荣闹市区里的闲逛者,他们穿着燕尾服和黑衣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对于一去不返的旧时代的无情的哀悼。似乎在说,美好的时刻就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抓住瞬间的美好——这些描述性的思想,均出自波德莱尔,福柯以肯定的口吻,几乎原封不动地加以引用。这里所肯定的,与其说是随境而生、稍纵即逝的快活,不如说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谓“人死了”的潜台词:人是不可定义的,不能从一个固定的本性判断人,而在此之前,萨特有一个说法:“人不是自己所是的,人是自己所不是的”,这都是在批评笛卡尔将人的存在=我思。福柯同意拉康对笛卡尔的讽刺:“我在我不思的场所”,这之前有诗人兰波说过“我是他人”,而再之前,克尔凯郭尔明确反对笛卡尔,因为笛卡尔把事情的顺序弄反了,因为为了能思考,人首先得存在。
那么,人是什么,显然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任何试图给人下定义或者试图发现人的本质的说法,都只属于传统启蒙,而不属于现代性的启蒙。传统启蒙给人一个框子,只用这个框子解释人。例如“人是理智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或“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
当福柯说“人死了”,他的真实意图不是字面上的。在这里,福柯与德里达的想法是相通的。就是说,不能从概念或者判断出发,提出一般性的“什么是……”或者“是什么”的问题,而要问“是谁”,来自哪里?其特质是怎样的?人是由立体的元素组成的,而不能将人还原为一个平面的陈述句。在《词与物》中,福柯至少从三个基本元素呈现人的活动场景:生命(有欲望、有激情)、劳动(物质的、财富的)、语言表达(自身情形的再现)。将有限性融入这三种元素之中,不必直接说“人”,人已经显露其中了。
有理由相信福柯在以上《词与物》中得出“三维人”的灵感,与他阅读波德莱尔有关(当然不仅于此)。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又一次引用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对画家贡斯当丹-居伊的赞美:“自然”的东西“不止于自然”,而“美”的东西也“不止于美”,个体的对象又象是“被赋予一种象(它们的)创造者的灵魂一样的充满活力的生命。”这指的是绘画作品,它显露人的欲望(美的生命冲动)、身体劳动(画布)和语言(绘画语言)。“将自己的身体、行为、感觉、情绪乃至他的生存本身,都变成一件艺术品。在波德莱尔看来,作为现代人的人不是去发掘自己,发掘自身的秘密和隐藏着的真实,而是要去努力创造自己。”(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对于波德莱尔眼中的现代人的评价)。换句话说,一个现代人,不是像传统启蒙思想家所教诲的那样,去挖掘人的本质,而是使自己变身为别一种样子的人,使从前的自己不再认识现在的自己。这相当于把自己创造成一件艺术品,就像一个美术老师这样回答一个学生的问题——学生问老师:“什么时候才可以说我画得很好了?”老师回答:“当你对自己的画作感到诧异,问‘难道这是我画的吗?’的时候。”
福柯说,不能用传统的人道主义绑架启蒙,他“不愿意接受那些最糟糕不过的政治制度已在整个20世纪一再重复了的塑造新人的筹划。”这就重拾起康德的启蒙精神:“启蒙”一词,不与学者而是与哲学家站在一起,它意味着批判,与传统的断裂。
但是,在最后的总结中,福柯对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呼吁的走向成熟的理智时代,似乎并不完全认可。什么叫成熟呢?它默许了一个成熟的标准、一块思想之路上的界石,我们最好不要到达这块界石,否则就会提出“成熟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是的,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终于娜拉觉醒了,她离家出走了,但这种非此即彼、毅然决然的态度假设了有理想状态的存在,其实是没有的,没有不包含幼稚成分的所谓“成熟”。因此,对于批判哲学,还要继续批判,其中就包含了对成熟本身的批判。因为就像萨特在《恶心》中这样讽刺自学者,虽然你毅力非凡,虽然你实现了宏大的读书计划,读遍了图书馆里从A到Z开头的所有作者的书,你也没成熟,因为你只是高兴了一小会儿,就会这样问自己:“往下呢?接下来我怎么填满自己的时间呢?”这个问题对于娜拉同样存在,她离家出走之后,该去哪里呢?如何解决自己的生活欲望呢?生活世界是由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甚至都比自己年轻,我不想和他们一样,但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他们的,如此等等。我想不出答案,就不可以说我很成熟,但用“幼稚”来形容我,似乎也没有说到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