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雨果
在群星璀璨的北宋文坛,欧阳修是泰山北斗般的存在,他领导诗文革新运动,开创一代文风,是诸多后世文豪名家心中不灭的灯塔。
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欧阳修的伟大在于,他不但个人成就卓越,而且心胸宽广、爱惜人才,发现并举荐了很多青年才俊。唐宋八大家中,除了唐朝的柳宗元和韩愈,再除了欧阳修自己,其余五人都曾得到过他的举荐。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
欧阳修比王安石年长14岁,王安石初出茅庐时,欧阳修早已是文坛领袖。王安石高中进士后,早期一直在地方做官,而欧阳修却是京官,所以二人起初并不相识。但是,王安石一直仰慕欧阳修的学识,欧阳修对王安石的才华也有所耳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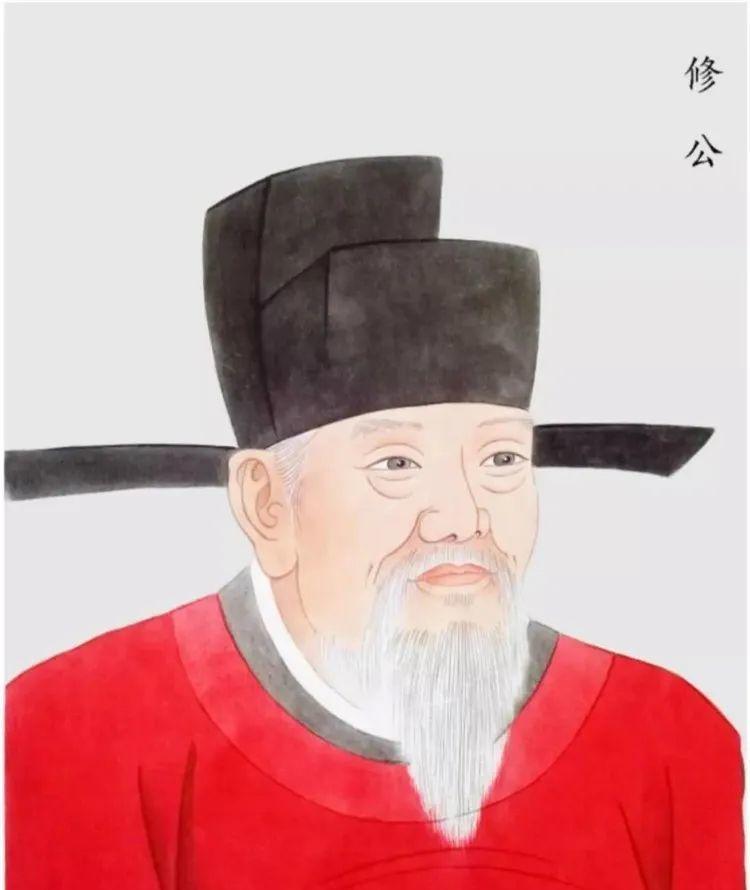
(欧阳修画像其一)
终于,在欧阳修的主动邀约下,王安石欣然登门拜访。两大才子坐而论道,这是一次堪称伟大的会面,二者具体聊了些什么,后世不得而知,但很明显,他们一见如故、彼此欣赏。何以见得呢?有诗为证。
相谈甚欢,情到深处,欧阳修主动赠诗一首: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王安石画像其一)
这首诗叫《赠王介甫》,介甫是王安石的字,《赠王介甫》的意思就是写给王安石的诗。欧阳修的这首诗,简直是把后生晚辈王安石捧上了天。
“翰林”指翰林学士李白,“吏部”指吏部侍郎韩愈(有争议,详见后文),前两句是说王安石写诗堪比李白,写文堪比韩愈。第三句感慨自己虽然年事已高,却雄心尚在,第四句又转向夸赞王安石,发出疑问:以后的人还有谁能与你一争高下呢?
第五句第六句的意思是:如今官员腐化,贪图享乐,你我却不随波逐流,仍然心系社稷。第七句第八句再次恭维王安石:很早就听闻你的大名却未能有幸相见,如今相逢何不把酒言欢?
(欧阳修画像其二)
受到文坛泰斗如此抬举,王安石自然要写诗回赠,于是提笔写下一首七言律诗: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这首诗名叫《奉酬永叔见赠》,永叔是欧阳修的字,《奉酬永叔见赠》的意思就是写给欧阳修的回诗。
(王安石画像其二)
前两句是说:对于传扬孔孟之道我还是有雄心的,但对于写诗作文,我实在感到力不从心。第三四句的意思是:有朝一日如果能领悟孟子道义的奥妙,我就心满意足了,岂敢奢望像韩愈一样成为一代文豪呢?
第五句和第六句是恭维欧阳修:作为众多仰慕您的晚辈之一,我能来拜访您已经感到非常荣幸。第七句和第八句再次自谦:您写诗如此褒扬我,我深感惶恐,只怕自己是浪得虚名。
总体来看,诗的前四句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志向,是对欧阳修赠诗前四句的回应;诗的后四句表达了对欧阳修的尊敬和感谢,是对欧阳修赠诗后四句的回应。
(欧阳修书法)
相对于欧阳修赠诗的真情实感、直抒胸臆,王安石的这首回诗却十分值得玩味,看似谦虚恭敬,却暗藏野心与分歧。
回诗中,王安石反复强调自己志不在写诗作文,而在于宣扬孔孟之道。何为孔孟之道?治国平天下也!欧阳修欣赏王安石,在于学问、在于才华、在于写诗作文的水平。但是,这些都不是王安石追求的,他的志向在政治,而不在文学。
王安石的回诗暗含了这样的一层意思:“您小看我了!我的才华岂肯局限在文学上?我的理想是为万世开太平。”诚然,李白诗才虽高,在仕途上却一无所成,韩愈文章虽好,终其一生也不过做到吏部侍郎,而王安石的目标却是位极人臣,既致君尧舜上,又为百姓谋福利。欧阳修确实是看错了王安石。
另外,对于欧阳修的赠诗和王安石的回诗,还有一个有趣的乌龙事件,非常值得一聊。
(王安石书法)
南宋文学家陈鹄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欧阳修《赠王介甫》中“吏部文章二百年”一句,其中的“吏部”本意是指谢朓。而在王安石的回诗《奉酬永叔见赠》中,则有“终身安敢望韩公”之句,很明显,王安石理解的“吏部”是代指韩愈。所以当欧阳修看到王安石的回诗后,不禁感叹道:“介甫错认某意!”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欧阳修和王安石到底谁用错典故的争论。
欧阳修的支持者认为此处的“吏部”当是谢朓。理由如下:第一,谢朓曾任吏部尚书,沈约曾夸谢朓之诗“二百年来无此作”,与“吏部文章二百年”相合;第二,如果 “吏部”指的是韩愈,从他当吏部侍郎到欧阳修写《赠王介甫》,时间何止二百年?
王安石的支持者认为,此处的“吏部”理解为韩愈更合适。理由如下:第一,韩愈曾任吏部侍郎,向来有“韩吏部”之称;第二,孙樵上韩愈书,也有“二百年来无此文”之赞誉;第三,“吏部文章二百年”,很明显,说的是文章,韩愈以写文见长,而谢朓主要是以诗闻名。
(韩愈画像)
笔者以为,既然韩愈和谢朓都曾在吏部任职,又都曾得过“二百年来无此作/文”的赞誉,那么,欧阳修和王安石的用典都不能算错。若非要一较高下,说出二者谁的用典更加准确,笔者倾向于王安石。毕竟,“韩吏部”之名远胜“谢吏部”,前者为“熟典”,后者为“僻典”,即便欧阳修写诗时心里想的“谢吏部”,王安石理解为“韩吏部”也未尝不可。只能说,欧阳修读书多,敢用“僻典”,王安石也不差,能将“僻典”置换成更符合语境的“熟典”。
欧阳修的《赠王介甫》,王安石的《奉酬永叔见赠》,这一老一少,一来一回,两个人,两首诗,其中竟然蕴含着这么多学问,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么多故事。那么,从历史成就、才华能力、道德品质、写诗水平、用典准确等各方面来看,你更敬重文坛泰斗欧阳修,还是更钦佩政坛新秀王安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