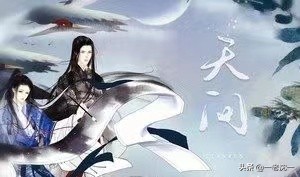
中国的先民,一定相当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头顶上的“天”。
更早先民的这种关注,现在的人,已经无法确切知道其究竟。
好在,万年以前的岩画、壁画这一类“物质文化遗产”,寥可使对当时人们关于对天地的认知,了解一二。
所以,文字就尤显重要。
即便是几千年前的文字,所记录的,或许包含着更久远之前人们的“文化”。
比如“天”。
《说文》曰:“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
《尔雅.释言》:“颠,顶也。”
段玉裁说,凡物之“顶”皆言“颠”。如“山顶”即“山巅”。
而“天”作为“顶”,如许慎所云,是“至高无上”之“顶”。
“颠”的本义,是人的头盖骨,所以有“头顶”一词,又称“天灵盖”。
许慎收入《说文》的小篆“天”字,一定来源于甲骨文,尽管他本人并无缘见到此源头。
甲骨卜辞中的“天”,或为表示“人形”的“大”之上,加一“短横”;或在“大”上加一“口”字——“头顶”之上皆为“天”,或者,人之“颅顶”即“天灵盖”。
不论甲骨文还是小篆,“天”,都是“会意”。所以,“从一、大”。
“从一”,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意,后面会讲到。
“从大”,则指“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没有比“天大”之“更大”。
这是古人对“天”最原始最直观的认知。
可知,先民最初是从“空间”角度为“天”下“定义”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爆发“农业革命”的三个原发地之一。于是,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那时中国的先民,应该已经开始从“时空统一”的角度来观察和定义“天”了。
《尔雅.释天》云:“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另有一说是“春为昊天”“夏为苍天”。
郭璞《注》曰:苍天“万物苍苍然生。”昊天“言气皓旰。”旻天“旻犹愍(悯)也,愍万物雕落。”上天“言时无事,在上临下而已。”
北宋邢昺《疏》:“言上所陈是四时天之名也。”
“苍天、昊天、旻天、上天”,是“四时”即“四季”的“天之名”。
“天”,不仅是“空间”概念,也是“时间”概念,是“时空” 的统一。
冬天为“上天”,因为“言时无事,在上临下而已。”显然,这与冬天是农闲季节有关;但是,“在上临下”,已经将“天”人格化,或曰开始“神化”了。
《诗.王风.束离》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人何哉!”
平王东迁,镐京荒废,遍地禾黍。此诗因之感叹道——“高高在上老天爷,这是何人在施咒!”
这个“苍天”,已不是春季之“天”,也不是夏季之“天”,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灵”了。
古人对于非人力可控的事物、事件,大多也归于了“天”,如“天产”“天灾”等等,或曰“天意”这也增加了“天”的神秘色彩。
有意思的是,甲骨卜辞中,“天”有“颠顶”之义、“广大”之义、兼作人名、地名、方国名,至目前,未见直接代指“神灵”之义。“帝”或“上帝”是“天上”的最高神;包括成为“神”的先祖先公,也居于“天”。但是,“天”,只是“神”之居所。
至周初,“天”,则成了有意志的神,而且是万物的主宰。至少从周初流传下来的典籍中是如此。
《尚书.多方》曰:“洪惟图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这是说,夏商末代君主败坏上天之命,又不敬念于祀礼。于是“天帝降灾异以谴告他们”。
顾颉刚和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中说,“殷人言帝,周人言天”。
当然,殷商卜辞中,并不乏惧畏“天谴”的思想,只是,皆以“帝”或“上帝”不高兴或怪罪表述之,与周人用语的确不同。
这是一个“重大区别”。
《诗.周颂.昊天有成命》,是周王祭祀成王的乐歌。其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此言,“昊天”之神,降大命于文武二王。这与前述“苍天”不独指“春”一样,“昊天”亦不独指“夏”而亦为“神”。
《尚书.尧典》说,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如月星辰”。或因《尧典》成文于周,同上理。
另,《尚书》之《甘誓》中的“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汤誓》中的“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盘庚》中的“予迓续乃命于天”,都应该是依周人语言所记录之。
可见,周初,具有“国家色彩”的“政.治观”,已完全成熟并形成体系。其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曰“君权天授”;二曰“奉天承运”,后世称为“天命观”。
《诗.大雅.大眀》,是周族重要史诗,集中表达了上述思想。
其诗云:“天监在下,有命既集。”
是说,上天监察人间世,天命已然归周邦。
又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是说,天帝有命从天降,运命降给周文王,建都周京兴周邦。
这样的“政.治观”,滋生了“皇天”一词。
伪孔传古文《尚书.大禹谟》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许慎所著《五经异义》引《尚书说》:“天有五号:尊而君之,则曰皇天;元气广大,则曰昊天;仁覆悯下,则称旻天;自上监下,则称上天;据远视之苍苍然,则称苍天。”这是古文经学的代表性观点。
古代中国最早的“国家”,大约形成于距今6000年前后。从考古成果来看,红山文化时期已具有了国家雏形。
这只能说是“大约”,或许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这个时间还会提前。
插上一句,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界和史学界学者,将“国家”、宗教的产生和“城市”的形成,作为评判“文明”的新标准。国际上,也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这一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委员会,将良渚遗址认定为“典型的城市文明”,是最好的例证。
上述的“政.治观”,一定是伴随“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然而,其又不可能凭空突然产生。
实际上,在这之前,上古先民已经更早开始了对“天”的观测,并根据想象,形成了对“天”,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的崇拜。
因此,前述“政.治观”产生的前提,第一是更早的先民对“天”之观测;第二是基于想象,由对“天”的崇拜而形成的“原始宗.教”。
西水坡古墓图片
关于先民对“天”之观测,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是最好的考古实证。
其45号墓,显然是依据“观象授时”,按照“正北正南”的“子午线”和“正东正西”的“卯酉线”精心设计的。墓中摆放的“髀骨”和用蚌壳摆成的“北斗星宿”图案,说明当时的古人,已经掌握了“髀表测影”和“北斗定时”的方法,并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以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无疑是“东宫苍龙”和“西宫白虎”的象征,鸟和鹿的图形,极可能是后来的“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的最初体现。这表明,当时古人,已对太阳视运动轨道之“黄道”周边的星群星宿,有了足够详细的观测。
关于古人基于想象的对“天”之崇拜,最好的实证,同样是西水坡古墓。
墓中,发掘出三组蚌壳图案,展示了目前已知最早关于人死后灵魂升天的“理想路径”——死者头南足北,居北;南面有人骑龙图案,这与古人所认知的地于北、天于南一致。而龙、虎、鹿、鸟等,皆为“四灵”,即负人之灵魂飞升至天的“工具”,称之为“灵蹻”。这所表达的,应该就是古人“以祖配天”的古老理念。
红山文化遗址中,将死者头下枕垫中空的礼玉枕;马王堆汉墓“非衣”上的升天图;以及众多大型古墓皆以南向墓道为长,等等,都应该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周髀算经》云:“知地者智,知天者圣”。“圣人”,是古代最早对掌握王权者的代称。
西水坡古墓距今6500年,当时是否已经形成了雏形的“国家”尚难定论。但是,45号墓主的入藏实景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史实——在那个时候,贫富和社会地位的差距已然形成,死后“有资格”灵魂升天的,不是“国家”的君主,也必定是部族的首领。
还有一点更重,即当时的“天文”知识及其观测,一定掌握在少数“巫觋”手里。这些人,本就处在社会各阶层的顶端。通过“观象授时”,则更使他们找到了论证自己“识天”“通天”“受命于天”的根据。
前面引述了《尚书.尧典》的记述: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论语.尧曰》又云:“‘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
“观天授时”和制定历法,是一种“特权”,并且是“君权天授”之“天命论”的政.治基础。
如前述及,这就不仅有了“皇天”一词,也有了“天子”“皇帝”等代表权力的称谓,并形成了最初的“天人合一”哲学。
《礼记.曲礼下》曰:“君天下曰天子。”
说到“哲学”,“天”,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原初”概念。
《周易.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天”是“阳”,“地”是“阴”;“天”是“乾”,“地”是“坤”;“天”是“一”,“地”是“二”……。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阴阳易变转圜”哲学。
《周易.系辞上》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还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道”“天道”“天理”,无疑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念。这些理念后来的“衍化”不算。
古代,对“天”之观测和历法制定的“专业化”,应于周代始。
《周礼》记载了周王室官职,设“天官”位。当为后世“礼部”之渊薮。
周代,也有了“专业化”的天文著作,《周髀算经》为其代表,其中,记述了更早先民的天文和数学成就。
先秦诸多天文成就中,以数学方法对“天”之测量堪称惊艳,后世称之为“勾股定理”。
《国语.楚语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注》云:“咫,言少也,此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
可知,春秋战国时,天文已普及到与治诸侯之国紧密相连。
这一时期,与诸子百家争鸣相吻合,人们对“天”的探讨愈渐活跃。代表性的,是《楚辞》中的《天问》。《天问》,即是“问天”,询问了与“天”有关的一连串问题。“天有九重”,亦是最早的文字记载。
《荀子》也发表了自己的著名见解:“天无实形,地之上至虚者,皆天也。”
然而总体上,此时的“宇宙观”,即“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这在《周髀算经》中,已经清晰表述过了。其“以方出圆”和“七衡六间图”,绝对是先秦时期领先世界的“科学”创建。
而这个理论已知最早的原型,至少可前推至距今6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的圜丘和方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