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的一天,一架银色飞机穿梭于苍茫云海间,从北京正飞往福建。机舱内,坐着一位年逾古稀的白发老人,外表坚毅而平静,心中的思绪,却犹如机舱外翻涌的云海,急迫地奔向千里之外。
他,就是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陆定一。早年曾任红军、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日报》总编辑,是中共老一辈革命家,新中国的元勋之一。他的文章《老山界》《金色的鱼钩》,都被列入小学语文课本,读起来脍炙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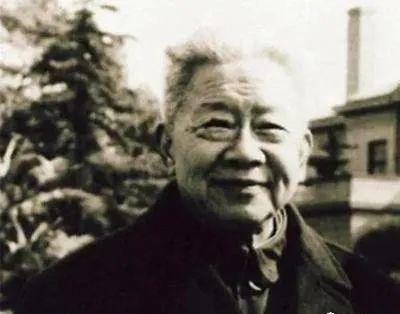
他的文章确实是好,后来还帮他找回了自己的女儿。不过,这里暂时按下不表,先说他要去了却一桩46年的心愿……
福建闽西长汀县奎田村的一户农家里,相依为命地住着一家三口:范其标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范家定。多年来,让范家定疑惑不解的是,每每逢年过节,父母都要在饭桌上多放一副碗筷,而那个位置,却总是空席。
终于有一天,范家夫妇对儿子道出了原委:他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位女红军,并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生母遗物给他。经过艰难的辗转、周折、等待,在知情人的帮助下,范家定终于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
随着飞机的降落,陆、范两位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范其标老人用颤抖的声音说:“陆老,总算……,总算把他带到您面前了,现在该让他改回陆姓了。”
“不!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是你们抚养了孩子,你们是他的再生父母,孩子就继续留在你们身边,孩子的姓也不必改了。”双方谦让之下,陆定一最后表示,将孩子的姓改为“陆范”,代表孩子是两家的人。
失散多年重逢必然有着万分的思念,思念儿子的同时,也思念着孩子的生母——唐义贞,她已牺牲多年;同时,也思念另一个至亲骨肉。陆老告诉儿子:“你还有一个比你大3岁的姐姐,她至今还下落不明!”
“爸爸,既然我还有个姐姐,那还等什么,我们快点找吧!”陆范家定得知还有亲人在世,急切地说道。
“已经找了几十年了,如果她还在的话,应该是50多岁了……”陆老感慨地说道,心里一直在呼唤:“女儿啊,你到底在哪儿啊?”
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不远处的邻省江西,有一女子常常对着星空,伤心哭泣:“我命苦哟,我天生就没有父母,没有啊……”
1987年9月的一天,南方冶金学院社科系的一位名叫赖章盛的教师照例来到系资料室看书。他在一本《风展红旗》的书中,看到了陆定一的文章《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文章写于1981年底。从这篇文章中,赖章盛了解到,唐义贞是陆老的亡妻,17岁参加革命,红军时期牺牲于福建。
文章中还介绍了唐义贞烈士所生的两个孩子。老二是个儿子,已经找到;老大则是个女儿,失散了47年,至今杳无音讯……
赖章盛越读越是激动不已,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就属于红军失散子女,至今尚未找到亲生父母。等读完全文,他再也按奈不住心情,立刻提笔给陆老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您女儿仍无下落,这使我联想到我乡下母亲的身世。我的母亲,也是红军长征前留下的子女,现在仍不知亲生父母是谁。但从名字、年龄、寄养地点和时间看,我母亲与您失散的女儿叶坪,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赖章盛在信中用四个数据对自己母亲是陆老女儿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一是名字。首先引起赖章盛注意的也是名字,陆老文章中提到的失散女儿的名字叫“叶坪”,而赖的母亲张来娣的小名叫“野萍”,这个小名只是当年来托孤的张德万口述,到底是哪两个字,早已无人知晓。那么,“野萍”不排除就是“叶坪”的可能。
二是年龄。陆老文章中说自己女儿是1931年生的,按时间推算此时应该56岁了。这一年龄正好与赖母同岁。
三是寄养时间。陆老文章所述寄养时间是长征时,中央红军长征是从1934年10月开始的;而赖章盛记得祖母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母亲是在“挖番薯的时候”被人带来的,当地农村挖番薯的时间是11月份左右,考虑到母亲可能是红军出发后辗转来到赖家,有所延迟,所以月份基本吻合。从年份上讲,赖章盛知道自己母亲是3岁时被寄养过来的,她又是31年出生的,送过来时正好是1934年,所以,年份也对上了。
四是寄养地点。陆老文章中写的是“寄养在雩都”,而赖章盛家乡于都以前就是写为“雩都”,地点也相符合。
从以上四点判断,她们还真可能是同一个人!
那么,赖章盛的母亲究竟是不是陆老的女儿呢?陆老收到赖章盛的来信后,心中当即一紧:这不是跟1956年那次调查是同一家吗?难道那次调查有所疏忽?他立刻请来亡妻唐义贞的八妹唐义慧商议。
“再也不能错过了!那年,您让我验证那张照片,我说不太像。如果她真的是叶坪,就是我一句话误了31年呀!”唐义慧老人脸上淌着泪水说道。
唐义慧老人已经74岁高龄了,她为找不到姐姐的女儿而难过了大半辈子。她永远不会忘记,两个哥哥为寻找她在江中遇难!母亲面对她的画像,恋恋不舍地离开人世!
陆老听后,当即委派身在福建的儿子陆范家定去江西调查核实。江西省委、省政府对此事也高度重视,派出联合调查组,与陆范家定一起来到赖章盛的家乡。经过严格而缜密的调查,终于把当年的情况和多年来几次阴差阳错的轶事给理清楚了……
唐义贞出生在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大哥唐义精就与董必武、恽代英交往甚密,五哥唐一禾受闻一多爱国思想影响,是一名坚定地反帝反封建分子。受兄长的影响,她很快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唐义贞受党组织委派,前往苏联学习,那是她梦想的地方,但此时的她毕竟才18岁,而且当时母亲正患有病毒性痢疾,多日昏迷不醒。她真不忍心离开,但为了革命,她不得不忍痛离别。临行前,她跪在母亲床前,拜了三拜,流着热泪而去。当时她并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唐义贞在反对王明一伙的斗争过程中,认识了陆定一,他们从相识到相知,建立了感情,不久就结为革命伴侣。
后来,她和陆定一先后回国,并到了中央苏区工作,在这里,他们又重逢了,并于1931年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由于出生在江西瑞金的叶坪,所以取名“叶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本来,唐义贞可以随主力红军走的,但是她再次怀了孕,行动不便,按照当时的规定,她必须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于是她不得不再次与丈夫陆定一分别;又因为行动不便,也不得不与女儿“叶坪”分别。
因为长征,许许多多中共党的领导人,都这样将自己的孩子秘密留下了。毛泽东的儿子小毛就是这样留下的,刘伯坚的儿子刘豹,以及林伯渠的儿子,邓子恢的儿子也是这样留下的……
红军主力长征后,唐义贞把3岁的女儿“叶坪”托付给一个叫张德万的红军同志,让他把孩子带到瑞金之外的农村找个人家寄养。张德万是江西吉安人,因为生病而不能参加长征。后来张德万把孩子交给于都一户农民家庭。
骨肉分离的时刻,唐义贞心如刀绞,望着张德万背着孩子远去的身影,不禁泪如泉涌,却怕惊到孩子,又免不了难舍难分,只能咬着嘴唇,尽力不哭出声来……
分别后,唐义贞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跟随毛泽覃突围到了福建,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在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下,唐义贞拖着身怀六甲的躯体,东躲西藏,最后在受伤红军范其标的家里生下了一个男孩,也就是她的第二胎——陆范家定。
然而,还没等儿子满月,因敌情紧急,唐义贞被迫含泪吻别襁褓中的小家定,回归队伍。唐义贞回到所属红军游击队后,由于众寡悬殊,很快被国民党军包围。
在突围的过程中,唐义贞不幸被捕,而后寻机逃脱,又被捕。敌人恼羞成怒,将她捆起来施以酷刑,皮鞭和棍棒像雨点般打在她瘦弱的身体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留下殷红的血迹。为了逼迫她招供,敌人两天两夜没给她一口饭、一碗水,但她始终不肯吐露一个字。气败急坏的敌人终于失去耐心,于是唐义贞牺牲在刑场上,当时的场面极其悲壮,据目击者陈六嬷后来描述:“刀子一下一下砍下去会痛呀,血水在天上飞哟,义贞姐一声也没有吭哟……唐姐姐可是个美人哩!”敌人始终不明白,这位年轻的女红军怎么会如此坚强,她当时才25岁!
由于陆老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跟妻子和子女暂时失去了联系。长征途中,他担任了红一方面军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
工作虽然繁忙,但他心里一直记挂了留在南方的妻子和儿女,从爬雪山过草地直至延安的宝塔山下,他曾无数次回忆那生离死别的场面,无数次地问自己:“义贞怎么样了,孩子怎么样了?……”
1937年,他打听到自己的女儿叶坪,由唐义贞原单位一位被称为“好妈妈”的同志带着,寄养在于都一户农家里。同年,他在奔赴抗战前线之前,专程去了一趟岳父家,告知这一消息,委托唐家去寻找。
唐义贞的大哥和五哥即刻动身去江西寻找,一处处地寻觅,一次次的失望。大哥唐义精还按照母亲的意思,仿照唐义贞小时候的样子,画了一幅扎两根小辫子小女孩的画像,把她当成想象中的叶坪,思念心切时,就对着画像悲切地呼唤:“孩子啊,你在哪里?”
更加不幸的是,寻找叶坪的两位舅舅,后来却在渡江时因为船翻而遇难,依靠唐家寻找叶坪的希望就此终止了。
1943年,唐义贞留守中央苏区时的战友贺怡,也就是毛泽覃的夫人,从江西来到延安。从她口中,陆定一惊闻唐义贞已经英勇就义的噩耗,顿时仿佛心碎了,此后连续半个多月,他都是彻夜无法入睡,思念着牺牲的爱妻和不知所踪的儿女,哭得眼泪都流干了。据陆老后来回忆:“从此以后,不论大喜大悲,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伴随失去妻子的沉痛悲伤,陆老更加坚定了找回儿女的决心:必须去找,哪怕踏破铁鞋!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在南京办了一个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陆老了解到后,便写信给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邓颖超,也就是女儿叶坪的“干姥姥”,委托她请李德全帮忙寻找自己的女儿。
可惜,此后没多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战时妇孺保育救济机关解散了,这一条寻亲路线也走不通了。
再说叶坪这一边。红军战士张德万按照唐义贞的委托,带着小叶坪来到江西于都,投靠了当地一户赖姓农家。开始时,张德万还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待叶坪非常好,天天形影不离,叶坪很亲热地管他叫“好妈妈”,当时村民们还很奇怪:这孩子怎么叫一个男人妈妈呢?主要是因为张德万在唐义贞还在世的时候,就成天带着叶坪玩耍,当时叶坪还很小,正在牙牙学语,只会简单的“爸爸”“妈妈”的口语,所以叫他“好妈妈”。
由于张德万不是本地人,迫于被还乡团清查外乡人的压力,他不得不含泪离开,回了老家吉安,临走把小叶坪托付给了赖家。由于不知道叶坪的名字到底是哪两个字,赖家人顺着谐音,读作了“野萍”。
3年后,抗战开始,当局停止了“剿共”,张德万特地又来到了于都看望“野萍”。这次他在赖家只待了3天。在这3天里,他和“野萍”又是朝夕相处,每顿饭都要亲自喂她,尽管小姑娘已经已经能够自己吃饭了。白天他总是领着“野萍”,还反复念叨:“当时,好妈妈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到老家,要不然就不会撇下你了!”
3天后,张德万又独自走了,还是没有带走“野萍”,或许是他意识到自己的虚弱的身体可能撑不了多久了。此后再也没有来过,因为他回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也带走了“野萍”身世之谜。
而随“野萍”刚来时带着的小孩衣物,后来也因为一场火灾而付之一炬。
所幸的是,赖家待“野萍”还算不错,视如己出。只不过家里穷,日子过得比较艰苦,“野萍”早早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成天干活,拔猪草、打柴,一天书也没读过。9岁时,“野萍”给人当学徒,学做瓦,她在艰苦生活中,力气慢慢变大,一次能提4个瓦,长大后成了能干的农妇。
19岁时,就与赖家儿子赖普恩圆了房,像每一个普通农妇那样,生儿育女,照顾家庭。她生孩子的时候,按照当地的风俗,娘家要带鸡蛋来看分娩的女儿的,可是没有人来看她,因为她没有妈妈……
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工作繁忙,虽然一直有去江西寻找儿女的念头,但迟迟难以成行,遂委托闽、赣两省帮忙。两省有关部门整理了唐义贞烈士有关资料,通过走访、贴布告等方式到处查找,找到过好几个疑似叶坪的人,但经过反复比对,确认都不是他女儿。
1956年的时候,陆老差点找到了真“叶坪”。当时赖普恩所在单位——铁山垅钨矿在审查职工档案时,发现赖普恩的履历表上没有填岳父母的信息,当时政审非常严格,填写信息不全是非常严肃的事。赖普恩被询问到时,就说了自己妻子的情况。
党委书记郭若珊是军队转业干部,对老苏区寄养孩子的事情非常敏感,做事也非常认真,派人了解情况后,整理了一份材料寄给了中宣部长陆定一。
不久,赣南区党委宣传部奉中宣部指示,派人调查核实。这种调查最看重原始物证,但是因为家里穷,“野萍”没有小时候的照片,唐义贞给她的衣物当年也被火灾烧没了,只好临时拍了张当时的照片。
调查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证据,“野萍”的照片寄到北京后,陆定一的小姨子,也就是唐义贞的八妹唐义慧看了之后,觉得不太像。这条线索就被搁了起来,结果这一搁就是31年。
直到前文所述,陆范家定于1987年,按照父亲的指示再次来到赖家核查。调查组人员在与“野萍”交谈过程中,提到了一个问题:你管张德万叫什么?“野萍”回答:叫“好妈妈”。
陆范家定听到这儿,顿时激动了起来:陆定一曾跟他说过,叶坪是交给了一个叫“好妈妈”的男同志!
调查组离开后,又来到张德万的家乡吉安,了解到张德万兄弟3人,都参加了红军,张德万是老大,没有留下后代;老二张德清牺牲在战场上;老三张德明有个儿子叫张永济,据他说,张德万生前曾告诉过家人,他在于都县寄养了一位战友的女儿。
不久江西省政府做出结论:“野萍”就是陆定一53年前失散的女儿叶坪!
1987年的11月30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对于陆老一家来说,又是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81岁的父亲与56岁的女儿终于团聚了,当年分离时,一个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是嗷嗷待哺的婴儿,而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见面之前,秘书交代过叶坪,陆老年龄大了,见了面不要哭。她答应了秘书,到时候只笑不哭。为此,她前一天晚上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整整哭了一夜!
可是,见面之后,看着陆定一慈祥而激动的面容,叶坪肚子里积累了53年的泪水,远远没有因为前一夜的哭泣而流完,此刻再度溢满眼眶,泪如泉涌,伴随而出的还有迟到了53年的一声呼唤:“爸爸!”
听到这深情的呼唤,陆老紧紧拉着叶坪的手,兴奋异常,说道:“孩子,我找了你53年……”他拒绝了做亲子鉴定的建议,因为虽然叶坪脸上已布满沧桑,他仍能一眼认定:她就是他的女儿!
后来,有记者问叶坪:你父亲当年“丢掉”你,你恨他吗?
叶坪说:“不恨,恨他干什么,那时候要长征,他也没有办法,不是故意丢掉我的。有时候我想,要是我爸爸是个叫化子,不是大领导,我也不会那么苦。可是为革命牺牲没有办法,我知道这个,我理解。”
是啊!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做了严格规定:路上谁也不准带孩子,不论职务多高。为了长征,为了革命,当年有多少红军乃至高级干部都跟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家人生离死别、天各一方。后来,有的找回来了,有的历经千辛万苦找回来了,而有的却一生一世还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