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的一天,一架銀色飛機穿梭于蒼茫雲海間,從北京正飛往福建。機艙内,坐着一位年逾古稀的白發老人,外表堅毅而平靜,心中的思緒,卻猶如機艙外翻湧的雲海,急迫地奔向千裡之外。
他,就是原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陸定一。早年曾任紅軍、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解放日報》總編輯,是中共老一輩革命家,新中國的元勳之一。他的文章《老山界》《金色的魚鈎》,都被列入國小國文課本,讀起來脍炙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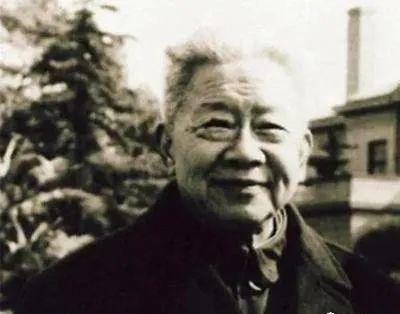
他的文章确實是好,後來還幫他找回了自己的女兒。不過,這裡暫時按下不表,先說他要去了卻一樁46年的心願……
福建閩西長汀縣奎田村的一戶農家裡,相依為命地住着一家三口:範其标夫婦以及他們的兒子範家定。多年來,讓範家定疑惑不解的是,每每逢年過節,父母都要在飯桌上多放一副碗筷,而那個位置,卻總是空席。
終于有一天,範家夫婦對兒子道出了原委:他不是他們的親生兒子,他的母親是一位女紅軍,并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生母遺物給他。經過艱難的輾轉、周折、等待,在知情人的幫助下,範家定終于了解到,他的父親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國家上司人。
随着飛機的降落,陸、範兩位老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範其标老人用顫抖的聲音說:“陸老,總算……,總算把他帶到您面前了,現在該讓他改回陸姓了。”
“不!在這樣艱難的歲月裡,是你們撫養了孩子,你們是他的再生父母,孩子就繼續留在你們身邊,孩子的姓也不必改了。”雙方謙讓之下,陸定一最後表示,将孩子的姓改為“陸範”,代表孩子是兩家的人。
失散多年重逢必然有着萬分的思念,思念兒子的同時,也思念着孩子的生母——唐義貞,她已犧牲多年;同時,也思念另一個至親骨肉。陸老告訴兒子:“你還有一個比你大3歲的姐姐,她至今還下落不明!”
“爸爸,既然我還有個姐姐,那還等什麼,我們快點找吧!”陸範家定得知還有親人在世,急切地說道。
“已經找了幾十年了,如果她還在的話,應該是50多歲了……”陸老感慨地說道,心裡一直在呼喚:“女兒啊,你到底在哪兒啊?”
或許他并沒有意識到,在不遠處的鄰省江西,有一女子常常對着星空,傷心哭泣:“我命苦喲,我天生就沒有父母,沒有啊……”
1987年9月的一天,南方冶金學院社科系的一位名叫賴章盛的教師照例來到系資料室看書。他在一本《風展紅旗》的書中,看到了陸定一的文章《關于唐義貞烈士的回憶》,文章寫于1981年底。從這篇文章中,賴章盛了解到,唐義貞是陸老的亡妻,17歲參加革命,紅軍時期犧牲于福建。
文章中還介紹了唐義貞烈士所生的兩個孩子。老二是個兒子,已經找到;老大則是個女兒,失散了47年,至今杳無音訊……
賴章盛越讀越是激動不已,因為他知道自己的母親就屬于紅軍失散子女,至今尚未找到親生父母。等讀完全文,他再也按奈不住心情,立刻提筆給陸老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您女兒仍無下落,這使我聯想到我鄉下母親的身世。我的母親,也是紅軍長征前留下的子女,現在仍不知親生父母是誰。但從名字、年齡、寄養地點和時間看,我母親與您失散的女兒葉坪,很可能是同一個人……”
賴章盛在信中用四個資料對自己母親是陸老女兒的可能性進行了分析。
一是名字。首先引起賴章盛注意的也是名字,陸老文章中提到的失散女兒的名字叫“葉坪”,而賴的母親張來娣的小名叫“野萍”,這個小名隻是當年來托孤的張德萬口述,到底是哪兩個字,早已無人知曉。那麼,“野萍”不排除就是“葉坪”的可能。
二是年齡。陸老文章中說自己女兒是1931年生的,按時間推算此時應該56歲了。這一年齡正好與賴母同歲。
三是寄養時間。陸老文章所述寄養時間是長征時,中央紅軍長征是從1934年10月開始的;而賴章盛記得祖母在世的時候曾經講過,母親是在“挖番薯的時候”被人帶來的,當地農村挖番薯的時間是11月份左右,考慮到母親可能是紅軍出發後輾轉來到賴家,有所延遲,是以月份基本吻合。從年份上講,賴章盛知道自己母親是3歲時被寄養過來的,她又是31年出生的,送過來時正好是1934年,是以,年份也對上了。
四是寄養地點。陸老文章中寫的是“寄養在雩都”,而賴章盛家鄉于都以前就是寫為“雩都”,地點也相符合。
從以上四點判斷,她們還真可能是同一個人!
那麼,賴章盛的母親究竟是不是陸老的女兒呢?陸老收到賴章盛的來信後,心中當即一緊:這不是跟1956年那次調查是同一家嗎?難道那次調查有所疏忽?他立刻請來亡妻唐義貞的八妹唐義慧商議。
“再也不能錯過了!那年,您讓我驗證那張照片,我說不太像。如果她真的是葉坪,就是我一句話誤了31年呀!”唐義慧老人臉上淌着淚水說道。
唐義慧老人已經74歲高齡了,她為找不到姐姐的女兒而難過了大半輩子。她永遠不會忘記,兩個哥哥為尋找她在江中遇難!母親面對她的畫像,戀戀不舍地離開人世!
陸老聽後,當即委派身在福建的兒子陸範家定去江西調查核實。江西省委、省政府對此事也高度重視,派出聯合調查組,與陸範家定一起來到賴章盛的家鄉。經過嚴格而缜密的調查,終于把當年的情況和多年來幾次陰差陽錯的轶事給理清楚了……
唐義貞出生在一個進步的知識分子家庭,早在五四運動時期,大哥唐義精就與董必武、恽代英交往甚密,五哥唐一禾受聞一多愛國思想影響,是一名堅定地反帝反封建分子。受兄長的影響,她很快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唐義貞受黨組織委派,前往蘇聯學習,那是她夢想的地方,但此時的她畢竟才18歲,而且當時母親正患有病毒性痢疾,多日昏迷不醒。她真不忍心離開,但為了革命,她不得不忍痛離别。臨行前,她跪在母親床前,拜了三拜,流着熱淚而去。當時她并沒有想到,這一走,竟成了永别!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唐義貞在反對王明一夥的鬥争過程中,認識了陸定一,他們從相識到相知,建立了感情,不久就結為革命伴侶。
後來,她和陸定一先後回國,并到了中央蘇區工作,在這裡,他們又重逢了,并于1931年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由于出生在江西瑞金的葉坪,是以取名“葉坪”。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了舉世矚目的兩萬五千裡長征。本來,唐義貞可以随主力紅軍走的,但是她再次懷了孕,行動不便,按照當時的規定,她必須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争。于是她不得不再次與丈夫陸定一分别;又因為行動不便,也不得不與女兒“葉坪”分别。
因為長征,許許多多中共黨的上司人,都這樣将自己的孩子秘密留下了。毛澤東的兒子小毛就是這樣留下的,劉伯堅的兒子劉豹,以及林伯渠的兒子,鄧子恢的兒子也是這樣留下的……
紅軍主力長征後,唐義貞把3歲的女兒“葉坪”托付給一個叫張德萬的紅軍同志,讓他把孩子帶到瑞金之外的農村找個人家寄養。張德萬是江西吉安人,因為生病而不能參加長征。後來張德萬把孩子交給于都一戶農民家庭。
骨肉分離的時刻,唐義貞心如刀絞,望着張德萬背着孩子遠去的身影,不禁淚如泉湧,卻怕驚到孩子,又免不了難舍難分,隻能咬着嘴唇,盡力不哭出聲來……
分别後,唐義貞根據組織上的安排,跟随毛澤覃突圍到了福建,繼續開展武裝鬥争。在國民黨軍的瘋狂圍剿下,唐義貞拖着身懷六甲的軀體,東躲西藏,最後在受傷紅軍範其标的家裡生下了一個男孩,也就是她的第二胎——陸範家定。
然而,還沒等兒子滿月,因敵情緊急,唐義貞被迫含淚吻别襁褓中的小家定,回歸隊伍。唐義貞回到所屬紅軍遊擊隊後,由于衆寡懸殊,很快被國民黨軍包圍。
在突圍的過程中,唐義貞不幸被捕,而後尋機逃脫,又被捕。敵人惱羞成怒,将她捆起來施以酷刑,皮鞭和棍棒像雨點般打在她瘦弱的身體上,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留下殷紅的血迹。為了逼迫她招供,敵人兩天兩夜沒給她一口飯、一碗水,但她始終不肯吐露一個字。氣敗急壞的敵人終于失去耐心,于是唐義貞犧牲在刑場上,當時的場面極其悲壯,據目擊者陳六嬷後來描述:“刀子一下一下砍下去會痛呀,血水在天上飛喲,義貞姐一聲也沒有吭喲……唐姐姐可是個美人哩!”敵人始終不明白,這位年輕的女紅軍怎麼會如此堅強,她當時才25歲!
由于陸老随中央紅軍參加了長征,跟妻子和子女暫時失去了聯系。長征途中,他擔任了紅一方面軍宣傳部長,抗日戰争爆發後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八路軍前方總部野戰政治部副主任。
工作雖然繁忙,但他心裡一直記挂了留在南方的妻子和兒女,從爬雪山過草地直至延安的寶塔山下,他曾無數次回憶那生離死别的場面,無數次地問自己:“義貞怎麼樣了,孩子怎麼樣了?……”
1937年,他打聽到自己的女兒葉坪,由唐義貞原機關一位被稱為“好媽媽”的同志帶着,寄養在于都一戶農家裡。同年,他在奔赴抗戰前線之前,專程去了一趟嶽父家,告知這一消息,委托唐家去尋找。
唐義貞的大哥和五哥即刻動身去江西尋找,一處處地尋覓,一次次的失望。大哥唐義精還按照母親的意思,仿照唐義貞小時候的樣子,畫了一幅紮兩根小辮子小女孩的畫像,把她當成想象中的葉坪,思念心切時,就對着畫像悲切地呼喚:“孩子啊,你在哪裡?”
更加不幸的是,尋找葉坪的兩位舅舅,後來卻在渡江時因為船翻而遇難,依靠唐家尋找葉坪的希望就此終止了。
1943年,唐義貞留守中央蘇區時的戰友賀怡,也就是毛澤覃的夫人,從江西來到延安。從她口中,陸定一驚聞唐義貞已經英勇就義的噩耗,頓時仿佛心碎了,此後連續半個多月,他都是徹夜無法入睡,思念着犧牲的愛妻和不知所蹤的兒女,哭得眼淚都流幹了。據陸老後來回憶:“從此以後,不論大喜大悲,我都流不出眼淚來了。”
伴随失去妻子的沉痛悲傷,陸老更加堅定了找回兒女的決心:必須去找,哪怕踏破鐵鞋!
抗戰勝利後,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在南京辦了一個戰時婦孺保育救濟機關。陸老了解到後,便寫信給中央駐南京辦事處的鄧穎超,也就是女兒葉坪的“幹外婆”,委托她請李德全幫忙尋找自己的女兒。
可惜,此後沒多久,蔣介石發動了内戰,戰時婦孺保育救濟機關解散了,這一條尋親路線也走不通了。
再說葉坪這一邊。紅軍戰士張德萬按照唐義貞的委托,帶着小葉坪來到江西于都,投靠了當地一戶賴姓農家。開始時,張德萬還在村裡住了一段時間,他待葉坪非常好,天天形影不離,葉坪很親熱地管他叫“好媽媽”,當時村民們還很奇怪:這孩子怎麼叫一個男人媽媽呢?主要是因為張德萬在唐義貞還在世的時候,就成天帶着葉坪玩耍,當時葉坪還很小,正在牙牙學語,隻會簡單的“爸爸”“媽媽”的口語,是以叫他“好媽媽”。
由于張德萬不是本地人,迫于被還鄉團清查外鄉人的壓力,他不得不含淚離開,回了老家吉安,臨走把小葉坪托付給了賴家。由于不知道葉坪的名字到底是哪兩個字,賴家人順着諧音,讀作了“野萍”。
3年後,抗戰開始,當局停止了“剿共”,張德萬特地又來到了于都看望“野萍”。這次他在賴家隻待了3天。在這3天裡,他和“野萍”又是朝夕相處,每頓飯都要親自喂她,盡管小姑娘已經已經能夠自己吃飯了。白天他總是領着“野萍”,還反複念叨:“當時,好媽媽不知道還能不能活着回到老家,要不然就不會撇下你了!”
3天後,張德萬又獨自走了,還是沒有帶走“野萍”,或許是他意識到自己的虛弱的身體可能撐不了多久了。此後再也沒有來過,因為他回去不久就離開了人世,也帶走了“野萍”身世之謎。
而随“野萍”剛來時帶着的小孩衣物,後來也因為一場火災而付之一炬。
所幸的是,賴家待“野萍”還算不錯,視如己出。隻不過家裡窮,日子過得比較艱苦,“野萍”早早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擔,成天幹活,拔豬草、打柴,一天書也沒讀過。9歲時,“野萍”給人當學徒,學做瓦,她在艱苦生活中,力氣慢慢變大,一次能提4個瓦,長大後成了能幹的農婦。
19歲時,就與賴家兒子賴普恩圓了房,像每一個普通農婦那樣,生兒育女,照顧家庭。她生孩子的時候,按照當地的風俗,娘家要帶雞蛋來看分娩的女兒的,可是沒有人來看她,因為她沒有媽媽……
新中國成立後,陸定一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工作繁忙,雖然一直有去江西尋找兒女的念頭,但遲遲難以成行,遂委托閩、贛兩省幫忙。兩省有關部門整理了唐義貞烈士有關資料,通過走訪、貼布告等方式到處查找,找到過好幾個疑似葉坪的人,但經過反複比對,确認都不是他女兒。
1956年的時候,陸老差點找到了真“葉坪”。當時賴普恩所在機關——鐵山垅鎢礦在審查職工檔案時,發現賴普恩的履曆表上沒有填嶽父母的資訊,當時政審非常嚴格,填寫資訊不全是非常嚴肅的事。賴普恩被詢問到時,就說了自己妻子的情況。
黨委書記郭若珊是軍隊轉業幹部,對老蘇區寄養孩子的事情非常敏感,做事也非常認真,派人了解情況後,整理了一份材料寄給了中宣部長陸定一。
不久,贛南區黨委宣傳部奉中宣部訓示,派人調查核實。這種調查最看重原始物證,但是因為家裡窮,“野萍”沒有小時候的照片,唐義貞給她的衣物當年也被火災燒沒了,隻好臨時拍了張當時的照片。
調查沒有獲得實質性的證據,“野萍”的照片寄到北京後,陸定一的小姨子,也就是唐義貞的八妹唐義慧看了之後,覺得不太像。這條線索就被擱了起來,結果這一擱就是31年。
直到前文所述,陸範家定于1987年,按照父親的訓示再次來到賴家核查。調查組人員在與“野萍”交談過程中,提到了一個問題:你管張德萬叫什麼?“野萍”回答:叫“好媽媽”。
陸範家定聽到這兒,頓時激動了起來:陸定一曾跟他說過,葉坪是交給了一個叫“好媽媽”的男同志!
調查組離開後,又來到張德萬的家鄉吉安,了解到張德萬兄弟3人,都參加了紅軍,張德萬是老大,沒有留下後代;老二張德清犧牲在戰場上;老三張德明有個兒子叫張永濟,據他說,張德萬生前曾告訴過家人,他在于都縣寄養了一位戰友的女兒。
不久江西省政府做出結論:“野萍”就是陸定一53年前失散的女兒葉坪!
1987年的11月30日,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日子,但對于陸老一家來說,又是一個極不平常的日子。81歲的父親與56歲的女兒終于團聚了,當年分離時,一個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是嗷嗷待哺的嬰兒,而如今,都已是白發蒼蒼的老人了。
見面之前,秘書交代過葉坪,陸老年齡大了,見了面不要哭。她答應了秘書,到時候隻笑不哭。為此,她前一天晚上在招待所的房間裡整整哭了一夜!
可是,見面之後,看着陸定一慈祥而激動的面容,葉坪肚子裡積累了53年的淚水,遠遠沒有因為前一夜的哭泣而流完,此刻再度溢滿眼眶,淚如泉湧,伴随而出的還有遲到了53年的一聲呼喚:“爸爸!”
聽到這深情的呼喚,陸老緊緊拉着葉坪的手,興奮異常,說道:“孩子,我找了你53年……”他拒絕了做親子鑒定的建議,因為雖然葉坪臉上已布滿滄桑,他仍能一眼認定:她就是他的女兒!
後來,有記者問葉坪:你父親當年“丢掉”你,你恨他嗎?
葉坪說:“不恨,恨他幹什麼,那時候要長征,他也沒有辦法,不是故意丢掉我的。有時候我想,要是我爸爸是個叫化子,不是大上司,我也不會那麼苦。可是為革命犧牲沒有辦法,我知道這個,我了解。”
是啊!長征出發前,中央紅軍做了嚴格規定:路上誰也不準帶孩子,不論職務多高。為了長征,為了革命,當年有多少紅軍乃至進階幹部都跟自己的兒女、自己的家人生離死别、天各一方。後來,有的找回來了,有的曆經千辛萬苦找回來了,而有的卻一生一世還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