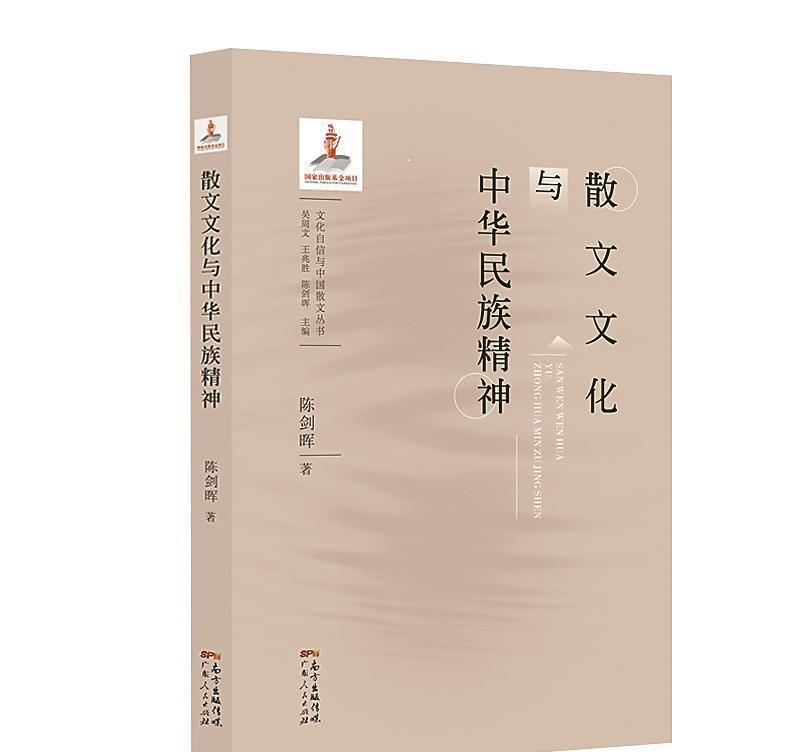
□华紫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散文日益兴盛,研究文化散文的文章也不时见于各种报刊,但研究文化散文的专著却极为鲜见。陈剑晖教授最近出版的《散文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填补了这一空白,首提“散文文化”这一概念,从文化学批评切入,对“文化散文”与百年散文文体的发展作了全面深入的探究。
作者之所以独立提出“散文文化”这一概念,旨在彰显散文的地位及其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从文学史的演进发展来看,“文”对中国文化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大,它比诗歌更全面、更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化。作者认为,“散文文化”又不能等同于“文化研究”。“散文文化”的文学阐释主要应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诗的体验,即从生活着的个体出发去感受现实和历史,去把握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二是着眼于文化与审美的交融。亦即诗、思、史三者的深度融合。鉴于当代散文创作路子越走越窄,“越来越技巧化、精致化”,他认为有必要回归到产生诗性的原初,回归到我国“文”的伟大传统中。这无疑是切中肯綮的药方。
“文化散文”与“散文文化”是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是近三十年兴起的一股散文创作热潮,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散文的创作观念。陈剑晖认为,“文化散文”至少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创作主体定位应该是文化人。他们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具备历史文化的解读能力,是传统文化、文化明的传播者。第二,创作内蕴具有文化诗性的品格。第三,创作思维是以个人解读的方式,对历史文化进行理性的思辨,同时融入个体生命的体验。第四,创作艺术是对话式的议论,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充满人文情怀的抒情。”
这就把“文化散文”的概念、特征与内涵都说清楚了。他还概括提炼出“文化散文”的意义,认为它突破了传统散文“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创作模式,融文学、美学、史学及其他学科于散文创作;结构上,运用多维度、多层面、辐射式的构思方式,大大拓展了散文创作的空间,从文化的视角展示历史事件、文化人格的底蕴,比以往那种“写景抒情”、“托物言志”、“轻灵精致”的传统散文自然更丰富、更深刻、更有魅力。
该书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中国散文文体的嬗变,对古代、近代、五四时期及百年散文文体的发展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文体的变革做了深入的梳理与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作者指出,先秦时期的散文文体,以论说为主,两汉以历史散文为主要文体形态;唐代的古文运动,瓦解了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形成了叙事、议论与抒情三位一体的古典散文格局;明代以后,以小品笔记为主要散文形态。古代散文文体的自觉,主要体现在“散骈并用”“诗文互渗”。作者对近代梁启超创造的“新文体”散文的过渡性的转型意义,对五四时期,现代散文文体的实现的自觉与成熟,对周作人“叙散文事”、“抒情散文”、“议论散文”的新思路,对朱自清“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文学性散文与非文学性散文分开的观点,对五四时期至30年代散文文体的具体模式即报章体(时评)、情志体(美文)、闲聊体(小品)……都分析得精细、精辟、严谨,以此说明散文文体的变化与重大进展。作者还将现代散文归纳出“抒情独语体式”、“闲话聊天体式”、“幽默谐趣体式”等散文文体体式,以散文体式的建构与语体风格的形成,说明散文文体的成熟。至1936年后,报告文学、通讯特写崛起,50年代末、60年代初“形散神不散”与“诗化”散文理论的提出,再到70、80年代报告文学、特写从散文家族中剥离,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散文文体的多元审美性潮流……作者条分缕析,均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作者从“辨体”与“破体”入手,认为文体作为一种长期形成且相对稳定的共同审美形态,它有其特殊的构成因素和独特的表现手法,创作者在创作时一般应尊重各种文体的艺术规律,但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任何文体也不可能凝固和绝对化。它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作者认为,散文近些年来被冷落、被边缘化的原因,是由于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文学理论。有感于此,他努力探索现代文体,构筑属于散文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这本《散文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这方面探索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