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宋明帝刘彧去世,后废帝刘昱刚继位,年龄尚小,朝廷大权基本都在袁粲、褚渊、刘秉、萧道成等大臣手中。萧道成在四人中权力最小,地位最低,不过在一次藩王叛乱中,萧道成发现了机会。
宋明帝刘彧在位时,为了防止皇位被人夺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清洗活动,把几乎所有的皇室子弟屠戮一空。当然这其中还有漏网之鱼,这位就是桂阳王刘休范,因为刘休范没什么能力,脑子也比较愚钝,刘彧认为刘休范不可能威胁到他。
事实则恰好相反,脑子笨不一定做不了大事,刘彧死后,袁粲、褚渊、刘秉等人成了顾命大臣,却没有刘休范什么事。恼羞成怒的刘休范决定起兵反叛,想干掉刘昱取而代之,在那乱世的南北朝时期,这种事很常见。
尤其在南朝刘宋,皇室相残就好像家常便饭,加上皇帝大多不太靠谱,战争时有发生。很快刘休范一呼百应,招募了两万多士兵,五百多匹马。看起来兵不算多,可是当时已经不是刘宋的全盛时期,建康(今南京)内外防卫空虚,对于常年搞内讧的国家,可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史料记载''
元徽二年五月,举兵于寻阳,收略官民,数日得士众二万人,骑五百匹。
''
皇帝刘昱得知后马上召开战前会议,当皇帝问大臣们如何应对时,下面一片寂静。有些人对朝廷失去了信心,有些则只是混吃等死,面对如此局面江山随时易主,谁也不想做那个出头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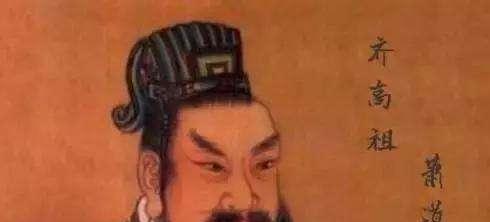
萧道成看无人答言,作为军方主要领导,他得发言了,萧道成说:
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至于覆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念远,若偏师失律,则大沮众心。宜顿新亭、白下,坚守宫掖、东府、石头以待。贼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征北可以见甲守白下;中堂旧是置兵地,领军宜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诸贵安坐殿中,右军诸人不须竞出。我自前驱,破贼必矣。
意思是我们要吸取以往的教训,防守不能求远,应该在新亭、白下、宫掖、东府、石头等地防守。叛军远路而来,且是孤军,给养供需肯定不足,经不起长时间的战事,自然会土崩瓦解,我自愿到前线请战,必定破敌。
萧道成看似是冤大头,但正是这场战役使他获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所谓富贵险中求就是如此。萧道成驻守新亭(建康南面),防御工事还没有完成,叛军就到了,为了安抚军心,萧道成明知军情紧急,仍在帐内睡觉。
战争打响了,两军厮杀在一处,战场上喊杀震天,叛军势头很猛,宋军有低挡不住,情势危机。萧道成却依旧镇定自若,从容指挥部队迎敌,眼看快抵挡不住了,萧道成计上心头。
刘休范有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头脑愚笨,萧道成抓住这一点,派出黄回、张敬儿两位大将,去叛军营中诈降。这种伎俩一般来说很容易识破,偏偏刘休范就相信了,不仅如此,刘休范还派自己的儿子做人质。
也许黄回、张敬儿演技太出彩,成了刘休范的亲信,于是在一次酒宴上,张敬儿趁虚而入砍掉了刘休范的人头。刘休范虽然死了,但叛军还不知情,攻势依旧很猛,萧道成不得已亲自冲锋在前线,稳定军心。
当时情况紧急,皇城内外全是叛军,刘休范虽然死了,而叛军中的很多高层将领严密封锁了消息,所以效用也有限。只有萧道成挺身而出,率领军队顽强抵抗,士兵看到主帅都和敌人在前线肉搏,随即奋勇杀敌,在危机边缘挽回了败事。
史料记载''休范即死,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千数,太祖随得辄烧之,乃列兵登城北,谓曰:「
刘休范父子先昨皆已即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善见观。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惧也。
」''
另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以为朝廷将失陷,刘休范将取而代之,所以很多人找刘休范投诚,随后这些信件被萧道成截获。在那个危机关头,萧道成并没有追究这些人的责任,而是一把火烧掉了信件。正是萧道成的冷静思考、准确判断让建康城躲过一劫。
参考资料:《南齐书·卷一本纪第一》
历史纪闻:深浅度挖掘历史故事,民间野史,古史杂谈,述古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