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深深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沼不能自拔。当我偶然读到《荷马史诗》中西西弗斯的故事时,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这种重复又无望的推石头生活像极了抽象意义上的现代人,正符合我对现代人的看法。我不可避免接触到了加缪的哲学散文《西西弗斯神话》,我发现我之前心中的困惑早有先辈做了解答。在陆续读完加缪的几部荒诞作品之后,我不禁对加缪产生了好奇,他早年曾作为法国共产党人,崇尚马列唯物,但后来他与萨特决裂,不再从事共产事业。这种转变使我感到极为惊讶与不解,我不得已把目光转向马列的经典论述中去,好在我得到了一些答案,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加缪本人人生态度的前后变化。
首先要从历史唯物角度看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和国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哲学观点也不过是人类生活态度的一种高度抽象化总结,而一切的精神生活是以物质为基础而存在,它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在原始时代,人类以氏族为生活单位,以狩猎和采摘等方式进行最原始的生产生活。这时的生产力极为低下,所有的产出只能勉强维持族群的生存,根本没有剩余产品用来交换,因此也不存在分工,更不会存在政府形式的权利机构,因为没有多余的产品可以供养这些机构。氏族制度是一个利益界限比较模糊、社会结构极为简单、基本靠习俗和传统维系的制度。
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可能是狩猎技术的提高、初步农耕技术总结的出现,氏族中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这为交换活动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一些人只需专注于一件事也可获得生存资料,分工也随之出现,逐渐出现了专职商人、手工业者等农民以外的职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交换活动和货币、商品的出现,私有制的萌芽在此诞生。在这一过程中,氏族首长利用自身特殊的地位侵吞共有财产,每个人的利益诉求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社会开始分裂为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同,导致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阶级对抗越来越剧烈,矛盾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为了把对抗的复杂利益要求简明化、把混乱冲突的局面秩序化,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诞生出来,恩格斯有个经典说法:“公共的政治机构”的基本功能就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让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也就是说,国家就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不受更高权力的限制,但却可以限制其他集团权力的最高决定权。
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工进一步细致化,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了奴隶制和佃农的大量使用以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发展,于是,血缘障碍被打破,民族形成了,军队、常设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变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氏族机制瓦解,私有制下奴役人民的公共权力不断生长壮大。
紧接着,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到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它所造成的第三次大分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深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乡村开始逐渐凋敝,城市最终成为人类生活的文明表征,而作为这种文明的必要补充,则是发展了大量独立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以后,经济上居于优越地位的阶级就必须以公共权力的名义,运用军队、官僚、警察以及一系列的附属物,如法庭、监狱和其他强制机关,强迫那些在感情上、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变得与现存秩序格格不入的人们表示服从,至少是表面上的服从”。这也直接导致加缪产生“一个最真实的人注定与这个世界的人格格不入”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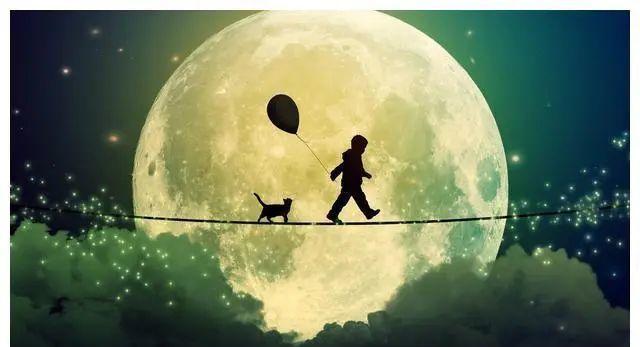
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生活深刻的归纳演绎,一个理智的人不得不相信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事实,但也这种现实太过冷酷无情。它告诉你,人类不过是客观环境的产物,客观环境自有其运行规律,它不会理会个人热情的呼喊,历史自会被生产力推动发展,与单个人并没有太大关系。这也正是加缪所论述的“荒诞”的根本来源——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个人意识失去了灿烂的颜色,个人也逐渐失去了对环境的掌控感,陌生感充斥着现代人类,尼采的超人哲学在历史的力量下变成了不可能的幻想。人类面对着的不过是不断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和交换的冰冷冷的现实——个人全部的人生意义,就是他本人所有的实践活动,这就是人生的全部,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带来的最朴素冰冷的现实,所有一切美好的祈求和愿望在此都失效了,人心开始变得干涸。
尼采说:“上帝已死”,因此人类需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马克思又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个人任何本能的追求如果不顺应历史潮流,就往往变为疯子的臆想。而这在加缪看来,历史重新占据了上帝的位置,成为了人类新的主宰,这种将历史上升为整个人类追寻的意义,在理智上看是正确的,但在情感上却难以接受。为了应对这种没有任何感情、难以忍受的环境力量,他唯有示以冷漠去反抗:“他说我实际上没有灵魂,没有丝毫热情的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据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则,所有这些都与我格格不入,毫无关系”。
而我自己呢?我无法接受把一个此生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认清现实,接受现实,然后拥抱现实,像《鼠疫》中奥兰城的里厄医生一样,一生忠于自己的职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