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春三月,四川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新發現,引起了全國轟動。沉寂良久的媒體疾呼:神秘的三星堆遺址,引發了一場大衆“考古旅遊熱”。面對席卷而來的“考古旅遊熱”,博物館、文旅部門又該如何應對呢?
按說,考古新發現首先是考古人心情激動,因為通過他們的辛勤努力,發現了曆史文明演進的新證據,有的可能會改寫已有的曆史,與此同時,一些考古專家和研究者也會興奮,因為新文物将會提供更多的研究空間。至于旅遊者,尤其是大衆旅遊者,絕大多數是看熱鬧的,急于“打卡”多是好奇心驅使,欲先睹為快。如此激起的“熱”會讓有關博物館的訪客摩肩接踵,但未必能夠成為一種有效的旅遊營銷,其效果也未必是東道主和客人真正希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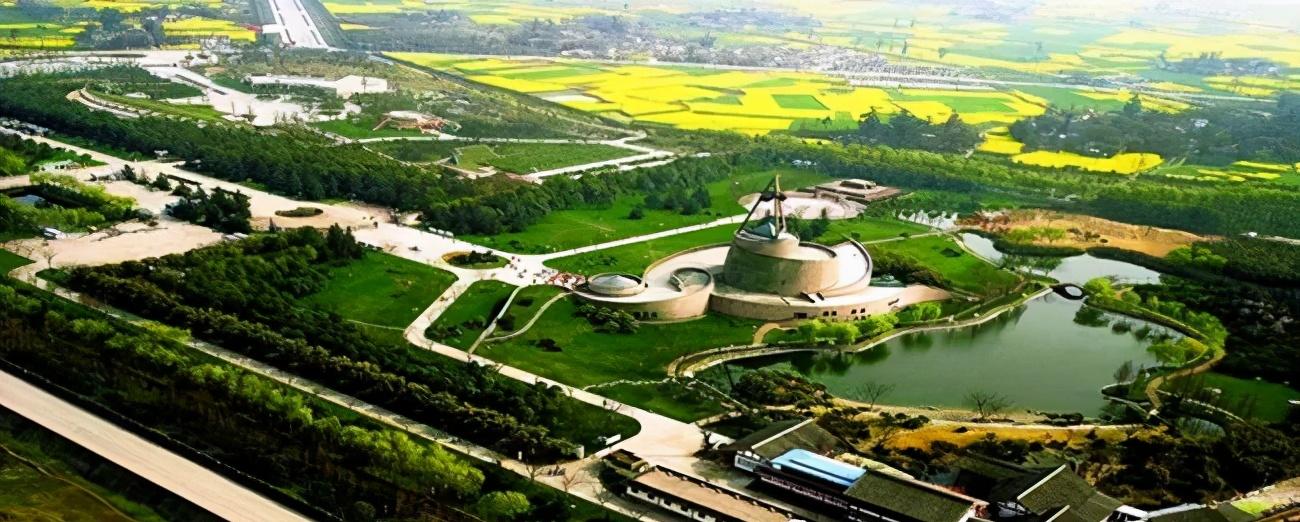
文物和考古是一個專業的領域,觀賞文物和觀察考古,雖然有不少人會覺得有趣,但沒有一定的專業知識,真正到了現場,被人群裹挾下看上幾眼,搶拍到幾張照片發到朋友圈之後,很快可能就忘卻了。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文物遺産的存量與考古新發現的頻率比世界很多國家都多。然而,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一般公衆對本國文物遺産的了解和參與考古活動的興趣都不算高,一方面是我們國家的寶貝太多了;另外一方面,我們對文物和考古的知識普及和基礎教育乏力,這既反映在國民的文化素質上,也展現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機構功能的定位上。抛開文物與考古活動的專業性之外,面對日益興起的大衆旅遊來說,有三個問題需要認真考慮,我們也不妨從國外的好的案例中學習一二。
其一是,文物和考古活動需要良好的解說。我曾三次參觀過倫敦的大英博物館,然而在那裡參觀時,我的第一個印象是那裡的孩子特别多,國小生、中學生都有,有的是老師帶領,有的是家長陪伴,孩子們不是在偌大的博物館裡亂跑亂轉,而是集中在一個館或展室聽講,他們用畫筆把看到的畫出來,或用筆把懂得的東西記下來,并不時圍着老師問問題;另外一個印象是,那裡很多觀衆是抱着書來參觀的,有的拿着導遊指南,有的拿着曆史或文物專著……顯然參觀者是帶着問題而來,他們會在一個館裡待很久,看上去有些人并非是初訪。還有一個和我們博物館不同之處,幾乎見不到漂亮的導遊姑娘舉着話筒帶着遊客參觀的場景,但現場有很多帶着講解員徽标的志願者,他們中有不少人是教師、教授或博士,而博物館中有大小不等的講座室,室外張貼着演講人和演講主題,遊客可以預約聽專題講座及參與讨論。
其二是,曆史遺址和博物館應當為遊客創造體驗的機會。現代人對曆史一般都是陌生的,一般性的參觀可能對特定文物會有些印象,然而,有親身體驗的過程則會使印象更深刻。我在2002年參觀埃及金字塔時,發現一個可以鑽進金字塔内的參觀活動。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在狹窄昏暗的石洞内,踏着濕漉漉的台階向上攀登,有的地方得用手緊握欄杆,有的地方則是手腳并用地爬行……在喘息的間隙,我會閉着眼睛冥想幾千年之前開鑿這種通道的艱辛,靠什麼樣的理念、智慧和毅力才能夠完成這樣的工程。其實,好不容易到了金字塔頂尖處,隻是一個小石頭房間,除了一個石台之外,什麼也沒有,真正的文物早已放到博物館裡展示。但是,我對當時鑽洞的選擇一點也不感到失落或後悔,那次獨特的經曆讓我對博物館中文物有了不同的感受。
其三是,對待大衆旅遊者,文物部門還要在擴大社會認知,形成廣泛吸引力上多下功夫。對于文物或博物館來說,大衆旅遊者渴望的是一部“百科全書”,而不是“專業詞典”。2015年我在溫哥華市中心參觀了“溫哥華比爾·瑞德西北海岸藝術館”,那裡以雕刻藝術作品介紹了加拿大土著居民海達人(haida)的曆史和風情。沒有想到的是,在加拿大西部,精湛的海達藝術不僅在博物館中可以看到,在許多公共場所,如機場、書店、大型購物中心都有展示,而且海達藝術還變成了各種的日用品,從名貴的首飾、箱包和服飾,到日用的茶杯、鑰匙鍊和冰箱貼等,讓更多人可以了解和欣賞這一特殊文化,并傳播到世界各地。從旅遊的角度,這才是真正把曆史文物、藝術和文化的優勢發揮到了極緻,海達人和海達藝術也逐漸被列入很多導遊指南,成為到加拿大訪客不容錯過的旅程。
從這些例證看,公共文化設施的文物博物館發展旅遊,更應從長計議,通過各種途徑宣傳其内容和知識,讓有興趣的人有準備地到博物館裡去品文物,增長知識。其實文化和旅遊的融合并不像一些學術論文講得那麼深澳與複雜,功夫放到大衆的實際需求上,一定能夠産生良好的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