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1年中國誕生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電影新聞紀錄片《武漢戰争》,到今天各類型各題材的紀錄片在各平台上充分湧流,中國電視紀錄片的曆史至今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發展曆程。紀錄片與曆史上的報紙、電影一樣,它的創作必定會受到當時所處時代政治、體制、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反過來對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社會發展有一定的積極和消極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紀錄片發展也進入到一個新的曆史發展時期。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蘇六将新中國成立後的紀錄片史,劃分為四個階段:政治化紀錄片時期(1958-1977年)、人文化紀錄片時期(1978-1992年)、平民化紀錄片時期(1993-1998年)、社會化紀錄片時期(1999-2004年)。
《望長城》作為人文化紀錄片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掀起了一場“新紀錄運動”,徹底擺脫了政治化紀錄片時期的創作模式。《望長城》的誕生絕非偶然,是當時代各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今天,我們就從其誕生的前一個時代——政治化紀錄片時期說起,解讀這部裡程碑式的紀錄片如何被時代所孕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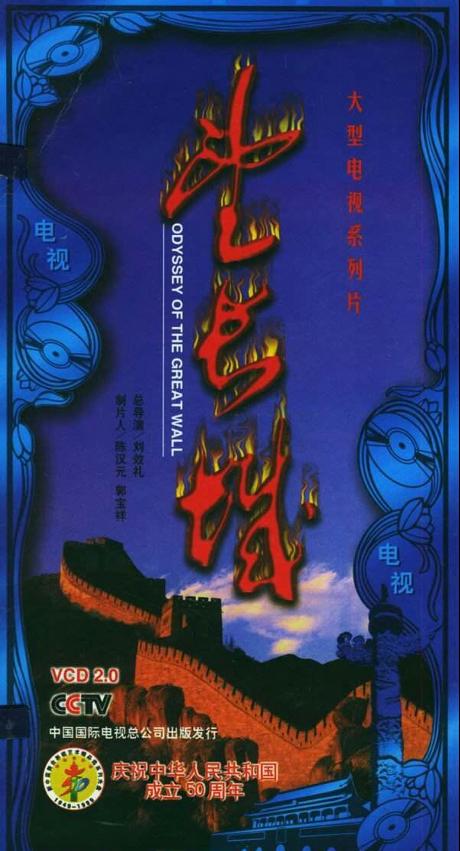
建國後的中國電視紀錄片
1958年,我國第一台電視機“華夏第一屏”在大躍進運動中誕生。同年,中國的第一座電視台——北京電視台,也由新華社宣布成立。正值新中國曆史上有名的“三年困難”時期,也是國家财政異常緊張的困難時期,電視台在當時建立,實際上是一種國家行為,是當時複雜的國際關系和政治工作的一部分。這樣的誕生環境,就為這一時期的中國電視紀錄片制作奠定了基調:電視節目的播出要起到反映國家政治的作用。
中國第一台電視機“華夏第一屏”
中國的第一座電視台——北京電視台
在後來的30年裡,中國接連經曆了中蘇關系惡化、“大躍進”、“三面紅旗”、 “反右傾”、“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政治環境動蕩起伏不停,紀錄片的制作主體基本保持着軍事化管理模式——電視新聞紀錄片在播出前,必須通過中央廣播事業局、電視台和電視新聞部三級上司的共同預審,進而保障紀錄片播出的安全。
這一時期的紀錄片創作理念,主要受到格裡爾遜的“形象化的政論”的影響。創作模式上,主題先行,政府利用紀錄片進行政治宣傳與大衆教育,通過紀錄片讓人民知道建國計劃的内容以及得到人民的協助。是以,無論是在選題、手法、觀念,還是在風格上,這時期的紀錄片都散發着濃厚的政治意味:
在選題上,以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國家上司人的外事活動為主;在形式上,聲畫分離,主持人慷慨激昂的播報,加上黨報社論般的解說詞,無不洋溢着濃重的理想主義氛圍;在觀念上,集體主義和國家利益的觀念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個人處于一個無我、忘我的狀态。在政治化因素較強的題材中,個人主體意識尤為缺失。
《收租院》是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電視紀錄片,由陳漢元撰寫解說詞,朱宏、王元洪擔任攝影。這部紀錄片實地拍攝了四川大邑縣的真實人物、史料和收租院泥塑,再現了中國農村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深刻揭露了惡霸地主劉文彩的血腥罪惡,喚醒人們勿忘曆史,勿忘苦難。電視紀錄片同時與當時正在展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配合,主要是起到政治性的宣傳教育的作用。
電視紀錄片《收租院》
荷蘭著名的紀錄片導演伊文思評價當時的中國紀錄片:“中國紀錄片總是同新聞報道聯系在一起,同時也經常緊密地和政治聯系在一起,是以就很難從藝術上獲得很大的發展。我在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同行們,長期以來受到這樣的限制,在紀錄片中總是一個模式。總是上來就解說,上來就規定你怎麼想,總想通過語言告訴你應該怎麼想,應該怎麼做。”
改革開放迎來中國電視紀錄片的黃金時代
1978年,全國展開真理标準問題的大讨論,提出應該求真務實。中國終于打開國門,走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改革開放為社會帶來劇變,無論是社會政治、經濟,還是人們的思想、觀念,都處于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激烈變動中。
政治環境開始寬松化,中國新一代的電視人也逐漸開始發現了專題紀錄片的拍攝制作的問題,希望改革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在意識形态至上的電視觀念長期壟斷電視創作的時代,人們對專題片的居高臨下的說教已經十分反感”——中國傳媒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朱羽君指出。
全方位的改革也給社會帶來一個比較穩定而多元開放的社會環境,人們的精神生活日益豐富,那些重大而統一的時代主題已經不能完全涵蓋民族的精神走向,出現的是價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狀态,時代聲音開始由多層次的聲音所構成,“人”的意識慢慢從被過分強調的“集體意識”當中解放出來,逐漸獲得比較“個人化”的屬性,人文觀念開始确立。
在技術上,eng(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電子新聞采集系統也強烈地影響了中國紀錄片的發展。eng最大的特點就是攝錄同步,它可以把電視記者在新聞事件現場的采訪、報道、直接聲形并茂地展現在觀衆面前。這就為紀錄片通過同期聲展現紀實作場奠定了技術基礎。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後,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高,電視接收機的生産能力和消費能力也大幅提升。電視由原來的奢侈品逐漸變成了普通的生活消費品,“電視熱”在全國蔓延。在1976年,全國性的電視廣播網絡初步建成,此時全國人口的電視覆寫率達到了36%,而在遼甯、湖北、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覆寫率更是超過了50%。
正在這樣的生态環境下,思想解放運動風起雲湧,中國電視紀錄片也開始全面起步,進入了八十年代中國電視發展的黃金時期,開始出現了大量不同題材、不同樣式的電視紀錄片——《望長城》就是其中之一。
《望長城》誕生前,狂歡已悄然開始
《望長城》的誕生開啟了“新紀錄運動”,使電視紀錄片運動創作達到了第一個高峰。但這并偶然,在《望長城》以前,中國電視紀錄片已經開始湧現出一大批與傳統政論性紀錄片相差別的作品,悄然開啟了中國紀錄片的狂歡時代。
文革的風暴肆虐過中國文化界,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場風沙中傷痕累累。80年代,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漸漸落幕,知識分子們在痛定思痛後開始思考“人”背後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民族文化心理,一場浩浩蕩蕩的“文化尋根熱”悄然開啟。思想上的啟蒙主義、美學上的現實主義、成為這一時期的兩面文化旗幟,對現實和曆史的批判,對人文理想的追求,也成為這一時期最基本的藝術主題。
1980年,由中央電視台與日本廣播協會合作拍攝的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大型電視紀錄片《絲綢之路》在央視播出。它以一股灼熱的激情,回溯了中華文明古國的源遠曆史,對盛極一時的文化遺址、民族、宗教習俗進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掃描”。
大型電視紀錄片《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播出後不久,中央電視台又馬上組織一批人馬開始了《話說長江》的拍攝,當年為《收租院》撰稿的陳漢元,又擔任了《話說長江》的編劇。1983年上映,《話說長江》引發萬人空巷、集體與時代記憶。繼《話說長江》以後,延續《話說長江》的形态,《話說運河》也接踵而至,編劇同樣由陳漢元擔任。從《收租院》中的解說詞:“鬥啊鬥,吃人的口……”,再到《話說長江》中的《長江之歌》:“你從雪山走來,春潮是你的風采,……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各族兒女。”
紀錄片從濃重的政治性,演變到政治性與藝術性的兩重标準在“話說”系列中巧妙融合。以祖國大江大河為題材,“話說”這種全新的叙述方式,用浪漫又抒情的叙述口吻,帶領觀衆進行長江、黃河沿岸的熒幕旅行,觀衆通過日常化的觀看方式欣賞紀錄片,跟随錄影機鏡頭進行熒幕旅行,給中國電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視聽盛宴。
1987年,陳漢元又擔任了《唐蕃古道》的編劇。紀錄片沿着當年唐代文成公主進藏的路線,在展現西部壯麗的河山風光、富饒的地産資源、珍貴的曆史文物古迹的同時,也将鏡頭對準了青海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展現了他們的生活風貌、民族風情,歌頌了源遠流長的漢藏傳統友誼。周圍的人和現實世界,終于被電視紀錄片以人性化的、平視的眼光來看待。原來的英雄主題被取代,宣傳味道也逐漸被淡化,紀錄片創作者開始主動将鏡頭對準平民大衆,對準弱勢群體,對準邊緣人的小人物,以平視的視角觀察社會與個體生命。
1988年,由夏駿擔任導演,蘇小康、王魯湘擔任總撰稿人的《河殇》在中央電視台播出,震動了中國社會。不能忽視的是,此時主管這項工作的中央電視台副台長,也正是陳漢元。《河殇》從對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進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漸引入對西方“蔚藍色文明”的介紹。對包括“長城”和“龍”在内的許多長期被中國人引以為榮的事物進行了辨析和評判,認為中國以河流、大地為根基的内向式“黃色文明”導緻了保守、愚昧和落後。為了生存,中國必須向以海洋為根基的“藍色文明”學習,并應該建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體系。《河殇》對華夏文明的起源、中國的曆史以及它面臨的挑戰進行了反思,主題是沉重的,貫穿始終的沉思和诘問也是沉重的,引發起一代人對曆史和文化的思考,帶來了沉重的哀痛和憂傷。強烈的民族主義和人文追求,在這部紀錄片中達到了高潮。
紀錄片《河殇》
康健甯和高國棟于1989年拍攝的《沙與海》,用鏡頭記錄了生活在大漠裡與大海邊的兩戶人家的普通生活。從真實的生活出發,用藝術的形式進行加工,透過兩個生活在大漠中和大海邊的家庭的生活狀态,我們能看到兩位導演對生命、對生活的普遍思考。從片中的劉澤遠和劉丕成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最純樸的地道地道的農民:他們或許目不識丁、習慣了對困境逆來順受,但他們也不會投機取巧,踏踏實實地用勤勞來應對生活的苦難。這種掙紮,正是我們民族的根。
王海兵的《藏北人家》也是這樣,片中的藏北,雲朵自由漂浮,蔚藍天空下牛羊成群。藏民措達一家從清晨到夜晚的一天都被鏡頭所記錄,飲食、起居、婚姻、祭神、審美、剪羊毛、嬉戲、跳舞……正也是藏北每一家牧民們的日常生活。人與自然的和諧與抗争、人在自然中創造與生存的話題,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之間的人們,都是共通的。
紀錄片《藏北人家》
經過長時間的積累,以紀實主義為代表的創作浪潮結出了一大批豐碩的果實。由陳漢元擔任制片、劉效禮擔任導演的《望長城》,正是在80年代這個中國電視紀錄片的黃金時代中所誕生。中國電視紀錄片在摸索中前行,經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之後,《望長城》看似平地起驚雷般出現在中國電視紀錄片界,為中國電視紀錄片發展史立下一座裡程碑,但其實早已厚積薄發,在一次又一次的震動之後,終于将中國紀錄片的狂歡時代推向高潮,開啟了“新紀錄運動”。
那麼,從紀錄片創作的角度,《望長城》究竟實作了怎樣的突破,才讓它成為中國紀錄片史上一個繞不開的坐标點,如一座不朽的豐碑伫立在曆史的長河中呢?紀念《望長城》30周年系列文章,第三篇文章将為你解讀,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