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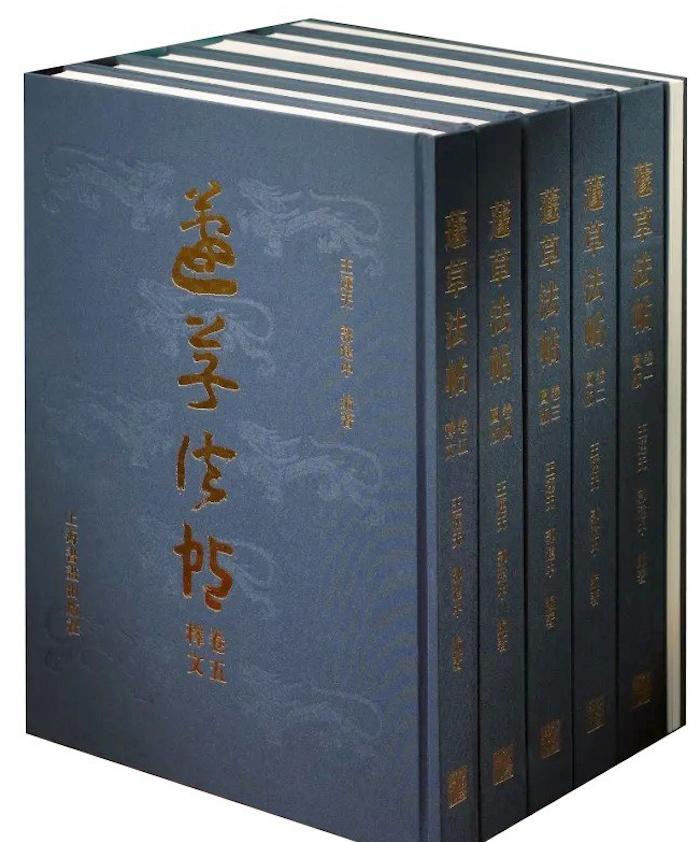
《草法報》,王雲田、郭建中編輯,上海畫書院2020年4月出版,1656頁,3980.00元
王玉昌(1900-1989)
《草法報》是王玉昌先生的通訊集,出版意義重大,要研究草,再研究王玉昌先生,是毋庸置疑的。當然,這套書的意義并不僅限于此。
草法律郵報有極大的美麗。最突出的,也是最大的貢獻,是書法的美。王玉昌先生的《張草》,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座巅峰之作,名字"雜草",最早出自謝日留先生的口中,已被廣泛認為是一種曆史評價。謙遜内向的王玉昌先生,對自己的書法成績也應該非常自以為是。《命運》中有很多證據。
例如,他在"右後方軍隊1,652年"的背面印有一個派對,編輯将其印在封底上。關于這次印刷的起源,書中也有一句道,在《馬國權力的後記》中,王玉昌先生有一篇關于嘉興桐鄉陳玉如的短文。這邊的印刷,是陳,然後介紹說,這種語言"本武試給語言",王先生的父親認為,這種印刷"比錢十蘭的冰,然後直到小生活'的篇章,包含了很多。錢十蘭,也就是錢蠻,字捐獻,10号蘭,是清朝大儒家錢大昭的侄子,"S"即李氏,"冰"是李陽冰,兩李數完我,好錢的書是以自命不凡,當然是相當自負的。相比之下,王玉昌先生的印刷确實有點低調。
"後右軍1,652歲"印刷
比如王右軍有"十七個崗位",王先生應該是學生馮啟勇先生的邀請,打"十八崗",第一個溝通雲:"第18冊"。反複要我的書《18個崗位》,怎麼敢繼續正确的軍隊。但用足夠的言語來真心掏錢,卻不忍心拒絕。書的第一篇有"18号"字樣,在卷之前,也就是"18個文章"可以嗎?一個微笑。"這十八篇通文精巧,修辭有趣,堪稱草範式。其中,很有意思的,《問郵報》王先生回答了馮先生的問題,評論王偉的書法雲:"玉花"收到了《畢峰》《菊元》《安和》《餘玉》《清河》的每一篇文章,頗為放縱,近乎開心,但似乎并不完整。雲層過後,很多自然,難以攀登第一名。越晚你進入這個領域,這本書為什麼是神聖的,又是神聖的?餘增臨沂上百次,是以稍微知道一下它的需求,敢于為哥哥說話。"後右軍1652歲"的國王經常說右軍,并說右軍上百次,充分說明草的勝利,它的起源。
十八個職位
書中還透露了一個有趣的手掌:1978年8月25日給老朋友潘博川"熱"雲:"前一天同一個女兒王康孫),熊(即兒子王興孫)到複旦泰晤士河虎曲院,簡稱日本書審判書雲:"中國書法有着優良的傳統,古老的王瑜之,現在還有王琦。這是一個偉大的聲譽,博兄弟笑了。"潘先生是王先生在無錫州立大學的同僚。信中透露,王岐山從胡錦濤那裡得知,這個東方鄰居在1978年有"古代國王,現在是國王"的美譽。今天,這句話是衆所周知的。我們知道,這封信是手寫的信件,最好地展現了作者的性格和寫作風格。《草法郵報》收錄了500多封信,最早的一封是1925年6月寫給王偉先生的,最後一遍是1989年10月24日寫給兒子王興孫的,那天晚上王先生心髒病發作,第二天就死了,是一支筆。時間跨度長達六十四年,幾乎涵蓋了王玉昌先生書法創作、研究草的全過程,這本書堪稱第一寶庫。
《熱帖》
其次,是人格之美。本來,人格之美遠比書法之美重要。之是以要從書法出發,自然是因為這本書叫《草的法則》,不過,讀書如果隻看書法,而忽略王玉昌先生的個性,那就可惜了。王先生的學生、《人民日報》前主編範敬義先生說:"就王先生而言,認為他是我國傑出的書法家是不夠的。與他深厚的成就和成就相比,書法隻是他的冰山一角,或者說隻是他的"殘餘"。我們要想充分了解王玉昌先生,就不能學他的書法,學他的書法,學他的知識,學他的學,更不能學他的個性。在他身上,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書法是這種統一的外在表現,就像人體一樣。範先生不停地,澄清了書法、學識和性格之間的關系。你也可以把這段話想象成這套書的編輯思想和靈魂。
個性是個大話題,在這個隻有簡說了兩端,一個為瓦斯節,一個為老師。
讓我們從瓦斯節開始。抗日戰争期間,王玉昌先生堅決不承擔不法職責,誓言要搞得不一樣。在無錫國立學院任教的陳竺與王玉昌先生有過師友情誼,抗日戰争期間在王晖的僞統治下擔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并給王先生寫了一封信,讓他出山,信健拒絕了。在書中,""""王先生在抗日戰争期間寫了許多反敵詩,并在報刊上發表。1948年初,他的弟子吳偉的表演被編入《反軍集》出版,其中詩篇65、50篇,這封信也被收錄在書中。
和對老師的尊重。老師唐文志先生的生活是受人尊敬的。1954年,在他去世前,唐先生告訴王先生要恢複無錫國立學院,三十多年後王先生沒有忘記,書中有很多信是專門為王先生回校寫的,收件人是美國計算機王安、複旦大學校長謝希德等人。 你可以看到王先生是如何為此辛苦勞作的。王先生親身經曆了高校院系的調整,不一定沒有意識到國立高校複課的渺茫希望,還是知道它不可能為它,為什麼呢?在給長子王福孫的"漸進回信"中,王先生透露了自己的心聲:"這不是國家獨有的民族傳統,親身承擔着唐老頭的死,永遠獻身于心,渴望做到。"王先生的人性化方式也深受唐先生的影響。在《小北京郵報》給孫皇後小靜的《小京》中,王宇爺爺常說,在他二十歲之前,他也"喜歡和人争吵,或者不理人,或者發脾氣"。後來,聽完唐先生的教訓,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轉述了唐先生的話:"人最要培養、培養的,就是獲得氣質,當事情不盡如人意的時候,也要忽略。"讀到這裡真的很感人,很感人。
前一段說書法,這部分人格,不妨提一下學習的"三位一體"。Sinzarido是禮物的數量,父母短缺,說醫學理論,甚至微不足道的日常。不過,書中卻包含了給研究所學生石志偉和戴紅才的兩封信,都是答案。看王先生的方式,細細的回答,筆直如聽先生講課,精彩,看先生并肩招聘,信手拉手,不能不尊重貝利先生的富足。雖然隻是一封讀信,但也能一睹王先生的博學淵博。
《草法郵報》問世後不久,就被評為"中國年度書法",成為榜單上的兩部書法作品之一,可以說是真名。在整本書中,王玉昌先生用文字,而不是一個詞,甚至在他晚年給孫子孫女寫信。王先生出生于1900年,比魯迅小十九歲,比胡石小九歲。魯迅、胡石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将領,早在王偉昌年輕時就開始寫白話。而王先生的年齡相仿的朱子清、冰心、沈從文、老舍等,都是書寫的白話大師,這個名單也可以打開一長串。王先生一輩子都寫不出一個字?我想,這不也是,不能不也。有一次,王先生還委托一位老朋友将他的話"翻譯"成白話。他就是鄭一梅先生。說到這裡,鄭先生比王先生大五歲。請看鄭志的《如活着的文章》:
在晚報上反複朗讀名人轶事,栩栩如生,向貝聿銘付出!有真心人,明年為誕辰120周年唐老人、門衛等意為盛大紀念,我們打算寫,為文字,大膽懇求花錢成文字,簽上大名,送報紙出版,讓社會各界知道, 沒有一種無敵感。
"比如一個活生生的文章"
所謂"夜報",也就是我工作的"新人民晚報"。《夜報》是上海市民的愛,王先生也來自,讀書很親切。我自然好奇,這部"文字轉說話"的作品,鄭一美先生接手了嗎?在數字時代,容易檢索,我很快找到了鄭文,1983年8月3日出版的《新人民晚報》增刊《夜光杯》,标題叫《唐文志120周年慶典》。文章不長,隻有700多字,但細節生動,生活靈活,是标準的"一美風格",全文是記錄下來的。
交通大學,人才一代,最早的校長,是唐老文智。他還是無錫國立學院的校長,解放後,他成為中國美術學院的院長。今年是唐老誕辰120周年,兩校同學們正在共同準備隆重的紀念活動。溫台省的全國大學生也在為遺體的出版做準備。唐老的大風音樂節,加上音樂和教育的天賦,确實是典型的腳藝。
唐老主持交通大學十餘年,開創了鐵、電、管理三大專業,籌建了科普圖書館和電動機廠,作為該校唯一的創始人,也配得上物質文明與公德心的結合。他的老人是人,有很多談話和幫助。他小時候,家人很冷,晚上讀書燈油不夠,燒棒香到光,導緻書上出現牌匾,很多灰痕。十四五歲,已經讀完四本書五、十七歲,村裡為人測試中國風。在外交部,深深談到泰俄外交的困難,認為要了解對方的知己,首先要學會讀俄語,他經常讀俄語到C夜。他從小到中失明,視力下降。曾經擔任過農工商務部、商界頗有傳承,他一一拒絕,正如巅峰所熟知,李玉堂真是個紳士。有一次父親生日,有一個捐贈緞子、金字的例子,用金紙包裹棉,這個人為了尋求差異,不是心不在焉,容易真金,他很生氣,馬上就扔回去,說:"應該嚴格,阿姨,免檢",它的人類老鼠沖走了。辛亥革命軍唐老毅然申請清朝皇帝的職位,冠代眉哭泣,跪着站起來,地上捧着紅頂花,說:"朝臣的意義,做這個!"辦學時,視弟子如血肉之軀,知道重病,一定要送人慰問,而且越發白恐怖的時候,他保護學生的地下工作,如秦鶴鳴、馮啟勇等,照顧不一樣,大學被包圍後,尋找更多的學生, 他與張元基緊急談判,共同抗議,要求立即釋放。危險的巢穴必須是雞蛋,學生們都覺得自己在穿。他引誘回來,不遺餘力。凡有好文字、有名氣的,又能背誦其警句,如果不是中檔,則嚴厲訓斥。在教室裡很莊嚴,平淡卻容易走近人,和親戚朋友交談,有時還夾雜着幽默。喝了一天酒後,他對來賓們說:"我的唐門弟子有三個丁家,圓的形狀為王玉昌,名單眼為陳竹尊,為錢仲蓮探索花朵。"說笑,有這很有趣。
有意思的是,文章結尾,王玉昌先生是《唐門園》的素材,這正是王先生寫的。他在《如一個文章》中有一個特别的描述:"'三鼎A'雲雲,同濟大學系教授為其派子周琦,康逸唐門弟子也。"王先生在這裡,少了同濟教授的名字,應該姓康。
事實上,在新民晚報中,王玉昌先生也有朋友,他就是沈玉剛先生。《新人民晚報》老報人如明星,林推、a、秦青支的散文都在紙面上流行。與他們相比,沈先生和他的筆名"它的派",認識的人并不多。不過,要談及與文化名人接觸的深度,沈先生在老報紙人中,是第二大人物之一,再加上沈先生擔任副主編、長期主編的《新人民晚報》副刊副主編,是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先生的朋友圈決定了《新人民晚報》的文化高度。王玉昌先生是沈先生的朋友之一。
我去報社的時間很晚,與沈先生沒有聯系,對他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在《草法報》上,王某寄給沈新座十一世的收入,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
第一封來文寫于1982年3月12日,本傳《江剛報》說,"已經在一起四十多年了",相比兩份履歷,很有可能沈先生在江大,王先生任教的地方,有師生之間的友誼,是以王先生稱沈先生為"學的哥哥"。他感歎道,"現在足思已經五十年了,輕蔑已經過去了,八十三年多了",四十多年後,接到同學們的來信,王先生很開心,說"不打算問,什麼更快了。"他在信中告知了自己的位址,并歡迎沈先生作為客人。
沈先生是報紙編輯大師,是以在接任後,王先生立即發展成為"夜燈杯"作家。他不寫白話,那麼他寫什麼呢?舊式詩歌和成對。當師生的關系變成了作者和編輯的關系時,兩者之間的交流往往圍繞着稿件展開。經調查,王先生首次在1982年7月2日出版的《夜光杯》中發表了手稿,标題為《嶽無木墓》,共六首詩。這首詩發表的第二天,王健林寫信給沈先生,為《郵報是什麼》寫信,信中說這封信是"懷疑1985年"寫的,應該是1982年。信中說,"看報紙的意義,還多快",還說,"有一些錯字,學校就像左派一樣",手稿不長,錯位多達五個地方。這在經過精心編輯的"夜光杯"中很少見。王先生的章草,相當難以辨認,失誤的手是老百姓的必然。是以,沈先生采取了出樣的方法,先送給王先生進行修改。在《兩個文章》中,王總說,"小樣本學校,謝謝你到最後",就是證據。在當今的電子時代,這樣的制造已經不複存在。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新人民晚報》以"飛進普通人家"為目的,推廣大衆,淺薄。《新民老報》人的文章樸實無華,王玉昌先生的詩,雖然他加了很多筆記,但對于晚報的讀者來說,還是顯得深奧的。是以沈先生向王先生提出了這個問題。王先生在《極端郵報》中回答:"詩歌一定是流行而簡單的,非常,被鄙視不擅長,為了仇恨的耳朵。"雖然對方說'非常肯定',但還是做了一個小小的'掙紮'——我寫得不能淺薄。王先生太固執了,很可愛。
書中還收錄了《解放日報》前主編王冬雲先生給《解放日報》的幾封信,同樣的方式和貢獻。20世紀80年代,王先生在解放報、文彙報和新民報上發表了五十多首詩。王滬甯的最後一篇文章發表在《新民晚報》上,發表于1989年9月12日,也就是他去世一個多月後。本文标題為"聯合語言偶爾",它有一個關節,是祝願《新人民晚報》成立60周年聯合"一代新人,手持花甲;作為後人報紙,當想起"正念"這個詞時,有四個字。
負責編輯:鄭世良
校對:張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