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傑伊·溫特
摘錄 |劉亞光
美國著名的戰争史專家傑伊·溫特(Jay Winter)讨論了這個問題:你如何喚起人們對紀念碑背後所代表的東西的集體記憶?此外,他的想法更進一步。記憶領域的問題不僅涉及觀衆,還涉及設計本身。猶太人如何紀念人類悲劇,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大屠殺,這些悲劇是"失去意義"的?這些問題不僅與紀念碑的設計有關,而且與曆史的姿态有關。他還認為,隻有嵌入屬于家庭的私人記憶,才能使承載着宏偉集體記憶的紀念碑煥發活力。以下内容經出版社授權,摘自《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删去,小标題由編輯添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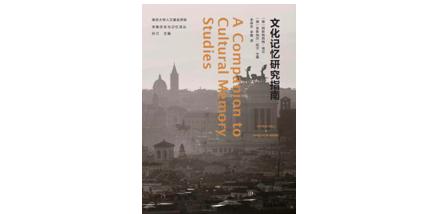
《文化記憶研究指南》,阿斯特麗特·艾麗/安斯加爾·努甯編輯,李全中、李霞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2月
紀念和公權力
"記憶場"是人們參與公共活動的地方,進而表達了"關于過去的知識的集體分享......這些知識是一個群體的團結感和個性的基礎。去這些地方的人群繼承了事件本身的内在意義,并為其增添了新的意義。他們的活動對于紀念遺址的表達和儲存至關重要。當這個群體消散或消失時,記憶領域就會失去最初的活力,甚至被完全抛棄。
諾拉引入的術語已經擴充到許多不同的文本,從傳說到故事和概念。這篇文章更具體地定義了"記憶領域",僅指進行紀念行為的實體場所。在20世紀,絕大多數這樣的遺址都因在戰争中喪生而被人們記住。
這個記憶領域往往有自己的生命曆程。首先是啟蒙和創造階段,這些階段是為特定的紀念目的而建構或轉換的。然後有一個制度化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它們的使用往往成為例行公事。有關标志,例如表明在特定時間應舉行何種紀念活動的時間表,可能會持續數十年或可能突然暫停。在大多數情況下,記憶領域的重要性會随着發起行為的社會群體的消失而消失。
近代以來,大多數記憶場都嵌入在與宗教議程截然不同的事件中。當然,也有一些重疊。在一些國家,在停戰日(11月11日)參觀紀念場所讓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非常接近天主教萬聖節(11月2日),而在一些擁有大量天主教徒的國家,這兩個日期都占據了近乎神聖的公共紀念空間。首先是參觀紀念公墓,然後參觀戰争紀念館或其他地方。5月8日是歐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停戰日,也是聖女貞德的周年紀念日。參加當天紀念活動的人要麼是世俗的,要麼是天主教徒,而其他人則同時使用這兩種儀式。一般來說,地點的選擇意味着日期不同。
在紀念場所舉行的紀念活動是一種源于信仰并由大型社群共享的行為。紀念的時刻既意義重大,又包含道德意義的資訊。記憶領域以物質形式呈現這些資訊。民族屈辱的時刻很少以有形的方式被紀念或标記,盡管有一些例外,即鼓舞人心的例外。在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日,公衆紀念活動的标志性口号是"永遠不要重複它"。廣島公共建築的外殼讓每個人都想起了這座城市被第一次原子彈襲擊摧毀的那一刻。如果關于戰争或公共政策的道德問題持續存在,那麼紀念碑要麼難以修複,要麼有争議。這就是為什麼法國人試圖紀念阿爾及利亞戰争的結束,而美國人試圖在沒有明确日期或地點的情況下紀念越南戰争的結束。關于沖突的性質沒有道德共識,是以對于公衆應該記住什麼,何時何地,沒有道德共識。
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既是對普通士兵的敬意,也是對戰犯的崇敬。參觀比特堡的德國士兵公墓也是如此,一些前黨衛軍成員被埋葬在那裡,那些沒有犯下戰争罪的人也是如此。然而,這兩個地方都是一種記憶場,無論是有争議的記憶還是讨厭的記憶,最終都是一種記憶。
《記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與變化》,作者:Aledda Asman,潘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3月
記憶領域的本質是,它們不僅是災難性事件幸存者的參考點,也是事件發生很久後出生的人的參考點。當經曆過它的人直接死去的時候,過去的叙事變得流行起來,"記憶"變成了隐喻,而記憶的領域不可避免地變成了二手記憶的地方,也就是說,這裡的人記住了别人的記憶,就是那些事件的幸存者的記憶在這裡被标記出來。
圍繞記憶領域的許多學術辯論都集中在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一個社會主導政治力量的工具上。一種觀點強調,這些場所的公共活動有助于政治精英建立其統治的合法性。對于其中一些事件,請觀察誰掌權 - 巴黎的巴士底日,費城的獨立日或美國的其他周年紀念日。其他事件與推翻舊秩序和新秩序的建立密切相關:11月7日标志着布爾什維克革命和俄國共産主義政權的建立,這一天象征着新秩序及其對世界敵人的挑戰。莫斯科克裡姆林宮外的閱兵式既是紀念的時刻,也是非常自豪的時刻,展示了蘇聯軍隊在俄羅斯和世界曆史上的地位。
這條自上而下的道路強調了記憶領域作為國家,帝國或政治身份的有形載體的重要性。澳新軍團日,4月25日,被慶祝為澳洲國家的誕生。它紀念1915年澳洲和紐西蘭軍隊作為英國上司的遠征軍的一部分在土耳其登陸。登陸失敗的事實并沒有削弱澳洲人眼中當天的标志性性質。正是在這一天,他們活了下來,他們的國家長大成人了。這一天有很多回憶。首先,人們可以去澳洲各地的戰争紀念館。然後是國家社交場合,堪培拉的澳洲國家戰争紀念館,該紀念館以伊斯坦布爾的哈加索非亞大教堂為藍本,并刻有在戰争中喪生的所有澳洲士兵的名字。最後,每年還有一次加裡波利海灘朝聖之旅,直到21世紀,仍有許多人參加。在那裡,澳洲人繼續在當年登陸的海灘上進行加裡波利登陸。
并非所有的紀念館和記憶都與戰争有關。君主或已故總統的生日也以類似的方式紀念。維多利亞女王的生日,5月24日,被慶祝為英聯邦日,大不列颠帝國日,自1999年以來一直慶祝。周年紀念日是一個更廣泛的運動的一部分,一些學者稱之為"傳統發明" 。換句話說,在19世紀末,新興的民族國家和已建立的帝國主義列強加強了對儀式活動的使用。然後,權力光環的放大被欺騙性的血統所證明。展示據說與曾經存在于遙遠而模糊的古代曆史中的習俗或形式相關的特定儀式可以有效地掩蓋政治變革,不穩定或不安全等因素。有趣的是,這個傳統與一個地方之間隻有微弱的聯系。是以,對于那些想要發明傳統的人來說,他們的選擇更加靈活。
這種對紀念活動的功能性解釋受到了挑戰。第二派強調了記憶和相關紀念活動領域如何有可能幫助他們的主導群體公開戰鬥,以擺脫他們的從屬地位。許多政治上司人或其代理人試圖設計新的紀念活動,但對官方紀念文字的颠覆性或創造性解釋還有很大的空間。在11月11日的停戰日,不同的團體前往戰争紀念館,有些是為了宣傳軍事價值觀,有些是為了诋毀軍事價值觀。和平主義者通過出現在這個記憶中來宣布他們相信"永不重複",而士兵和他們的支援者則利用這樣的時刻和這些地方的氣氛來美化他們的職業,并表明公民義務,如果有必要在未來可能的戰争中為他們的國家而死。同時,同樣的空間,表達的形式是沖突的,這個問題從未得到解決。
這種對記憶領域政治意義的新解釋強調了記憶行為的模糊性,以及新群體出于新原因盜用舊記憶領域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紀念碑通常是多種聲音的合唱,有些聲音比其他聲音更大,但從不獨奏。分散紀念的曆史可以使我們意識到紀念行為的區域,地方和異質特征。自上而下的路徑必須輔之以自下而上的路徑,以檢查關于過去的腳本如何在村莊,城鎮,省級城市和公權力中心的紀念領域發揮作用。
一次偶然的機會,這些不和諧的聲音聚集在一起,創造了一個民族記憶的時刻。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上司者不會被分組到一個單一的記憶領域中。這種記憶傳播的例子可以在1919年至1938年間每年11月11.m 11點觀察到的兩分鐘沉默中看到。接線員拔掉了所有的呼叫插頭,交通中斷,正常生活暫停。然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突然轉向戰争,這不符合國家的利益。從那時起,兩分鐘的沉默被改為最接近11月11日的星期日。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裡,它成為了一個全國性反思的時刻,無處不在。早期的社會調查組織"大衆觀察"(Mass Observation)采訪了數百名普通英國人,并詢問他們在兩分鐘的沉默中的想法。
他們回答說,他們想到的不是國家,勝利或軍隊,而是那些不在場的人。這種沉默是對國家缺席的沉思。通過這種方式,它從政治交響樂滑向家族曆史的領域。當然,這個家庭對親人的紀念是在更大的社會和政治架構内進行的。然而,最豐富的紀念形式總是存在于家庭生活中。正是公共與私人、宏大曆史與微觀曆史的交彙,賦予了20世紀紀念活動力量,使其呈現出豐富的戲劇形式。然而,這些紀念過程的複雜性意味着記憶領域并不總是紀念的焦點。
此外,一些建築物可以非正式地轉變為記憶的地方。勞工們在電影院組織了罷工,婦女在家中建立了婦産中心或兒童保育中心,因自然災害而無家可歸的人找到了一所學校作為避難所,對于那些在這些地方度過了一些重要時刻的人來說,這可以成為記憶之地。當某些團體自行行動時,官方證書不是必需的。
《記憶的領域:法國民族意識的文化與社會史》,皮埃爾·諾拉編,黃豔紅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8月
美學與救贖:紀念碑形象的改變
記憶領域的生命曆程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姿态和物質任務。記憶領域往往也是一種藝術形式,包括藝術的創作和安排,以及對一些重要行為的诠釋。這可以從兩個不同的層面進行分析:首先是美學,然後是符号學,它們密切相關。
某些形式的紀念隻屬于一個民族,具有獨特的特征,而其他形式則由多個國家的人民所共有。在法國,作為民族國家的象征,全國數千個小城鎮的市政廳都有瑪麗安的形象,這在德國和英國是無法使用的。在德國,勳章上的鐵十字表明了它所紀念的地點和傳統。德國英雄的森林或堡壘也被折疊起來,并嵌入巴頓的曆史中。
有時,一個國家的象征意義與另一個國家的象征意義相吻合,即使這兩個國家可能是競争對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完全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第一次工業戰争,許多形式的紀念活動都采用了中世紀的符号。在整個歐洲,戰争的革命特征都以一個向後看的象征為标志。中世紀英雄和聖戰士的形象重新喚起了一個發生在個人之間的戰鬥時代,而不是在非人格化,不平衡的決鬥中發生在武器和人肉之間。空中的戰争伴随着騎士和浪漫,中世紀的風格在赢家和輸家身上都複活了,這在許多教堂褪色的玻璃窗中顯而易見。在這些地方,對兩次世界大戰的紀念與早期的宗教形象和目标非常相似。通過這種方式,20世紀的戰争呈現出神聖的色彩,因為它的記憶領域位于神聖的建築中,在神聖的法律的背景下。
直到20世紀末,戰争紀念館仍然以人類的形式存在。有些地方選擇經典的男性健美形象來紀念"戰争死亡的精英一代",有些地方統一使用更加堅忍、勇敢的男性形象。在大多數情況下,勝利要麼是部分的,要麼是完全被壓倒性的失敗所掩蓋。在這種美學景觀中,傳統的天主教母系氏族長非常普遍。悲傷的聖母的形象是地方和國家層面婦女集體悲傷的标志。
在新教國家,美學争論具有準宗教性質,這些國家的戰争紀念館冒犯了清教徒。他們認為,16世紀的宗教改革拒絕了這種"天主教"的象征,方尖碑是可以接受的形式,而且相對便宜。在法國,戰争紀念館是合法的公共場所,不能建在教堂的場地上,盡管許多當地團體設法規避了這一規則。在學校和大學中,這些紀念碑的位置觸及到這個問題。有的位于學校的附屬小教堂内,這是一個神聖的空間,有些位于附屬小教堂周圍,這是一個準神聖的空間,有些位于世俗空間中,作為街道和火車站的公共空間,還可以為戰争死者名單提供庇護所。位置表示含義。
20世紀的戰争使喪親之痛"民主化"。以前,軍隊主要由雇傭兵,志願者和職業軍人組成,但1914年後,每個人都參加了戰争,戰争傷亡的社會影響發生了變化。在英國、法國和德國,幾乎每個家庭都曾失去過一個人,無論是父親、兒子、兄弟、堂兄還是朋友。許多遇難者 - 也許是其中的一半 - 由于西線戰場的膠水粘附狀态,沒有特定的墳墓。是以,标記死者的名字成為紀念他們的最重要方式。名字是死者留下的所有名字,刻在石頭或牌匾上,并成為當地和國家公衆紀念的焦點。
紀念碑上刻着死者的名字。在極少數情況下,例如在澳洲,戰争紀念館列出了所有軍人的名字。這種方法經常導緻批評,因為很明顯他們的名字沒有刻在紀念碑上。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死者的名字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們隻能按字母順序排列,而不是社會等級。絕大多數戰争紀念館都以這種方式列出死者的名字,少數根據死亡日期或年份進行排名。但是,紀念碑是為幸存者和幸存者的家人建造的,他們需要能夠輕松找到留給他們的死者的名字。
二戰後,在銘文上墨迹的基本做法已成為紀念形式的基本風格。1945年後,許多地方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館中添加了名字。部分原因是人們意識到20世紀的兩場大沖突之間存在聯系,當然也是為了經濟。越南戰争後,刻字仍然是紀念他們的重要方式。與此同時,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碑的啟發,已經豎立了許多戰争紀念碑,最着名的是位于華盛頓特區的Maya Lin設計的越南榮民紀念館.C。她的作品借鑒了由埃德溫·盧琴斯爵士設計并于1932年建造的蒂普瓦爾索姆河失蹤者紀念碑的模型。
越南榮民紀念碑由美國著名華裔建築師、林慧英的侄女林瑪雅設計
到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藝術觀點和審美品味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以至于用于表示記憶的關鍵語言已經變得抽象。是以,雕塑和裝置藝術與特定民族的表達分開,不像早期那樣關注人物。前蘇聯的紀念藝術是一個例外,他們堅定地走在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道路上,以展示他們所謂的偉大衛國戰争的意義。在西歐,在許多情況下(當然不是全部),有些人建議缺席或虛無主義表達,取代了紀念藝術的古典,宗教和浪漫概念。
這種轉變在紀念大屠殺時顯而易見。對于大屠殺記憶的遺址,特别是集中營,滅絕營和猶太人在大屠殺前居住的地方,未來的生活不能被視為對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喪生的人的紀念。困難在于三個方面。首先,需要避免使用天主教符号來代表猶太人的災難。其次,嚴格教條的猶太人更厭惡具象藝術,這是正統猶太傳統所禁止或抵制的。同樣,受害者的死亡沒有反映出任何進步、意義或目的感。大屠殺的受害者可能已經證明了他們的信仰,但謀殺一百萬兒童的意義何在?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死亡毫無意義,大屠殺是以毫無意義。
以特定的方式表現出"無意義"是一種挑戰。一些藝術家提供的裝置藝術通過訪客的存在而消失。還有一些消失世界的照片,張貼在仍然屹立不倒并被非猶太人占領的建築物的外部。其他人則使用後現代形式來暗示迷失方向,空虛和虛無主義。由丹尼爾·裡伯斯金德(Daniel Libeskind)設計的柏林曆史博物館的猶太館就是這樣一個場所。它曾經被比作一顆爆炸的猶太恒星,或石頭和玻璃的閃電。在任何寓言中,它都展示了一些無法以令人不安的,令人心跳加速的非線性方式表達的東西。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念活動與大屠殺紀念活動混雜在一起。這既帶來了美學挑戰,也帶來了社會和政治挑戰。世界大戰的紀念形式,從無數老兵的逝世中,探索出一些意義和内涵。這些紀念碑中的許多都有警告的内涵。"永不重複"是它的終極意義。但"從不"持續了不到二十年。結果,對意義的追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變得更加複雜。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喪生的平民比在軍隊中喪生的平民更多,這使得人們更難想象紀念的藝術。
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極端性質也挑戰了藝術,任何藝術,表達損失感的能力,特別是當它與種族滅絕或原彈的毀滅有關時。前面已經提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如何否認通常的意義表達,盡管仍然有人試圖利用某些救贖的元素。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也是如此。記憶領域是人們确認曆史具有某種意義的信念的地方。當大多數人看不到時間和空間标記的事件有任何意義時,哪個地方合适?不可能忽視奧斯威辛集中營或廣島。但是,将它們放在早期的紀念結構或形式中要麼是有問題的,要麼是荒謬的,要麼兩者兼而有之。
當儀式嵌入家庭時,它們就可以生存下來。
公開紀念行為是由參與者的姿勢和語言決定的,他們聚集在記憶領域,回憶他們過去曆史的特定方面。在這種時刻,人們往往不僅會回想起固定的文本,或者會根據政治上司人嚴格制定的腳本來鞏固他們的權力地位。記憶總是不可避免地與政治衝突重疊,但無論如何,它不能被描述為權力關係的直接功能。
公開儀式的曆史至少有三個階段。我們已經讨論過的第一階段,即紀念形式的建構。但是,在紀念碑的生命周期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儀式行為在日曆中的根深蒂固,以及這種行為的日化。第三階段是活躍的紀念場所的轉變或消失。
這種軌迹可能有一個例子。1916 年 7 月 1 日不是英國的國定假日,但這是英國人開始進攻索姆河的标志日,象征着工業戰争的可怕本質。那天,英軍的傷亡總人數達到了曆史最高水準,而那天,一支志願軍及其背後的社會團體充分了解了20世紀戰争的恐怖。這一天,在沒有國家合法授權的情況下,人們湧向索姆河戰場紀念這一時刻。
它的儀式受當地因素的影響。來自諾森伯蘭郡的一些男人和女人把他們的風笛放在一個巨大的火山口中,以紀念索姆河戰役的開始,并確定它不會被犁地和遺忘。還有諾森伯蘭人前往博蒙特哈梅爾地區剩餘的戰壕系統,他們的祖先于1916年7月1日在那裡被殺。戰場上還有一座北美馴鹿的銅像,将這個地方與紐芬蘭的景觀聯系起來,紐芬蘭當時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人們在那裡組成了一支志願軍為國王和國家服務。11月11日是法國的公共假日,但在英國不是。立法機構編纂了來自地方一級并由後者推動的法案。
1939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遇難者的紀念碑定于11月11日之後的星期日舉行。最值得注意的是,教會成為了一個紀念的地方。新教教堂的儀式馴化了戰争紀念館,削弱了它們的吸引力。直到2006年,仍然有一個緻力于恢複戰争紀念館的運動,無論11月11日恰好落在哪一天。
柏林猶太博物館
公衆紀念活動在公民社會中蓬勃發展,當然不是在專制政權下。在斯大林主義的俄羅斯,公民社會是如此支離破碎,以至于不可能獨立于黨和政府舉行紀念活動(見梅裡代爾)。但在其他國家,當地團體和家人一樣運作良好。當紀念碑嵌入社群的節奏,特别是家庭生活時,它就存活了下來。當公共紀念位于國家曆史與其家族曆史重疊的地方時,它可以持續下去。許多花時間參加儀式的人都懷念這些盛大事件所感動的家庭成員的記憶。這就是為什麼在戰争或革命爆發後很久出生的人也會記住這些事件作為他們生活的基本要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孩子,并告訴他們的孫子孫女他們童年家庭的故事。兩三代人之間兒童記憶的傳遞賦予了家庭故事一些力量,當時機成熟時,它們轉化為行動 - 紀念。
有時家庭本身會成為記憶。著名的德國雕塑家和藝術家K.T.珂勒惠支離開了他死去的兒子的房間作為神社,因為他在1914年自願參加戰争。在巴黎的一個勞工階級社群有一個公共住房項目,每套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門上都列着一名在世界大戰中喪生的士兵的名字。這也是他們的家,一個隐喻的家,為那些被剝奪了像幸存者一樣生活和死亡機會的人提供了一個地方。
曆史叙事的家庭傳播架構是公共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使我們能夠了解為什麼某些形式的記憶會改變或消失。當家庭生活和公衆紀念之間的聯系被打破時,這種紀念形式的強大支柱就被移除了。然後,這種形式的記憶很快就會縮小并消失。公共增援可能有助于保持紀念和實踐的活力。但是,當事件與最初為它們注入生命的許多小社會機關分離出來時,它們就會變得空洞。
同時,紀念場所和做法可以重新激活或挪用。用于此目的的紀念網站也可以用于其他目的。但大多數時候,記憶領域會經曆自己的生命周期,就像我們這些還活着的人一樣,總有一天它會消失。
這種自然的解體過程結束了記憶和公衆紀念的領域。事實正是如此,因為它們的出現是為了滿足特定群體的需求,即将他們的生活與無聲的曆史事件聯系起來。随着這種需求的消退,維持這種社會行為的線索也随之消失。集體記憶消散,記憶領域瓦解,或者變成純粹的風景。讓我們看兩個這樣的例子。幾十年來,由埃德溫·萊亨斯爵士(Sir Edwin Lechens)設計的都柏林國家戰争紀念館(National War Memorial)一直長滿了雜草。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這絕非偶然。一百萬愛爾蘭人為英國的國王和國家獻出了生命,這個問題在1918年後的愛爾蘭曆史上很難解決。
然而,随着宗派暴力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消退,雜草被砍伐,紀念碑重新出現,就好像它們是憑空出現的一樣。誠然,記憶的領域已經消失了,但當人們再次決定紀念他們紀念的時刻時,他們可以再次被召喚。有時候,記憶領域的複活變得更加困難。多年來,我一直在問我在劍橋的學生,他們在從火車站到城鎮的第一個十字路口看到了什麼。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沒什麼可看的。他們沒有看到的是鎮上的戰争紀念館,一個勝利的士兵在第一個紅綠燈進入鎮上時大步回家的圖像。他們沒有看到紀念碑,因為它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隻是石頭上的白噪聲。對于那些看到它的人來說,需要指出,并且有人想要組織紀念活動。如果沒有這些努力,記憶領域将隻是在那裡,憑空消失。
在這一點上,我們已經到了堂吉诃德的盡頭。公開紀念既不可抗拒,也不可持續。記憶領域的建構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行為,但這些地方正處于變化的過程中,就像創造和維持它們的人一樣。人們不時來到某些地方,聚集在某些記憶場前,從過去的重大事件中尋求意義,并試圖将它們與他們較小的社會生活網絡聯系起來。這種結合注定要解體,将被其他形式、其他需求和其他曆史所取代。就此而言,記憶領域,即創造、制度化、解體的生命軌迹已經走到了盡頭。
該指南校對|趙琳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