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已齋文存
二《阿前》被認僞以來的錯綜糾纏
文/梁中和
古人不懷疑本篇不是因為他們完全信任所有挂名柏拉圖的著作,比如《愛克西亞斯》(Eryxias)和《阿克西庫斯》(Axiochus)就一直被認為是柏拉圖的“私生子”,有别于其他“嫡出”的對話;也不是因為對哪些屬于柏拉圖對話完全模糊不清,比如龐克提烏斯(Panactius)曾指出《斐多》是僞作,阿赫斯濤克塞努斯(Aristoxenus)認為柏拉圖《王制》大量剽竊普羅泰戈拉的著作;也不是因為由于對本篇的忽略,而沒有質疑其權威性。它一直作為柏拉圖的著作被廣泛閱讀和引用了一千多年,而且是作為進入柏拉圖哲學的門徑。
但到了近代,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首先質疑《阿前》作為柏拉圖著作的權威性,在我們進入具體讨論之前,先來聽聽黑格爾對施萊爾馬赫咬文嚼字的不屑:
從國文學的觀點去研究柏拉圖,如施萊爾馬赫先生所作的評注那樣,對這個或另一個次要對話去作批判式考察,看看是真的還是僞品(按照古代人的證據,絕大部分是無可懷疑的。)——這對于哲學也是多餘的,這也是屬于我們時代過分瑣細挑剔的批判。
很可惜,這種瑣碎挑剔的做法在今天學界仍頗有影響,單說學界不重視翻譯和引用柏拉圖疑僞著作便可看到這點。
不過施萊爾馬赫的工作,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和哲學依據,他對本篇對話的處理方式,也讓他成為開啟曆史的或文字考據路徑的代表人物。他受浪漫主義影響,對于現象的個體性(the individuality of phenomena)有特别的感觸,而對個體的發現也确實是浪漫主義文化的偉大成就,但那個著名的警句——個體是“須避諱的(不可說的)”以及不可能對個體的單獨性,進行概念性把握的想法,也都在浪漫主義時期冒出來了。在施萊爾馬赫那裡,人們發現了一組非常靈活變通的辯證而又特别的思考方式,給人以古典人道主義的博學和深刻的印象。他使前蘇格拉底研究的道路光亮起來,而且直接激發了以策勒爾(Eduard Zeller)為代表的柏林曆史學派的研究。
施萊爾馬赫指責前人,不加懷疑地接受了古代以來對本篇對話的過高評價,他認為那些從古至今給予這篇對話尊貴地位的人們,根本發明不出什麼原創的東西,隻是一味的遵從傳統,當然其中也包括黑格爾,隻是他沒有注意到黑格爾根本不關心哪篇對話如何,他首先承認了所有柏拉圖作品然後總體考量,這是古代就有的做法,古代注疏單篇并不是隻研究其中内容,而施萊爾馬赫自己開啟了一種研究單篇對話的方式,這是曆史學家最感興趣的做法,就是要對每一篇具體考察内容,對其中一些提出質疑并解釋其理由。後來發展成劃分著作年代,分出對話早中晚三期,然後在其中尋找柏拉圖哲學發展的軌迹,這是現在中國學界仍然流行的做法,國外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經有很大改變。
施萊爾馬赫針對本篇對話他的主要批評如下:
對于那些按照慣例對這部小書籠統地誇贊一番的人而言,它曾是一個受到最特别的贊賞的主題,但與我們而言,它卻是乏味而無關緊要的,以至于我們不能将此歸咎于柏拉圖,任何可以确認其精神的人都會在這篇對話中看到這一點。
他認為這篇對話在文字上和蘇格拉底人物塑造上都缺乏一緻性,他沒有引證篇中那些柏拉圖式的文字,而是引用一些“無價值”的片段,讀來像是篇殘損的對話,關于柏拉圖式的文字,他認為也隻是模仿其他傑出的柏拉圖作品,而且效果稀松平常,他認為本篇中的蘇格拉底,更像是色諾芬筆下的而非柏拉圖的,比如篇中有一大段誇贊斯巴達和波斯的話,在真僞争執中這段話是最重要的糾纏點。
最後他推斷說本篇是一個後世學生,得到一篇柏拉圖遺棄的對話寫作計劃,柏拉圖準備把本篇中的主題分散到其他各篇中分别讨論,這個學生自己又加入一些内容,是以顯得整篇對話不一緻。
施萊爾馬赫的這一評價影響極大,使本篇立刻失寵,但當時并沒有達成共識。英國著名希臘史學者格羅特(George Grote)認為本篇和《阿爾喀比亞德後篇》在主題和風格上都是極好的蘇格拉底對話,隻是勉強承認後者價值要次一等。他認為施萊爾馬赫批評的“不一緻”,是柏拉圖對話本身在人物和會話程序中,所具有的複雜性和超乎尋常的特性造成的。
後世學者大多受施萊爾馬赫影響,不很關注本篇對話。比如紹瑞(Paul Shorey)大體贊同施萊爾馬赫的評價,但他全文注釋了《阿前》,指出本篇對話之是以不像柏拉圖的,是因為它太過學究氣,太過精心安排,同時他也認為本篇柏拉圖對話内容中有兩個新穎之處,一是明确指出身體是靈魂的手段,一是首次提出因為眼睛隻有在反映中看到自己,是以靈魂必在其他靈魂那裡反思自己的說法。對于它究竟是不是柏拉圖本人作品還有疑問。
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下半葉,人們主要認為本篇是僞作或有保留的猜測是柏拉圖早期作品,其中我們熟悉的是泰勒那看似折中的評價,他說:
在範圍和價值方面是這一批(疑僞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篇,因為它包含了蘇格拉底——柏拉圖關于善的衡量标準和靈魂‘照料’說的極好的全面總結……該書一點沒有實際上配不上柏拉圖的地方。
他認為本篇的确如前人所說,是柏拉圖倫理和政治哲學的極好的導言,但恰恰就是因為這種性質,才讓它成為可疑之作,因為它太過井井有條,太像教科書而非柏拉圖願意寫的對話了。
古典學者們這種對《阿前》的輕蔑,帶來了不幸的影響:即人們确實覺得需要讨論其權威性了,然而他們提出的證據往往不能充分支援他們的質疑。比如有人說本篇用了罕見而文學性詞彙κρὴγυος和ἄχραντος,以此證明本篇不是柏拉圖作品,我們不應該否認柏拉圖可以運用這些表達,來達到自己希望的效果,因為在亞裡士多德之前的哲人,很少直接在作品中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表達觀點(即便在亞裡士多德那裡,也不能認為亞氏所寫的就完全是他個人的觀點),在對話創作中,為符合各種場景完全可以有很多種表達,不能因為一兩個生詞就否認一篇對話;還有就是像泰勒這種看法,認為它太柏拉圖化了,但我們為什麼不想想隻有真作才最像真作呢?因而直接以一種假設而否定本篇的人,往往看到本篇既和其他對話有很相似之處又有不同點,就像各篇對話一樣,他隻是孤注一擲地賭它是僞作,但沒有發現這種賭博遊戲根本不值得做。
近代以來還有兩種可以看似更科學的辨識真僞作的方法:“語言風格計量學”(Stylometry)和“年代學”(Chronology)。後者是通過文本語言分析确定著作年代,前者主要是通過用語分析判定作品作者。萊芝(G.R.Ledger)曾用電腦對柏拉圖著作進行了語言風格計量,得出了驚人的結果,他說如果我們把《阿前》當成僞作的話,那麼那篇對話的作者,在柏拉圖風格作品的寫作上是極賦天才的,這篇對話與其他被認為真的對話之間,比那些真作互相之間更相比對。 但我們的确也不能完全信托這種分析,因為資料好總結,可究竟如何判定什麼樣的風格才是柏拉圖的,我們無法憑直覺确定,總是需要嘗試不同的模型。而年代學的讨論近來也有不少, 主要是配合原來發生學方法指導下的柏拉圖著作分期研究,它通過分析标明了柏拉圖的三組對話,在一些小詞的運用上展現出不同的風格,如果用這種分析來看的話,本篇無法歸入任何一組,因為它混雜地包含了三組中的典型特征,如果這種年代學的考察是正确的,那麼本篇的确可以被稱為是假的,但是問題就在于這種年代學的分析方法是否正确。因為我們知道,這種分析方法建立已是十九世紀末上世紀初,那時已經不将本篇列入總體分析,那些公認的篇目才構成分析内容,由此做出的結果也更多地适用于那些篇目,而且這種三組早中晚劃分本來就是粗略不當的,一些篇目兼具幾種不同風格,比如《會飲》,我們不能脫離内容的具體讨論,僅就文字來辨識真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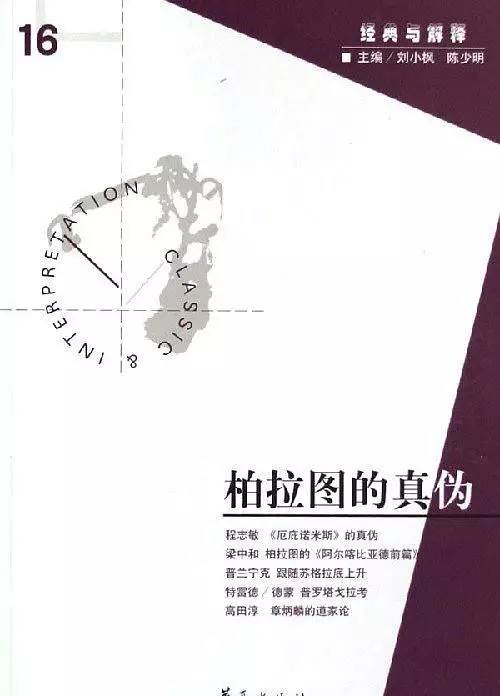
我們跟據普拉多(Pradeau)的統計, 下表顯示了從施萊爾馬赫到上世紀末,關于本篇真僞争論中的主要學者及其觀點:
上面的表格已經可以看到,其實學界對于本篇真僞,一直沒有統一的意見,特别是最近三十年,幾乎給人一種在承認它是柏拉圖作品的前提下,完全否定對本篇真僞讨論的必要的傾向。
上世紀二十年代福裡德蘭德(Paul Friedländer)已經有力地反駁了自施萊爾馬赫以來的觀點,他認為前人質疑的“不一緻”等,正是對話戲劇性反諷的典型表達方式,選擇蘇格拉底和阿爾喀比亞德作為對話人物,提高了對話的戲劇性張力。同時他首先強調了本篇的教育意義,影響了後人對本篇的關注。他還列舉了普魯塔克對本篇的引用、亞裡士多德對其中眼睛在其他眼睛裡看到自己的回應,和色諾芬在《蘇格拉底往事錄》卷三中蘇格拉底和格勞孔的對話對本篇的模仿等,來證明它的真實性。在對話内容的讨論中,他與施萊爾馬赫恰恰相反,認為那一大段讨論斯巴達和波斯的話,不光不是多餘的,反而是全篇的核心,是蘇格拉底能說服阿爾喀比亞德的主要原因。他的這一評論意義重大,大大改變了人們對待本篇的态度,又激發大家重新開始關注它。
近來,福德(Steven Forde)進一步從女性問題入手,來解釋福裡德蘭德認作全篇核心的,那一大段讨論斯巴達和波斯的話,用以精确定位女性在教育中的角色。 同樣也是針對這段話,盧茲(Mark Lutz)則從文化相對主義、民主政體等角度,了解蘇格拉底這篇對話,在其作為整體的教育中的突出地位,以及對現代的啟示。
讨論本篇真僞問題最全面的,是最近的普拉多編輯并加了導言和簡要注釋的《阿爾克比亞德篇》 和戴納(Nicholas Denyer)的詳細箋注本, 他們從多方面有力地證明了本篇是柏拉圖本人的作品,或判定其為僞作證據不足。
其實自福裡德蘭德以來,人們越來越不重視本篇的真僞問題,因為大家不再像一百年前施萊爾馬赫和柏林曆史學派影響下的學界那樣,以嚴格差別個體所屬作品來定位作為個體的哲學家的觀點,比如現在所謂的“蘇格拉底問題” 已經從偏重材料的讨論,過度到偏重哲學的探讨,哪些究竟是柏拉圖的真作,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作品的價值正在脫離“曆史檔案”的束縛而被重新考量,當然本篇對于我們的價值,也就不會因為這些在一定哲學構想前提下産生的真僞的辨識而有絲毫影響。
當我們從這些看似外在的争論中平靜下來時,不妨不懷偏見地了解一下這樣幾個問題:本篇主角阿爾喀比亞德到底是什麼人?他和蘇格拉底有什麼關系?本篇内容如何?從中又可以看出那些有意義的争論?
微信公衆号
江安柏拉圖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