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作者:張桃洲(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壯族詩人韋其麟是一個獨特而值得持續關注的存在。事實上,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至今,除特殊年代中斷十多年外,研究界一直保持着對韋其麟研讨的熱情,已有上百篇不同類型的論文闡述他,40餘種當代詩歌史、文學史著作也辟專門章節評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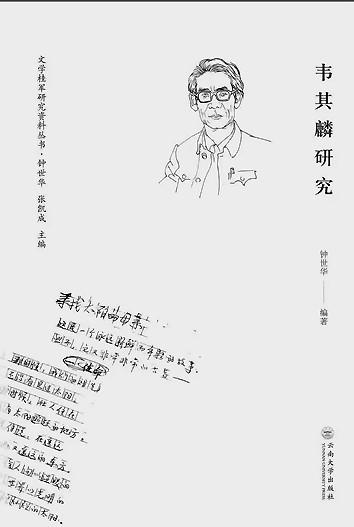
《韋其麟研究》鐘世華編著雲南大學出版社
一
曆史地來看,韋其麟構成了一種可予探讨的詩歌現象。這位早慧的詩人,1953年還是高中生的他就在《新觀察》上發表長詩《玫瑰花的故事》,從此步入缪斯的殿堂,多年來筆耕不辍,先後出版了各類作品集十餘部。他的詩歌最廣為人知的無疑是《百鳥衣》,這既是他的成名作,又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這部長篇叙事詩取材自壯族民間傳說,以動人的筆觸演繹了一對壯族青年男女的愛情和抗争的故事,詩中的主題、人物形象及語言、手法都有着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該詩最初發表于《長江文藝》1955年6月号,後轉載于《人民文學》1955年7月号,1956年4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各種版本累計發行逾100萬冊。該詩發表後不久,即有多篇關于它的專論在《文藝報》等刊物上登載,随後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編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科學出版社1962年9月出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作家出版社1963年11月出版)将《百鳥衣》寫入了當代文學史。此外,《百鳥衣》還被翻譯為近十種文字在國外出版。可以說,《百鳥衣》已經成為中國當代詩歌特别是長詩中的一部經典,正是它确立了韋其麟的詩歌史地位。
正如評論家張燕玲指出:“韋其麟……60年來一直以其高潔的為人和爛漫的詩意成為廣西文學的一個精神高度。”韋其麟作為一種詩歌現象所帶來的最重要啟示,就在于他通過富有創造性的寫作,展示了當代詩歌與民族文化、民間資源之間的緊密聯系,比如《百鳥衣》就蘊含了極為豐富的民族文化元素,他的其他詩作如《鳳凰歌》《莫戈之死》同樣如此。由此引發的諸多議題,如當代詩歌的民族性與民間性,少數民族詩歌在當代詩歌中的位置,以及韋其麟本人之于當下壯族乃至廣西詩歌的意義等,亟須進行資料和學術上的總結與探究。而剛剛出版的鐘世華先生編選的《文學桂軍研究資料叢書·韋其麟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可謂正當其時,恰好滿足了上述期待。
這部洋洋40餘萬字的研究論集,包含《韋其麟小傳》《研究綜述》《訪談·自述·印象》《評論文章選輯》《附錄》等部分,綜合、立體地展現了韋其麟60餘年的人生軌迹、創作曆程及其與當代詩歌和其他少數民族詩歌的互動關系,以及圍繞這些相關議題展開研究的總體格局和代表性成果。倘若說,韋其麟的親曆者角色和持久創作,讓他和其詩歌在很大程度上參與并見證了當代少數民族的發展曆史,能夠彰顯當代少數民族詩歌的某些特征,那麼這部論集就是對這些特征的全面把握和集中呈現,兼具文獻價值和研究價值,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
在收錄的韋其麟自述文字中,有不少珍貴的個人記憶和值得重視的創作經驗,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他的民族身份認同和以“民族特色”為切入點談論詩歌創作的取向。他主張“從民歌的土壤中吸取營養”,是因為“在民歌裡,那大膽的帶有浪漫色彩的誇張,和那豐富的比喻、起興、重複,是那樣形象、精确、具體、生動和恰到好處,給人的印象是那樣強烈、新鮮、明朗。那重疊的章句在反複吟誦時那樣深深地引起人們内心的共鳴”;但他反對在尋求民族特色時的某些偏頗做法,即“以一種獵奇的心理和态度專門注意那些奇風異俗,或在服裝衣飾上着眼”。這就顯示了一種辯證思維和更開闊的視野。
論集所收錄的代表性論文提供了多種探入韋其麟詩歌的角度和方法,也展現了60餘年韋其麟研究的更疊與創新,從早年的主題學和階級分析,到近年來的民俗學、神話學、修辭學、“原型批評”等,使得韋其麟研究漸趨多樣化。當然,研究者最為關注的還是韋其麟詩歌對民族文化的創造性運用和拓展,比如方焓的《叙事長詩〈百鳥衣〉的美學探微》一文認為,《百鳥衣》的獨特意義在于“在表現民族風情、民族精神、倫理教化中注入生命氣象”;莫奇的《重讀〈百鳥衣〉》一文注意到了韋其麟詩歌基于民族文化元素的音樂美學:“似乎不是一幅幅迷人的勞動場景在我們眼前交替,而是一曲曲動人的勞動歌聲在我們心際回蕩。這些重疊、反複的詩句适如琴弦上回旋的樂曲,一陣陣加劇了我們為之激動的心情。”這些都是閃爍着真知灼見的論述。編選者鐘世華本人這幾年緻力于韋其麟研究,先後發表了《壯族身份認同中的民族尋根與文化守護》《〈百鳥衣〉的經典建構與影響焦慮》等論文,探讨韋其麟詩歌的“民族氣質的尋根”“地域文化的守護”與“民族形式的創新”,他還完成了《韋其麟年譜長編》初稿。他耗費巨大心力編選的這部論集,想必會得到研究界的認可。
程光炜的《中國當代詩歌史》提到,在20世紀50年代,一批少數民族詩人以“群體”姿态引起矚目,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當時與韋其麟一道亮相詩壇的,有巴·布林貝赫(蒙古族)、鐵衣甫江(維吾爾族)、饒階巴桑(藏族)、汪承棟(土家族)、包玉堂(仫佬族)等詩人;他們創作的《百鳥衣》《生命的禮花》《雪蓮花》《虹》等長詩,以少數民族叙事長詩的絢爛光譜,構築了當代詩歌史上長詩創作的奇特景觀。這些詩人和作品無疑是民族詩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共同鋪就了優秀民族文化傳統得以留存、延續和發揚的路徑:将民族文化轉化為詩歌創作的動力和資源,這些經典性作品在傳承民族文化的同時,也豐富了民族語言表達。期待這一領域湧現出更多像《韋其麟研究》這樣進行系統探究的著作。
《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05日07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