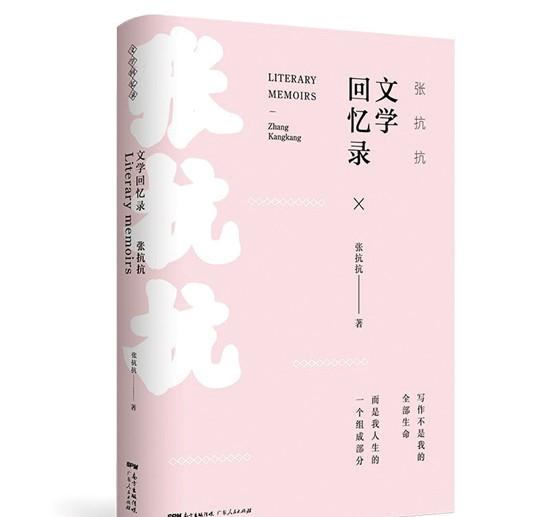
4月25日,“一席美談——《張抗抗文學回憶錄》新書分享會”在廣州圖書館舉行。
“大家好!我系廣東人!”分享會一開始,作家張抗抗就用粵語熱情地和大家打招呼,一下子就拉近了和大家的距離,現場掌聲笑聲響成一片。接下來,張抗抗和大家交流了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文學、網絡文學、全民閱讀等問題的看法。有讀者當場表示,想成為張抗抗這樣的人,張抗抗聽到後馬上說:“你不要成為我,要成為你自己啊!”
《張抗抗文學回憶錄》收錄張抗抗有關文學創作的回憶與反思,以及在文學創作道路上對人生、社會和曆史等問題的思考。張抗抗說,這本回憶錄是個人與文學關系的一次回顧。
張抗抗
1950年出生于杭州,祖籍廣東新會,從事專業文學創作40年。已發表小說、散文共計800餘萬字,出版各類文學專著近百種。代表作:長篇小說《隐形伴侶》《赤彤丹朱》《情愛畫廊》《作女》《張抗抗自選集》5卷等。曾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等。有多部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曆任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九屆、十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2009年被聘為國務院參事。
訪談
從文學的角度記錄改革開放40年
羊城晚報:這次出版的《文學回憶錄》有什麼特點?
張抗抗:這本書是對我大半生文學創作的概括和記錄。之前我的作品大部分是小說、散文随筆,但這本書是我在幾十年的文學道路上寫下的對文學觀的記錄,記錄了我的文學成長道路;還有大量的訪談,這是當時當地的采訪,是以是真實的,有當時的痕迹在裡邊。對于文學史來說有一定價值,是研究作家的寶貴資料。這本回憶錄裡的文章,最早的寫于上世紀70年代末,最晚的文章截至2018年,剛好是改革開放這40年的記錄,這些文章,可以說是從文學的角度記錄了改革開放的社會熱點、思潮和重要社會變化。比如裡面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深圳文稿競價活動,當時記者采訪,我就記錄了當時的想法。如果當時沒有記錄下來,現在問我,我肯定就不記得了。是以,廣東人民出版社的策劃,是有創新性的,和常見的文學回憶錄都不一樣。
羊城晚報:在您現在看來,最喜歡的,或者說最重要的作品是哪一部?
張抗抗:早期的作品裡,我最喜歡《北極光》。那是一種心懷希望的寫作,充滿着一種青春的感受。它就像北極光,可能自己一生都未必能遇上,但它是存在的。這也是在1980年給我留下的一個真實感覺。後來的作品我會比較在意1996年的《赤彤丹朱》。在裡面我寫了我的家庭、我的父母,通過寫作重新認識了父輩的曆史。
回頭看過去有争議的作品,更加心平氣和
羊城晚報:您的一些作品引起過比較大的争議,比如說《情愛畫廊》,現在回過頭看,您有怎樣的感受?
張抗抗:有争議其實是很正常的。如果我們出來的作品,大家都叫好,那麼我覺得寫作的意義就沒有超過當時的時代。有些寫作可能是超前的,也可能表現得比較偏。我覺得我當時也不是特别在意,最多就是安慰自己說,你看那麼多人反對我吧,可見我的作品多重要。其實作在回頭看,可能更加心平氣和。
有時候,我們也要換位思考。當時他們這麼想,是有他們的道理的。回想起來,我們在觀念上、文化上,對愛和美的認識是比較缺乏的。這個作品出版已20多年,讀者已換了另一代人,現在20多歲的女孩讀這本書,我覺得可能就能接受了。
羊城晚報:從事創作40年了,每次在寫作前是否會有突破慣性或挑戰自身局限的壓力?是怎麼解決的?
張抗抗:在每一次寫作前,當然都有希望挑戰自身局限、突破自身慣性的願望,每次都想要超越自己,至少不是重複自己以前的作品,對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是這樣的。從構思一個作品開始,就需要反複地去琢磨最适合表現自己作品的方案,這個構思需要是有所創新的,有所突破的,無論是切入的角度,還是表達的内容,都是有新鮮感的。就像掘進的礦井,到達一個新的層面。至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多想、多讀,也會有些試驗性的文稿,有可能一稿寫得不夠好,甯可把它廢棄,推倒重來,但還是不一定能夠把它解決得很好。
“50後”作家介入時代比較深
羊城晚報:您曾被歸入“知青作家”。您認同這個說法嗎?
張抗抗:知青作家,那是我40年前的身份。現在還把我歸入到這裡面,是不對的。包括我在内的知青群體,他們在返城後已經融入各個社會階層中去了。隻能說知青是我們曾經的身份,知青的痕迹或者我們所書寫的知青生活,也已經變得很遙遠了。當然,如果我對知青有新的認識,我也會寫,我在十年前就寫過一個這方面的短篇小說。
羊城晚報:如何評價“50後”作家的特點?
張抗抗:“50後”作家是一個經曆了很多事情的群體,每一個人的經曆都是他們的财富。是以,基本上“50後”作家的寫作都是建立在他們的經曆的基礎上。他們是介入時代比較深的一代人。“50後”作家不像今天的一些年輕網絡作家,可以不顧現實生活,穿越到曆史當中,寫作和現實關系不大密切的東西。但是“50後”作家又通常都帶着這種鮮明的時代特征、年齡特征在寫作。
羊城晚報:今天的作家們大多有着“長篇崇拜”情結,而網絡時代中的讀者閱讀卻越來越追求“短平快”“碎片化”。在這種潮流中,作家應該如何自處?
張抗抗:這個問題很重要。實際上,一方面我們的讀者希望“短平快”,另一方面我們的網絡文學卻越來越長。這裡面有商業原因,這裡就不說了。這個問題對傳統作家而言,調整是會有的,但作家的寫作基本上是從自我出發的,當他形成了一個比較飽滿的東西,他就會動筆寫長篇。如果他有很多小而有意思的故事,他就寫短篇。寫作怎樣的文體,實際上由他們的生活體驗來決定,他們并不會很多地考慮市場。
中國盛産長篇小說,但是中國的人均閱讀量的确偏低。對此我也很困惑,但我并沒打算調整自己。因為我覺得哪個适合我寫,我就寫哪個。我曾經說過一句很不謙虛的話,不是我們跟着市場,而是我們要引領市場,我希望我能引領上。
(朱紹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