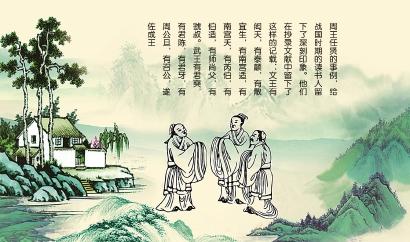
柳友娟 制圖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人們都認為西周社會(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階層固化非常嚴重,很少有社會流動。如許倬雲所言:“春秋以前,中國由封建領主統治着,社會有嚴格的等級分層。”言下之意就是,西周時期鮮有社會流動。然而,從史料記載來看,西周統治者其實有着強烈的尚賢意識,非常重視求賢任賢。 ■王進鋒 總結夏商興亡經驗教訓 西周的尚賢意識,是在總結夏商興亡的經驗教訓中樹立起來的。周王朝建立後,統治者在總結夏商兩族發展的經驗和覆亡教訓時,充分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 梳理史料可以發現,商王朝在曆史上的大發展,與不同時期傑出人物的輔佐是分不開的——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鹹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商湯時,任用“三宅三俊”等人才。是以,商王朝“其在商邑,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然而,到了商代末年,商纣“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與慣用刑罰、行為殘暴的官員,同在國家中;與慣于作惡的官員,共同辦理政治),以緻“智藏瘝在”。于是,“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周文王、周武王時期大發展的先例,也是尚賢的重要依據。周文王時期,“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祯。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意思是說,很多卓越之士出現在周王國内,這些人成為周王國的棟梁,文王依賴他們才使國家得以安甯。 周公進一步指出,“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宮括”的輔佐,才能“德降于國人”;有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宮括“四人昭武王”,才能“鹹劉厥敵”。殷商遺臣箕子也曾向周武王建議,要使“有能有為”之人“羞其行”,這樣自然會“邦其昌”。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周代統治者給自己定下了任賢的要求。他們希望,自己能“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即謹慎自己的德行、提拔國内傑出的人才,以達到完美的執政境界。用周公的話來說就是,希望周王“克用常人”。 “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西周不同曆史階段的統治者,有一系列任賢的實際行動。 周文王時期,為了網羅人才,可以“禮下賢者”,甚至“日中不暇食以待士”。是以,各方賢能之士“多歸之”。同時,周文王和周武王都好用“明德”之人,故“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周王任賢的事例,給戰國時期的讀書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在抄錄文獻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文王有闳夭,有泰颠,有散宜生,有南宮适,有南宮夭,有芮伯,有伯适,有師尚父,有虢叔。武王有君奭,有君陳,有君牙,有周公旦,有召公,遂佐成王。” 周成王時期,将大批殷遺民遷到成周洛邑。周公模仿商初任用夏朝官員的先例,任用了一些殷遺民中的有德之人,甚至“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恐失天下之賢人”。 西周末年的宣王時期,繼續“進用賢良”,任用樊仲山父、尹吉父、程伯林父、虢文公、申伯、韓侯顯父、南仲、方叔、仍叔、邵穆公、張仲“為卿佐”。 選官的任賢傾向,為西周社會流動開啟了視窗。從相關材料來看,西周朝廷确實任用來了一批出身寒微卻富有才華之人。例如,周文王曾經“舉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太公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後被文王“舉而為天子師”。周武王滅商後,不少出身寒微的功臣、謀士得到任用。 另外,鄉、遂裡的賢人也可以通過鄉大夫、遂大夫的考核和推薦來實作向上流動。例如,西周貴族畢公家的家臣獻,因為賢能就被家主推薦到楷國國君處任職。 可見,西周時期并不像一些專家所說的階層固化,而是存在社會流動的。 中低層人士占比逾97% 西周時期存在社會流動,提醒我們去了解和研究當時中低階層人士的狀況。 目前,還沒有見到關于西周時期總人口數量和中下層人士數量的确切記載。然而,傳世文獻記載了西周時期的軍隊建制,其中有全部人員的數量和各階層人員組成情況的大緻記錄。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典型案例裡中低階層人數的比例,來推測整個西周社會中低階層的情況。 西周時期的天子、諸侯可以擁有軍隊。按照級别和大小,他們擁有的軍隊數量是有所不同的。《周禮》雲:“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每個“軍”中士兵和将領,是怎樣設定的呢? 一般認為,每個軍有12500人,設軍帥1人;每個軍轄5個師,每個師2500人,設師帥1人;每個師轄5個旅,每個旅500人,設旅帥1人;每個旅轄5個卒,每個卒100人,設卒長1人;每個卒轄4個兩,每個兩25人,設兩司馬1人;每個兩轄5個伍,每個伍5人,設伍長1人。 另外,每個軍還設定府、史、胥、徒官職。《周禮》記載,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學界認為,這些官員為“非常也,有軍則置之,無則已”。也就是說,這些官員是在戰時配備的,戰争結束就會取消。 以上軍中的各級将領和官員,根據身份和稱謂來區分,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和府、史、胥、徒屬于貴族,兩司馬和伍長為中低層人士。 西周軍隊中的士兵,往往來自社會底層。這從《詩經》中的一些詩篇可以看出。《豳風·東山》是一名跟随周公東征3年的戰士,回到家後所作的詩篇。該文描寫了他在回家途中和回家後看到的景況與心情,其中提到:果臝之實蔓延于屋檐,甲蟲生息于房内,蜘蛛結網于室内,宅邊的空地,變成了野鹿活動的場所。這位士兵出征期間,家裡的情景竟如此凄涼,可見他應當來自社會下層。 事實上,周朝軍隊裡這樣的士兵不在少數。周平王時期,一位女子為懷念在外服兵役的丈夫,作了《君子于役》一詩,收錄在《王風》裡。她哀怨道: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埘,雞窩;桀,雞栖的木架。這位女子在家養雞、羊和牛,應當是個農人。《鹿鳴之什·采薇》是西周時期一位戍邊的士兵在返鄉途中所作的詩,其中感歎:因為征伐猃狁,以緻沒有室家。 西周時期士兵來自社會中低階層,也可從每個軍的建制與社會基層行政機關相對應的情況得到驗證。西周時期,基層行政機關設定狀況為: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闾,使之相受。四闾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赒。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行政機關和對應的家數為:5家一比,25家一闾,100家一族,500家一黨,2500家一州,12500家一鄉。征兵的時候,每家出一人當兵;再按照伍、兩、卒、旅、師、軍來編制入軍,終于達到“伍一比,兩一闾,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由此,西周時期的基層行政機關與軍隊建制就一一對應了起來。 根據以上不同階層人士的資料來計算,在總人數為12500人的軍中,貴族将領和官員有274位,中下層将領和士兵有12226人。可見,中低層人士所占比例為97.808%。這為我們了解西周社會的階層情況提供了參照。考慮到中低階層人士所占比例如此之高,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客觀上也需要為這些人的向上流動提供管道。 (作者機關: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