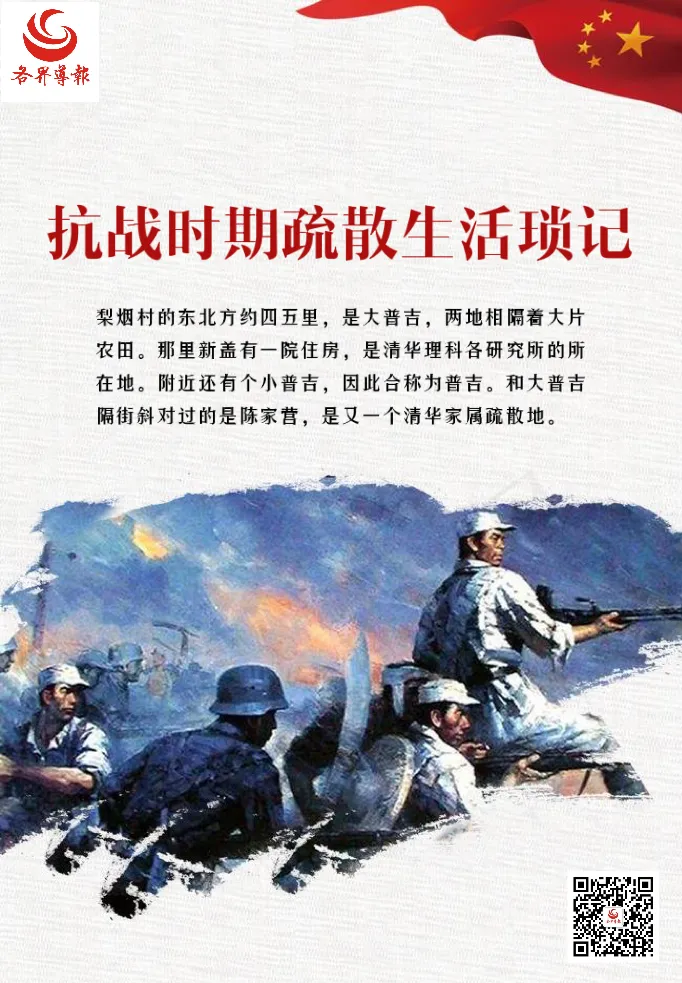
一
一去四五年
1939年初,先行遷校到昆的父親,結束了手頭的工作,來到香港,把母親和我、妹妹、弟弟接到昆明。那時西南聯大連校舍都還困難,哪顧得上安排教職員宿舍,各家各戶隻好自己去租民房住。我們家圍繞着清華辦事處這個中心,最初住在才盛巷,後來住過錢局街、文林街、青雲路。兩年不到的時間裡,搬過四次家,我也随之上過三所學校。1940年冬,大西門一帶遭到日機轟炸,我們家受到嚴重破壞。于是按照學校當局的疏散安排,我們随同其他清華家屬,疏散到了離城二十裡外的昆明西北郊的梨煙村。
梨煙村的東北方約四五裡,是大普吉,兩地相隔着大片農田。那裡新蓋有一院住房,是清華理科各研究所的所在地。附近還有個小普吉,是以合稱為普吉。和大普吉隔街斜對過的是陳家營,是又一個清華家屬疏散地。
唐紹明
從大普吉向南行,有一條河堤,堤上有路可以行小汽車,是大普吉通往昆明市内的唯一通道。約行四五裡,正好和一條從梨煙村出來向東行約三四裡的小路相遇,構成一個居民點,叫大河埂。潘光旦先生和趙世昌先生兩家住在這裡。就這樣,以大普吉(包括陳家營)為工作兼居住的主體,形成一個“大普吉——梨煙村——大河埂”方園不到十裡的三角地帶,聚集了一大部厘清華教職員及其家屬,是一個凝聚着豐富的知識财富和精英的地區,那麼熠熠生輝,成為我心中難忘的“金三角”。
這批師長當中,研究人員一般去大普吉上班,教學人員到城裡西南聯大上課,職員則分别在城裡西倉坡和大普吉兩地上班都有。他們在艱苦條件下,堅持抗戰,堅持教學和科研,為國家培養和儲備了大批優秀人才,為發展我國科教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無怪乎當年李約瑟博士參觀大普吉後,把它稱譽之為“中國科學家的搖籃”,我有緣在這戰時清華的大學營裡生活了四五年。
二
衣食住行難
梨煙村坐落在玉案山腳下,坐西朝東,村後大山橫亘。全村南北展延約三、四裡,一條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兩旁散落着農家住戶,樹叢、池塘和打谷場點綴其間。據說過去村裡梨樹很多,有“梨園”之稱。在雲南話裡“園”和“煙”相諧,是以通常在文字上把這個村子寫成“梨煙村”,後來正式定名為“龍院村”。村民們對待疏散來這裡的清華家屬很友好,兩位士紳特地騰出私宅供清華家屬居住。當時那疏散情景,在馬文珍先生的詩中曾有過記述:“收拾衣裳又遠行,父老媪妪笑相迎。門前一片梨花樹,座座青山似畫屏。”
我們的住所在村子的盡北頭,是當地一位姓李的士紳的一座新院子,通稱“李家院子”,和他家的老院子相毗鄰,掩映在樹叢中。這位士紳當過廣東軍政府的司長,人們還用老稱号稱他“李司長”。
戰時昆明的生活本來就很簡樸,鄉村生活更是簡陋了。對住慣城市生活的人來說,最感不便的是沒有電燈,連煤油燈也沒有,隻好自己弄個碟子,盛上菜油,用燈心草芯浸油,然後點著燈芯照明。這燈心草遍地皆是,把它采集回來就成了我們孩子們的任務了。把燈心草的杆皮剝去,抽出杆心,就制成燈芯。至于用水,要到門外不遠一個菜園子的水井那裡去打。後來大家合夥雇了一個青工,每天給各家挑一擔水;如果不夠用,就得自己去打了。我常常在下午和母親兩人擡着一個鐵皮桶把水打回來備用。沒有廚房,各家就截出門前一段走廊,安上一個泥爐,點木炭,燒水做飯。糧食和蔬菜等物,到“街子”(集市)去買或拿東西去換。
那時,生活很清苦,基本上吃不上肉。記得父親每隔一段時間,會把我、妹妹和弟弟拉到身邊,輪個地看我們的臉色,然後連連搖頭說“面有菜色,面有菜色”,于是讓母親買點肉,第二天餐桌上才能出現點肉絲。大家總是特别地高興,盼着下一次。至于衣著,隻能翻箱底,大人穿舊了的給小孩穿,大的穿不下了改一改給小的穿。
住的樓房品質很差。牆壁單薄,上端打通,誰家說話聲音稍大,能傳到左鄰右舍。腳步重了,樓闆都在晃動。有一回,我們吃完午飯,打算掃一掃掉在地下的飯粒、菜屑,誰料驚動了樓下正在吃飯的梅家。他家三女兒在院子裡向樓上喊話:“請等會兒再掃,我們在吃飯哪!”原來樓闆有縫,樓上掃地正好給樓下餐桌撒上“胡椒面”了。
我這時在城裡上中學,寄宿在府甬道清華職員單身宿舍裡,每星期六下午回梨煙村,次日下午返城,來回靠步行。開始有父親陪我走,後來有史蓁先生的兒子史濤和我作伴,再往後就是我一人獨行了。父親不放心,委托工友老張每次安排我上路。有一回,出校門時已晚,老張勸我明天早上再回,可我歸心似箭,執意要走。過了黃土坡,來到向西拐彎的地方,隻見太陽快下山了,大地忽然暗了下來,路上沒有行人,心裡緊張,拼命趕路。眼看快到離村還有三四裡的大石橋時,聽見後面響起“唰!唰!唰!”腳步聲,有一群人追了上來,吓得我趕緊往路邊躲,恨不得鑽進黑黢黢的農田裡。猛地聽到一聲吼:“娃子,哪裡去?咋一個人走!”我趕忙回答說:“回家去,村子裡的。”幸好他們并不理會我,一陣風似地從我身邊掃過。我這才松了口氣,趕緊連跑帶奔地跟着他們,走完了這最後一段回家的路程。撲到家門時,“媽,我回來了!”連喊帶哭地朝門闆一陣猛敲,滿身的疲累、驚恐和欣喜都在這一刻裡傾洩了出來。
就這樣,這條路啊,我走啊走,足足走了四、五年,由10歲走到15歲。那唯一的交通工具——馬車,我從來沒有沾過。口袋裡那點零用錢,我也舍不得花。從那時起,我習慣了用自己的腳闆,走出自己的世界。
三
友情暖心田
和村西北的李家院子相對,在村子的中部偏東處,有一座惠家大院。惠家大院比李家院子大,主人姓惠,也是當地一位士紳,曾經當過學校校長,被人尊為“惠校長”。他把前面的老院子騰給清華人住,自己則搬進建立的後院去住。老院子的東面,即靠外面一邊,有一座馬蹄形的二層木結構樓房,南北長,東西兩邊稍短。據我片斷的記憶,吳有訓、任之恭、趙忠堯、楊武之、趙訪熊、吳達元、楊業治等教授住在這裡,餘瑞璜教授住在院子外另一處。梅校長家後來也搬進大院,住在幾間臨時修建的房子裡。
住在這裡的師長們大都在大普吉上班。他們的孩子有的還小,不到上中學的年齡。于是大家商定,在大普吉為這些孩子辦了一所臨時國小,請來兩位女老師,由我父親負責行政管理,我的妹妹和弟弟就在那裡上學。孩子們和大人一樣,每天步行于梨煙村——大河埂——大普吉之間。一天,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任之恭先生在從大普吉下班回家的河堤路上,被兩個歹徒攔住,搶走了身上唯一值錢的一塊懷表,幸好人還平安。這個事件,一度弄得大人和小孩惶惶不安。
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陳岱孫、梅贻琦、吳有訓、馮友蘭、葉企孫
惠、李兩院相距不遠,我常在下午三四點時到惠家大院找夥伴玩,一個夥伴是楊武之先生的三兒子楊振漢。他年齡比我小,但彼此談得來,談的話題多是清華園的舊事和南下避難的遭遇。有一次他對我說:“你見過駱駝嗎?”他說他在北平西直門見過駱駝。“好家夥!坐下來有這麼高。”這時他把身子蹲下,比着手勢;“站起來有這麼高。”這時他把身子挺起來,手勢也随之由低到高,直到踮起腳尖,把右手伸得老高老高,“有城牆那麼高!”還學着駱駝邁了幾步。他那生動的描述,使我相信駱駝的确了不起,這印象一直留在腦子裡。
還有一個夥伴,是吳有訓先生的兒子吳惕生,他告訴我他是1931年出生的。那一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他父親給他取名“惕生”,以示時刻警惕日本帝國主義亡我中華的野心。我喜歡聽他轉述他父親的巴黎見聞,那雄偉的凱旋門和華麗的香舍麗榭大街,令我神馳。有一次,我向他介紹魯迅的故事新編的《理水》,對文中諷刺拄拐杖的學者和說話口吃的學者感到不解。我們揣摩,這是對當時一部分留學生脫離人民大衆的批評。我們回顧眼下許多留洋學者,抗戰爆發後颠沛流離,輾轉昆明,特别是今天又來到鄉下生活,變化多大呀!吳惕生說:“這算是走出‘象牙之塔’,來到大衆中間吧?”那雙聰慧的眼睛,在銀邊眼鏡圓鏡片後閃爍。
在大普吉旁的陳家營,散居有黃子卿、聞一多、餘冠英、華羅庚等教授家,可能還有其他一些人家。黃子卿先生的兒子黃志淵,也是我常去找的夥伴。他家藏書很多,通俗演義不少。我曾向他借過一套演義中的三本,不料還未看完,其中一本被我那時寄宿的親戚家的一個朋友拿去看了,後來沒有還我,人也找不着了,我無法向黃志淵交待。後來我借給了他三本書去看,算作補償吧。當然,套書最怕缺冊,這樣的遺憾是無法用其它辦法補償的。
鄉間生活住久了,大人之間的交往也頻繁起來。住在同院裡的各家天天見面,過從甚密,自不待言。隔院的人,也常互相串門。比如,住在惠家大院的吳達元、餘瑞璜太太,時不時會過來看望我母親;因為都是廣東鄉裡,開口就講廣東話,往往人未到,聲先行,十分親切。餘太太看見我床上放有一本《隋唐演義》,就借回去看,沒過幾天就還書來了,說好看,問還有沒有下冊?可惜這本書我不記得是怎麼得到的了,當時就隻有上冊沒有下冊,我沒法幫她再找到下冊,對此我一直感到遺憾。
那時各家還經常做點小吃之類,互相贈送、品嘗。抗戰後期,父親經潘光旦先生介紹,在昆明圖書館兼了一份差,每月可以得到幾鬥米,生活條件有了改善。母親常拿米磨成米面,做廣東糕點送人,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蘿蔔糕”,聞起來怪怪的,吃起來很香。潘光旦太太對人和善,樣樣為人設想,常從大河埂到梨煙村來串門,每次都帶來一些江南小吃。任之恭太太和我母親也常來往。1945年我們家先搬回城,任太太特地送來一籠屜熱氣騰騰的包子,為我們送行。
難忘一次大河埂聚會。主人是潘光旦太太,專門邀請李家院子全體家屬,包括大人和孩子,去她家作客。那是一個獨院,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坐北朝南,院子北邊是一座二層木樓,他們住在樓上,前面是院子。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擠滿了人,小孩子更是鬧成一團。潘太太準備了各種菜肴,大家自己動手做着吃。我還是頭一次看到面筋是怎樣從面粉中做出來的,感到新鮮和好奇。潘太太還事先向門前田主買下田裡一茬蠶豆,這時發給每個小孩一個籃筐,領着大家到田裡摘蠶豆。我們專撿嫩的摘,不管是生吃還是做菜,都特别香。這種抗戰“牙祭”,既飽了大家的口福,還增進了彼此的友誼。這是同甘苦、共患難的友誼,是平等的真情,是戰時艱苦環境的産物,這無論在戰前或戰後都是不多見的。
四
求師思奮進
大普吉清華研究所的大院裡,住有湯佩松、戴芳瀾、孟昭英、葉楷等教授和一批年輕的研究人員、職員。進入大門向右拐,緊貼院牆的一排房子,就是戰時的清華圖書館了。館長是潘光旦先生,父親和馬文珍先生是具體負責人,好象還有一位尹先生及其他人。說它是圖書館,其實就是一間沒有割段的大房子罷了。裡面約占總體4/5的空間是書架,擺滿書刊;旁邊過道放兩張大辦公桌,父親和馬先生各用一張。進門處約占總體1/5的空間是閱報處,中間擺了一張長條茶幾,四周圍了一圈沙發,這裡也可當作休息室用,經常有許多研究人員來看報、喝茶、聊天。他們關心時事,時而高談戰局,時而闊論形勢。除這間大房子外,還有幾間工作室。大房子正對門有一單間,裡面堆滿了舊雜志和國外書刊廣告,我曾經有好幾次鑽進去翻看國外舊畫報。
記得我第一次來到這圖書館時,面對如此豐富的書刊資料,眼花十分缭亂。有一次我在父親辦公桌旁的書架上随手抽出一本硬殼書,是洪深寫的劇本《五魁橋》。這是我第一次看劇本,對裡面的對話體覺得新鮮。記得劇中講農民受壓迫起而反抗的事,我心想這是不是就是常聽說的“普羅文學”?還有一次,隻有我一人在閱報處茶幾旁翻看雜志,發現一本雜志裡夾着一個沒有封皮的小冊子,标題是《評“中國之命運”》,還有一本雜志裡夾着小冊子《新民主主義論》,後來知道前者是陳伯達著,後者是毛澤東著。
20世紀30年代的清華大學圖書館
我每次從大普吉圖書館出來,總喜歡抄近路,穿過陳家營,沿鄉間小道回梨煙村。是以常常會碰上住在這裡的教授們,慢慢地也就和他們認識了。有一次我從城裡往回走,聽見後面有汽車開來,就本能地往路邊閃開。車子突然在我身邊停下,有人從車窗探出頭來,原來是華羅庚先生。沒想到他沖着我說:“你是唐先生的小孩嗎?住在哪兒?要不要送你一段?”我說是,告訴他住在梨煙村,他說:“好,可以在大石橋把你放下。”于是招呼我上了車。那時華先生剛從英國回來,舉世揚名。我下車後,看着汽車調頭向北開去,心中充滿感激之情,默念着他是那麼出奇的平易和親切。
又一次,穿過陳家營回家時,太陽已經西斜,看見聞一多先生在田埂上散步。他身穿長褂,面蓄美須,背後襯托着夕陽的霞光,緩步走來。聞先生那時除在大學教書和做研究外,還常到中學去開展學生輔導活動。我參加過他和光未然同志到我們中學開的詩歌朗誦會。光未然同志朗誦《阿細的先雞》。聞先生朗誦艾青和田間的詩,熱情地贊頌詩歌的人民性、戰鬥性,表明自己要和人民一起戰鬥的決心。
我還有機會一覽潘光旦先生的書房,在大河埂他家的二樓上。坐北朝南,北邊牆上開了一個大敞窗,可以展望遠山景色:一側是螺峰山,因山上石頭多呈田螺狀而得名;一側是鐵峰庵,是一處建有廟觀的名勝地。這也許就是潘先生為書房起名“鐵螺山房”的由來吧?看到潘先生的書桌、書架、書籍和馬燈,不由得想起他那時發表的許多文章和詩抄,那些具有影響的民主政論,都是在這裡辛勤筆耕出來的,不禁使我想到他那博學多才的學問家的睿智,想象着他沉思凝想做學問的樣子,心中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
在枯寂的鄉居生活中,我記得看過一場電影。一天晚上,在梨煙村北頭一塊打谷場上,扯起一塊螢幕,放映從大普吉借來的一些科普資料片,各家大人小孩自帶小闆凳前來觀看。一放映,傻了眼,是英文片,看不懂也聽不懂。于是有人提議:何不把楊家老大找來給大家翻譯?不一會兒,楊振甯出現在螢幕旁。他身穿淺綠色美軍夾克,雙手插在夾克兜裡,邊看邊翻,簡單明了,輕快自如,到關鍵地方還作點解釋。講到水有軟水、硬水之分,硬水因含礦物質,肥皂不容易溶解,需加熱後變成軟水,才可用于洗衣服。坐在我前面的楊武之太太聽後,環顧左右說:“對啦!以後用井水洗衣服,得先熱一熱再用肥皂搓啊!”
1944年過去了,戰局有了扭轉。疏散人口逐漸返城,有的離開昆明,有的繞道印度出國遠行。梨煙村已風光不再,住戶越來越少了。李家院子先是史蓁先生走了,繼而搬進了赫崇本先生,他後來也走了。沈履先生在樓下住了幾年,後來搬走了;樓上姚均先生一家接着搬進了城。這時,隻剩下樓下的朱蔭章先生一家和樓上我們家還住着,原本不大的院子頓時顯得冷清、空蕩。1945年中,我家也搬進城;三個月後朱家也搬進了城,清華人和李家院子的一段抗戰情緣就此結束。
來源:各界雜志2021年第3期
作者:唐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