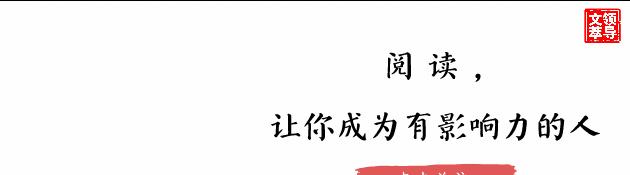
古代官場暗流湧動、風雲多變,稍有不慎,輕則罰俸摘官去爵,重則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元朝政壇有着封建官場的一貫風貌,明争暗鬥層出不窮,也有着自身特色,所謂“鈎考”即是其中之一。在元朝,特别是元初的官場中,“鈎考”可是個要人命的詞兒。蒙漢色目官員,可謂是“畏鈎如虎,人人談鈎色變”。
所謂鈎考,又稱理算,意即現在所謂的審計制度,依據鈎考的結果,可以當即問責處罰官員。審計巡察中國自古就有,所謂“上計”“勾複”“磨勘”等。但元朝的鈎考理算,結合了蒙古從波斯學來的“忽爾紮”(特别法庭)制度,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展現着其背後錯綜複雜的政治路線鬥争,規模和殘酷程度可謂空前。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與忽必烈有關的兩次大鈎考</h1>
元朝最早的鈎考可能是在元憲宗四年(1254)春天,蒙哥汗派遣耶律鑄、帖木而忽秃赤到燕地區核算錢糧,七月又“诏官吏之赴朝理算錢谷”。這些鈎考理算規模小,還未掀起大浪,真正有元朝特色的大鈎考,還是發生在憲宗七年(1257)的阿藍答兒鈎考。
阿藍答兒鈎考的緣起本身就有着複雜的政治背景。其時,元憲宗蒙哥作為蒙古大汗,坐鎮漠北和林,以大半個歐亞大陸主人的身份,統領大蒙古帝國全局。他委任他弟弟忽必烈,也就是後來的元世祖,總領漠南漢地事務,同時負責對南宋作戰。
忽必烈為統治好中原漢族地區,重用漢人,身邊圍繞着窦默、姚樞、劉秉忠、郝經等漢族大臣,以漢法治漢地,恢複經戰火洗劫的中原經濟。此外,忽必烈在軍事上也立下赫赫戰功。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忽必烈的所作所為遭到了嫉恨,有人便向蒙哥檢舉忽必烈,說他“王府諸臣擅權為專利事”。蒙哥是個專斷的人,他也擔心忽必烈功高震主,威脅到他的位置。于是便對忽必烈安排了一次鈎考。
此次鈎考,由丞相阿藍答兒、參知政事劉太平主持,設立“鈎考局”,鈎考對象為忽必烈主管的陝西宣撫司、河南經略司等。鈎考目的是清查忽必烈王府擅自截留征收的錢糧稅賦,并強制其立即清還。
此次鈎考相當嚴苛,執法也十分嚴酷。“虐焰熏天,多人迫與死”,忽必烈手下大量親信官員,廉希憲、趙良弼等都被鈎考局拿下,不少人被嚴刑拷打,死在獄中。忽必烈為避災禍,聽從謀士姚樞的建議,交出權力,親奔漠北向蒙哥謝罪,事情才由此作罷。
忽必烈用切身經曆,體會到了鈎考的厲害。在他上台以後,就把鈎考作為一項好用的政治工具,使用十分頻繁。
鈎考是對官員的考核懲辦,自然會成為官場鬥争中整治政敵、打擊異己的絕佳武器。就拿至元十七年(1280)阿合馬鈎考江淮行省一事來說。中書省平章政事阿合馬與江淮行省平章阿裡伯、江淮行省右丞崔斌不和,就想着鈎考江淮行省,把這兩個人搞掉。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鈎考局查出阿裡伯“擅支糧四十七萬石”,應追還寶鈔一萬二千錠,涉及金額特别巨大、情節特别嚴重、性質十分惡劣。阿裡伯和崔斌被以“欺盜官糧”之罪處斬。
但風水輪流轉,阿合馬掌權時得罪了太多人,最後被“義士”刺殺。他死後,他的爪牙親信也都被鈎考了一回。至元十九年(1282),浙西宣慰使遊顯又鈎考了江淮行省,查出贓款合計四百餘萬。江淮行省原先依靠阿合馬得勢上台的黨羽們這可真倒了血黴,罷官的罷官、下獄的下獄。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3">“打鐵自身不硬”的鈎考</h1>
簡言之,鈎考是元朝蒙漢雜糅的政治制度展現,也折射出元朝漢法和蒙古法兩條發展道路之間的沖突。
遊牧民族落後的劫掠習俗,導緻了元朝财政的超限支用。頻繁鈎考意義在于追征稅款,是確定财源的重要手段。
遊牧民族長期以來通過劫掠手段擷取财富,領主也通過分封土地、賞賜珍寶手段籠絡下級。這種習俗在元朝國家财政方面得到了延伸滲透。元朝政府無視經濟發展的正常需要,竭力搜刮地方财富,以供皇室消費,或用于賞賜功臣貴族。毫無節制、濫行支用的開支,導緻了财政上的巨大壓力。至元二十六年(1289)一年财政赤字就達到白銀一百萬錠。故此,元朝廷任用商人出身的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理财名臣”,通過加稅、增發貨币、撲買包稅等手段擷取掠奪民間财富。
鈎考則是對這種“劫财”手段的補充保證,查一查該征的稅是不是都收齊了,稅是進了國庫,還是被下面的貪官污吏吃掉了。
頻繁鈎考也是提高中央集權、限制地方權力的手段。蒙古的傳統是實行分封制度,把地封給下屬,能按期上貢就行。但随着蒙古政權接手對農耕地區的統治,為适應新形勢,便推行“漢法”,設立郡縣,建立中央集權制政府。
對地方行省、府路州縣進行鈎考,正是朝廷強化集權、控制地方官員的良策。欽差大臣定期不定期地來檢查工作、審你的賬、治你的罪,讓你整日擔驚受怕,隻得對上面唯唯諾諾、俯首聽命。
由于鈎考的主要目的在于為統治者斂财,鈎考局的官員很多“打鐵自身不硬”,說是來整饬腐敗,自己卻腐敗得要死,借機來吃拿卡要。這導緻了鈎考局所到之處民怨沸騰。宋元之際的文人鄭思肖通過漁夫鸬鹚捕魚的比喻,揭露鈎考強制追征稅款,對百姓的壓榨盤剝:“鸬鹚得魚滿颔,即為人所抖取;鸬鹚更取魚,人又抖取;勞無窮,利甚鮮。”
對鈎考不堪其苦的還有各級地方官員,特别是漢族士大夫們,他們一向對鈎考持反對态度。反對鈎考的奏疏不斷,說鈎考“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财”,“剝害生民”,“大家巨室無悉破壞,甚至逼女為娼”。他們說鈎考淩虐百姓,自己為民請命,請廢鈎考,但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利益。
鈎考在朝野上下得罪人太多,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主持多次鈎考的權相桑哥倒台後,全國上下廢除鈎考呼聲高漲。十月,禦史中丞玉昔帖木兒上奏:“鈎考錢谷,自中統初至今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餘黨公取回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忽必烈出于安定統治集團人心的考慮,便順水推舟下诏,罷鈎考錢谷,“诏下之日,百姓相慶”,大呼皇恩浩蕩。
之後,忽必烈還處死了“迫殺吏民”的納速剌丁滅裡、忻都、王巨濟3名鈎考官,“以謝天下”。元初轟轟烈烈的大鈎考運動就此收場了。
摘自 |《上司文萃》2021年10月下
稿件來源 | 《廉政瞭望》
本文作者 | 大獅子
責任編輯 | 蕪影
微信編輯 | 又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