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一、“發動戰争的責任”還是“戰争失敗的責任”</h1>
1945年9月5日,在戰後召集的日本國會會議上,後來成為首相的議員蘆田均提出了《追究導緻大東亞戰争不利的結局的原因及責任》的意見書。他認為,戰争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官僚統治的失敗”。就是說,由于“官僚極端的利己和腐敗導緻了官民的對立”,言論的控制“封住了對國家忠心耿耿的人們的言路”,是以“國民對國家的一切都漠不關心”,進而使政府陷入孤立。他認為,由于這場戰争是舉全日本的國力進行的“總力戰”,是以為取得勝利,“必須讓每個國民都認識到戰争的責任。而如果隻有政府和軍部有責任意識的話,隻能是失敗的結果”。蘆田均的主張反映了一部分不贊成政府與軍部在戰争中決策的人們的想法。循着這一思路,12月,議員鸠山一郎提出了《關于議員的戰争責任的決議案》,議員一宮房治郎也提出了《關于戰争責任的決議案》,等等。
這些追究戰争責任的議案,被認為是從日本内部開始的對“官僚”、“軍閥”、曆任總理大臣及這些人的“追随迎合者”的戰争責任的追究。不難看出,這種追究是站在“總力戰”的立場上,追究的是導緻戰争失敗的責任,而不是發動侵略戰争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追究是否定戰争指導者在技術層面的責任,而并不否定他們發動戰争的動機。那麼,如果日本在那場戰争中取勝的話,是不是就不會有這樣的追究了呢?顯然,這種思維方式與前面所介紹的從外部對日本“反和平”和“反人道”罪行的追究是完全不同的。而循着這種追究的立場,雖然也可能會觸及戰争中日本政治的腐朽性,觸及軍國主義盛行的問題及一些人的法西斯政治傾向,但是與徹底追究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争的責任畢竟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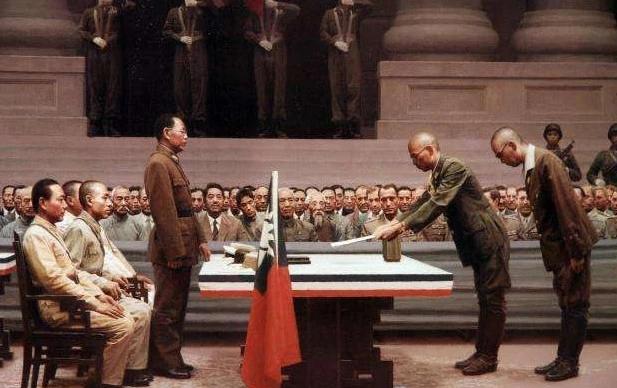
從技術層面來說,也有一部分日本政治家、軍人或主動或被動地承認自己的責任,一些人在戰後選擇自殺、自決,其實也有表示承擔責任的意思。但正如有學者一針見血指出的:“這些人自覺承擔的責任充其量是使日本陷入戰敗境地的責任,而并非發動、推行不義戰争的責任。他們所認識的責任基本上是對天皇的責任,并不是對在自己上司下飽嘗悲慘的、難以言表的痛苦的國民的責任。當然,更不是對在中國、東南亞地區那些被日軍殺戮的1000萬死者的責任。”然而,這些人的做法,居然博得了日本社會上一部分人的認可,甚至認為這些人維護了日本的“自尊”。
從戰敗後日本部分上司人對戰争責任問題的認知上看,他們即使承認戰敗,也不可能承認戰争對其他民族的巨大傷害這一客觀事實;相反,他們一方面要竭力維護所謂大東亞戰争的正當性和對亞洲的所謂解放的意義,一方面還要把日本國民拉入到承擔戰争責任的行列。他們認為:對于日本的戰敗,雖然從法的角度來看,政治家控制的國家應負責,但從道義的角度,國民也應承擔責任。
之是以産生這樣的情況,與提出追究戰争責任的人的身份有很大的關系。在許多國家,戰後追究戰争責任的運動是由在戰争中受到迫害甚至被迫逃亡到外國的政治家或知識分子發動的,被迫害和被迫出國的經曆給了他們吸收新的思想與語言體系的機會。而在日本,提出上述議案的這些人基本是戰前的執政者和知識分子。以首先提出戰争責任問題的蘆田均來說,蘆田均在戰争期間并沒有反對過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但他對西方人道主義立場的反軍思想有所贊同,是以在1940年日本衆議院迫于軍部的壓力開除齋藤隆夫的時候,蘆田均作為持反對意見的七名議員之一表示了意見。在那之後,他也曾對大政翼贊體制表示過不滿。由于有這樣的背景,是以在戰後能夠提出追究戰争責任的主張。但是從根本上說,他的曆史認識仍局限于“皇國史觀”對侵略戰争的本質并無認識。
一些日本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出于對戰争時期日本腐朽專制的法西斯政治持批評立場而提出他們的戰争責任論,盡管其中包含了對戰後日本走民主化道路的要求,但是從根本上來說,他們對戰争的侵略性質并沒有清醒的認識與檢討,他們追究的依然是“戰争失敗的責任”,而不是“發動侵略戰争的責任”。雖然他們也慷慨激昂地抨擊戰争時期的政治,但正如有人批評的,那不過是面對失敗的沖擊而自然産生的心理性的防衛,這種防衛用民族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說穿了,他們仍然期盼戰争的勝利,隻是在沒有取得勝利的無奈下才被迫思考失敗的責任。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二、被引上歧途的戰争責任追究</h1>
以追究“戰争失敗的責任”為出發點,戰後初期日本社會從内部進行的對戰争責任的追究被引上歧途,出現了十分奇特的現象:許多狂熱的軍國主義者也積極地參與對戰敗責任的追究。
鼓吹“世界最終戰争論”、主張以日本為代表的東洋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洋進行前所未有的決戰的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不僅是九一八事變的積極策劃者與參與者,而且也是扶植“滿洲國”傀儡政權的元兇。僞滿洲國建立後,他還在關東軍中擔任副參謀長。後來因與東條英機政見不同,于1938年辭職,作為中将師團長在1941年成為預備役軍官。此後,石原莞爾組織東亞聯盟協會,繼續堅持他的所謂“大東亞”幻想。因為在他看來,隻有日本能夠擔當上司東亞的責任。日本戰敗後,石原莞爾不僅沒有銷聲匿迹,相反卻活躍起來。1945年8月28日,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出:“打倒官僚主義的專制是目前第一位的任務,應在此基礎上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的民主主義國家。”他還提出廢除特高課,恢複政黨自由活動。在他看來,戰争失敗的原因是由于官僚、軍閥對言論結社自由的束縛和抹殺“阻礙了國民力量的發揮”。可以看出,石原對自己骨子裡的“神國日本”優越感根本沒有任何反思,他之是以批評官僚、軍閥,是認為那些人沒有實作自己的“東亞同盟”的理想。
許多支援了戰争的政治家在戰後也積極地響應上述議員們追究戰敗責任的提案。日本著名的婦女運動家市川房枝(1893~1981)是從戰前起就緻力于婦女參政的社會活動家,在戰争中成了十分積極的民族主義者,曾擔任“大日本言論報國會”的理事,積極發表支援戰争的言論。為此,戰後她曾被褫奪公職3年多。市川房枝自己也坦承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污點。在處分解除後,她又當選為參議員,對日本婦女政治地位的提高作出過重要貢獻。但是在戰後初期,她對自己的戰争責任并無任何自覺,而是積極響應一些議員提出的追究戰敗責任的主張。她強調,“由于被軍人和官僚控制,雖然在大東亞戰争中組成了婦女會,但是婦女仍然是沒有自主性的行動的”,其實是借呼籲婦女權利而為自己的責任開脫。
無論是石原莞爾還是市川房枝,他們在戰後提出的官僚制度問題、婦女參政問題确實存在,他們對日本社會民主化的要求也是正當的,但是,這并不能取代對發動侵略戰争責任的追究。而且,早在日本戰敗前,就有人從這一角度提出了民主化的要求。如作家石川達三早在1944年7月就在《每日新聞》上發表文章,呼籲說:“批判和壓抑不能鼓舞戰鬥士氣”,“得不到國民信賴如何進行總力戰”?為了建立更有效地進行總力戰的基礎而呼籲民主,其實就是在鼓吹戰争。他們所期待的民主即使發生,官僚制度即使有所變化,日本仍然不可能擺脫在戰争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的趨勢。何況,在遭遇徹底的失敗之前,即使是這樣的民主要求也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認可。
戰争時期,日本的國會議員幾乎毫無例外地擁護軍部的戰争政策,争先恐後地表達對戰争的支援,如果這些人在戰後不對自己的責任進行深刻的檢討,沒有否定自己在戰争中的表現的決心,追究所謂戰争責任的提案隻會是浮在表面上的行動。這種膚淺的追究當然不可能涉及對亞洲各國的加害責任,不可能涉及違反國際法的戰争犯罪,更不可能涉及天皇與一般國民的責任。直到1945年12月,隻有蠟山政道等11名衆議員出于對戰争期間接受大政翼贊會的推薦當選為議員的行為感到“自責”,主動表示辭職,而發動了侵略戰争的許多軍國主義者則始終躲在幕後。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1">三、“一億人總忏悔”——欺騙性的戰争責任論</h1>
戰後日本國會對戰争責任的“追究”之是以出現這種局面,其實是戰後日本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戰争剛剛結束,以日本皇室為首的上層就開始處心積慮地為掩蓋侵略戰争的責任而活動了。
1945年8月28日,擔任戰後第一任首相的皇族東久迩宮稔彥(1887~1990)在會見記者時發表“日本再建方針”,同時提出了所謂的“一億人總忏悔”的戰争責任論。
與上述國會中的提案一樣,東久迩在他的“日本再建方針”中也把戰争失敗的原因歸咎于日本國民的戰鬥積極性受到對言論自由的限制而沒有被充分發揮出來。他認為:“國民被束縛,什麼也不能做是戰敗的一大原因”,是以提出将來要活躍言論,發展結社。前述如蘆田均等議員的提案至少還批評“官僚”、“軍閥”及“追随迎合者”,而東久迩則完全回避了那些人的責任,直接将批評的矛頭明确地指向群眾,認為戰争之是以失敗是國民沒有對國家盡忠。他甚至認為:以黑市經濟為代表的社會現象标志了“國民道德的低下”,主張應“将一億人的總忏悔作為我國再建的第一步”。
以皇族為主導的日本政府之是以強調“忏悔”,是為了把戰敗的屈辱感轉移到國民的“自省”上而不是自己檢討上,避免出現因批評“官僚”、“軍閥”而把追究侵略戰争責任的矛頭引到自己身上的情況。“一億人總忏悔”針對的是所謂“國民頹廢”,并沒有觸及出現頹廢的原因。根據這一理論,首先成為追究對象的不是戰争的發動者,卻是戰争中的和平主義者,是對戰争持懷疑态度或在戰争中态度消極,沒有積極配合政府戰争政策的人;至于反戰的人,更被認為是導緻戰争失敗的“大逆不道”的日本的罪人,積極的戰争鼓吹者反而成了日本的“英雄”。
1945年12月,衆議院中讨論很激烈的問題就是對“戰争旁觀者”的批判。有人提出:“在戰局十分緊張,國家處于生死存亡之際,那些人還袖手旁觀,真是太冷酷無情了”,“如果容忍這樣的人存在,甚至讓持這種态度的人作為建設新日本的擔當者,會使社會産生誤解,是以是萬萬不可的”。甚至一些戰後的和平主義者,當時也對“戰争旁觀者”的态度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一億人總忏悔”主張的所謂“忏悔”,是指國民向國家和天皇忏悔,而不是向亞洲被害國的國民以及向盟國謝罪,不是對侵略戰争責任的檢討。結果是包庇了發動侵略戰争的戰争指導者,而打擊了反戰人士和反戰思想,從根本上扭轉了追究戰争責任的大方向,扭轉了日本國民思考戰争責任的方向,也是對戰後價值觀的一大挑戰。
如果說蘆田均等議員們批評官僚的提案在日本社會還能夠獲得一部分人認可的話,那麼“一億人總忏悔”的論調提出來後,在日本社會引起的反響則更多是批評。一般的日本人對這一論調的第一反應是:所謂“一億人”,就是指在戰争中承受了巨大苦難的所有的日本人,“本來是責任最重的人卻呼籲那些責任最輕的人一律進行總忏悔,是無視兩者在責任程度上的重大差異”。他們本能地意識到:在舊體制下握有權力的那些人是導緻失去300萬同胞并使國民痛苦的罪魁禍首,而依據“一億人總忏悔”的原則,這些人的責任卻被解除了。因為所有人有責任,實際上意味着誰也沒有責任。
于是,1945年9月8日,有人向《每日新聞》投稿,反對“一億人總忏悔”的原則:
讓一個人不剩地檢討,讓一個人不剩地忏悔,這不是對整個國民開刀嗎?直到天皇宣布停戰前,我們不都是在拼命地努力嗎?配置設定不公正啦、各種事業上的消極和失誤啦,所有視窗的不明朗啦,導緻戰鬥力低下的,難道不是那些官僚嗎?而現在那些達官貴人們有哪一個說“應當檢討”,“應當忏悔”了呢?你們難道不扪心問一問自己:能讓那些特攻隊和其他戰死者的遺屬們,讓那些在工廠戰死的遺屬們同罪孽深重的官僚們一起忏悔、一起檢討嗎?
這一意見立即在全社會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各大報紙都發表了許多人撰寫的支援文章。國會中也有人對“一億人總忏悔”論提出了批評,認為追究責任不能追究到一般國民。
其實,“一億人總忏悔”論并不是東久迩的發明。在戰争中,日本政府和軍部特别強調所謂的國民道德的建設,當時的口号中就有“沒有道德就不能勝利”、“‘人和’就能構築光明的大東亞”等内容。所謂“一億人總忏悔”,不過是戰争中強調國民道德建設口号的延續,是與鼓吹戰争的理論一脈相承的。另外,在日本投降前,當時負責日本國内治安的内務省警保局鑒于日本國民對戰争的不滿情緒,就曾向警察部長提出過一項建議,稱“對戰争責任者的種種議論和破壞軍民關系的言論今後可能會越來越多,在鎮壓的同時,應當宣傳這樣的觀點,即對于現在的局面,應當由軍、官、民共同承擔”。很明顯,這一建議與東久迩的“一億人總忏悔”如出一轍,目的就是将全體日本人都牢牢地綁在軍國主義的戰車上。這也從反面進一步證明:東久迩提出的“一億人總忏悔”,其實就是在繼續戰争中的價值觀,而與否定侵略戰争的檢討背道而馳。
雖然“一億人總忏悔”論很快就暴露了當政者掩蓋自己戰争責任的目的,但是像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一樣,“一億人總忏悔”命題的提出與對這一命題的反對,也存在兩面性。
一方面,“一億人總忏悔”論是政府站在“總力戰”的民族主義立場上要求群眾全體對戰争失敗原因進行的忏悔,并不要求對發動侵略戰争的責任進行任何忏悔,是以掩蓋了戰争指導者發動和上司侵略戰争的責任。但是,“一億人總忏悔”論中涉及的對戰争中日本人“道德頹廢”的指責也并非空穴來風。戰争導緻的“道德頹廢”是對日本社會造成巨大破壞性影響的問題,如果不正視日本人的“道德頹廢”,戰後日本也不可能實作道德重建。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德重建”的确是整個日本民族必須嚴肅地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另一方面,“一億人總忏悔”論存在掩蓋戰争指導者戰争責任的根本錯誤,但是,全力支援戰争的日本國民難道不需要整體地、主動地對戰争責任問題進行思考嗎?難道将戰争責任全部簡單地推給軍國主義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嗎?這也是日本人作為整體需要檢討的問題。
要求一億人向天皇和政府忏悔戰争的失敗,固然是肯定戰争的理論,但是,借對“一億人總忏悔”的批評而忽視群眾的戰争責任,也會使戰後日本社會對戰争責任的追究發生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