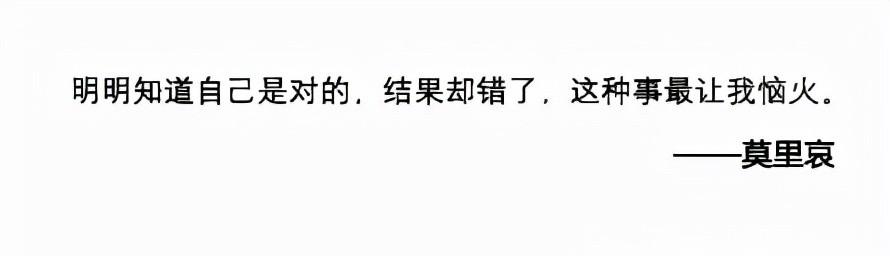
犯錯。具體說來,是關于作為文化群體, 我們如何評價錯誤,以及作為個體,當内在信念崩潰時,我們會如何處理。既然大 家都享受正确的感覺,把正确當做一種常态,那麼你可以想象,犯錯之後大家會作 何感想。一方面,我們會覺得這是偶發的特殊狀況,是莫名其妙的秩序失常,另一 方面,我們會覺得很傻很丢臉。就像看到考卷上打滿了紅叉一樣,犯錯之後,我們 也會瑟縮,也會癱倒在座椅上,然後心情低落,怒火漸起。往好了說,錯誤是件煩 心事,往壞了說,錯誤就是個噩夢。不管怎樣,我們都覺得錯誤讓人洩氣又尴尬, 跟正确時那種流過全身的暖流,不可同日而語。
而這僅僅是噩夢的開始。在大家的集體意識中,錯誤不僅跟愚蠢和恥辱挂 鈎,還跟無知、懶惰、心理病态甚至道德淪喪聯系在一起。意大利認知科學家馬西 莫•皮亞泰裡•帕爾馬裡尼(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精辟地概括了這種觀念。他說,我們犯錯是因為(包括但不限于)“心不在焉、分神、興趣寥寥、缺乏準備、 資質差、膽量小、眼高手低、情緒失控,或者我們在價值觀、種族觀、社會觀、愛 國觀上存在偏見,或者過于雄心勃勃,以及善于自欺”。照這種普遍流行的悲觀觀點 看來,我們所犯的錯誤,證明了我們在社會、智力和道德方面的嚴重失敗。
在我們犯下的所有錯誤裡,對“錯誤”的錯誤認知恐怕應當名列第一:我們連 “錯誤”是什麼都弄錯了。犯錯并不能代表智力的低下,反倒是提升人類認知的關 鍵。犯錯也不是道德瑕疵,反倒跟人性中最崇高的一面有深刻淵源,與同情心、樂 觀、想象力、信念和勇氣分不開。錯誤也并不是冷漠或褊狹的代名詞,而是我們學 習和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有了錯誤,我們才能不斷修正對自己的了解以及對 世界的認知。
既然錯誤對我們的智商和情商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便無須為犯錯而 尴尬,更無須視之為一個問題。相反,正如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言,錯誤是透視人 類本性的一扇窗戶,從中可以看到我們馳騁的想象、無限的潛能和不安分的靈魂。無論錯誤帶給了我們怎樣的迷惘、痛苦和打擊, 歸根結底,它才是教我們懂得自己的良師,而不是正确。
這不是什麼新觀點。但奇怪的是,我們所處的文化一邊鄙視錯誤,一邊又強調 錯誤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何以見得?在我們談論自己的方式中就有所展現。每當我 們犯了錯,總是聳聳肩,推說“是人都會犯錯” 了事。就像蝠蝠對應蝠蝠俠,懶漢 對應懶散一樣,“人類種族”便直接跟“任何事情總能弄砸”挂鈎。在諸多宗教、哲 學、科學文獻中,但凡涉及人類的部分,幾乎都寫到“人類天生具有犯錯傾向氣而 且提到,錯誤并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膚淺瑣事(不像指甲那麼膚淺,也不像打嗝和 幻覺那樣一閃而過)。早在勒内•笛卡兒(Rene Descartes)提出那句著名的“我思故 我在”之前1 200年,哲學家兼神學家(後成為聖人的)奧古斯丁就寫過:“我錯故 我是/ (fallor ergo sum.)依照他的這種表述,人類不僅會犯錯,而且從某種意義上 說,人類就是錯誤本身。
愛犯錯的傾向雖然已經融入了我們的血肉筋脈中,但融入的方式,很像彈簧小 醜被塞在盒子裡,你明知道一開盒子小醜就會跳出來,可每次還是會被吓得措手不 及。由此看來,錯誤類似于死亡,都是“人類” 一詞的隐含屬性。而我們認識錯誤 也正如認識死亡,覺得這是每個人都必經的事情,但總覺得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更别說高興。正是這種心态作祟,我們不管犯了什麼錯,往往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 或者不應該發生。于是,要麼死不認錯,要麼厚臉皮辯解,要麼裝作沒犯錯,要麼 對錯誤輕描淡寫,要麼把錯誤推到别人身上。
--[美]凱瑟琳•舒爾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