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相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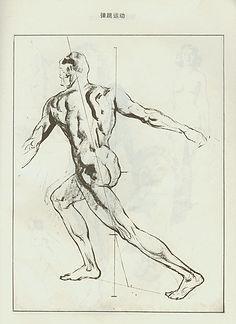
身體美學(somaesthetics)作為一個術語,正式出現在美國學者舒斯特曼發表于1999年的一篇論文中,這位學者又在2008年出版了專著《身體意識——凝視的哲學與身體美學》。我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突出了副标題中的“身體美學”而将之譯為《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身體美學由此引起了國内學者的較多關注。但綜觀國際學術界,真正以“身體美學”作為标題的專著并不多見,王曉華的新著《身體美學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簡稱“王著”)是我所見的首部同類著作。
客觀地說,王著的書名有點“文不對題”,因為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身體美學”—不是研究身體作為審美對象、身體作為審美主體、具身的審美活動等問題的著作,而是“回歸身體”或“回到身體”的美學。作者特别強調的是,他要“在身體的基礎上重建一切”,徹底地把美學界定為伊格爾頓所說的“有關身體的話語”(第19頁)。作者甚至提出,美學就是“研究身體與世界審美關系的學問”(第一章第三節标題),美學就是“身體美學”(第36頁)。這就意味着,王著所說的身體美學已經不是美學大家族中的一個成員,而是整個美學領域的全部—它與其他美學形态諸如藝術美學、環境美學、身體美學、日常生活美學等已經不是并列關系,而是涵蓋關系。這顯然已經大大超越了舒斯特曼身體美學的學術意圖。
為了實作自己的學術雄心,王著首先對關鍵詞“身體”進行了重新了解: 身體就是從頭到腳的整個“全體”,也就是說,身體包括“頭顱”。這個近乎常識的出發點推導出了王著所堅持的“身體一進制論”:頭顱是身體的一部分,頭顱裡面有大腦,大腦的功能是思維和意識,而思維和意識在哲學史上通常又被稱為“心”或“心靈”,心靈的形而上層面則又被稱為“精神”或“靈魂”。既然大腦是身體的一部分,那麼,心靈甚至靈魂也都順理成章地是身體的一部分。是以,以笛卡兒為代表的“身心二進制論”隻不過是在宗教神學影響下所産生的錯誤觀念;根據生态學家海克爾的有機體一進制論可知,隻有“身體一進制論”。是以,王著提出,通常所說的“我有一個身體”是不準确的表達,因為它一方面隐含着“我還有一個心靈”這句潛台詞,另外一方面還隐含身體是由獨立于身體的“先驗主體”所“擁有”的;準确的表達應該是“我是身體”—除了身體之外,我一無所有,一無所是。“有”與“是”盡管是一字之差,但其隐含的哲學立場卻天壤之别:前者是身心二進制論,後者則是王著堅持的身體一進制論。正是借助身體一進制論,王著回答了“為什麼美學必須回歸身體”這個關鍵問題。
從進化論、生理學或生态學的角度來說,身體一進制論或許很容易了解,但是,對具有濃厚宗教傳統的西方文化來說,公然否定靈魂存在的觀念總會産生震動。是以,即使那些極其重視身體的西方哲學家諸如梅洛一龐蒂、舒斯特曼等,都在身心問題上模棱兩可。而王著則斷然宣稱,宇宙間并不存在靈魂,隻有身體一進制論才能恰當地解釋人的生命及其審美活動。這既是對于西方身體哲學的一個大膽突破,又是對西方靈魂形而上學的一次批判,其學術勇氣頗為可嘉。
在提出并解釋“為什麼美學必須回歸身體”這個問題之後,王著以身體主體論作為立足點,用五章篇幅依次讨論了審美的發生、審美的過程、審美的二重性、自然審美與藝術審美等五個問題。其中,最有價值的是第五章對于自然審美的讨論。衆所周知,自然審美(近似于通常說的“自然美”)問題是美學理論的難題,甚至是一種美學理論學術水準的“試金石”:衡量一個美學系統的理論價值及其成熟程度,首先應該看它能否适當地解釋自然審美問題。王著從追溯身體與自然的關系人手,從審美史的角度審視了“輕視身體”與“低估自然”兩個不同問題的内在關聯,然後從論述“重身與體物”的關系入手,相當充分地論述了“自然審美的可能性”問題。其最精彩的地方是借鑒生态學思想,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的“共産主義”( communism)了解為“共同體主義”(第218頁)。“共同體”( community)又稱“群落”,是生态學的關鍵詞,美國學者利奧波德甚至将生态學稱為“研究共同體的科學”。從生态哲學的角度來看,共同體之中的所有成員都是共同體不可或缺的成員;人和其他物種之間的邊界并不那麼清晰,并非隻有人才是主體,萬物也都是主體;共同體所有成員之間的關系不是傳統哲學所說的“主體一客體”關系,而是“主體一主體”的關系,即“主體間性”關系。人以自己的身體建構自己的世界,萬物也都以自己的身體建構各自的世界。比如,一朵花,也通過自己的生命活動建構屬于自己的世界,這個世界就是生态學所說的“生境”< habitat)。對于花的欣賞,就不是傳統審美理論所重視的欣賞花的優美形狀、豔麗色彩、芬芳氣味等,而是“進人花的世界”,“以花的身份去生活”;此時的花不再是物,“而是與我進行呼喚響應的主體”(第122頁)。這些論述明顯超越了傳統的自然審美理論,特别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人化自然”理論,是對于當代生态審美思想的重要貢獻。而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作者長期的生态研究。身體美學與生态美學由此彙合在一起。
上文提到,王著的主體部分依次讨論了五個問題。我們不禁要問:這個問題清單當中,有哪些是作為“身體美學”的美學所提出的新問題?如果這些問題都是已有的美學問題的話,那麼,這個追問就可以換一種方式來問:為什麼該書之前的“心靈美學”也能夠提出這些問題?作者對此顯然沒有深究。其實,從當代美學前沿領域來說,環境美學已經對此問題有所探讨。環境審美不同于藝術審美的根本特點是,欣賞者隻有走進并融人環境之中,才能對環境進行适當的審美欣賞;走進環境之中的顯然不是人的“心靈”或“精神”,而是人的“身體”:實實在在的身體作為欣賞者的審美基點,通過相對于身體的不同方向(前後左右上下)、身體的高度或姿勢(或直立、或彎曲、或坐、或躺等),根據欣賞者的審美興趣,從包含着豐富資訊的環境之中,選取引起審美關注的事物組建成審美對象,也就是動态地、随機地與環繞欣賞者的周圍事物構成審美欣賞關系。正因為如此,環境美學也非常重視身體。這不正是作為審美主體的身體所引發的新的審美問題嗎?我們不妨創造一個新的術語來概括這個審美問題,比如說,“身體關聯”( somatic relevance )。從這個地方,我們又看到身體美學與環境美學互相貫通的學術契機。誠如是,王著試圖以身體美學一統美學天下的學術雄心或許可以進一步嘗試,其學術思路是,對于其他美學形态進行更加全面的把握與整合。
從論述方式的角度來說,筆者覺得王著也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王著的學術抱負是從身體一進制論、身體主體性出發,對美學做出“原創性建構”(第26頁),進而“由理論的學徒升格為創造者”(第43-44頁),這是令人極其敬佩的學術魄力。但是,我們都知道,不要說“原創”,就是一般的“創造”,也必須以此前的美學史作為基礎。如果對于美學史沒有足夠深刻的把握,除了像維特根斯坦那樣的天才之外,“原創”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創造”了出來了,在缺少美學史參照的情況下,其創造性也難以衡量和評價。我之是以很少提“美學創新”而長期堅持“審美理論知識有效增長”這種學術信念,原因就在這裡。
根據這種學術信念,我對王著提出如下質疑:既然王著認定美學必須回歸身體而成為“身體美學”,那麼,它所隐含的理論前提就是此前的“心靈美學”無法恰當地解釋審美現象,是以才需要改弦更張。那麼,更有說服力的論述方式,就是根據“審美理論知識有效增長”這個原則,層層遞進探讨如下五個個問題:心靈美學的思路是什麼?其理論貢獻是什麼?其理論缺陷又是什麼?身體美學為什麼能夠彌補這些缺陷?身體美學的獨特審美問題又是什麼?其中,第四、第五兩個問題應該是學術研究的落腳點和獨特貢獻之所在。比如,康德美學可以說是西方心靈美學的典型代表,它建立在康德的先驗觀念論之上,從中基本上無法看到身體的影子。但非常有意思的是,王著不少地方卻引用了康德美學來支援自己的觀點,這就造成了一個疑問甚至悖論:作為心靈美學代表的康德美學,為什麼能夠支援王著這部身體美學著作?康德心靈美學的合理性來自哪裡?身體美學又在何種意義上克服并超越了它的局限?
探讨這些問題無疑會大大增加王著的工作量,但無疑也會大大增強王著的說服力和理論厚度。黑格爾說過一句很有道理的話:哲學就是哲學史;我們可以套用過來說:美學就是美學史。離開了對于美學經典的研讀、反思和批判,美學研究必将成為空中樓閣,“原創”雲雲頂多是美好的學術願望而已。有鑒于此,王著大量地追溯了西方美學史,但是,其學術針對性和批判力度都還有待加強。好在作者正處于學術創造的活躍期,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他不久就會拿出更加厚重的學術力作。
源發刊物:中國圖書評論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