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祖輩起就生活在被稱為“大白渠”畔的土地上,身為泾陽人最不能忘記的人就是李儀祉先生,自小時老人就不曾一次說過,李儀祉是我們的恩人,對于這片土地上的人有着巨大的恩賜。從小家人對我要求極其嚴格,小時吃飯時要求不能有任何浪費,米粒大的飯渣掉在地上都要撿起來,這種習慣的養成原因等到成年之後才深深的了解。說到這裡不能不提九十多年以前的那一場災難——民國十八年年馑。在那場由天災和人禍造成的人類災難中,整個陝西省受災人口960萬,餓死、逃亡和被販賣的人口多達320萬,家裡老人講述段故事時總是指着村裡某處某地說,原來某某家死絕了,早已沒有子嗣,那處崖壁上的小洞都是薚滿了死人,村裡到處是空莊子。某某饑餓無奈之際,吃觀音土以緻無法消化,最終腹脹而死,某某餓斃前以狂歡的形式耗盡家财吃頓毒餃子……而終結這段慘烈場面的就是門前的這條大渠,當時人或稱為大渠,或是白渠,它的真正名稱叫泾惠渠。提到泾惠渠不能不提到李儀祉先生,我國偉大的水利大師。每年清明節是我國傳統祭祀先人的日子,而李先生長眠之處總是人若潮湧成千上萬,鞠躬行禮,靜默繞陵寝一圈,出自本心來祭奠救人與水火的恩人,這種行為早已成為傳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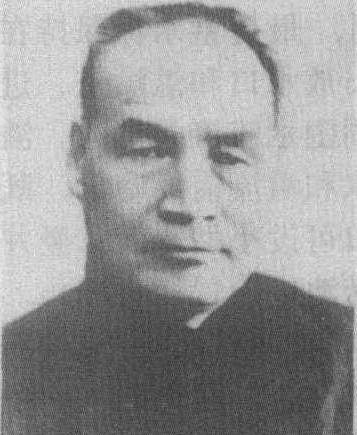
一、做事不為官,求實不務虛
李儀祉先生是蒲城鄉黨,很早與泾陽縣結下不解之緣,他出生于富有革命傳統的家庭,父親與伯父是陝西辛亥革命中堅力量,是早期同盟會成員。他一八九八年就到泾陽縣城裡富有維新思想的崇實書院求學。在父親、伯父及劉時軒老師的熏陶下,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與愛國主義教育。目睹國家的貧弱、人民群衆的困頓不堪,立志于科技救國,工程興國,為解救貧勞動人民疾苦,為人民群衆謀取幸福而學習。
1891年少年的他寫文章就說出“不求有用初學,顧乃溺思淪精于此,吾為為也”這樣的話語,1919年時他的文章《工程家面面觀》中明确提出工程技術救國的概念,他說道:“一般青年學生,醉心于德谟克拉西,以服務社會自任,社會救星自命,改良社會為目的,那知要為社會盡一番責任,再已工程家易于為力。 實行愛國,惟有工程家做得遠大,實行打倒帝國主義,亦惟有工程家做得徹底。”從這些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遠大志向,立志于解決民生疾苦,為人民謀福利的思想。李儀祉最為人稱頌的一句話,是對于農校(西北農林大學前身)水利組第一期畢業典禮對學員所講:“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一切事情都應求實際,不要争虛名。”(鄭慧涵《愛國育才的教育家李儀祉》),雖然講話的時候面對是學生,可也是對于他一生活動的精準概括。
不要虛名,力求實際。他畢業于京師大學堂,僅僅領了畢業文憑,舉人的身份證明——官照他沒有領,就回到了陝西老家。到德國留學時,由于他認為幫助完成學業的是陝西父老,由于學位考試還需要500馬克,是以兩次留學他都沒有參加學位考試,為的就是能為國家省些錢,他說:“我不遠萬裡來到德國求學,求的是學問,而不是學位,學位對我毫無用處;而且我是公費學生,用的錢是老百姓給的,能省一文是一文,無論如何不能浪費的”。李儀祉學成回國之後,當了許多地方的大官,據不完全統計由國民黨中央任命職務就達15個,由省級或地方任命職務有36個。1928年李先生任華北水利委員會主席兼總工程師,在水利事業即民生福祉的北方幹旱地區,蔣介石都羨慕他既能收獲良好的聲望,一個武夫、政客竟然也給自己弄了個導淮水利委員會委員長來當。
可是李先生做官就是為了做實事,就是為了解救由于幹旱而流離失所,嗷嗷待哺的貧苦大衆,李儀祉少年時期經曆以及曆史上的數次幹旱導緻大災,餓斃北方千萬人以上的旱災往事不遠(注:光緒三年1875,辛醜年1900中國北方地區數省餓死人數計千萬以上,1920年大災受災面積北方五省,涉及數千萬人口,死亡仍達近百萬。)。他曾說過“救危定難,自愧無方,愛國憫人,亦何能後。”能做事拯救人民群衆于危難之中,能為人民謀取幸福,這個官他就當得,否則就不必挂這個虛名。李先生辦河海大學、治理淮河、修建泾惠時,憚精竭慮,勞苦異常,可他認為這個官就當得“舒服”。反之,工作時受製肘,事事不順,僅有官位的虛名,這個官位再高也不值得留戀。1933年任黃河水利委員會之後,對于黃河治理與黃土高原水保研究投入大量精力,黃委會工作卓有成效。僅1935年十個月内“他赴京五次,赴汴十次,赴陝六次,赴津三次,赴鄭二次,赴濮陽三次,赴陶城埠二次,赴貫台四次,赴董莊三次,赴魯四次,赴蘇一次,赴平一次,赴朱口及漢口各一次,席不暇暖”(胡步川 《李儀祉年譜》)。調查研究指導水利工作,治理黃河著述無數,建議又何止十萬言,由于某種原因,他的治黃主張政策不被政府采納,沒有辦法将自己的理念應用,導緻國家在黃河上浪費了大量錢财。他決然辭掉了所謂部長級的高官,放棄了月薪800元的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欣欣然回到陝西專門當那個月收入隻有150元的水利局長,繼續緻力于陝西水利事業。(1936.4.7李儀祉複全國經濟委員會鄭肇經書:餘在水利局,每月僅支一百五十元,已頗敷家用,而此等精神相濟之人心,則萬金難買,故甯舍彼而守此也。)
陝西泾惠渠從勘測到修建以及至完工是個極為曲折艱難的過程。李先生出國求學之際就以恢複鄭白為宿願。自清代拒泾入渠以龍洞篩球等泉水為灌溉水源,全盛時期僅灌地八萬餘畝,後由戰亂毀壞失修至民國初年隻有一萬多畝。戰亂未息之際李先生即投身于陝西的灌溉事業。1913受郭希仁之囑修習水利,1922年郭希仁病中電請托咐鄭白水利大業、靖國軍李仲三再請回到陝西任事,兼陝西水利局長和渭北水利工程局總工程師,立即開展前期水文、地形勘測工作,他與河海大學弟子組成的測量隊伍親入數百年從無人蹤的深山峽谷之中,風餐露宿,爬山涉水,條件艱險異常,稍有不慎即有性命之虞,至1924年測量繪圖工作完成,泾惠渠工程設計完成。可是北洋軍閥統治下的陝西督軍劉鎮華隻知道占地盤争名奪利,之後的軍閥馮玉祥也隻會口頭應付,工程費沒有着落,李先生隻能依靠個人能力争取,到北京聯系華洋義赈會和美國亞洲建業公司,多次籌措四處碰壁之後,陝西戰火重燃之後李先生的第一次努力失敗了。
離陝之後他又分别聯系過于右任希望能重新開機引泾工程,結果隻能是以長歎一聲告終。陝西大災初起之時,他奔走呼号,對于引泾工程進行廣泛宣傳,以期引起當局者以足夠重視,卻被人嘲笑,三上北平,兩下南京,卻未能阻止一場慘絕人寰重大災難的發生,1928年至1930年三年陝西旱、蝗、兵匪災接踵而至,至1930年初赈災委員會發電稱死亡250萬,婦孺被販賣為婢為娼者40萬(僅陝晉川交界處統計,見于右任《陝災述略》1931.1.19),白骨千裡關中悲,死氣彌漫秦陝境。最直接的誘因就是三年沒有一場有效降水,導緻三年六料莊稼顆粒無收,這就是不重視水利工作,水利設施長期失修直接後果。
離開陝西之後他放心不下還是老家的水利事業,在與興平趙玉玺(趙寶珊或趙寶山,當時為陝西省水利局代局長)通信中說:“陝西父母之邦,弟何愛塗山,遂忘泾渭。果當局有興工之心,聚焦可靠之經費,弟不再為局長,但畀以工頭之職,畚锸徑施,弟即奮然歸矣。”
1930年楊虎城入主陝之後,政局稍有穩定,他立即辭去淮河水利委員會總工程師職務,回陝着手引泾事業。泾惠渠工程1930年12月舉行開儀式,1932年6月第一期工程放水。泾惠渠的修建采用以工代赈手段,在食極度物匮乏情形下直接拯救成千上萬難民于瀕死之中。泾惠渠開工之間,又立即着手規劃渭惠、洛惠、梅惠等十多條灌溉工程,1935年泾惠二期工程之後。李先生的同僚汪胡桢來到泾惠灌區時,昔時的人間地獄已大變少有樂園,他看到“時灌區已澆地六十萬畝,農民連續兩年獲得大豐收,灌區内情況大變,到處人民熙熙攘攘,喜氣洋洋,無論男女老幼,都穿着新衣服……農家屋舍已修飾一新,找不出舊時破爛痕迹。”值1937年抗日戰争前後,關中四渠完工灌溉面積達一百三十多萬畝,改善陝西境内勞動人民生存環境,有力支援全國抗日戰争。
生來隻為做實事,從來不重虛與名。數十年連續大負荷的工作與研究讓他的身體健康受到嚴 重損害,1938年2月底,他心力交瘁,重疾卧床的時候還忘不了渭惠渠的工程進展,彌留之際手書是與渭惠渠相關的兩個字“土壩”,1938年3月8日,李儀祉先生與世長辭。他以數十年工作诠釋了少年時的願望,将生命的全部獻給多災多難的國家與人民。
二、清正自律,廉潔自好
李先生有個外号被稱為“聖人”,這個綽号最早源于小時學習“自造漢字”,被劉時軒老師笑罵“你是聖人嗎?”言中之意不應該搶倉颉聖人的飯碗。後來在留學德國因不肯與他人流連歡樂場所,卓而不群、嚴于修心修德而被同學呼曰“聖人”。說李先生是聖人與曆史上的三皇五帝孔孟等人物并列,這個贊譽有些過,但縱觀李先生短暫的一生,他确實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在工作與生活方面從不肯逾規,對于工作他忠于職事,兢兢業業全力投入,在别人認為屑屑小事,不值一提而對于他卻反映了他為政清正,廉潔奉公的高尚品質,也反映了他不忘自小立志救國救民的初衷。
封建時代的官僚在大堂上挂着大匾,總是書寫“公正廉明”四個大字,能做到這一點的卻寥寥無幾。民國時期也有一心為民的官僚,可更多的人利用權力大肆A錢斂财,滿足自己的私欲,與其所标榜的清明公正基本沾不邊。李先生數十年也身為民國高官,多數時期身兼數職,同時負責着全到多處的水利工程,修築水利工程所用的銀錢過手何止千千萬萬,經手了大量工程經費,可從來沒有一點浪費。他在進行工程預算時能充分考慮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竭力落實,是以他所主持修建的工程項目,沒有超過預算。對于國家與人民的錢财用之有方,用之有道,從不靡費鋪張。他的清廉還展現在對于處理個人和公家财産方面能做到公私界限分明,公家的财物絕對不能私用,哪怕是一張三分錢的郵票,幾張紙片。據他的學生胡步川先生回憶說:“有次去儀師辦公室請示工作,親眼看到儀師正在交代秘書讓之寄發大堆檔案,秘書剛走到門口,隻見儀師站起身來,摘下眼鏡對秘書強調說其中有兩封是私人信件,要自費寄出。這個場景,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想想,那時寄出一封信件僅折合現在的3分錢。”
儀祉先生的書房總是上鎖,就是怕孩子進行亂翻折騰動了公家的東西,有一次他發現孩子寫信用的是水利局的便簽,馬上就對任職水利局的侄兒李賦林和12歲兒子進行批評教育,“今後絕不容許把局裡的任何東西帶回家,即就是一張紙也不能帶出水利局大門。國家财産,個人決不能動用一絲一毫。”還有一次他的孩子發高燒不退,家裡打電話告急,但拿出了二塊錢讓侄子雇黃包車拉兒子上醫院,這個時候停留在院子裡的是他專用的小汽車,也幸虧送院及時才沒有造成遺憾。公車公用私事一點都不能動用,特别是自己的親屬。兒子有病不用,就是他本人在辦私事時,也不動用。
别人當官家私萬貫,豐裕富足,李先生多年高官卻是清風兩袖,家徒四壁,他放棄南京的各種兼職每月近千大洋的高薪,回到陝西為民規劃籌修關中八惠,隻領陝西省水利局局長每月150大洋的薪水“這點低薪,一半用來養活一大家子人口,另一半則捐出修建水利工程,這種情形已經成為慣例,當時水利局同仁衆所周知、欽佩不已。(李賦林語)”誠如其言。李儀祉先生去世後,遺留下的所有财産僅僅隻有一所房屋,此外沒有任何存款和有價或無價物品。他去世後的1943年,李賦洋因家庭經濟一般,為對方家長看不起,被迫與女友分手。1949年李賦甯回國到西安看望母親,先生遺孀竟然拿不出像樣的小小見面禮,最後幸虧小兒媳解決老人家難堪,将其陪嫁的金戒指送于老太太渡過難關。
李先生為官清廉,潔身自好,他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是自己,而是時時刻刻牽挂的是國家與人民。也為正是因為他廉政自律,一心為民才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水利工作者追随,“在陝工作之技術人員,完全以精神相團結,忠誠努力,而彼此毫無閑言”(《李儀祉複全國經委會書》),整個民國時期水利工作尤以陝西最為出色,水利工程技術最為先進,不能不說李先生厥功至偉。
三、人溺已溺,悲天憫人
李儀祉先生的綽号曾為聖人,對于為官同僚花天酒地,怠惰懈政表現出剛正不阿,不肯屈服,甚至敢給犯上怼财政部長宋子文。1927年為水利經費問題李先生當宋子文面拍桌子,扮難看,甩袖子,甚至在蔣介石聘其當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時,他也不給面子,講道:“我不懂經濟,更不懂什麼政治,我隻懂修水利,那樣的高官我做不了,沒錢治淮,那我在南京還有什麼意義。”然後,然後就走了,噎得蔣介石悶聲無語,長時間之後才自語:“政府再多有幾個像李協這樣的人,國家幸甚,民之幸甚。”斥責楊虎城為接待政府要員何某浪費公帑,“如今整個國家陷于民窮财困之中,外寇欺淩,陝西今年又是荒年,而西安的軍政人員卻撂下公務去花天酒地!”待楊将軍上門緻歉後才平息憤怒。
與普通群眾相處則心存悲憫,寬容有加。他走上水利事業道路就是因為在幼小之時體驗到了家鄉缺水造成農業歉收,勞動人民流離失所,也看到故鄉餓殍遍地的慘狀,才決心要用自己的力量改變一次又一次慘像的發生,才對陝西的水利事業情有獨鐘。前面他說過隻要陝西興辦水利,工程師可以不做,哪怕就是做一個一般的小工頭也要參與到引泾工程中去。他對一般的人民群衆有着深厚的感情,事事也能立足普通群衆的視角考慮問題,生活中有很多他與一般勞工、農民和難民的交往,有許多和藹有加,寬待他人的細節,正是從側面反映了他“人饑已饑,人溺已溺”,能處處為别人着想,将别人困難看做自己難處的博愛思想。
陝西大災期間,旱情、災情撕扯着先生的痛苦心靈,他不斷呼籲重建陝西水利,災區的慘狀讓他感到必須有所作為,他對于一般的赈災建言“移粟移民非救災之道,亦長治之策。鄭白之沃,衣食之源也。”據段惠誠《陝西興修水利之回憶》1929年段惠誠諸人在導淮工作最為關鍵之時與李先生會晤,依然允諾當陝西省工程款項有所着落之際,當傳回陝西興辦水利。1930年,楊虎城主政陝西,時局稍穩即“決然舍棄,歸而相助,誠以救民水火之舉,不能漠視之也!”
有次一個難民偷了他的東西,了解情況後,不僅沒有懲罰這個難民,反而給了一塊銀元,還給他找了工作。感動得難民淚眼連連,說“遇見活菩薩了”。給司機張羅婚事,李儀祉先生與專職司機陳阿金多年朝夕相處,感情很深。不止一次對陳阿金說:“我走遍了大半個中國,發現泾陽、三原這地方确實不錯,你的年齡也不小了,整天跟着我四處奔波忙碌,也該考慮成個家了。上海那邊你也沒有親人,不如在這裡安個家吧。”
臧克家詩《有的人》就是對李先生一生最準确地概括,李儀祉先生俯下身子為人民當牛做 馬,為普通群衆謀福祉,他去世距今已有八十多年了。去世之後僅泾陽縣當地有數千名群衆自發為他戴白花送行,自此年年歲歲已成當地清明習俗,至于全國水利受惠群眾時時拜谒則天天有之,從未斷絕。當地人贊譽他為“活龍王”,為幹旱的關中平原、黃土高原送來了賴以甘霖,使廣大群衆過上幸福的生活。
最後借用《他在彌留之際最後寫下了什麼∣今天,先生逝世78周年了》結語對于李儀祉先生進行一個概括:“國際上有種觀點認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全世界隻有兩個半水利泰鬥:一個是德國的恩格司,一個是中國的李儀祉,半個在日本;在國内,當代水利學術界有一個通識,即是:李儀祉把中國傳統水利思想向現代水利進行了轉變,研究李儀祉水利思想就是研究中國近代水利思想。二〇〇一年九月,在中國北京召開的國際水利學大會上,李儀祉被确定為二十世紀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自從李儀祉先生一九三八年逝世後,國共兩黨及政府、民間各種紀念李儀祉先生的活動從未間斷,可見李儀祉先生身上具有一種遠遠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時空的震撼力。故去八十載,但彰顯人格魅力和特定精神内涵的李儀祉先生,仍在影響一代代學人。”
參考資料:
1、《工程家面面觀》 李儀祉
2、《愛國育才的教育家李儀祉》鄭慧涵
3、 《李儀祉年譜》 胡步川
4、《李儀祉複全國經濟委員會鄭肇經書》1936.4.7
5、《李儀祉複全國經委會書》
6、《陝西興修水利之回憶》 段惠誠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