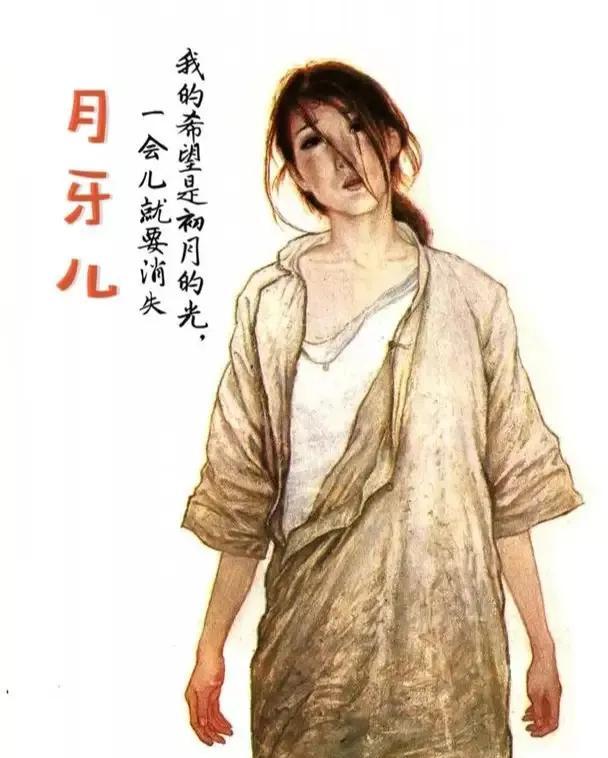
老舍最善于描寫底層人民的面對生活的掙紮,每每讀完他的小說,總會有一種說不出的壓抑,在心頭久久無法散去。
《月牙兒》成書于1953年,以第一人稱講述了舊社會的一對底層母女,為了那“隻有的一張嘴”而淪為暗娼的故事。
這部小說是老舍僅有的,以女性為題材的作品,卻真實地還原了20世紀30年代,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吃人”社會之下,底層女性所要面臨的生存困境。
全書共是43個章節,僅有1.6萬字,卻深度地刻畫了母女兩代人,最終都淪為暗娼的無奈和心酸,鑄造了一部時代的悲歌。
魯迅說,悲劇就是将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老舍的這一部《月牙兒》,将母女兩代人的人生,打碎了,揉開了,扔到了最卑微的黑暗裡。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母親的掙紮和抗争:</h1>
“我”的爸爸病重,把母女倆丢棄在了這個混亂的時代。
生活的最初尚且可以以典當度日,直到母親把外婆給她的最後一支銀簪,也拿去典當之後,母女倆真的山窮水盡了。
母親開始以幫人洗衣服過活,每次洗完都被臭襪子熏到吃不下飯,本來白皙的手上起了魚鱗一樣的老皮。
可即使是這樣的活,也不是常有的。沒有工可做的日子裡,母女倆隻能忍饑挨餓。
此時的母親尚且年輕美麗,但母親的精神卻被這種非人的操勞不斷摧殘着,再看着饑腸辘辘的女兒,狠了狠心決定改嫁。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5">母親的兩次委身于男人:</h1>
饑腸辘辘的肚子是不長耳朵,也不長心的,跟着母親的花轎進了一個陌生男人的家,“我”也被迫要叫那個人爸爸,這是母親對生活的第一次妥協。
繼父對母女倆很好,女兒甚至得意去學校讀書,可是經過了幾年穩定的日子,繼父卻不辭而别。
被抛棄的母女倆隻能再次面對生活的壓力,母親把家裡能當的東西都當了,最初還倚在門前等男人回來,後來心死了,開始漸漸做起了暗娼的生意。
日子久了,母親老了,就開始再次尋求新的出路。因為她的姿色和精力已經不允許她再伺候多個男人了,這時饅頭鋪的掌櫃願意接納她,母親就急着嫁了過去,這是母親對人生的第二種妥協。
“我”已經大了,不友善跟過去,就隻能自己找出路。跳過關于介紹“我”的情節,以為不複相見的母親,文末再次出現。
那時的母親已經是十分蒼老,饅頭店的掌櫃偷偷回了老家,沒給她留下一個錢。母親隻能輾轉的找到女兒,依靠女兒做暗娼的錢過活。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2">“我”的掙紮與抗争:</h1>
母親嫁給了饅頭店的掌櫃,“我”能為自己想到的辦法就是去求校長,校長管了我的兩餐,我堅信讀過書後,我可以以女性的獨立和自尊靠自己的能力生存下去。
然而學校後來換了校長,胖校長說他無法保證新校長是否會以她的标準待我。我開始以給學生織東西來賺些工錢,但是杯水車薪。我想轉頭去找媽媽,卻不忍給她添麻煩。
此時我仿佛開始了解那個曾經洗過臭襪子的媽媽,那個為了有口飯吃兩次嫁人的媽媽,那個為了活着,甘心當暗娼的媽媽。
我開始在飯店當女招待,但卻不能像别人那樣忍受被當衆調戲,賣弄風情,于是隻能再次失業,沒有工作可做。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7">“我”曾經想依靠男人:</h1>
“我”去找校長幫忙的時候,見到了一個青年,校長的侄子免費幫我租了房子,恍惚間讓我以為自己遇到了愛情,找到了依靠。
直到他的老婆找上門來,那是一個老實本分的女人,我答應他會離開這個男人,但我并不知道離開他之後要怎樣活。
終于為了這張嘴,我走上了媽媽的老路,回到了最初的地方。饑餓是人的本能,我無法抵抗。在生存面前,教育賦予我的一切道德信念,都是那樣的蒼白無力。
“我”一點點丢了至尊,将生而為人的衣服一件件脫下,變成了一具沒有感情的軀殼。
在“我”的世界中,從沒有見過滿月,總是見到那個斜斜的,充滿寒氣的月牙,它像極了我那凄涼的命運,也成為了千萬底層婦女的代表。
“母親是愛我的,可貧窮比母愛更有力量。”母女相逢後,身份對調,我要依靠就做暗娼,來養活自己和母親。小說的最後我被抓進了感化院,進而被送進了監獄。
然而對于我來說,監獄甚至比外面要好,因為現在的外面既沒有希望,也不再有母愛。
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女人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附男人,可是女人寄希望于男人的結局是可悲的,到最後,隻能被迫将“生而為人的衣服”一件件脫下,靠自己曾經所唾棄的職業過活。
母女兩代人最終都被迫淪為暗娼,即便如此,也沒有過上安穩的生活。隻是“我”比母親要有着更多的情感和思想上的掙紮。
母親最後完全信奉了男尊女卑的社會規則和金錢萬能的價值觀;而我因為那些知識文化和人格意識上的獨立,使我産生了自我懷疑,甚至自我毀滅的報複。
《月牙兒》到最後也沒能為女性生存撥雲見日,在感化院中所謂的教育就是“找個人嫁了”,而所謂的的嫁人,不過是男人來花兩塊錢手續費選女人領走。
小說的最後,“我”甯可選擇進監獄,也不願再回到社會中,去體會那貫穿始終的饑餓感和令人絕望的窒息感。在監獄中,至少不需要考慮下一餐在哪,至少可以保留做人的最後一絲尊嚴。
至此,為了獲得人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我”不僅脫下了“生而為人的衣服”,還決然地抛棄了作為人這個個體,本應獲得的自由。
-END-
世界那麼大,感謝你,可以看到我!
【本文由 唯唯安 原創出品,抄襲必究/圖檔來自網絡,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