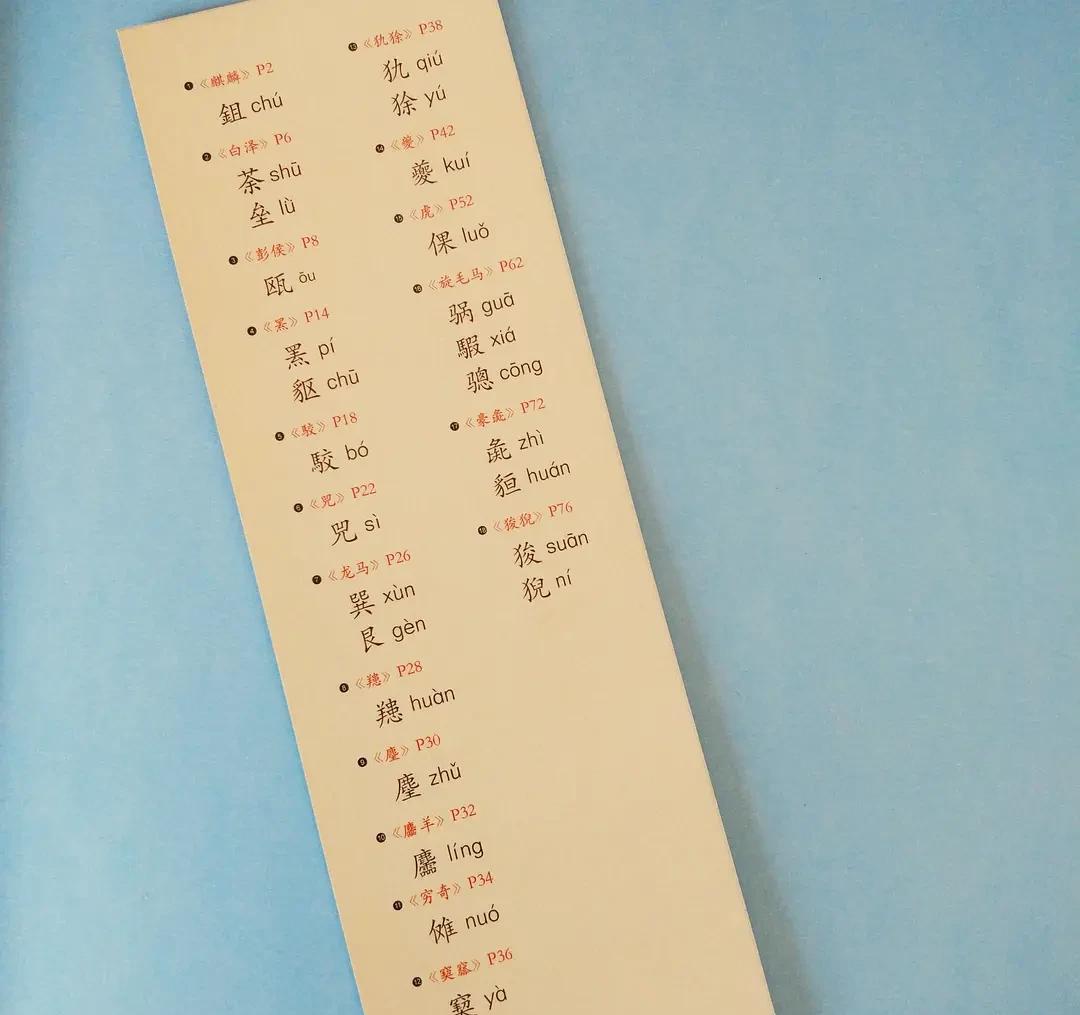
《山海經》之《海内南經》: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如牛,蒼黑,一角。
這是講兕這種獸,多出沒于湘水南岸。而它長什麼樣呢?青色,頭上有一個角,身重,像野牛。
說起大青牛來,不由地讓人想起《西遊記》中的“獨角兕大王”,這個原本太上老君的坐騎,趁看守人不注意,偷了金剛琢偷偷下凡,成了山大王,擄走了唐僧,與孫悟空大戰幾十回合不相上下,還用金剛琢收走了衆人的兵器。最後還是太上老君前來将其收服。
除了像青牛,還有一種說法是兕更像犀牛,但不管哪一種,兕在古代都是瑞獸。青銅器上也常常出現兕的圖像,用以象征高尚品德。
在《紅樓夢》元春判詞裡也提到兕:“虎兕相逢大夢歸”,意為兩種猛獸争鬥,喻指元春身亡以及大家族由興轉衰的結局。
兕,一直是中國文化裡一個常見的意向,一般都是指的一種大型的像是牛一樣多猛獸,常常用“虎兕”(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資治通鑒》)、”狼兕“(蔓草猶不可長,況狼兕之寇乎!——《晉書》)、”虎豹犀兕“(其獸多虎豹犀兕——《山海經》)等詞語之中,與虎狼并列,可見其兇猛,又卻是常用。
最知名的就要數孔子那句”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椟中,是誰之過與?“(季氏将伐颛臾)了,據說當年和珅就是靠這個梗發的迹,前幾天我媽在看延禧宮略,裡面女主也說了這個典故:
史籍載稱,乾隆四十年的一天,和珅随駕出宮。“上偶于輿中閱邊報,有奏要犯脫逃者,上微怒,誦《論語》‘虎兕(sì)出于柙’之語”,扈從校尉不知此系何意,和珅卻立即對答說:“爺謂典守者不得辭其責耳。”乾隆聽後很高興,問和珅:“讀過《論語》?”和珅說,讀過。“又問家世、年歲,奏對皆稱旨”。乾隆“見其儀度俊雅,聲音清亮”,“矯捷異常”,十分贊賞,“自是恩禮日隆”。
而從《詩經》開始,兕觥,用兕角做的酒杯(或者是做成兕角形狀的酒杯)也是常常出現的意向。可謂: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卷耳》“
以及知名的《七月》結尾的那句:”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飨,曰殺羔羊。跻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一直到了唐代,《新唐書》裡寫揚州的土貢,裡面就有”水兕甲“:揚州廣陵郡,大都督府……天寶元年更郡名。土貢:金、銀、銅器、青銅鏡、綿、蕃客袍錦……水兕甲……糖蟹、蜜姜、藕、鐵精、空青、白芒、兔絲、蛇粟、括姜粉。(《新唐書·志·卷三十一》)。
到了唐代,水兕甲還是一種揚州的土貢,和金銀,銅器,青銅鏡,藕什麼的一起進貢。照理說,又是和虎狼一起使用,常常用作酒杯,和金銀綿藕一起進貢,那應該是一個實際存在之物。
太上老君的坐騎下凡為妖之後的名字,诨号兕大王,一頭牛為什麼要叫這個名字呢?因為他不是普通的耕牛,而是犀牛。晉代學者郭璞在《山海經注》中說,兕形似水牛,青色一角,體重可達三千斤。根據史料中的記載,直到西漢時期,中原大地上都還有兕這種動物,又被稱為獨角黑犀牛。
如“虎兕出于柙 龜玉毀于椟中”這樣的詩句,就是現實世界動物的真實寫照。
隻是後來中原環境不再适合它生存,如今它已經成了瀕危動物,全世界不超過一百頭。
屈原《九歌》中曾經描述過一場戰争,其中的百越國軍士就是以獨角犀也就是兕的皮作為铠甲的。
《山海經·海内經》中記載,有獸曰兕,其狀如牛,蒼黑一角。蒼就是青色,難怪人們會認為老子的坐騎是青牛,其實是青黑色的犀牛,後來這種動物不存在了,人們就在現實中給它腦補成了青牛。
在《說文解字》這本嚴肅的學術書籍中,也有兕的身影,書中說:“兕如野牛而色青”。《詩經》中也有“匪兕匪虎,率彼曠野”這樣的明證,佐證兕在古代中國曾經是一種比較常見的動物。
我們再來對照兕大王的外形,就可以發現更多的證據。《西遊記》五十回說他“獨角參差雙目亮,頂上皮粗耳根黑。毛皮似青似靛,像是犀牛不照水,說是黃牛不耕田”。
很顯然,如果是普通的青牛,它就不可能是獨角,皮毛也沒有那麼堅硬;耕牛也沒有青色和靛藍這樣的毛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