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奔競請托、行為張揚、隐漏錢糧、好持公論、包攬詞訟是明後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會形象。紳士更結社成幫,黨同伐異;幹預行政,把持鄉裡;侵奪小民産業,橫行不法;肆意奴役鄉民;接受投獻,蓄奴成風;奢侈淫佚,醉生夢死。然而經過清朝初年哭廟案、奏銷案和虧空錢糧清查案等大案要案的打擊,江南士人的行為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紛紛放棄土田經營,深切明白以早完國課為第一要義,平時以足不入公門、不與外事為自處準則,士風軟熟化過程加緊發展,不少士子人生進取目标也發生轉向。時世不同,士風也随之不同,清代江南士人為官沒有明人張揚,其聲勢沒有明代江南仕宦顯赫,對于地方官府和地方事務的影響力,較之明代江南鄉宦也要小得多,士人的氣節和社會責任感比之明人更相去遠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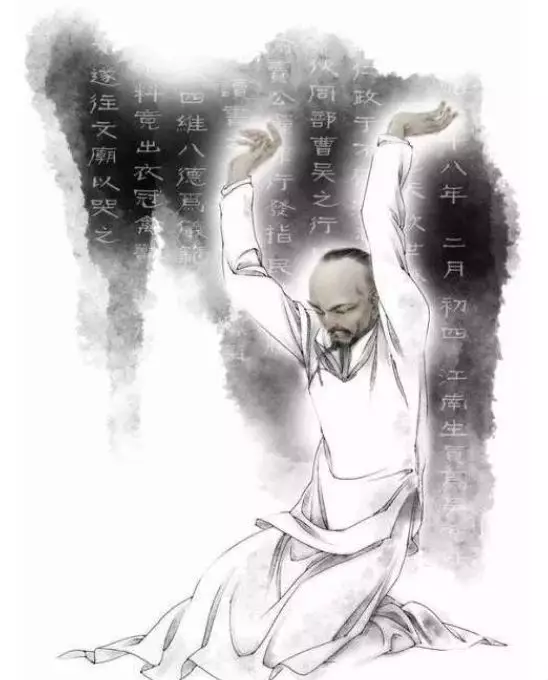
明後期至清前期,江南士紳在鄉居生活與地域政治方面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既有研究大多将明與清截然分開,明自明而清自清,因而未能揭示江南士人前後轉向的特色,更看不到影響其前後轉向的原因;①或者專論儒士群體,未能概括明清江南士人的全貌。探讨江南士紳由明入清取向的轉變及其原因,當有助于深化江南士紳和江南人文的研究。
<h2 class="cps_inner_info_title">
</h2>
一、明代江南士紳聲氣之張揚
明代後期江南的生員,實際上大多并不按照朝廷要求,在校認真讀書,學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事,而是利用本人免役的特權和高于普通平民的社會地位,混迹社會,不少人成為地方的邪惡勢力,幾乎無惡不作。對此,生員出身的明末清初大儒昆山人顧炎武曾總結道:“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于鄉裡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噪,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可見,出入公門,勾結胥吏,幹預行政,武斷鄉裡,操持輿論,是明後期生員的基本社會形象。有鑒于生員的惡習劣行,顧炎武甚至将生員與鄉官和吏胥,比作“天下之病民”的三種人,主張:“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②生員的乖張惡劣行徑,具體說來,大要有五:
一是奔競請托。萬曆時給事中浙江定海人薛三才說,士習日以澆漓,學政日以廢弛,挽救之舉“莫如禁奔競”,蓋因“彼頑鈍衰暮,藉衣冠為壟斷者無論,青年俊茂之士,率多投贽呈身,納交有司,歲時而薦筐篚,慶賀則緻帳詞者比比也。而江南為甚。有司不勝桃李之私愛,亦或嘔煦受之,因而開請托之路,長奔競之風。夫士為諸生時,已奔競若是,異時勢利熏心,安所不至。有司以提調為職,作興自有常典,而假此以樹私交,是誨之使競也,何可不嚴為禁戢也”。③按照薛三才的說法,當時士子大多交通官府,歲時令節緻贈行賄,而地方官府也喜樹立門牆,予以照拂,因而請托之路大開,奔競之風大長,尤以江南最為突出。
二是行為張揚。明後期,是江南士子行為最為張揚無所顧忌的時期。據說原來“吳中士習最醇,間有挾娼女出遊者,必托名齊民,匿舟中不敢出”。萬曆十五年(1587),南京兵部尚書太倉人淩雲翼,家居驕縱,毆打諸生,群情激憤,三吳士子進京伏阙訴冤,給事中、禦史連章彈劾,朝廷下旨逮系鞫治,淩被削職奪銜,行兇者其義子遣戍,人心大快,而“此後青衿日恣,動以秦坑脅上官,至鄉紳則畏之如伥子,間有豪民擁姝麗遊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④當然江南士子舉止粗野行徑惡劣,絕不始于此事件,而是長期潛移默化的結果。早在萬曆初年,太倉人王世貞就曾緻書大學士同鄉人王錫爵稱:“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嘩伍者,青衿之能卷堂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驕子矣。”⑤其實不少山人也隻是生員出身。此類澆漓行為,多系生員所為。生員之敢于罷學,挾脅上官,甚至連鄉紳也畏懼三分,實在也是官府長期慫恿巨室過于溺寵的結果。
松江地方文獻将生員入學前後異境視為迎送之變,稱:“初子弟遊庠及送科試,有司例用彩絨花披紅藥絹及紅旗一對,有乘肩輿者,亦有步行者。今新進送學,巨室宦家多乘馬張蓋,羅绮綢纻,彩旗百竿,簪花至用珠翠作金龍以耀首,親戚争以酒禮花币迎者,交錯于途。自郡齋至文廟谒拜始各歸家,設燕以待。鄉薦南歸,舟至西墅,迎接亦如之。讀書人才少進步,正當教以儉約,士大夫不宜以此訓子弟也。”⑥士子一旦入泮,家人親友就百般寵愛,備加呵護,迥超于前。嘉興地方文獻則論師生前後地位變化道:“國初,民間有以生員舉者,辄相怨詈,如服重役。蓋學規甚嚴,諸生俱宿齋舍,日夕課業有程,不得休沐,人以為苦也。其時師道也甚尊嚴……今師道日替,弟子視其師顧如侪偶,相谑者有之矣。”⑦明末清初,江南士子更被社會視為是非之人,敬而遠之。禦史陳玉輝說:“吾少時鄉居,闾閻父老,闤阓小民同席聚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斂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秀才行于市,兩巷人無不注目視之。”⑧
明後期,生員常常在鄉宦支援或慫恿下,公然篾視官府和官員,難堪甚至淩辱官員。萬曆時華亭人範濂就說:“士風之弊,始于萬曆十五年後,迹其行事,大都意氣所激,而未嘗有窮兇極惡存乎其間。且不獨松江為然,即浙直亦往往有之。如蘇州則同心而仇淩尚書,嘉興同心而讦萬通判,長洲則同心而抗江大尹,鎮江則同心而辱高同知,松江則同心而留李知府,皆一時蜂起,不約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變也。”⑨隆慶元年(1567),無錫知縣韓錦川,因某事不厭衆心,緻使諸生大嘩,當面唾罵。同年,常州知府李幼滋,被五縣諸生合擊,差點斃命。⑩萬曆四十四年(1616),原禮部尚書董其昌的宅第被焚,被地方官定性為“難發于士子而亂成于奸民”。崇祯七年(1634),複社領袖張溥與蘇州府推官周之夔論戰,緻書京官黃道周、蔣德璟等,生員則起哄張貼檄文驅逐周,迫使周改任吳江知縣,而生員又集中到吳江舉行排周運動,終使其不安于位而辭職。(11)兩起地方大事,皆因生員發起。最為突出者,可謂崇祯十五年無錫生員驅逐縣令一事。按慣例,明末無錫生員每年可免糧銀五錢,若無田需免,可直接領銀,稱為“扣散米”,生員的待遇相當優厚。知縣龐昌胤未能按時發米,五月初三日,生員杜景耀等約同學群哄縣堂,打碎堂上紗廚。龍教官令生員跪,生員也迫令教官跪。市民更毀碎縣令轎傘、執器,圍住馬素修家。龐縣令步行至西門下船出城,極為狼狽。故事,無錫縣令出西門,即不得複入。當時諸生大書一紙雲:“逐出無錫知縣一名龐昌胤,不許複入。”用殊筆傍豎,粘于蘆席上,作為牌子高擎,并将縣衙吏役笞散。龐昌胤出城後,城門即關閉。後龐悄悄入城,初五日下午,秀才又哄鬧縣堂。龐昌胤哭訴于巡撫,調為嘉定知縣。事隔很久,官方隻逮系帶頭鬧事的五六人,革去生員功名,竟不置重典。(12)無錫生員借錢糧好處未能及時發放,小題大作,竟然将朝廷命官堂堂知縣“驅逐”出境,目無法紀已極,而當局居然不予深究,從輕發落,江南生員氣焰嚣張可謂登峰造極。
三是隐漏錢糧。明後期,士紳隐漏賦稅錢糧,自是常态,人稱“一青衿寄籍其間,即終身無半镪入縣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屬,其所飽者更不可勝計,以故數郡之内,聞風猬至,大僚以及諸生,紛紛寄冒,正供之欠數十萬”。(13)松江一府,華亭人範濂記載,“自貧儒偶躐科第,辄從縣大夫幹請書冊,包攬親戚門生故舊之田實其中。如本名者僅一百畝,浮至二千,該白銀三百兩,則令管數者日督寄戶完糧……是秀才一得出身,即享用無白銀田二百畝矣”。(14)可見江南錢糧拖欠嚴重,與生員免役逃稅大有關系。清人形容明末江南生員逃稅漏稅行徑道:“明季廪生,官給每歲膏火銀一百二十兩。三科不中,罰為吏。五等生員,亦罰為吏。五年期滿,撫按考選,分别等次,以八九品未入流铨補,仍準鄉試。歲考等次,臨時發落。始知前後不先出案。又貧生無力完糧,奏銷豁免。諸生中不安分者,每日朔望赴縣懇準詞十紙,名曰‘乞恩’。又攬富戶錢糧,立于自名下隐吞。故生員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謠。”(15)生員不但自身漏稅,更包攬富戶錢糧,隐吞應納錢糧。
四是好持公論。明後期的江南輿論,是由鄉紳和生員制造和掌控的。崇祯中期嘉善知縣李陳玉說:“此中士習,矜尚名誼,與他邑不同,弟甚喜之。但憂其過于标表,或未底于粹耳。乃近來細察,衿尚固佳,引類聚哄,一概視為矜尚,美事則誤矣。”(16)明後期江南士子喜好集衆倡言是出了名的。清人陸文衡說:“吳下士子好持公論,見官府有貪殘不法者,即集衆倡言,為孚号揚庭之舉,上台亦往往采納其言。此前明故事也。”(17)把持公論的行為之一是造作流言蜚語嘲笑地方官,成為一時風俗。明後期,蘇州、吳江、松江、嘉興、無錫等地士子好為谑語,嘲諷守令。嘉靖時華亭人何良俊說:“松江舊俗相沿,凡府縣官一有不善,則裡巷中辄有歌謠或對聯,頗能破的。”(18)萬曆時華亭人範濂說:“歌謠詞曲,自古有之,惟吾松近年特甚。凡朋輩諧谑,及府縣士夫舉措稍有乖張,即綴成歌謠之類,傳播人口。”(19)清人董含記:“将吏茲土者,往往不能廉潔。有李正華者,小有才,矯廉飾詐,下車之日,行李蕭然,及其歸也,方舟不能載。有輕薄子投以一絕雲:‘吳地由來異郁林,歸舟壓浪影沉沉。不須更載華亭鶴,江上青山識此心。’”(20)吳江知縣祝似華,初到時以風力自命,禮部尚書湖州南浔人董份有田數萬畝在吳江境内,祝立意摧擊,不久因暮夜得賄,遂改初衷。民間即有詩傳誦道:“吳江勁挺一莖竹,才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幹梢,登時改節彎彎曲。”(21)故沈德符說:“至近日吳越間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辄以惡語谑之”,而“大抵嘲守令居多。”(22)這種公論,當然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而民意實際上是由生員等造作出來的。
五是包攬詞訟。明後期的生員,在民間訴訟中極為活躍,常常造事生非,興訟攬訟,覓取好處。沈德符說:“至民間興訟,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吳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語。”(23)時語“雇秀才打汝”,反映出生員在官司詞訟方面的優勢地位和惡劣行徑。
生員如此,較生員功名更高、社會地位更加顯赫的江南士大夫,更是氣勢非同一般。家居時,雖然也有人限制檢點,自重自愛,但絕大部分,特别是嘉隆以後的江南士大夫,則是暴橫霸道,為害一方。杭州人原來自诩,“仕者鹹以清慎相饬勵,多無田園宅第”,“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可萬曆時杭州府志的編纂者陳善卻說:“今士大夫居鄉者,高爵厚祿,身占朝籍,抗禮公府,風雷由其片言,或壟斷罔利,莫之敢争,煦之則生,噓之則枯,侵官浸訟,納賄千金,少亦足抵數吏之入,剝衆肥家,豈其微哉!”杭州鄉紳名聲稍佳,尚且如此,蘇松一帶,更為了得。華亭人董含的族曾叔祖董容概括松江府缙紳居鄉行為時說:“吾郡缙紳家居,務美宮室,廣田地,蓄金銀,盛仆從,受投谒,結官長,勤宴饋而已,未聞有延師訓子,崇儉寡欲,多積書,絕狎客者。”(24)明清時人論到其時的江南缙紳,幾乎衆口一詞,深惡痛絕,前述顧炎武将仕宦與生員列為天下病民的三種人中的兩種人,清人概而言之,“前明缙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林,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其立身行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齒”。(25)江南紳士家居行徑,歸納起來,約有如下數端:
一是結社成幫,黨同伐異。明末江南沿宋元舊習,結社成風。崇祯初年,松江有幾社,浙江有聞山,昆陽有雲簪社,蘇州有羽朋社,杭州有讀書社。各地文社均統合在複社的旗幟下,同聲相求,“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26)吳振棫說:“盟社盛于明季。江南之蘇、松,浙江之杭、嘉、湖為尤甚。國初尚沿此習。順治十七年(1660),從給事中楊雍建請禁同社、同盟名目。”(27)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理學名儒嘉興人張履祥回顧、總結明代江南士人結社之消極後果說:“士人勝衣冠,即無不廣交遊,談社事,浸淫既久,乃至筆舌甚于戈矛,親戚同于水火。予歎息而言,疇昔之日,數十人鼓之,數千萬人靡然從之,樹黨援,較勝負,朝廷邦國,無不深中其禍。政事之亂亂于是,官邪之敗敗于是,人心之溺溺于是,風俗之敝敝于是。今者,禍亂已極,一時人士不能懲創既往,力圖厥新,顧乃踵其失而加甚焉。”(28)
二是幹預行政,把持鄉裡。江南缙紳以其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影響力,幹預中央和地方行政,時時事事無不要展現其意志,維護其利益。
江南士紳影響朝政,早在萬曆中期東林學派講學,“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時已開其端。後來更集社結會,利用铨選官員的選人大權,在朝和在野互相輿援,大造聲勢,對中央行政施加各種影響。常熟縣民張漢儒就曾控訴東林骨幹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畏明論,不懼清議,吸人膏血,啖國正供,把持朝政,濁亂官評,生殺之權不操之朝廷而操之兩奸,賦稅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兩奸,緻令蹙額窮困之民欲控之府縣,而府縣之賢否,兩奸且操之”,劣迹多達58款。(29)言雖不無過激之處,所論卻多系事實。崇祯中期,宜興周延儒任内閣首輔大學士,複社領袖張溥認為時機已到,“欲盡用其黨人,而殺異己者,書二冊以進,延儒秘而藏之”。後來張溥死,周延儒才松了一口氣,說:“天如死,吾方好作官。”人驚問其故,周延儒将張溥所書二冊名錄出示座客道:“此皆天如所欲殺之人也,我如何能殺盡?”(30)張溥氣焰之張狂、周延儒應付之難度,可以想見。這些都是極為彰顯的事例。其實明代江南官紳平時出處行事類多如此。清初,葉方霭在朱家角鎮,洞庭商人許某出示吳中諸前輩手迹,其中董其昌手書多至百幅,“内數幅則自京所寄書也,皆家常瑣屑受賄請托語”。(31)真憑實據,所書皆記錄“受賄請托”之事。
在地方,士紳更是出入公門,左右掣肘,對官府和官員施以各種影響。萬曆時,趙南星将鄉官之害稱為天下“四害”之一,謂:“夫吏于土者,不過守令,而鄉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淩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32)天啟二年(1622)的狀元修撰文震孟,由其《文文肅公日記》所記,可知其緻仕在家,自天啟二年五月至天啟六年,幾乎每天忙碌不停,或出外與友朋相聚,讨論時局,或接待、訪谒、緻書地方官員,日記中時有“往谒撫台”、“報谒撫公”、“報訪二署邑”、“訪太尊”、“撫台來”、“撫公來”、“按台來”、“劉學師來”、“訪郡尊及吳縣公”、“往晤撫按道府”等記錄,(33)差不多所有地方官員均與其有往來。文震孟的事例,形象地說明江南官紳無論在朝在野,中央行政、廟堂大事,地方事務,都是他們時刻所系念的。崇祯時,松江地方文獻則稱:“缇帙之變,初鄉大夫諸生與郡縣交際絕少,近辄用冊葉、錦屏,冊詩則倩代作,以士大夫署名,或有摹石刻棗裝為墨帖者,計潤計工,率倍收之。一錦屏不下百人,而裝池之費,每計數十金,主者遍索授紀綱,紀綱因而為利,且藉此阿上官。遂有亡行者,身犯大垢,甘與金木為伍而不悔。”(34)崇祯初年當祁彪佳出任蘇松巡按時,同樣是那個複社領袖張溥,前往谒見,即“袖出一揭,乃蘇州各屬者,雲系名士”,要求予以照應,紳士吳偉業、賀王盛、賀鼎、徐憲卿、陸獻明、朱大烈、朱大治、莫俨臯、範允臨、沈彥威、蔣鐄、李逢申、趙士履、姜雲龍、李世祺、張肇林、談自省、施元征以及難以記憶者,都紛紛前往谒見請托,(35)演出了一幕幕生動的人情戲。請托之風如此熾烈,出面關說者如此位高爵顯,地方官員自然難以施展手腳。以緻有位知府将士夫幹請之書與山人詩卷、僧徒募緣之冊合稱為吳下“三厭”。(36)是以崇祯十五年劉宗周憤憤地說:“江南冠蓋輻辏之地,無一事無衿紳孝廉把持,無一時無衿紳孝廉囑托,有司惟力是視,有錢者生。且亦有釁起瑣亵,而兩造動至費不赀以乞居間之牍,至轉輾更番求勝,皆不破家不已。甚之或徑行賄于問官,或假抽豐于鄉客,動盈千百,日新月盛。官府之不法,未有甚于此者也。”(37)清乾隆後期生員顧公燮甚至認為,明後朝的江南鄉紳,“尤重師生年誼,平昔稍有睚眦,即囑撫按訪拏。甚至門下之人,遇有司對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喚,立即扶出,有司無可如何。其它細事,雖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38)鄉宦眼中并無官府,竟視公堂如私室,勢焰十分嚣張。是以,所謂士論民心,實皆士論而已,鄉紳之見而已。明後期的江南地方政權,一定程度上是操在這些有财有勢的鄉紳之手的。
涉及地方利益時,各地缙紳更與生員結成蠻橫勢力,幹預地方官府行政。萬曆時期嘉興府嘉善縣的争田鼓噪事件,可稱最典型事例。明代嘉興一府,各縣之間田地互相錯壤,即戶籍在此縣而田在他縣,尤以嘉善與嘉興和秀水兩縣之間最為突出。萬曆年間,三縣為交賦稅而長期形成沖突,到萬曆末年,延續30年未解的争田發展成鼓噪事件。萬曆四十四年,三縣知縣會勘田糧,四月二十六日,嘉善鄉宦五人到府衙,知府以查冊丈田之說與之辯論,鄉宦堅持依據嘉善之虧冊抽丈嘉善之虧田。二十八日,知府邀集三縣鄉紳在城隍廟集中,反複申明前說,令三縣會議具稿,傳示三縣鄉紳次第書押,隻有莊鄉宦不肯書押,漏下三鼓,各人散去,抽丈之議格而不行。五月初三日,嘉善錢鄉宦再次到府城,邀同吳知縣議事,并送上公述公書一紙,稱田不宜丈,冊不宜查。五月初六日,嘉善生員四五十人、豪民三四百人,先至知府衙堂喊冤,後到嘉湖兵巡道叫嚷,各級官員反複曉谕,诟谇如故,甚至打傷旗鼓手,打壞鄉宦門庭桌椅。初八日,嘉善沿街遍貼傳帖,聲稱道府聽信叛賊嶽元聲,本縣當圖大舉,先接吳知縣歸縣等。此次争田鼓噪事件,兵巡道佥事王重岱形容其“篾視法紀”的嚴重程度“恐夷虜不是過”,嘉興知府則稱其“兇橫暴戾,無複子民之分”,“猖獗之勢成,屑越紀綱,決裂名分,真宇内異變”,以緻提出辭職。在此事件中,嘉善鄉宦和生員的嚣張氣焰,堅持地方利益不依不饒,一再要挾府縣衙門,豪橫把持,目中了無法紀和官府之尊,使得嘉善知縣和嘉興知府先後提出辭呈。(39)這個争田鼓噪事件,其實質,誠如廖心一所說,“是兩個鄉紳集團的鬥争”,(40)充分反映了鄉紳濃重的地方利益行為。
三是侵奪小民産業,橫行不法。江南缙紳仗勢欺人,指使、縱容家人子弟奴仆侵奪田産,弱肉強食,刁鑽殘暴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而又隐漏納稅田畝,将應納賦稅千方百計轉嫁到小民頭上。按照松江鄉紳何良俊的說法,江南人直到憲宗成化朝時尚未積聚,自武宗正德朝開始,“諸公竟營産謀利。一時如宋大參恺、蘇禦史恩、蔣主事凱、陶員外骥、吳主事哲,皆積至十餘萬”,後來則一中進士之後,“而日逐奔走于門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處有莊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幹;或某人借銀幾百兩,歲可生息若幹;或某人為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礙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銀若幹,則欣欣喜見于面”。(41)而到嘉靖時,“競以求富為務,書生惟藉進身為殖生階梯”,“吳中缙紳士夫多以貨殖為急,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興販鹽酤,其術倍克于齊民”。(42)到隆慶時,巡按直隸禦史董堯封奏,查出蘇松常鎮四府投詭田1595470畝,花分田3315560畝。(43)萬曆中期,常熟知縣譚昌言說:“吳中士大夫田連阡陌,受請寄,避徭役,贻累闾裡,身殁而子孫為流庸者多矣。”(44)以緻萬曆中期華亭人範濂說,當時缙紳,“營營逐利,雖有陶朱猗頓之富,日事幹請,如饑犬乞憐”。(45)清乾隆時常州人趙翼說:“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缙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為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46)如常熟徐鳳竹,官至工部尚書,其孫蔭為部郎,“居鄉恣橫不法甚”,被縣官逮治。(47)如淮揚巡撫太倉淩雲翼,“家居驕縱,給事、禦史連章劾之”。(48)這些人的居鄉不法行徑,較之那些勢力更為顯赫的缙紳的巧取豪奪,隻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如嘉靖末年的内閣首輔華亭人徐階,“子弟家奴暴橫闾裡,一方病之,如坐水火”。應天巡撫海瑞與蘇州兵備道蔡國熙勒令徐階退田,二人反被徐階先後以勢以金唆使給事中劾論去職,以緻時人感慨道:“此一事也,見方正之難容焉,見法紀之澌滅焉,見家居之罷相能逐朝廷之風憲焉,見瑣闼之言官甘為私門之鷹犬焉。”(49)又如南京禮部尚書華亭人董其昌,三個兒子“素不加檢束,而仲尤甚。有幹仆陳明父子,更倚勢煽虐,鄉裡側目久矣”。(50)更有甚者,如無錫秦梁之子秦燈,與太倉王世貞之子王士骕、華亭喬敬懋之子喬相,自負貴介,挖空心思,詐人錢财,“或與百金,或數十金,不則目懾之曰:‘爾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筆剿汝矣’”。(51)宜興周延儒為大學士,陳于泰為翰林,二家子弟暴橫鄉裡,群眾至發掘周家祖墓,焚燒陳氏兄弟宅第。這批鄉宦惡少,兇神惡煞,實乃社會惡勢力。缙紳侵奪田産最常見的手法是逼迫勒令小民投獻,有的投獻雖出于自願,但都是缙紳豪橫欺隐的結果。徐階、董份、申時行、董其昌等缙紳占有的動辄數萬畝、數十萬畝膏腴田産,就是不擇手段從小民那裡劫奪過去的。明後期江南土地兼并形成高峰,也正是這些豪紳顯宦巧取豪奪的結果。
四是肆意奴役鄉民。缙紳賤視鄉間小民,頤指氣使,任意役使,“淞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多取自舊冢中,無足怪者。’”(52)可見缙紳自家中瑣事至興築工程,随意役使鄉民已成習慣。
五是接受投獻,蓄奴成風。明代仕宦享有蓄奴特權,他們更濫用這種特權,遠超法律規定大肆蓄養奴仆。華亭人範濂稱,“自鄉宦年久官尊,則三族之田悉入書冊……故一官名下,有欠白銀一千餘者”。(53)顧炎武論到江南士大夫蓄養奴仆之風時,又說:“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原注:……今吳中士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54)徐階、董份、董其昌家,投靠家奴皆達上千。所投靠者,表面上出于自願,多半卻是因為缙紳大戶獨多,享受優免特權,繁重的賦役負擔全部落在小民頭上,小民出于無奈而不得不投靠勢家以求庇護。如董其昌就是“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遊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55)董其昌宅第被鄉民焚毀,家财被掠。明清鼎革之際太倉、上海、嘉定、昆山、石門、金壇、溧陽廣及蘇松常嘉四府之地紛紛發生奴變,索契殺主,實在是缙紳地主長期作威作福的結果,咎由自取。明末江南奴變最為激烈,與當地豪門最為集中、蓄奴風氣最盛、馭下最為苛酷是有着必然聯系的。個别豪奴恃仗主人勢力,成為主人鷹犬,為非作歹,為所欲為。如宜興縣民周文攘、張瑞、劉甯、蔣美、胡成,都是本縣鄉官陳一教的義男;張鳳池、樊士章、張成等,都是鄉宦徐廷錫的義男。他們“倚藉主勢,收租勒索贈耗,放債逼寫子女田房,各卻蔽主釀禍,造孽多端”,(56)劣迹斑斑。事實上,不少豪強巨紳的萬貫家财,正是靠這些家人義男從細民處掠奪勒逼來的。
六是奢侈淫佚,醉生夢死。江南缙紳,宦囊既豐,又兼營市利,鲸吞小民脂膏,百般役使細民弱戶,積累起了巨額财富。身處繁華之鄉,又見過世面,因而講排場,擺闊氣,蓄優童,擁麗姬,精賭術,已屬尋常,甚者荒淫糜爛,追求畸形生活方式,了無讀書入仕人的氣味。如無錫俞憲,與談恺、安如山、秦瀚、王瑛五位鄉宦結成五老會,“樓船、鼓吹、園池、聲妓、服玩,使令之麗,甲于江南”,成天“沉酣聲色,廣取豔妓妖童”。秦瀚交結嚴世蕃,“極多奇味”。俞憲與安如山“皆有龍陽癖,既富且貴,以重資購得者,不可勝計”。如山孫紹芳也“大有祖癖”。(57)明後期各地士人多好此風,而以江南為甚。是以人稱“今吳俗此風尤盛,甚至有開鋪者”。(58)沈德符記時人風尚謂:“得志士人緻娈童為厮役,鐘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漸染于中原。乃若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傳遊壻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谑,以為佳事,獨北妓中尚有不深嗜者。”(59)
明後期的江南缙紳,以飲宴妓唱為樂事。如南京大手筆顧磷晚年家居,“喜設客,每張宴,必用教坊樂工以弦索佐觞,最喜小樂工楊彬,常詫客曰蔣南泠所謂消得楊郎一曲歌者也”。(60)如萬曆時禦史蘇州人錢岱,家居蓄養女優13人,女教師2人,“第宅之廣,姬妾之多,衣食供養之華且靡也,人人共見為富貴逸樂”,“優遊林下數十年,聲色自娛”。(61)整個江南士夫事實上常常沉浸在絲竹色場中。以緻明人沈德符說:“吳中缙紳,則留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坐命技,即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此習尚所成,亦猶秦晉諸公多娴騎射耳。”(62)缙紳居鄉放蕩,使得江南奢糜之風日甚一日。華亭人範濂說:“嘉隆以來豪門貴室,導奢導淫,博帶儒冠,長奸長傲,日有奇聞疊出,歲多新事百端。”(63)無錫人尤伯升也說:“吾邑本尚儉,始奢于馮龍泉、顧東岩,至嘉靖中,俞、談諸老争以奢侈相尚,而風俗益靡矣。”(64)湖州人李樂則說,風俗之陋,“作俑于大宦家”。(65)說到底,哪裡缙紳多,哪裡風俗就奢,可以說,江南風俗奢糜,正是由缙紳們一手導演出來的,其程度也正與缙紳勢力的興盛一緻。
二、清初懲戒士紳之大案要案
入清之後,江南士人仍然沿襲明末舊習,結社盟誓,大舉文會。時人稱:“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為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其最盛者,東越則甬上,三吳則松陵……松陵為東南舟車之都會,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66)蘇州有同聲社、慎交社、遙通社,吳江有驚隐社,婁東有端社、起韓、綠斐堂、七錄齋,浙西有澹鳴社、萍社、彜社、介社、觀社、廣敬社、澄社、經社等,“吳浙之間,各有部署……每社各數十人,以為倡和,推之各邑,無不皆然”。(67)無錫有雲門社,“名動遠迩”。(68)吳越之間的文社還互相聯絡,互為聲勢。越中文社名士百餘人,以駱複旦為領袖,“嘗率越士赴十郡大會,連舟數百艘,集嘉興之南湖”,與太倉吳偉業,長洲宋德宜等數十名士酬唱。(69)時人将當時的文社與明末文社比較,謂:“明季時,文社行,于是人間投刺,無不稱社弟。本朝始建,盟會盛行,人間投刺,無不稱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張為氣勢者,缙紳蹑屐問訊,亦無不以盟弟自附,而狂瀾真不可挽。”(70)似乎惡俗甚于明末。順治十年(1653),與明崇祯六年一樣,江南十府大社在虎丘大會。康熙十二年張履祥說:“今者,禍亂已極,一時人士不能懲創既往,力圖厥新,顧乃踵其失而加甚焉。”(71)結社風習直到康熙初年一如明舊。生員則仍然以撥弄是非為能事,熱衷于代人打官司。顧公燮謂:“康熙年間,男子聯姻,如貧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糾集打降,徑入女家搶親。其女必婿親扶上轎,仍以鼓樂迎歸成親,次日杯酒釋歡。又讦訟者,兩造各有生員具公呈,聽審之日,又各有打降保護。故曰打降之降乃行,非降下。善拳勇者為首,少年無賴,屬其部下,聞呼即至,如開行一般,謂之打行。今功令森嚴,此風不興矣。”(72)士紳劫奪小民弱肉強食,拖欠逃避賦稅如故,以緻稅糧逋欠多達上千萬石。
清廷為穩定在江南的統治,采取一系列極端措施整治士心,嚴懲偷漏賦稅行為。舉其要者,前後約有三大案。
一是哭廟案。順治十六年,朱國治就任江甯巡撫,索饋苛征,興起奏銷錢糧大案。新任吳縣令任維初,“開大竹片數十,浸以溺,示人曰:‘功令森嚴,錢糧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凡國課不完者日日候比,不必以三六九為期也”。(73)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一日,正是錢糧奏銷綦嚴之時,世祖駕崩哀诏至蘇,府衙設靈堂,巡撫、巡按率領屬官鄉紳哭臨三日。初四日,生員丁紫洄從府學教授程蒼翼處領得文廟鑰匙,生員倪用賓等到廟号哭,薛爾張作文,随而從至者生員百餘人,鳴鐘擊鼓,又至府堂,乘撫按皆在時,跪進揭帖,控訴任縣令濫用非刑,預征課稅之貪酷狀,相進而至者,更多達千人。巡撫大驚,下令左右逮治鬧事者,11人被擒。當時正好金壇有叛案,鄭成功北伐清軍失利于鎮江,朱國治乃上奏窮治。清廷派侍郎葉尼等四人鞫治,朱國治上疏紳衿抗糧,四出抄掠,貨賄器用,劫掠一空。有人同情被逮諸生,也被波及逮系,增至18人,俱着處斬,家産籍沒。這就是駭人聽聞的“枉法坑儒十八人”之哭廟大案。(74)哭廟案與錢糧奏銷案攪在一起,成為收拾江南士紳的開端。
二是錢糧奏銷案。關于奏銷案,當時人大多将其歸為江甯巡撫朱國治的暴政,說朱“因見協饷不前,創為紳欠,衿欠之法”,(75)或說“撫臣更立奏銷法”。(76)近人孟森先生和今人何齡修先生先後有文論述。(77)孟先生認為,當時江甯巡撫朱國治,因鄭成功兵入沿江列府,意所不怿,于是以逆案為名,任情荼毒江南士紳。孟先生又說:“整理賦稅,原屬官吏職權,特當時以故明海上之師,積怒于南方人心之未盡帖服,假大獄以示威,又牽連逆案以成獄。”何齡修先生在孟先生持論的基礎上,引述實錄所收上谕,專文考察浙江奏銷案,認為錢糧奏銷新例實際上是全國奉行的條例。兩人的研究,無疑均是符合史實的不易之論。結合興案者朱國治、上海人葉夢珠據當時蘇松常道奏文所述、華亭人董含所述和後來的昭梿所述,朱國治乃因當地紳衿拖欠錢糧嚴重,視為“抗糧”,出于錢糧考成,又意欲乘機懾服人心,乃釀成奏銷大案。朱國治謂:“吳縣錢糧曆年逋欠,沿成舊例,稍加嚴比,便肆毒螫,若不顯示大法,竊恐諸邑效尤,有司喪氣,催征無心,甘受參罰,苟全所家而已,斷不敢再行追比,撄此惡鋒,以性命為嘗試也。”(78)朱國治的奏疏,清晰地供認了他興起奏銷大案的動機。葉夢珠也謂:明末清初蘇松等地錢糧拖欠嚴重,守令往往因積逋罷官,“至順治之季,江甯撫臣朱國治無以支吾,遂歸過于紳衿、衙役。題參議處之令,先行常之無錫,蘇之嘉定,至十八年五月,通行于蘇松常鎮四府及溧陽一縣,所題陳明錢糧拖欠之由補入年終奏銷之例……奏銷一案,據參四府共欠條銀五萬餘兩,黜革紳衿一萬三千餘人”。(79)相關史料記載涉案人數雖微有差別,但均在13500餘人以上,牽連廣大。葉夢珠和董含的說法,在朝廷的谕旨可以印證。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世祖晏駕,是月二十九日,谕吏部、戶部:“錢糧系軍國急需,經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為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積逋,贻累後官;或系官役侵那,借口民欠。向來拖欠錢糧,有司則參罰停升,知府以上雖有拖欠錢糧未完,仍得升轉,以緻上官不肯盡力督催,有司怠于征比,枝梧推诿,完解愆期。今後經管錢糧各官,不論大小,凡有拖欠參罰,俱一體停其升轉,必待錢糧完解無欠,方許題請開複升轉。爾等即會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錢糧不完,或應革職,或應降級處分,确議具奏。如将經管錢糧未完之官升轉者,拖欠官并該部俱治以作弊之罪。”三月初一日,“定直隸各省巡撫以下州縣以上征催錢糧未完分數處分例”。(80)順治十八年三月初九日,上谕戶部:“近觀直隸各省錢糧逋欠甚多,征比難完,率由紳衿藐法,抗糧不納,地方官瞻徇情面,不盡法征比。嗣後著各該督撫責論道府州縣各官立行禁饬,嚴加稽察,如仍前抗糧,從重治罪,地方官不行察報,該督撫嚴察,一并題參重處。”(81)細繹皇帝上述兩則上谕,參閱清初人和地方官的記載,利用孟、何二位的研究,可知順治十七年,江甯巡撫朱國治有鑒于明末以來江南錢糧拖欠的現實,面對清廷足額征收田糧的要求,利用鄭成功北伐進軍江南的機會,以“拖欠錢糧緻誤軍需”事由條奏,嚴懲江南士紳的錢糧逋欠行為。清廷接受朱國治的奏請,戶部題有定例,在順治十八年頒發上谕,要求全國各地如江南一樣奉行查處。在前後過程中,江南因為賦稅定額最重,拖欠數量最多,紳衿人數又衆,足額征稅,既能滿足官員錢糧考成,同時又能摧折士氣,威懾人心,朱國治更特别殘暴,實行時又搞擴大化,大事株連,遂釀成褫革蘇松常鎮四府及江甯府溧陽一縣紳衿13500餘人之錢糧奏銷案。(82)
江南奏銷案,征收田糧之嚴,史所罕見。“凡紳衿欠糧者,無論多寡,一概奏請褫革,名曰奏銷”。(83)葉方霭的事例最為人樂道,即盛傳“探花不值一文錢”的昆山人葉方霭,因拖錢錢糧一厘(合錢一文)而被褫革一甲探花功名,(84)認為他确實因欠一文稅糧而遭黜革。實際上,依據葉方霭後來的申訴,他家應稅官田329畝,計稅銀44兩4錢6分零,順治十七年分實完稅兩已有46兩1錢5分5厘,并有完銀印票為證,不但未曾拖欠,反而多交了銀1兩6錢多,隻因奸書徐甯宇朦開他家欠銀一厘,是以被誣懲處。(85)多交了錢糧,隻要誣稱拖欠,就被涉案,而且不問青紅皂白,即予黜革,可見實行之嚴酷。
清廷在江南改變前明做法,足額督征田賦錢糧,嚴懲拖欠錢糧的士紳,既制定條例,推向全國,江南地方官更切實實行。也就是說,嚴懲拖欠錢糧,雖以奏銷案為最大焦點,而并未從此結束。順治十八年十月,韓世琦繼任江甯巡撫。據他題奏,“履任後,即将所屬江甯蘇松常鎮五府順治十八年分未完錢糧嚴督催征,仍一面将紳衿三戶有無挂欠責令各道府确查,造冊遵例奏銷”,據呈報全完後,“猶恐各州縣官徇庇不實,又經駁核,複據呈送各州縣紳衿衙役全完印結前來”。(86)奏銷案後,江南地方官切實遵照谕旨,嚴督催征錢糧。康熙二十五年,趙士麟任江蘇巡撫時,“用法嚴峻,意在鋤強去暴。一時勢惡土豪,剪除殆盡”。(87)直到康熙中後期,由江蘇巡撫宋荦所奏可知,地方官每至奏銷年限,“非不加意嚴催,以期賦完饷裕”,而因為江南蘇松常鎮财賦重地,歲征銀米特多,力難全完,以緻“經征經督各官降調接踵”。(88)奏銷案後,官府嚴格催征錢糧,長期力行不辍。
三是雍正時清查虧空錢糧案。順治末年奏銷案和哭廟案是利用賦稅錢糧打擊江南士紳的第一輪,第二輪即是雍正時清查虧空錢糧案。清查虧空并不限于江南,但江南拖欠錢糧最多,清查虧空影響也大。康熙後期,錢糧征收似乎較前稍為寬松,錢糧拖欠也就日益嚴重起來。江南數府,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錢糧積欠多達一千餘萬兩。雍正五年(1727),朝廷派遣戶部侍郎彭維新赴江蘇清查。彭在兩江總督尹繼善等人配合下,隻查拖欠,不管催征,“悉心查察,一一得實,俾官侵不混入吏蝕,吏蝕不混入民欠,民欠不混入官侵吏蝕”。(89)其做法原來與順治末年相似,“逮捕追比無虛日”,(90)後來似乎稍為寬松,将官侵吏蝕和實系民欠差別對待,并“不妄戮一人”,(91)不事株累,查出“官侵吏蝕四百七十二萬餘,民欠五百三十九萬餘”。(92)實際逋欠在民的錢糧,比例還是高過官侵吏蝕,說明當時江南士紳對如期足額完納錢糧又有所松弛,當然也說明江南的賦稅定額确實高出了能夠承受的能力,以緻在雍正、乾隆年間朝廷兩次減低蘇松兩府賦稅征收定額。
雍正初年大規模清查積欠錢糧後,江南士紳才進一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更加遵守法度,率先輸納。乾隆十一年,江蘇巡撫陳大受奏報說:“但江蘇錢糧,從前舊欠最多。自雍正年間清查之後,積弊已除。”(93)乾隆十二年,皇帝上谕:“從前各處鄉紳,侍勢武斷,淩虐桑梓,欺侮鄰民,大為地方之害。及雍正年間加意整饬,嚴行禁止,各紳士始知遵守法度,循分自愛,不敢稍涉外事。”(94)次年,署理兩江總督策楞上奏說:“臣等伏查,江蘇各屬,财賦甲于天下,而錢糧積欠亦甚于他省。其間役侵民欠,弊窦多端。自雍正年間奉旨清查之後,奸胥玩戶,始知儆惕,侵欠之風,得以少息。”(95)乾隆十四年,兩江總督黃廷桂也認為,當時“紳衿大戶,查現登仕籍者,無不遵奉功令,率先輸納,惟有名列衿監及捐職家居之輩,恃有護符,專以抗延為能事”。(96)乾隆後期的蘇州生員顧公燮也認為,江南紳衿勢焰嚣張,至康熙時仍沿此陋習,“迨我世宗憲皇帝整綱饬紀,一洗從前積習,紳衿皆知斂迹。非公不至,絕無坐大轎者矣”。(97)種種說法表明,在順治末年錢糧奏銷案特别是雍正年間的錢糧清查後,江南士紳雖然仍有人不知限制,但較之以前,及時完納錢糧的情形大為好轉。
三、清前期江南士風之轉變
随着政局漸趨穩定,江南地方官對士人的打擊接二連三,輔之以禁革文社和整頓風習之舉,(98)明末以來長期受到抑制的官氣逐漸鸱張,士紳張揚之氣迅速低落。持續不斷的三大案,對江南士紳人身、錢财以緻心理上的打擊極為嚴重,加以明史案等文字獄案,嚴禁結社和懲戒朋黨等措施,以及清廷對江南士大夫在打擊的同時,又百般籠絡、恩寵、眷顧和優厚,是以江南士人不獨足額交納賦稅的意識較前明确,而且從意志、心态到行為各個方面,較之以前有了根本的轉變。具體說來,約有數端:
一是奏銷等案使江南士紳紛紛放棄土田進而改變地權所有。江南田賦本重,官員錢糧考成嚴厲,征賦铢锱必較,官府小題大作,逃賦漏稅必遭嚴懲,因而整個江南以田為累。談遷說:“今江南溫室,或不能飽其孥,罄宅殚田,鬻子女而填囹圄,指不勝數也。蘇、松、嘉、湖,夙号腴畝,價逾十金,近委以與人,不得下直。哀哀生民,始困于明季,劇于今日。”(99)褚人獲說:“沈啟南(周)詠田字雲:‘昔日田為富字足,今日田為累字頭。拖下腳時成甲首,申出頭來不自由。田安心上長思想,田在心中慮不休。當初隻望田為福,誰料田多疊疊愁。’康熙初,吳中田産,皆應其言。”(100)黃與堅說:“故自早征之法嚴行以來,民無不破家離屬,以田為禍本,而亟亟以去之。夫田,民之是以為安也,盡力以取之,使之輕于去其田,而害将何所底。”(101)顧公燮認為,奏銷案後,“富人往往以田為累,委契于路,伺行人拾取,遽呼之曰:‘田已屬爾,我無與矣’”。在松江,“國初曹冷民,幼苦踐更,田畝悉書白券與人。李複興令婁,冷民作詩并書授之,宛然鄭監門圖也。及詳定均賦,乃悉取田籍焚之,曰:‘令子孫勿作汶陽想耳。’”(102)“鄉農以田為命,故尺寸動必相争,然亦各有其時。長老雲:‘自萬曆中年,嘉邑折漕,歲複屢稔,田價驟貴。至崇祯大祲,甚有以空契與人而不受,或遺之地,行者拾之,遂向追取糧饷。國朝順治年間,棉花倍收,花價又昂,田之棄于人者,無不翻贖,動至結訟。及康熙初,災祲連年,邑令比糧嚴酷,昔所買之田,不索直而還之,其人猶不受。’”(103)後人追溯當日情形也謂:“故當日多棄田而逃者,以得脫為樂,賦稅之慘,未有甚于此時者也。”(104)在浙江桐鄉縣,“桐邑瘠薄,近來紳士之産耗廢甚多,半為上農所得,半為市儈所有,是以佃戶益恣橫無忌”。(105)
如武進人邵長蘅,奏銷案被黜生員功名,心有餘悸,荒不擇路,急忙将祖遺田産送人。其《青門簏稿·與楊靜山表兄第二書》謂:“先人贻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間為某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隻白送與人耳。昨陳生來,辱垂谕:‘士君子制行不可好奇,恒産不可無。’非老成忠告某安得聞此言?顧某之為此,亦自有說。私念先府君、孺人與某極遲,又獨子,奇愛之。稍長略讀書識字,亦望稍有樹立。橫遭廢斥,此事便已。竊見兩年來,新法如秋荼凝脂,縣令如乳虎,隸卒如猘犬,書生以逋賦笞辱,都成常事。某實不忍以父母遺軀受縣卒擠曳入訟庭,僥酷吏裸體受杖,乃憤而出此,為纾禍計耳。然緣此得家累漸輕,故吾亡恙。罂有十粟之儲,家無打門之吏,菜羹啜水,讀書自娛,亦未必非息黔補劓之道也。緣雪兄長愛我之切,敢縷奉聞。”又如上海“新場儲鼎芳,有田三千畝,以欠糧監比;陸方中,田有數千,棄家遠遁。類此指不勝屈。時有以田為累,畝值銀四五錢。尚無售者”。(106)清代前期江南殊少明代後期那種田産跨州連縣的大地主,當與此錢糧奏銷大案後的地産所有權轉移大有關系。
二是錢糧奏銷和清查慘痛的教訓,使得江南缙紳以早完國課為第一要義。康熙九年,太倉王時敏家叔侄同登兩榜,王時敏“營魂回駭,夢寐不安”,以敬畏之心寫下家訓,其中有:“早完國課。方今田賦功令最急,苟有逋懸,禍亦最重,此天下皆然,而江南為甚。吾家清白之遺,家無長物,各房析箸時,惟分授田畝,贻之以累。當此春月開征,先期賠墊,鬻田路絕,無貸無門,且頭緒多端,以赤手四應,剜肉醫瘡,良為劇苦。然既有田在籍,雖膏枯髓竭,催科自難寬免,輸将豈容暫延。宜主人與管數家人時刻提心在口,殚思慮以籌畫,焦唇舌以督催,捃拾經營,陸續投納。完過随索印票總冊,照數填明,庶可杜移易飛灑之弊。乃家人輩往往吝惜小費,圖逸目前,事急則張皇失措,稍緩便不複經心,惟以遮掩欠數那延時日為能事,主人亦以窘困莫支暫圖休息,姑且聽之。不知完糧究不可遲,積累愈增繁重,譬如養癰,終必潰敗,所謂漏脯救饑,鸩酒止渴,謀身适以自戕,即至愚所不為也。惟是新舊相仍,追比殆無虛日,無可搜尋枝梧。田租雖微,猶必少藉牽補,決宜于秋成之後,計取所入,铢積寸累,盡以輸官。而家中日用,人事應酬,凡百務從節啬,切勿輕以租入用散,則雖箪食瓢飲,衣穿履決,而身心輕快,魂夢俱安,較之日夕驚憂者,所得孰多!使不然,而秋冬所入,随手用盡,一入新年,枵然赤立,數月間征比追呼,為期甚遠,粉骨難支,必至敗壞,不可收拾矣,可不為深慮乎?且有田供賦,固臣民通義,毋容逋緩,況吾家新登甲第,列在缙紳,而下同頑戶觀聽,亦甚不便。眉公先生曰‘士大夫居鄉,以早完國課為第一義’,誠為至言,所當時刻書紳,雖力有不及,而心竊自勉者也。”(107)王時敏此番語重心長之言,将江南士人經受奏銷案打擊後的恐懼惕息心理描摹得極為形象透徹,最具典型意義。葉夢珠也總結道:“自是而後,官乘大創之,十年并征,人當風鶴之餘,輸将恐後,變産莫售,黠術囗囗。或一日而應數限,或一人而對數官,應在此而失在彼,押吏勢同狼虎,士子不異俘囚……故當日多棄田而逃者,以得脫為樂,賦稅之慘,未有甚于此時者也。”(108)地方文獻至于總結其情形道:“富厚之家踴躍急公,輸将恐後。”(109)這種情形,在明後期是根本看不到的。
三是三大案的摧折使江南士人内斂自檢,以足不入公門不與外事為自處準則。地方文獻稱:經過奏銷案的打擊,江南士紳“半歸廢斥,大都以名義自處,雖登兩榜、官禁林者,卒安貧困守,或出入徒步,不自矜炫”。其地位也較明代一落千丈,所謂“裡巷狡猾不逞之徒見紳士無所畏避,因淩轹之,紳士亦俛首焉。又風俗之一變也”。(110)松江一府,原來兩榜鄉紳,出入必乘大轎,前呼後擁,“今則缙紳、舉、貢,概用肩輿,士子暑不張蓋,雨則自擎”,(111)頗知限制。“康熙以來,科第甚盛,士大夫當官多清正自守,居鄉不事幹谒,屏衣服輿從之飾,引掖後進,唯恐不及”,(112)出現了迥然不同于明代的景象。士人不但不敢幹預地方行政,或者交結官府,反以不涉公門自勵。蘇州一地,同樣如此。地方文獻稱:“明季士大夫好持清議,敦氣節,重名義,善善同清,惡惡同濁,有東漢黨锢諸賢之風,其小人亦慷慨慕義,公正發憤,然或時捍法網。本朝初載,遺風猶存,近數十年來缙紳先生杜門埽軌,兢兢自守,與地方官吏不輕通谒,或間相見,備賓主之禮以去。學宮士子多讀書自好,鮮履訟庭。”(113)前後情形迥異。士人個體,也自我限制,循規蹈矩。順治進士蘇州人顧予鹹,任過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因哭廟案差點被絞,奉旨複官,“尋入以奏銷案,竟落職”,自是居鄉,“風采益厲,忌者亦遂莫能難也。既罷官,無所施設,惟以行己矜式于鄉”。(114)翰林學士吳縣人汪琬奏銷案時奪二官,後休假鄉居,閉戶著述,不交世事,有居鄉清正之譽。奏銷案中降調的探花昆山人葉方藹,清操夙著,據說家無餘财,告老歸鄉時,有人誣告他居鄉不法,康熙帝讓江蘇巡撫複核,巡撫以鄉評之實奏告,确實如皇帝對他的印象鄉評甚好。乾隆進士蘇州人吳雲,官至山東彰德知府,退官後裡居不與外事。錢塘人大學士梁詩正之子、本身仕至侍讀學士的大書法家梁同書,名德日盛,地方大吏就任必定谒見他,他則“一報謝而止,終未嘗有所幹請”,自奉十分節儉,據說裘葛無備套,帽子數十年不換,“出行市,人往往環視匿笑”。(115)經過曆次打擊,士氣低沉,而官府的威嚴得到重塑。翰林學士韓英就曾論道:“自鄉先生之氣不伸而清議不立,大小吏益無所畏憚而治日壞。”(116)官府也名義上與鄉紳保持距離,不相交往,“遂有鄉紳與現任官不許接見之禁。上自督撫,下逮郡邑,皆不相聞問。所與造膝咨訪者,不過奸胥賤隸而已”。(117)清前期,一改明末的官弱紳強而為官強紳弱。概而言之,清代前期江南士紳整體而言在地方官府的影響已極為有限。這就導緻清代與明代江南士紳對地方事務特别是地方政治完全不一樣的态度和結果,江南士紳的力量到中期後才有所擡頭。明後期以來一直興盛的結社講學之風也戛然而止。哭廟大案後,人稱“講學之社,自是絕矣”。(118)
四是在經曆一系列大案、要案,包括江南、浙江奏銷案摧殘後,江浙士風的軟熟化過程加緊發展,(119)甚至告誡子弟切勿為士。康熙八年,歸莊主張戒子弟勿為士:“士之子恒為士,商之子恒為商。嚴氏之先,則士商相雜,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然吾為舜工計,宜專力于商,而戒子弟勿為士。蓋今之世,士之賤也甚矣,自京朝官外吏以至諸生,陷之以升頭逋賦,辄禁锢;鄉會試中式之士,久滞不選,而投誠者辄得官,薦紳制于賤隸,兩榜不如盜賊,今日為士之效如此,尚欲令子弟磨墨吮毫,作經義策論幹進之具,以為硯羞,此乃善用先生之傳器者也。”(120)不少士人轉而消極灰心,放棄科舉道路,那些劫後得保餘生的人大都隐居或教書終身就是明證。(121)
五是清廷打擊、限制與籠絡、眷顧兩手的交替運用,使得不少士子人生進取目标發生轉向。清初蘇州地方文獻标榜:“吳郡人文自有制科以來,名公钜儒先後飚起,皆崇尚正學,言坊行表,為後進倡率,士子讀書談道,喜為标榜重譽而矜節,時秉先正之遺規焉。”(122)“重譽而矜節”之淳厚風氣,自然起始于清初江南士子屢受打擊之後。
松江人董含,出身世家,順治十八年二甲進士,時年三十六歲,旋以江南奏銷案被黜,放歸田裡,“自以盛年見廢清時,既已嘿不自得,而其家徒四壁立。于是益修無憀,幽憂侘傺,酒酣以往,悲歌慷慨,遇夫高山廣谷,精藍名梵,喬松嘉卉,草蟲沙鳥,凡可以解其郁陶者,莫不有詩”。(123)從此官場少了一個顯宦,而詩壇多了一個行家。其弟董俞,已為舉人,以逋賦微眚見斥,“于是棄去帖括,究極于風雅正變之故,爰及漢魏,下訖三唐,朝齑暮鹽,蕭然如後門寒畯,而其詩亦闳深涵演,非複專家小乖所敢望”。(124)與其兄一樣,改而走上詩藝之路。後來江南文才源源湧出,而隻有文壇巨擘專門名家,卻絕少思想大家,追根溯源,無疑與此大有關系。
江南士人即使如願以償科第入仕,也大多不敢議論時事,“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四以緻平時出入,因為“功令嚴峻,紳士莫敢啟口及時政”。(125)不言時政,則将精力集中在考據等遠離政治的所謂學問上。現有研究表明,“從事考據的頂尖人物主要都是來自長江下遊核心地帶的科甲之士;有人對180種重要考據學著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差不多有90%的作者是江南人,有92%的作者得過科舉功名,超過一半的人(53%)是進士”。(127)說明江南士人的精力多半耗費在考據事業上了,清中期江南考據成就顯赫,與此背景實有關系。故清末民初學者劉師培确切地比較清代士人和明代士人截然不同的為學旨趣道:“清代之學迥與明殊,明儒之學用以應事,清儒之學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喬,清儒棄而濕。蓋士之樸者,惟知誦習帖括以期弋獲,才智之士憚于文網、迫于饑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汨于無形,加以廉恥道喪,清議蕩然,流俗沈昏,無複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榮辱,由是儒之名目賤,而所治之學亦異。”(128)按照他的說法,較之明儒不計得失剛直不阿,以經世之用為旨歸,清代士人則是明哲保身,以至迹近猥瑣,以官位崇卑為榮辱。縱觀清代江南進士官員的舉止言行,劉師培的描述是相當貼切的,隻是清儒廉恥道喪并不始于文網之嚴,早在錢糧奏銷案發時就發其端了。
清廷在賦稅錢糧、政治措施等方面的一系列打擊,使得江南士人的行為取向發生了根本變化。乾隆《長洲縣志》評論道:“吳下士大夫多以廉恥相尚,缙紳之在籍者無不杜門掃軌,著書作文,以勤課子弟為務,地方官吏非有公事不輕通谒,蓋素所矜惜也然也。士子讀書鹹知自好,有終身不履訟庭隻字不入公門者。富厚之家踴躍輸将,惟恐後時。此固教化之隆,亦足以觇風俗之厚矣。”(129)在籍缙紳矜惜名譽,惟以著書作文為業,而杜門不出,絕迹公門,這在明後期是難以想象的;士子讀書自好,終身不履公庭隻字不入公門,也隻有在清前期才能看到;富厚之家交納賦稅惟恐後時,當然隻是奏銷案後的現象。該志客觀叙述了江南士人迥異前代的風貌,而顯然有意掩隐了其前提背景。
江南士人保守本分的同時,等而下之者,更喪失了應有的風骨節操,成為政治和官員之附從,随形逐影。哭廟案、奏銷案後,董含總結當時士習道:“迩來士大夫日賤,官長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備極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禮獻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輩風氣愈盛,視為當然,彼此效尤,恬不為怪。”(130)官長地位日崇,士子地位日卑,奔競請托之風必然興盛。葉夢珠描述松江士風前後變化道:“吾松士子,昔年無遊學京師者,即間有之,亦不數見。自順治十八年奏銷以後,吳元龍卧山學士始人都援例入監。癸卯、甲辰,聯登科甲,選入庶常。其後遊京者始衆,其間或取科第,或入資為郎,或擁座談經,或出參幕府,或落托流離,或立登朊仕,其始皆由淪落不偶之人。既而缙紳子弟與素封之子繼之,苟具一才一技者,莫不望國都而奔走,以希遇合焉。亦士風之一變也。”(131)葉夢珠不經意間透露出重要的資訊:江南士子經過奏銷案的打擊,在進入官場前已在不擇手段鑽營奔走,喪失了知識分子應有的自身尊嚴。乾隆時無錫人黃卬對清代江南士人的總體評價是:“今科名日盛,列谏垣者有人,居九列者有人,百餘年來從無有抗權幸,陳疾苦,谔谔不回如古人者。雖謹慎小心,不敢放縱,要之,保位安身之念,周其胸中,久不知有氣節二字矣。故邑志于本朝先達,政績可以鋪張,即理學亦尚可緣飾,惟氣節不可強為附會。”黃卬還說:“前明邑紳之賢者,敦氣節,崇理學,今皆無之,其奢侈豪縱及奴仆之肆橫,今亦罕聞。”(132)士人群體失語,完全放棄了他們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針對士人不講節概的風氣,乾、嘉時金壇人段玉裁深有感慨地說:“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之學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故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133)不治宋學,不講義理,專治漢學,就像明人顧憲成所說,官辇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退居林下念頭不在世道上,立身處事,自然談不上有什麼節概。這樣的人進入仕途,是很難會有社會責任感的。
士人不講節概,沒有骨氣,出處行事沒有了顧炎武所強調的廉恥感,也就必然是貨賄是崇。時人董含感慨道:“曩昔士大夫以清望為重,鄉裡富人,羞與為伍,有攀附者,必峻絕之。今人崇尚财貨,見有擁厚資者,反屈體降志,或訂忘形之交,或結婚姻之雅。”(134)可見其時的江南士人,賈儒者比比皆是。乾隆二年恩科狀元官至大學士的金壇于敏中,其貪墨在乾隆前期就是出了名的,而且因為位高權重,還惡化了整個官場風氣。稔熟乾、嘉士風的天潢貴胄昭梿就說:“自于、和當權後,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135)以著名史評《十七史商榷》奠定身後文名的乾隆進士嘉定王鳴盛,時人王昶作傳谀他為“一介不取”,《清史稿》本傳贊他發迹後儉樸如寒素時,實則是個不太為人知的貪欲之徒。有記錄:“王西莊未第時,嘗館富室家,每人宅時必雙手作摟物狀。人問之,曰:‘欲将其财旺氣摟入己懷也。’及仕宦後,秦诿楚,多所乾沒。人問之曰:‘先生學問富有,而乃貪吝不已,不畏後世之名節乎?’公曰:‘貪鄙不過一時之嘲,學問乃千古之業。餘自信文名可以傳世,至百年後,口碑已沒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猶自在也。’”(136)王鳴盛自出道前到高官盛名後,貪欲之心一直熾烈,而且辯護得那麼振振有詞,那麼周密清晰,底氣十足,我們很難相信這些話居然會出自一個學術大師之口。口碑甚佳的名人王鳴盛如此,其他名聲欠佳的士人其行徑更可想而知。氣節敗壞,江南士人是要負相當責任的。
時世不同,清代江南士人為官沒有明人張揚,清廉儉樸者也複不少,其聲勢沒有明代江南仕宦顯赫,對于地方官府和地方事務的影響力,較之明代江南鄉宦也要小得多,士人的氣節和社會責任感比之明人更相去甚遠,江南士人漠視社會責任,但是平時出處行事講究聲色奢華卻一如明人,而更加講究奢侈優雅。清前期,人稱蘇州缙紳有三好:“曰窮烹饪,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間矣。”(137)無錫士紳則“以賭博為公務,非此無以度餘日”。(138)清中期常輝論江南風尚道:“近日士大夫最尚窯器,愈舊愈佳,取其形象古樸,火氣盡除耳。其值幾等于金玉,非大有力者不能得,且官哥汝定,非深有識者莫之辨……人情凡厭故而喜新,至于字畫玩器,反尚故。故江東風俗,凡贊賞物,莫不曰舊。”(139)終日講究此三者,無視社會現實,毫不關注日益下降的群眾生活,卻在官僚圈内十分吃得開。此三者,實際上任何一項都須财力雄厚者才能講究。清代江南士人官高名氣大,宦囊豐,各種無形收入多,有實力崇尚此道。士人如此所思所行,與社會現實、民生日用已相距日益遙遠。
直到後來,在豐亨豫大的清代盛世,江南士人鄉居行徑優于明,而社會責任感也大遜于明,因為漠視社會現實,遠離政治,可以潛心學問,無論經學、詩文、史評,還是天文、輿地、國小、音韻,乃至金石、骨董,江南士人皆能發揚光大,遠超明人。然而江南士人群體,在清代盛世,既缺少像明後期東林學派那樣關心社會現實的人,也缺少像明末徐光啟、張履祥那樣關注地方發展的人;在中西沖突、社會動蕩的道、鹹、同年間,既缺少像林則徐那樣苟利國家不計生死的社稷忠臣,也缺少像曾國藩、左宗棠那樣振衰起頹、力挽狂瀾的“中興”功臣;在新舊交替、民族存亡的晚清時期,既缺少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倡導改革變法的思想理論大家,也缺少像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那樣的熱血志士。清代江南士大夫是盛世的良臣,而非衰世的能臣,雍容華貴,宏篇巨著,增添絢麗的華章,是其所長,而開拓進取,力挽狂瀾,卻往往難見其人。追本溯源,與前此江南士人的遭際和清廷的軟硬措施兩手政策大有關系。
注釋:
①相關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日本學者岸本美緒的《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年)和山本英史的《清朝の江南統治と在地勢力》(參見岩井茂樹編:《中國近世社會の秩序形成》,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年),前者着重探讨明清之交江南士人的動向,後者探讨以衙蠹和紳衿為代表的地方勢力在清初的實态,富有學術價值。
②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2-23頁。引文中“胥史”當作“胥吏”。
③薛三才:《薛恭敏公奏疏》卷之二《禮垣·申饬學政疏》,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年影印本,第131-135頁。
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二《督撫》“海忠介撫江南”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556頁。
⑤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三《山人》“山人愚妄”條,第587頁。
⑥崇祯《松江府志》卷七《俗變》。
⑦天啟《海鹽縣圖經》卷四《方域篇》。
⑧陳玉輝:《陳先生适适齋鑒鬚集》卷四《規士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82冊,第102頁。
⑨範濂:《雲間據目抄》卷二《記風俗》,《筆記小說大觀》第13冊,揚州:江蘇廣陵書籍刻印社,1983年影印本,第8頁
⑩參見黃印:《錫金識小錄》卷四《司牧·手搏諸生》,光緒二十二年刻本,第8頁。
(11)參見陸世儀:《複社紀略》卷二,見《中國内亂外禍曆史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46年,第209-214頁。
(12)參見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一八,崇祯十五年,“無錫諸生逐令”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37-338頁。
(13)佚名:《研堂見聞雜記》,見《中國曆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第294頁。
(14)範濂:《雲間據目抄》卷四《記賦役》,第4頁。
(15)顧公燮:《丹午筆記》“明季生員”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8頁。
(16)李陳玉:《退思堂集》卷一一《奏牍·複李學博生虞》,崇祯刻本,第36頁。
(17)陸文衡:《啬庵随筆》卷三《時事》,轉引自何齡修《浙江奏銷案》,見氏著《五庫齋清史叢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18)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一八《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61頁。
(19)範濂:《雲間據目抄》卷二《記風俗》,第6頁。
(20)董含:《三岡識略》卷三“謠谶”條,沈陽:遼甯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9頁。
(21)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六《諧谑》“吳江谑語”條,第669頁。
(22)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六《諧谑》“松江谑語”條、“蘇州谑語”條,第667、668頁。
(23)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二《督撫》“海忠介撫江南”條,第556頁。
(24)董含:《三岡識略》卷四《補遺》“讀書種子不可絕”條,第95頁。
(25)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上“明季紳衿之橫”,《涵芬樓秘笈》第2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年至1921年景印本,第5-6頁。
(26)顧公燮:《丹午筆記》九七條“文社之厄”,第88頁。
(27)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二五,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27頁。
(28)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六《紀交贈計需亭》,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90頁。
(29)參見《張漢儒疏稿》,見《虞陽說苑甲編》第5冊,虞山丁氏1918年鉛印本,第1頁。
(30)周同谷:《霜猿集》卷二《二冊書成注複删》、《月堕西江歌舞闌》二詩注,《虞山叢刻》甲集,1916年至1920年常熟丁氏刻本,第4頁。
(31)嘉慶《珠裡小志》卷一七《雜記上》,《上海鄉鎮舊志叢書》第7冊,第228頁。
(32)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卷一九《敬循職掌剖露良心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68冊,第569頁。
(33)文震孟:《文文肅公日記》,稿本。
(34)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風俗·俗變》。
(35)參見祁彪佳:《按吳尺牍·與倪三蘭》,見《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930頁。
(36)馮時可:《雨航雜錄》卷下,《四庫全書》子部第173冊,第343-344頁。
(37)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七《文編四·責成巡方職掌以振揚天下風紀立奏化成之效疏》,第52-53頁。
(38)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上“明季紳衿之橫”,第5-6頁。
(39)參見劉一焜:《撫浙疏草》卷六《題嘉善士民鼓噪請旨查勘三縣田糧疏》,萬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具題,景照明刻本。
(40)廖心一:《略論明朝後期嘉興府争田》,《明史研究論叢》第5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6頁。
(41)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四《正俗一》,第312頁。
(42)黃省曾:《吳風錄》,《五朝小說大觀》本,第2、3頁。
(43)《明穆宗實錄》卷一三,隆慶元年十月庚寅,台北:台灣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校刊本。
(44)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五三《山東青萊海防督饷布政使司右參政贈太仆寺卿譚公墓志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32頁。
(45)範濂:《雲間據目抄》卷一《記人物·周思兼》,第3頁。
(46)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四“明鄉官虐民之害”條,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校點本,第527頁。
(47)參見李樂:《見聞雜記》卷一,第二十二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16頁。
(48)《明史》卷二二二《淩雲翼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861-5862頁。
(49)伍袁萃錄、賀燦然評:《漫錄評正》,《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70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543頁。
(50)曹家駒:《說夢》,《清人說荟初集》,上海:上海掃葉山房,1913年石印本。
(51)黃印:《錫金識小錄》卷一○《前鑒》。
(52)文林:《琅琊漫抄》,陶宗儀輯:《說郛》續卷一七,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鉛印本,第2-3頁。
(53)範濂:《雲間據目抄》卷四《記賦役》,第4頁。
(54)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三“奴仆”條,黃汝成集釋本,長沙:嶽麓書社,1994年,第497頁。
(55)翁元升參董其昌折,轉引自謝國桢《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15頁。
(56)祁彪佳:《宜焚全稿·題為豪奴蔽主啟釁頑民結黨搶燒已經擒獲首惡解散協從事》,見《祁彪佳文稿》,第56-90頁。
(57)黃卬:《錫金識小錄》卷一○《前鑒》。
(58)田藝蘅:《留青日劄》卷三“男娼”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15頁。
(59)沈德符:《敝帚軒剩語》卷中“男色之靡”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8冊,第508頁。
(60)康熙《江甯府志》卷三三《摭拾上》。
(61)佚名:《筆夢》,《虞陽說苑甲編》,第1、8、9頁。
(62)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四《技藝》“缙紳餘技”條,第627頁。
(63)範濂:《雲間據目抄》卷二《記風俗》,第1頁。
(64)黃卬:《錫金識小錄》卷一○《前鑒》。
(65)李樂:《見聞雜記》卷一○,第十三條,第10頁。
(66)楊鳳苞:《秋室集》卷一《書南山草堂遺集後》,《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第10頁。
(67)佚名:《研堂見聞雜記》,見《中國曆史研究資料叢書》,第284-285頁。
(68)黃卬:《錫金識小錄》卷四《綜考·雲門十子》。
(69)光緒《諸暨縣志》卷三一《人物志·列傳五·駱複旦》。
(70)佚名:《研堂見聞雜記》,《中國曆史研究資料叢書》,第306頁。
(71)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六《紀交贈計需亭》,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90頁。
(72)顧公燮:《丹午筆記》卷二六八“打降”條,第188頁。
(73)顧公燮:《丹午筆記》二二四“哭廟紀聞”條,第155頁。
(74)參見顧公燮:《丹午筆記》二二四“哭廟紀聞”條,第154-163頁,見《清稗類鈔》獄訟類“康熙庚午哭廟大獄”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排印本,第3冊,第1022頁。文中庚午誤成康熙朝,應為順治朝。
(75)陸文衡:《啬庵随筆》卷三《時事》,轉引自何齡修《浙江奏銷案》。
(76)佚名:《研堂見聞雜記》,《中國曆史研究資料叢書》,第297頁。
(77)參見孟森:《奏銷案》,見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34頁;何齡修:《浙江奏銷案》。
(78)《哭廟記略》,《痛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鉛印本,第3頁。
(79)葉夢珠:《閱世編》卷六《賦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6-137頁。
(80)王先謙:《東華錄》康熙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487、488頁。
(81)《清聖祖實錄》卷二,順治十八年三月戊午,僞滿影印本,第3-4頁。
(82)參見《清聖祖實錄》卷三,順治十八年六月庚辰,第3頁。
(83)顧公燮:《丹午筆記》二二四“哭廟異聞”條,第154頁。
(84)參見又褚人獲:《堅瓠丁集》卷三“長洲酷令”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記奏銷之嚴謂:“康熙初,長洲縣令彭口,賦性貪酷,設立紙枷、紙半臂,使欠糧者衣而荷之,有損則加責罰。滑稽者改清明祭掃一詩,粘于縣牆雲:‘長邑低區多瘠田,經催糧長役紛然,紙枷扯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紅杜鵑,日落生員敲凳上(時撫院朱國治奏銷之後,辄以抗糧為名而撲責之),夜則皂隸鬧門前,人生有産須當賣,一粒何曾到口邊。’百姓怨恨。”
(85)參見韓世琦:《撫吳疏草》卷六《葉方霭欠糧疏》,《四庫未收書輯刊》第8輯第5冊,第528-529頁。
(86)韓世琦:《撫吳疏草》卷六《順治十八年三欠奏銷印結疏》,第527頁。
(87)顧公燮:《丹午筆記》二三一“趙士麟治吳”條,第169頁。
(88)宋荦:《西陂類稿》卷三六《酌議催科處分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3冊,第461頁。
(89)彭維新:《與馬虞樽少司空書》,《清經世文編》卷二七《戶政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影印本,第674頁。
(90)《清朝野史大觀》卷五“記江南清查事”條,上海:上海書店印行,1981年,第139頁。
(91)袁枚:《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繼善神道碑》,《碑傳集》卷一七,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标點本,第895頁。
(92)《清史列傳》卷一八《大臣劃一傳檔正編十五·尹繼善》,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點校本,第1357-1358頁。
(93)《蘇州巡撫陳大受為請于州縣設局先行核對錢糧簿串事奏折》,《曆史檔案》1995年第1期,第5頁。
(94)《清高宗實錄》卷二九六,乾隆十二年八月甲子。
(95)《署兩江總督策楞為遵旨籌辦清理積欠善後事宜事奏折》,《曆史檔案》1995年第1期,第12頁。
(96)《兩江總督黃庭桂為遵旨籌辦額賦年清年款事宜事奏折》,《曆史檔案》1995年第1期,第14頁。
(97)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上“明季紳衿之橫”,第6頁。
(98)佚名:《研堂見聞雜記》(《中國曆史研究資料叢書》,第306頁)謂:“至康熙初年,朝廷以法律馭下,嚴行禁革,此風遂改。于是不稱盟而稱同學矣。”參見顧公燮《丹午筆記》二二三“湯文正治吳”條(第169-170頁)載,當湯斌出任蘇州巡撫時,“缙紳尚沿明季陋習,花朝月夕,挾妓宴飲……公未赴任時,韓宗伯菼緻書各紳,謂新撫軍品行端方,慎勿再蹈此習。于是蘇州之造牌、打降,聞風早遁”。
(99)談遷:《北遊錄紀文·上大司農陳素庵書》,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263-264頁
(100)褚人獲:《堅瓠丁集》卷四“詠田字”條,第11頁。
(101)黃與堅:《忍庵集》文稿一《三吳田賦議上》,日本内閣文庫影印本,第27頁。
(102)宣統《續修楓泾小志》卷一○《拾遺》,《上海鄉鎮舊志叢書》第6冊,第331頁。
(103)鹹豐《紫堤村志》卷二《風俗》,《上海鄉鎮舊志叢書》第13冊,第47頁。
(104)葉夢珠:《閱世編》卷六《賦稅》,第137頁。
(105)康熙《前朱裡紀略·風俗》,《中國地方志內建·鄉鎮志專輯》第21冊,第4頁。
(106)民國《二區舊五圖鄉志》卷一八《遺事》,《上海鄉鎮舊志叢書》第14冊,第157頁。
(107)王時敏:《奉常家訓》,《棣香齋叢書》金集。
(108)葉夢珠:《閱世編》卷六《賦稅》,第137頁。
(109)乾隆《元和縣志》卷一○《風俗》。
(110)《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一《風俗·占候》。
(111)葉夢珠:《閱世編》卷四《士風》,第86頁。
(112)嘉慶《松江府志》卷五《風俗》。
(113)乾隆《元和縣志》卷一○《風俗》。
(114)韓菼:《有懷堂文稿》卷二○《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顧先生墓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第245冊,第594頁。
(115)許宗彥:《學士梁公同書家傳》,錢儀吉《碑傳集》卷四八,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377頁。
(116)韓菼:《有懷堂文稿》卷二○《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顧先生墓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第245冊,第593頁。
(117)董含《三岡識略》卷一○“官紳接見有禁”條,第216頁。
(118)徐珂:《清稗類鈔》獄訟類“康熙庚午哭廟大獄”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排印本,第1022頁。
(119)參見孟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75頁。
(120)歸莊:《歸莊集》卷六《傳硯齋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60頁。
(121)參見何齡修:《五庫齋清史叢稿》,第684-685頁。
(122)康熙《蘇州府志》卷二一《風俗》。
(123)宋琬:《安雅堂文集》卷一《董阆石詩序》,《四庫全書存目存書》補編,第2冊,第63頁。
(124)宋琬:《安雅堂文集》卷一《董蒼水詩序》,《四庫全書叢目叢書》補編,第2冊,第76頁。
(12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18頁。
(126)乾隆《昆山新陽合志》卷一《風俗》。
(127)韓書瑞、羅友枝:《十八世紀中國社會》,陳仲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頁。
(128)劉師培:《左庵外集》卷九《清儒得失論》,《劉申叔先生遺書》,1936年校印本,第1頁。
(129)乾隆《長洲縣志》卷一一《風俗》。
(130)董含:《三岡識略》卷一○“三吳風俗十六則”條,第223頁。
(131)葉夢珠:《閱世編》卷四《士風》,第87頁。
(132)黃卬:《錫金識小錄》卷一○《備參》、《前鑒》。
(133)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七《孟子八錄跋》,《續修四庫全書》第1496冊,第297頁。
(134)董含:《三岡識略》卷一○“三吳風俗十六則”條,第225頁。
(135)昭梿:《嘯亭雜錄》卷一○“書賈語”條,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17頁。
(136)昭梿:《嘯亭續錄》卷三“王西莊之貪”條,第442頁。
(137)徐珂:《清稗類鈔》風俗類,“吳俗前後有三好”條,第2202頁。
(138)黃卬:《錫金識小錄》卷一○《前鑒》。
(139)常輝:《蘭舫筆記》,《吳中文獻小叢書》本。
文章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