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美]巴頓·格爾曼
摘編 | 徐悅東
近期,美國最大的油氣管道被黑客挾持,聲稱“不給錢不放人”。此舉直接導緻美國東海岸8800公裡汽油輸送“大動脈”癱瘓,首都華盛頓和東部17州,全部進入緊急狀态。這一新聞吸引了大家對于網絡安全的關注。
《華盛頓郵報》的前調查記者巴頓·格爾曼非常關注美國網絡安全和網絡監控的問題。為此,他耗時多年,深入調查了“棱鏡門”事件的來龍去脈。2013年,“斯諾登事件”曾火爆一時,他向全世界揭發了美國政府從網際網路巨頭收集使用者資料資訊的醜聞,引起國際社會一片嘩然。一時間,斯諾登也被貼上了“英雄”、“叛徒”等标簽。許多人一直不了解,斯諾登為何要自曝身份,揭露美國政府在網絡安全工作中的道德争議?他為何能夠勇敢地站出來?他又是怎麼做到的?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巴頓·格爾曼調查“棱鏡門”事件所寫的非虛構紀實作品《美國黑鏡》,他以采訪者的視角出發,層層剝開斯諾登的内心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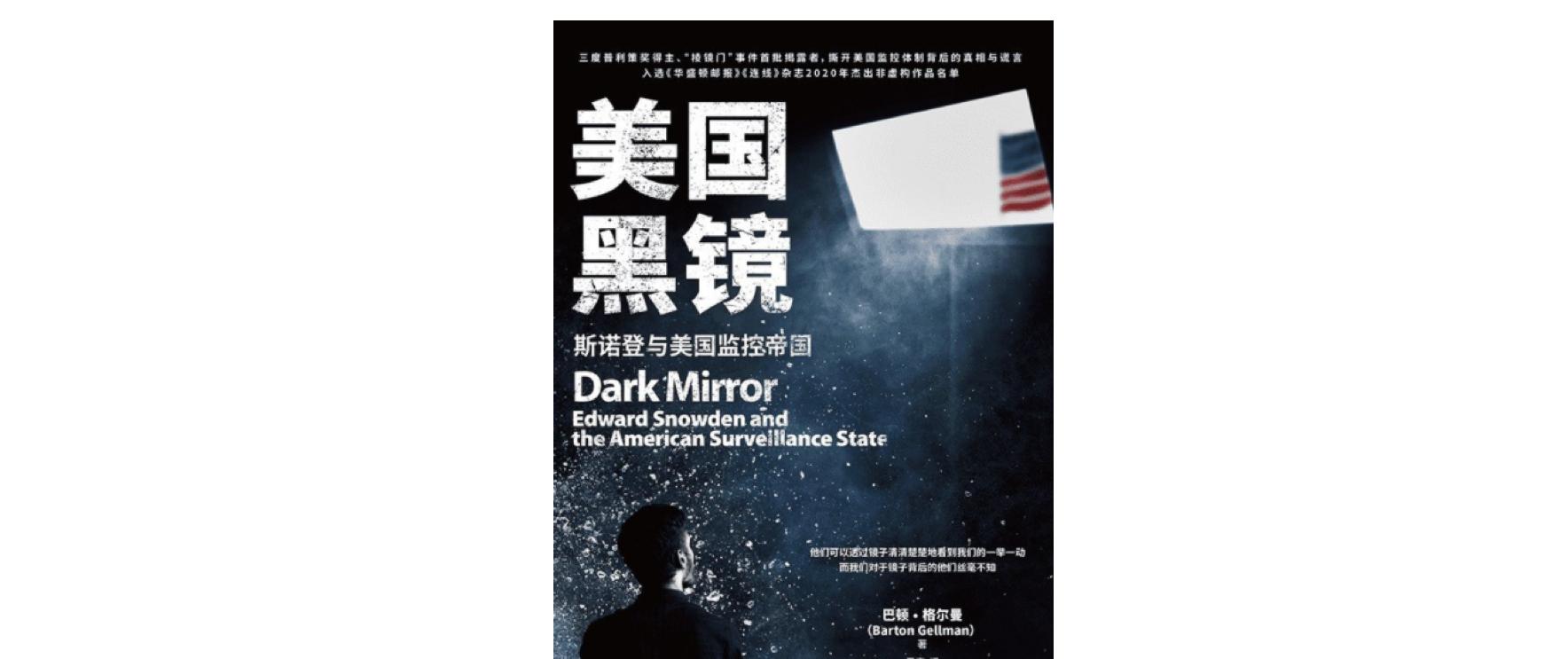
《美國黑鏡》,[美]巴頓·格爾曼著,思齊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3月版
斯諾登擁有追求卓越的性格
和黑白分明的道德觀
關上車窗,将收音機的聲音調大,愛德華·斯諾登駕駛着他那輛嶄 新的本田型格汽車,向北行駛在750号高速公路上。這裡是夏威夷州火奴魯魯,他的目的地是位于懷帕胡的一個地下堡壘。堡壘的入口看起來就像坐落于郊區停車場的一處礦井,當地人習慣稱它為“地洞”,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員工則習慣稱其為“隧道”,因為他們要穿過此處進入地下。這是2012年3月的時候,斯諾登來到庫尼亞地區安全作戰中心上班,距離這裡半個小時車程有一家芭斯羅缤冰激淩店,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在那個店裡打過工。盡管斯諾登聯系上記者是幾個月之後的事情,但此時的他已經位于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斯諾登将自己的手機鎖在車裡,沖保安亭亮出自己的證件,走過一道防護門,這道門長期用鉸鍊卡住,哪怕世界末日降臨也已經無法關閉。 整座建築都因年數太久而破敗不堪。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由于擔心珍珠港事件再次上演,軍事工程師建造了一些巨大的地下空間用于組裝飛機。但直到戰争結束,這裡的生産活動都沒有展開。于是,庫尼亞基地就變成了一個不受待見的“遺産”。
後來,它的用途不斷變化,先後被用作海軍軍械庫、空軍掩體、陸軍野外工作站、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的後備指揮中心。1993年,美國國家安全局入駐這裡,将其改造成為專門負責監聽、監視亞洲的情報中心。這裡本來是被設計作為臨時性場所, 但直到2007年才破土重建。直到5年後,斯諾登來到這裡時,據同期在此工作的人回憶,這裡仍然處于一片混亂的局面,重建工作一直沒有完工。
走下一條大約400米的斜坡之後,斯諾登來到一處旋轉閘門,這是一種雙門互鎖門禁系統,他進入閘門之後,隻有掃描了自己綠色的外包員工工牌,并且在鍵盤上輸入正确的個人識别密碼,才能走出閘門。閘門另一邊的建築規模十分龐大。那天早上,斯諾登穿過“隧道”,進入一片廣闊的區域,那裡布滿了格子間、網絡機櫃、安裝着密碼鎖的辦公室, 還有一排排長長的開放式辦公桌。這裡一共有三層,每層的面積都有一個足球場那麼大,容納了上千名員工,他們頭頂上的日光燈管,連起來可長達數英裡。“那裡就像是詹姆斯•邦德電影裡壞蛋的老巢,除了光照條件比較差,”斯諾登告訴我,“那裡的人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記得有一次消防演習,我都被那裡的人數驚呆了。”
不滿的情緒日漸滋生。斯諾登對于這種嚴格的指令體系心生叛逆并非始于庫尼亞,也未能終于庫尼亞。他最冒險的一次行動發生在到這之後的第二年。在庫尼亞東北方向5英裡的地方建立了一個以約瑟夫·J. 羅徹福特命名的指揮中心,斯諾登在該中心侵入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檔案系統。斯諾登從效忠美國政府轉向效忠美國人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曆了數年的利弊權衡。到他離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時,奮起反抗的想法才逐漸轉化成具體的計劃。
回到多年以前,正是從青少年時期到20歲出頭這段時間,斯諾登所掌握的技能、所形成的價值觀和強烈的自我意識,為其未來成為全球公衆人物奠定了基礎。他從高中辍學後,給自己制訂了一個學習計劃,主要學習計算機網絡、平面設計、中國功夫,同時對天馬行空的動漫世界、角色扮演、電子遊戲也有所涉獵。
這一切造就了他追求卓越的性格和黑白分明的道德觀,特别看重個人的美德和非凡的技能。後來,他發現了一條進入美國陸軍特種部隊的捷徑。于是,他放下手中的遊戲搖桿,換上軍裝,拿起武器。他在部隊非常努力,直至後來在一次訓練中不幸受傷。他通過考取一系列證書獲得了工程師資質,盡管他從沒有完整地聽完那些課程。再後來,他來到了庫尼亞。就是在這裡,斯諾登開始使用Verax 這一身份(除此之外,他還有很多身份),也是在這裡,他開始探入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防禦體系。
“我開始逐漸有所行動。”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夜,我們在莫斯科進行了長達9個小時的訪談,當訪談接近尾聲時,他短暫地卸下防備,向我回憶起當時的場景。
“你說的這句話似乎包含兩層含義,”想到之前他曾多次拒絕談論這個話題,我頗為謹慎地說道,“一層含義是指,你就是從那裡開始搜集資料,并從系統中将資料提取出來,就此走上不歸路;另一層含義是指,你是從那裡開始與記者聯系。”
“事實上,這不過是整個過程中的一個小節點,”斯諾登回答道,“它見證的是一種觀念的轉變,從‘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去做’變成‘我要開始去做一些事情’。”我試圖往下追問,但斯諾登避而不談了。
斯諾登
後來,他在一封郵件中寫道:“你這是在讓我明确表态,說出自己是否曾做出政府口中的那些犯罪行為。”還有一次,我想知道他是如何帶走如此多檔案的,于是提出了一些疑問,他便指責我的問題不像是主流媒體應該關注的,倒像是通俗小報才會關心的。“很明顯,你提出這一問題是出于個人興趣,出于好奇心,但你要學會克制自己。當你隻需要權衡利弊時,知道這些細節有什麼用呢?”
盡管如此,他還是忍不住透露出一絲得意。“我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有人關心我是如何做到這一切的,”他說道,“我隻能說,這一過程極為複雜,所有操作都是在極為受限的環境下進行的,需要十分謹慎,容不得一絲差錯。”
夏威夷的經曆為斯諾登
打開了通往“絕密資訊”的通道
斯諾登被調去夏威夷是出于對其身體健康狀況的考慮,這使得他剛好有機會來為自己的情報生涯畫上一個句點。之前他供職于美國情報機構的承包商——戴爾進階解決方案組(Dell Advanced Solutions Group),并被派去美國中央情報局擔任技術顧問。工作期間,他曾在幾個月裡先後數次出現眩暈的症狀,但都不甚嚴重,直到後來有一次與他的老闆通電話時突然癫痫發作,情況非常嚴重。根據最新的診斷結果,斯諾登不能再從馬裡蘭州開車到弗吉尼亞州的蘭利(美國中央情報局所在地)上班,否則就會被視為違法。
于是,戴爾将他調到位于世界另一端的夏威夷島,理論上來說,在那裡他可以騎自行車上班。斯諾登在懷帕胡租了一間平房,原本打算騎自行車上班,但當地人提醒他,大莊園路的北邊有一些視線不良的彎道,經常發生交通事故。他去考察了一下上下班的路線,認為自己開車上下班比較安全,盡管夏威夷州的法律規定,6 個月内有癫痫發病史者不得駕車。一如往常,他做好應急計劃,将自己的判斷置于規則之上。如果他感覺自己要發病,就往馬路東側的溝裡開, 這樣就不會危及他人生命。斯諾登已經熟悉那種奔波的感覺,之前在蘭利工作時,他曾以美國中央情報局技術官員的身份被派往瑞士,後來又以戴爾員工的身份被派往日本,為美國國家安全局工作。庫尼亞的工作 對于他來說,部分程度上是為了放松身心。
到來年春天的時候,斯諾登已經感到非常無聊,覺得一切都沒有意義。此前,他跟戴爾簽訂的合同是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國家威脅行動中心(NTOC)擔任分析師一職,主要工作職責是和該機構的軍職和文職人員一起,負責預測、偵察并挫敗外國黑客試圖對美國政府網絡系統發起的攻擊。就在前去就職的途中,斯諾登卻因公司内部的政治勢力鬥争而被解除了這一職務。該職務的總承包商加州分析中心(CACI)踢走了分包商戴爾的員工,換成了自己的員工。當斯諾登得知這一變化時, 他已經打包好行李并辦理了船舶托運。作為補償,戴爾在資訊共享辦公室的夏威夷技術小組(代号HT322)為他安排了一個相對清閑的臨時崗位。他的工作職責就是配置和維護涉密網絡伺服器,對每個賬号實施通路限制。
相比他原本要入職的那個崗位,這個補償性的崗位薪水更高,但工作内容極度無聊。幾周之内,他就已經能夠通過計算機自動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内容,比如編寫運維腳本以及一些其他的日常性工作。而此前,他的前任都隻能手動完成這些工作。斯諾登告訴我,大部分時候,他每天隻需要最多半個小時就能保證微軟SharePoint伺服器穩定地運作。偶爾,他會被叫去做一些非常基礎的技術支援工作。美國國家安全局内部并非人人都是計算機高手,很多人都還差得遠呢。
2012年8月,位于米德堡總部的一名同僚遇到了一個難題:不知道什麼原因,她無法打開從夏威夷發出的檔案。于是,她向系統的幫助台發送了一條緊急請求。8月24日,一名較資深的員工抱怨稱,這條請求已經“躺在那裡一個多星期了,沒人處理”,有人就把它發給了斯諾登。斯諾登當天就給那名同僚發去了解決方案,這條郵件鍊自此一發而不可收。直到8月30日,他才寫下最後的文字:“從程式清單中選擇‘Word Pad’程式,選中左下方的‘始終使用選擇的程式打開這種檔案’複選框,然後點選‘ok’。”斯諾登花了整整6天的時間,寫了幾千字,才徹底解決了那名同僚的疑惑。
在空閑時間,斯諾登開始浏覽自己管理下的檔案目錄。這并非他日常工作所需的操作,但也絕非明令禁止的行為。對于 SharePoint 伺服器上的任何檔案,斯諾登都有實施閱讀、編寫、複制或删除操作的有效權限。他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經理,一名職業文職人員,很快就擴充了斯諾登的通路權限。經理發現目前的工作對于斯諾登而言完全是大材小用,于是安排他去業務更加繁忙的 Windows 網絡部門做幫手。
嚴格來說,斯諾登新增的工作職責超出了聯邦承包工作相關條例的範圍。戴爾對此也許并不知情,但對于斯諾登超出合同約定的工作内容,戴爾根據工作時長向美國國家安全局計費。在美國國家安全局内部,這種私下的工作安排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般哪裡有需要就會把員工調去哪裡,倘若員工每增加一項工作内容都要展現在合同裡,确實也不太現實。斯諾登早在19歲時就已經是經微軟認證的系統工程師,并且有實際的網絡管理經驗。他的上級當然不想白白浪費他這些技能。
到4月時,斯諾登就已經位列庫尼亞Windows伺服器工程部門的“超級使用者”名單,僅有極少數人能夠進入這一名單。他超越了普通使用者賬号所受的限制,能夠深入網絡内部,改變其基本的運作方式。後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首席技術官隆尼·安德森表示,該機構的“系統管理者分為三個級别,分别是一級、二級和三級”。斯諾登已經成為最進階别的管理者,擁有“特許通路權”(PRIVAC)。在這個“隧道”裡,他可以自由通路任何一台擁有IP位址的Windows機器。
他告訴我,“我還同時還在支援Linux系統小組”。這裡他所說的Linux是一個與Windows相對的作業系統,被廣泛應用于計算機網絡。“是以你就知道,我擁有Linux系統工具、相關資格證書、虛拟伺服器等一切東西。是以,基本上,我可以通路一切事物,可以通路所有的資料共享,可以通路所有的伺服器,我熟悉所有的基礎設施。”
然後,他就遇到了名為“心跳”(Heartbeat)的項目。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通過這個項目打開了通往“絕密 / 敏感隔離資訊”(TS / SCI)網絡的通道,這些網絡的範圍遠遠超出庫尼亞,跨越太平洋,超越了美國國家安全局本身的數字邊界。這時的斯諾登尚未到而立之年。
斯諾登為何與中央情報局分道揚镳?
中央情報局的公共事務部員工對于斯諾登當時的工作職責或表現閉口不談,任由前員工随意評論。2013年8月之前在中央情報局擔任副主任和代理主任的邁克爾·莫雷爾,曾在2014年年初與我坐在一家室外咖啡館,俯瞰亞利桑那州的鴿子山。
邁克爾·莫雷爾
在斯諾登公開披露機密檔案時,距離莫雷爾退休還有三個月的時間,他曾打聽過斯諾登的相關資訊。莫雷爾 說,外界有人把斯諾登描繪成一個年紀輕輕就成就顯著的人或者位高權重的人,這太荒謬了。斯諾登的級别在基層員工中是最低的,他甚至勉 強能勝任自己的工作。按照莫雷爾的說法,中央情報局之是以會聘用斯諾登,隻是因為随着該機構在世界各地的運作節奏加快,電信官崗位急缺人才。
他表示,斯諾登之是以能蒙混過關,進入機構工作,隻是因為當時這個崗位缺人而臨時降低了錄用标準。莫雷爾的這些話中,有些明顯是假的。浏覽中央情報局招聘網站過往的說明,就可以發現,其崗位要求并沒有明顯的變更。和前幾年相比,斯諾登這批員工的聘用資格條件也不可能是難以查詢的國家安全機密。至于其他的問題,斯諾登的績效考評結果就可以直覺地說明一切。莫雷爾的表述明顯帶有故意貶低的色彩,很難解釋為何斯諾登的職位穩步上升。
斯諾登參加了接下來一期的教育訓練課程,為期6 個月,課程名稱是“基礎電信教育訓練課程”,教育訓練地點位于弗吉尼亞州北部沃倫頓的一處較為隐秘的中央情報局辦公樓。新進的行動官員,即該機構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是在一處更為知名的地點接受教育訓練,那裡通常被稱為“農場”。斯諾登以及其他科技官員接受教育訓練的地點則通常被稱為“山丘”。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詹姆斯·邦德電影場景中的大師Q博士,以一副說教的姿态解釋如何從遠端遙控的豪華跑車中發射飛彈。“山丘”的教育訓練課程大綱中,出現更多的不是阿斯頓·馬丁牌跑車,而是破舊的無線電。斯諾登說:“你基本上要學習如何處理任何一件可能出現在大使館裡的基礎設施。”他練習拆分和重新組裝路由器、電話、防火牆和通風裝置。他學習了密碼學的基本原理、發展現狀和曆史。
除了要了解最新的系統,他還必須要精通那些老派的大使和情報站站長可能會習慣使用的過時的裝置。螢火蟲鑰匙、四四方方帶有旋鈕和刻度盤的KG—84加密裝置,這些東西已經古老到被放在博物館當收藏品了,但斯諾登必須要精通它們。 他說,很多時間都被用來學習如何不被别人識破自己的僞裝。斯諾登和其他學員一起學習了作為中央情報局官員需要掌握的基礎的間諜情報技術,因為他們在國外可能會被監控。他們還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去适應自己在大使館使用的僞裝身份。這樣,就連他們以後在大使館的同僚,也不會知道他們背後真正的雇主。“有一門特殊的課程是要練習如何僞裝成美國國務院的員工,要了解這個機構是如何運作的。至少,你要能夠冒充國務院的人,他們有自己内部的語言,有自己習慣的簡略表達……你要能夠融入其中。”
斯諾登學習了如何識别自己有沒有被跟蹤,如何檢查車輛有沒有被動過手腳,如何讓自己的謊言更有說服力,哪些事情不可以告訴自己的伴侶(很多都不可以),哪些事情不可以告訴自己的孩子(所有都不可以)。還有一門課是教他們在執行外勤的時候如何寫電報,尤其針對如何寫作緊急報告提供了特别指導。這裡的緊急報告指的是,當情報的内容 非常重要的時候,從獲悉情報内容到形成書面報告,再到發送給總統,這一過程需要在10分鐘之内完成。緊急報告隻能用于特定情況,根據一份保密的簡報,隻有針對那些“能夠對美國的關鍵政治、經濟、情報和軍事利益造成緊急且嚴重危害”的事情才可以進行緊急報告。一名教育訓練 人員為了警示他們,給他們講了一個故事:從前受訓者中有一個倒黴蛋,把練習用的緊急報告真的發送了出去。這個故事是真實發生過的還是杜撰的,我們無從知曉。
另外,教育訓練人員在一張幻燈片上用醒目的大字告誡這些新的電信官:“務必排除任何不确定性!”所舉的例子是,1990年8月2日淩晨2點31分,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巴格達情報站發出簡報:“伊拉克軍隊出現在科威特,距離美國大使館一千碼範圍内發生輕武器交火。”
課程結束之前,斯諾登也教會了中央情報局一點東西。當認為涉及原則性問題時,斯諾登絲毫不害怕出洋相。和他一起接受教育訓練的學員抱怨他們住的地方是一個破舊的、搖搖欲墜的小旅館,還抱怨中央情報局拒絕支付他們加班費。斯諾登認為,中央情報局的這些行為違犯了勞動法、職業安全與健康法規。于是,他發起了一份正式的投訴,在教育訓練學校的負責人駁回了他的投訴後,他直接找到了中央情報局外勤事務組組長,然後又去找了這名組長的上司。最終結果是,斯諾登得以更換住宿條件,同時也因不服從指令而受到訓斥,但他對此絲毫不介意。斯諾登 回憶說,與身邊的其他人不同,他願意承擔“上升的代價”。
在教育訓練的最後一天,斯諾登和其他學員列出了自己優先願意被派往的地點。斯諾登的首選是戰區——伊拉克或阿富汗,第二選擇是日内瓦。他聽說在日内瓦的工作非常具有技術挑戰性,那裡的情報站擁有複雜的網絡基礎設施,而且那個城市的間諜人數和居民總數之比超過全世界其他大部分城市。2007年3月,中央情報局真的把他派往了日内瓦。斯諾登的照片印在鮮紅色的外交人員工作牌上面,照片中的他有着一張娃娃臉,穿着藍色制服、栗色襯衫,打着條紋領帶。在外界看來,斯諾登是美國派往聯合國日内瓦辦事處的外交事務專員,是美國國務院的員工,編号是64554。斯諾登的工作地點位于大使館辦公樓頂層的資訊技術中心。
中央情報局電信官的辦公環境是一間間裝有安全防護門的封閉空間。在它旁邊的是美國國務院的通信組,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局特殊情報搜集部門的員工,後者主要負責竊聽當地的一些目标人物。在這裡進行書面溝通時,斯諾登使用的名稱是“戴夫·M. 丘奇亞德”。這是一種預防性措施,自1979年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占領事件發生之後,這種措施開始被廣泛使用。這樣即使有人侵入保密記錄檔案,也很難發現他的情報人員身份。
中央情報局提供的薪水和津貼足夠斯諾登租下一套四房間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窗外就是日内瓦湖。他在瑞士過得很奢侈,買了一輛寶馬汽車,而且開始炒股。但他對那裡的生活也不無抱怨,他在Ars Technica網站上與人聊天時曾這樣評價:“物價貴得離譜,階級歧視嚴重得吓人”,但總體而言還是“相當不錯的”。他在日内瓦的工作和在蘭利作為承包商雇員時從事的網絡管理工作相差不大。但他不滿足于此,還自願承擔一些臨時配置設定的任務——日内瓦情報站經常會借調員工。
2008年春,斯諾登被借調至美國駐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大使館,不日,喬治·W.布什總統就要抵達那裡參加北約峰會。當時,斯諾登所在的是一個進階項目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将中央情報局的威脅評估結果發送給特勤局。“威脅報告的内容極為荒誕,”他回憶稱,“有些鍵盤俠在論壇上宣稱自己要開車從布什的身上碾過。”他認為這些線索都極不靠譜,不了解它們是如何被搜集起來的,為何會有人當真。但他對此也隻是一笑置之,認為政府隻是 在浪費時間和資源。
回到日内瓦之後,斯諾登見識到了一些事情,讓他感到非常困擾。其中一件事情是,兩名情報機構官員先是慫恿一名沙特阿拉伯的理财經理在喝醉之後駕車回家,然後以此為要挾,讓那名理财經理為他們辦事。“我們要與一些非常壞的家夥打交道,那些人真的非常難對付,但有利用價值,”斯諾登後來的一名同僚曾這樣說,“有時候我們要使用一些非常卑劣的手段,我為親身參與這種事情而感到羞恥。”
另一件令斯諾登感到幻滅的事情是,美國的間諜勢力已經廣泛滲透至在聯合國的外交官。斯諾登後來告訴我,他和中央情報局的三名情報官員共事時,他們曾私下咨詢他,如何才能侵入一名外交官員的電腦系統。“他們的問題往往類似于:我們要插入一個U盤,應該怎麼操作?有什麼訣竅?我們需要擔心什麼?要注意千萬不能搞砸什麼?可能會以何種方式被發現?被發現之後該如何解釋?要編出一些比較合理的借口。”斯諾登說,他明白監控盟友的行動能使自己處于優勢地位,但他并不認同這種行為。那時的他持有自由意志主義政治觀,反對美國在伊拉克發動戰争,反對秘密引渡那些所謂的恐怖分子,反對小布什總統對 2008 年股災的處理方式。他不明白為什麼美國總是試圖充當世界警察,試圖為企業提供安全保障?
馬瓦妮·安德森曾在日内瓦代表團中擔任法務實習生,在2007—2009年與斯諾登共事,在她的印象中,斯諾登是一個内向的計算機天才,習慣沉思。她說,當時的斯諾登面臨良知上的考驗。斯諾登說,他第一次産生想要揭發這一切的想法是在日内瓦的時候,但他抑制住了,因為擔心會将那些情報機構官員和特工置于危險的境地。他曾寄希望于新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希望這位總統能夠改變這些令自己困擾的政策。
2009年年初,他在Ars Technica網站上說話的語氣完全不像是一個會洩露機密的人。他寫道,那些洩露保密資訊的匿名官員,應該被“擊斃,有些資訊之是以保密是有原因的”。
大約就是從那時起,25歲的斯諾登與他的雇主中央情報局之間開始漸漸産生分歧。關于斯諾登離開中央情報局的原因,有三種說法,各不相同。一種說法來自《紐約時報》所報道的“兩名美國進階官員”提供的資訊,但并未引用他們的原話。據他們說,斯諾登在日内瓦的主管懷疑他曾試圖打開未授權的檔案。這名主管在斯諾登的人事檔案中記下了不好的一筆。出人意料的是,這篇報道發出的第二天,中央情報局公共事務辦公室就釋出聲明,否定了這篇報道的真實性。
斯諾登的檔案中确實存在一些不好的記錄,但原因遠沒有這麼嚴重。根據後來斯諾登自己的解釋,第二種說法,也就是官方說法,更為靠譜。斯諾登說,他在填 寫年度績效考評時發現了一個安全隐患,任何員工都有可能在機構的人力資源線上應用程式中輸入惡意代碼。斯諾登提議,在不造成任何損害的前提下操控系統,以證明這一漏洞的存在。在系統安全性研究中,這是一種常用的方法。斯諾登的想法是,令操縱系統突然彈出恐怖消息, 但他的上司勸他不要這麼高調。于是,在填寫完績效評估内容之後,為了證明自己可以“控制”這個網頁版的應用程式,斯諾登更改了頁面上的所有顔色。
據斯諾登自己說,這一行為惹怒了他上司的上司——負責整個歐洲地區的一名資深技術官,因為他感到自己被羞辱了。正是這名技術官在斯諾登的檔案中記錄下不好的一筆,基本上封鎖了斯諾登的晉升之路。一名退休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告訴《名利場》雜志,斯諾登“太過聰明,不可能一直安于那份工作”。在這名官員看來,這種沖突的根源在于“我覺得他可能更喜歡成為一名玩家”。
關于斯諾登離開中央情報局的原因,第三種說法來源于兩個與斯諾登的家人走得比較近的熟人,與前兩種說法并不完全沖突。據他們說,2008年12月,斯諾登飛回家參加父親在海岸警衛隊的退休典禮。斯諾登的父母注意到,兒子似乎總是咳嗽不止。中央情報局的電信官有時候會被派去銷毀一些機密資料,具體做法就是要将一些電子元件碾成微粒。 小朗尼·斯諾登認為,是因為中央情報局的疏忽,将他兒子置于矽塵濃度較高的危險環境中。他堅持要求兒子去看醫生。斯諾登去華盛頓特區咨詢了一些呼吸科專家。自那之後,斯諾登再沒有回到原來的崗位。日内瓦情報站派人去他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打包了他的行李,給他寄回了家。
編輯|張婷
導語校對|李項玲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