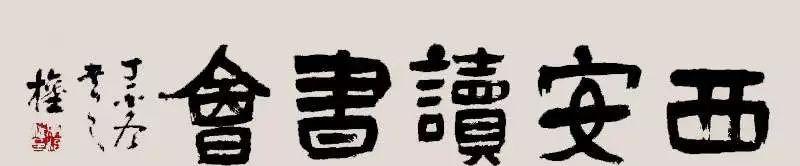
像孫少平這樣的青年農民,在邁向城市的程序中要付出多少慘重的身心代價?
時代沖突和困頓深處:回望孫少平
作者:金理(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從今天來看,《平凡的世界》無疑是一個“沖突叢生”的文本,囊括了叙述者及故事叙述年代所特有的複雜性。競争性話語的登台、角力,在一個漸次開放的曆史時空中青年人的活躍以及自我壓抑,作家在塑造這一文學形象時所參引的思想資源及遭遇的困境……凡此諸問題皆意味深長。
不妨從失戀的故事講起。在《平凡的世界》裡,孫少平在得知郝紅梅移情别戀愛上班長後很失落,為了平複這挫敗感,他産生了幻想:未來的某一天,當“我”已經成了一個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麼是工程師,穿體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鏡,從外面的一個大地方回到這座城市”,再路遇郝紅梅他們,會是怎樣的情形?……這是一個年輕人對自己未來的期待和假想,或者說是對“主體位置”的期待和假想。
對于普通群眾而言,其所模仿、追求的對象,往往來自于地位相距較近的階層。以此來說,出身貧寒的孫少平确實“雄心勃勃”。想象的力量是巨大的。孫少平身上産生的幻想與渴望,促使着類似的青年個體“進城”。随着孫少平們必然地“進城”,有知識的農村青年拒絕成為新一代的農業經營者,在田間地頭漸漸地隻剩下婦女、小孩和老人。今天我們檢讨這一困境,可能應該考慮到孫少平當時對“主體位置”的想象,以及由此引發的鄉村人才流失現象。
01
當孫少平接觸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後:他一下子就被這書迷住了。記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來往常他都要出山給家裡砍一捆柴;可是這天他哪裡也沒去,一個人躲在村子打麥場的麥稭垛後面,貪婪地趕天黑前看完了這書……他一個人呆呆地坐在禾場邊上,望着滿天的星星,聽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聲,陷入了一種說不清楚的思緒之中。這思緒是散亂而漂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測的。他突然感覺到,在他們這群山包圍的雙水村外面,有一個遼闊的大世界。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蘇聯] 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奧斯特洛夫斯基 著,曹缦西/王志棣 譯,譯林出版社
請注意這裡由“星星”和“流水”構成的景象,基本上是抽離了具體勞動的、純粹審美的對象,一個掙脫了原本參與其中的勞作環境的青年農民,此時如同“城鎮居民把自然作為永恒的審美景象來凝視”。這也是一種“風景的發現”吧。
首先,“星星”和“流水”構成的“自然風景”,是作為——借巴赫金的話——“片斷的美景”被納入到“個人私室的世界,隻是作為優美的片斷,在人們散步、休憩的時刻,當人們偶然一瞥眼前景物的時候”,才會出現的。後文的論述将會表明,這一“風景”的出現,“與田園詩或稼穑詩的自然截然不同”,它預示着“人的形象開始移向私人生活”。
其次,隻有閱讀後的人才能看到“星星”和“流水”,與之相伴随的,是以無以名狀的孤獨體驗——“這思緒是散亂而飄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測的”——而表現出來的個人意識的覺醒和内在“主體性”的獲得。“隻有對周圍外部的東西沒有關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裡,風景才能得以發現。風景乃是被無視‘外部’的人發現的。”也就是說,當“内在的人”發現“風景”的同時,他往往對“眼前的他者”、“周圍外部的東西”冷淡而無所關心。
我把它引申為一種對周圍人、事的隔膜、格格不入感:“孫少平熱愛自己家裡的每一個親人。但是,他現在開始對這個家庭充滿了煩惱的情緒。一家人整天為一口吃食和基本生存條件而戰,可是連如此可悲而渺小的願望,也從來沒有滿足過!在這裡談不到詩情畫意,也不允許有想象的翅膀……毫無疑問,他将再沒有讀書的時間——白天勞動一天,晚上一倒下就會呼呼入睡。……如果他當初不知道這世界如此之大也罷了,反正雙水村和石圪節就是他的世界。但現在他通過書本,已經‘走’了那麼多地方,他的思想怎麼還會再僅僅局限于原來的那個小天地呢?”
閱讀意味着發現一個“外面的世界”,與庸俗、讓人失望的當下生活迥異。越是沉迷于閱讀所通向的“外面的世界”,其個人的存在越是容易從他/她所置身的現實世界中,從其與周遭事物的互動關系中“抽離”出來。“抽離”還意味着,發現“遼闊的大世界”的同時,日常生活的焦慮也随之發生了。
當下生活的不如意,在孫少平這裡,表現為先前社會對個人發展空間的壓抑。閱讀是自我塑造的重要媒介:怎樣才可以稱為“人”,怎樣才可以實作完善的“自我”,這一自我如何認識世界,追求何種價值……當孫少平沉迷于《艱難時世》、《簡愛》、《苦難的曆程》、《複活》、《歐也妮·葛朗台》、《白輪船》……時,他彙入到了新文化運動以來、以“新人”為追求的閱讀工程和曆史脈絡中。孫少平希望通過閱讀重建自我的身份,他一次次去“縣文化館圖書館裡千方百計搜尋書籍”,閱讀量驚人,那些《馬丁·伊登》、《熱愛生命》等小說中孤身奮鬥的主人公,一次次進入他的夢鄉,所有這些人都給孫少平精神上帶來了從未有過的滿足。他現在可以用比較廣闊一些的目光來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因為對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審視的能力,并且開始用各角度從不同的側面來觀察某種情況和某些現象了。
當然,從表面上看,他目前和以前沒有什麼不同,但他實際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原來的他了。他本質上仍然是農民的兒子,但他竭力想掙脫和超越他出身的階層”。這種“超越”還以旁觀者田曉霞的觀感表達了出來:“我發現你這個人氣質不錯!農村來的許多學生氣質太差勁……”問題是,這隻是内在“氣質”的重組,而不是實際身份的轉變。誠如楊慶祥的洞見所示:當小二黑開始讀書的時候,“當小二黑變成了高加林”,他将必然意識到,“他的環境、他的階級身份不是給他帶來了精神上的愉悅和信心,而是苦悶和焦慮”。
孫少平必然要投向“外面廣大的世界”,不僅是借助閱讀中“想象的翅膀”,更得是現實中行動的腳步。然而當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啟動之後,孫少平們注定隻能成為進城的農民工。哪怕孫少平是一個如此獨異的個體,一個能在超強度的勞動後,還可以在燭光下忘我夜讀的打工仔:
戀人田曉霞和哥哥孫少安來找在黃原市打工的孫少平——
二樓的樓道也和下面一樣亂。所有的房間隻有四堵牆的架構,沒門沒窗,沒水沒電。兩個人在樓道裡愣住了:這地方怎麼可能住人呢?…… 孫少平正背對着他們,趴在麥稭杆上的一堆破爛被褥裡,在一粒豆大的燭光下聚精會神地看書。那件肮髒的紅線衣一直卷到肩頭,暴露出了令人觸目驚心的脊背——青紫黑澱,傷痕累累!
《平凡的世界》的讀者肯定會對上面這個場景過目難忘。孫少平“在一粒豆大的燭光下聚精會神地”閱讀,想必依然憧憬着“遠方的世界”、“生活在他處”;讓人動容之處在于,路遙以孫少平脊背上的“傷痕累累”,呈露出“現實”對“閱讀”的強行楔入。像孫少平這樣的青年農民在邁向城市的程序中要付出多少慘重的身心代價?
還需注意的是,孫少平對遠方的期待,與同一時期的香雪、鳳嬌們有所不同,後者“是具體的和實實在在的,是精神裡充滿了物質性的”(“鉛筆盒”、“挂面”、“火柴”、“發夾”、“紗巾”、“花色繁多的尼龍襪”……),而孫少平則以浪漫、激情的心态去憧憬抽象、理想的遠方,比如投身到“北極的冰天雪地裡”“赤手空拳”地戰鬥……這也與他身上的文學氣質有關,盡管實際上“他隻能象大部分流落異地的農民一樣”在工地上“扛石關、提泥包、鑽炮眼”。我們在感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時也被孫少平身上那種向往遠景、鬥争不已、不被轄制的力量所感動。
02
對于孫少平這樣的打工者來說,現代城市的吸引力來自于對未來的一種模糊、朦胧的希望和想象,恰恰是文學閱讀,有力地導引了這一希望和想象的過程。然而孫少平在城市所遭受的不平等、他脊背上的“傷痕累累”,預示着實作希望和想象的可能性實在渺茫。路遙如何處置、解決被閱讀所喚醒的孫少平内心翻騰的欲望、所遭遇的煩惱和困境?
孫少平是這樣一個“特異”的農民工:他出身農村,在城市接受教育,最終成長為模範的能動者,既非都市裡落後、低素質的外來人,也不是需要加諸同情的無助受害者(田曉霞曾檢討自己不該以憐憫的态度對待孫少平)。這樣的形象與貫穿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素質”為焦點的主流話語相吻合。“素質”用來指稱人的一系列屬性及其可塑性。從80年代早期開始,“素質”一詞頻繁見諸于主流媒體,成為有關現代性發展的各種表述中的核心要素。
自90年代以來,農民走出鄉村進城,似乎成為其素質得以改善的唯一途徑,就好像狹小的雙水村再也無法向孫少平提供認同。孫氏兄弟所選擇的不同道路,也正對應了農村發展、城鄉流動思路上的轉換,也是現實發生的轉換。《平凡的世界》中有一章描述孫少安苦勸少平回鄉而未果,其間作者隐秘的情感傾向頗值得玩味;而從整體篇幅而言,孫少平無疑是第一主人公——這些似乎都暗示了孫少平所代表的道路的吸引力、競争力。素質話語強調個體的忍耐、韌性、敢冒風險、吃苦耐勞、自我犧牲……這些被視作個人與民族發展所必需的價值觀念。而我們發現這也無一不是孫少平的典型性格。
就某種程度而言,孫少平這一人物形象如同一座曆史的“浮橋”,一方面暗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描述青年人在時代風暴中鬥争成長的“十七年”期間的革命經典;另一方面,孫少平也被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的社會工程所接納,最終将成為市場經濟結構中的勞動力模範。這就好像《人生》中,在亞萍的眼裡,高加林是保爾·柯察金和于連的“合體”。
我想,孫少平式的忍苦耐勞哲學提供了一種化解危機的“粘合劑”。《平凡的世界》展現了孫少平的“匮乏”和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孫始終将克服“匮乏”的途徑放在預設“匮乏”的前提之後的個體奮鬥與自我完善之上;将“不平等”待遇看作素質提升所必須經曆的嚴酷考驗(恰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我們還必須注目于孫的身份,像他這樣的青年農民、城鄉二進制結構下的“二等公民”,依靠自己的打拼來闖出一片天地,這也加劇、固化了那種将在生存競争中的成敗歸咎于自身原因的意識。這種意識在改革開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無所改變,新近的一份關于中國社會個體化程序的調查報告得出結論:年輕人日益将個人的成敗、進退歸結于個人責任,“盡管事實上他們并沒有很多可選之項”。正是在此意義上,孫少平這個文學形象深刻地嵌入到改革時代的社會肌理中。
孫少平的“個人化意識”和改革的大工程緊密相聯,前者内在地配合了後者,同時也是受後者持續影響的一個象征;在此互動中,其應負的責任順理成章地推卸、轉嫁了。而《平凡的世界》的“長銷”,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勵志型讀法”的接受視野,“以‘心若在,夢就在’之類修辭方式,将社會結構的問題轉化為精神世界的問題。隻要社會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轉變,《平凡的世界》就會一直‘長銷’”。
在對“素質話語”有所了解之後,讓我們重返孫少平的閱讀史。“現實”對“閱讀”的楔入,也正是“現實”對“文學”的打斷。客觀情勢即将封閉向“地之子”孫少平們提供選擇的可能性。是閱讀喚醒了孫少平并且訓示給他一個“遼闊的大世界”,路遙隻得仍然通過閱讀将所有的問題消解:“書把他從沉重生活中拉出來,使他的精神不緻被勞動壓得麻木不仁。通過不斷地讀書,少平認識到,隻有一個人對世界了解得更廣大,對人生看得更深刻,那麼,他才有可能對自己所處的艱難和困苦有更高意義的了解;甚至也會心平氣靜地對待歡樂和幸福。”
如上文所述,孫少平慣于将忍耐、韌性、吃苦耐勞、自我犧牲等“内化”為個人品質,将其自身遭受的“艱難和困苦”、脊背上的“傷痕累累”看作個體奮鬥與自我完善所必須經曆的嚴酷考驗。由此,閱讀賦予了孫少平一種關于忍辱負重的哲學(路遙所謂“更高意義的了解”),将苦難自我歸因。
與閱讀相關的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翻版了《班主任》的中心情節,孫少平在開班會——那天班上正在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的時候“偷偷把書藏在桌子下面看”,被同學揭發……這個場景——空洞高蹈、讓人漠然視之的學習,和忘我投入私人閱讀而無視去擷取能量的孤獨個體——一方面預示了此後社會的分裂,另一方面孫少平的姿态與上文提及的他(及路遙)總是将苦難自我歸因而“不假外求”的哲學因果貫通,自此喪失了阿倫特意義上我們在此相遇并共同擔負責任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末尾,這個“對世界了解得更廣大,對人生看得更深刻”的閱讀者重回煤礦:他在礦部前下了車,擡頭望了望高聳的選煤樓、雄偉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裡忍不住湧滿了淚水。溫暖的季風吹過了黃綠相間的山野;藍天上,是太陽永恒的微笑。他依稀聽見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滿活力的歌在耳邊回響。這是贊美青春和生命的歌。這個畫面看起來光明、美妙,其實脆弱、經不起追問。與特定社會階層相關聯的勞動、工作的環境(礦山、煤堆),被“永恒的審美景象”所置換,畫面中的“山野”、“藍天”、“太陽”,還是和孫少平最初憧憬的“外面廣大的世界”一樣朦胧、虛無缥缈,路遙/文學最終賦予了孫少平們“永恒的抽象”,而不再有“現實的具體”……
在80年代以青年人為主人公的小說中,我們一再可以發現類似的“妥協的結局”,在鐵凝為香雪設計的結尾中,陪伴着人物的是“不知名的小蟲在草叢裡鳴叫,松散、柔軟的荒草撫弄着她的褲腳”、小溪歡騰着“歌唱”、“嚴峻而又溫厚的大山”,恰似路遙最後給予孫少平的“山野”、“藍天”、“太陽”……
03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孫少平是一個文學青年。他不安于被轄制的氣質,使其在成為被現代化征用的資源的同時,又若即若離地産生沖突。孫少平的形象,在今天可以被了解為“活着”哲學、“奮鬥”神話出現的“前史”或“想象性的審美預演”。這當然源自後來者所作的曆史批判與反思。問題是,當代文學的生命力一方面在于把文學曆史化,另一方面更要在曆史化的過程中為文學與文學人物作出一個解釋——由路遙所展示的孫少平的命運,在時代節點與曆史現場中給出了何種努力,他的生存鬥争與精神生活在特殊境遇裡有何創獲。
複雜的是,在素質話語的籠罩下,在人物将忍辱負重等品質“内化”的過程中,我們也深刻體會到一種對内部精神的追求。也就是說,路遙了解的、孫少平追求的解放、自我完善、創進不已是對個人有意義的,而不隻是成為社會整體解放的一個零部件。“面對更好的‘機會’,省委副書記女兒的愛情,孫少平更看重的,不是寄生蟲的虛榮,而是勞動者的尊嚴——他是一個‘用雙手創造生活的勞動者’”,他甚至在市場初啟的大幕中想象一種超越雇傭關系的勞動者主體:“某一天,他也會成為一名包工頭……他不會像現在這些工頭一樣,神氣活現地把自己搞得像電影裡的保長一般;他要和他雇用的工匠建立一種平等的朋友關系,尤其是要對那些上學而出來謀生的青年給予特别的關照……”。
更進一步,與小說中其他人物不同,孫少平似乎永遠在流浪,執拗地拒絕固守本位:他首先走出以土地為象征的“超穩定結構”,當城市人的身份唾手可得之時又決然放棄。“迎着清冷的晨風,在靜悄悄的街道上匆忙地走着”——小說中反複出現的、孫少平類似“過客”永無止境地行走在當下的姿态,使得上文議及的自我“内在化”終究不同于“活着”哲學、“奮鬥”神話,不同于以賽亞·伯林批判過的“退居内在城堡”,因為孫少平拒絕種種“隐藏的強制者”試圖為他設定的條件,為他“發明出來的生活形式”。這樣的一種反抗中就有文學青年某種“不安分”氣質的參與。
根據斯圖亞特·霍爾的論述,權力的産生來自于“使人們(社會作用者)接受他們在既有事物秩序中的角色,因為他們無法看見或想象有其他選擇,或者因為他們認為這角色是天生或不可變的,不然他們就是視之為老天注定或對己有利的”。而孫少平拒不接受在“既有事物秩序中”被“派定”的“角色”,他身上天然的文學氣質集中結晶着這份抗拒和檢討。
我們不得不感歎,此時的“文學”依然具備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路遙并不自外于“現代化”的共識,我也并不将他誇張為主流意識形态的解構者,但是他賦予孫少平的這份“不安分”,這種盡管模糊、無法具體賦形卻又真真切切的對“其他選擇”的想象、遠見和不放棄,總能夠在此後曆史展開中為後人提供打開“理性”、“自我”、“發展”、“市場”、“現代”等合理化限制的可能。這難道不是20世紀中國文學最值得人去珍重的品質?
正是秉持着對人生的不竭思索,對未來的特殊想象,當改革開放初見成效,利益共同體初步形成,其他人都安于甚至急于“對号入座”在其中尋獲一份“歸屬感”之時,孫少平在不斷放棄固定自我的流動狀态中成就了一個豐富的主體。文學“既是曆史的符号又是曆史的反抗”。一方面當注重文學與社會環境的依存關系;但另一方面,這一依存關系并不意味着決定論式地将文學視作社會關系的必然産物,而應當在具體的曆史分析中,探析文學對社會環境作出的不同反應,尤其是這種反應的“自由”。
毫無疑問,80年代的現代化方案整合了當時整個社會群眾心理,路遙并不外在于這一共識,此共識也以素質話語的方式滲透到孫少平的意識中。由此這一形象有意無意地配合了社會整體性的規劃方案,但他又特殊地具有不假外求的自我創進的力量,從未喪失“對那個不管多麼狹小但在其中我們選擇做喜歡之事的領域的信念”,在不斷放棄中自由選擇。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孫少平為他所身屬時代的“同時代性”作出了聲明,“同時代性也就是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異聯系,同時代性既附着于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真正同時代的人,真正屬于其時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與時代契合,也不調整自己以适應時代要求的人……但正是因為這種境況,他們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覺和把握他們自己的時代”。經由這個卷入時代沖突和困頓深處的人物,我們能清晰地感覺到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文學的力量;而在今天,當越來越多的人,被打造成“給定”的、“合格”的個人的時候,回望孫少平愈發讓人覺得意義深長。
誠如研究者所言,孫少平的“方案”失敗了,“雙水村的後代們,将被‘看不見的手’驅趕到礦井中,生産出‘帶血的煤’”;但這個“失敗者”啟示我們他在曆史節點上曾經擁有的創造的自由。也許,他的主觀努力與精神創獲,在未來依然可以為變革客觀情勢提供可能……
本文節選自
▼
《曆史中誕生》
作者:金理
出版社: 複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3-7
~ 近期好書 好物 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