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也許真的有宿命這種東西,當一個人遇到危險時,總是莫名其妙地脫險,而仗義相救的那個人,也許就是你宿命的救星,救人者也許并不欠被救者什麼,也許是出于忠義,也許是身份地位使然,不管怎樣,那些從虎口救人得生者我們都是應該尊敬的,不管有沒有宿命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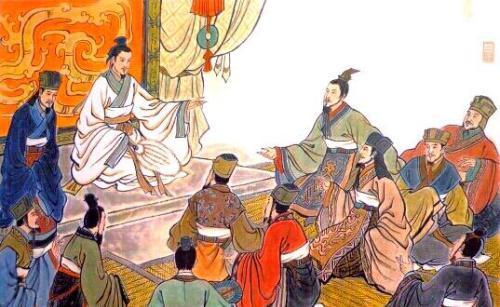
孫權和劉備是相處得最有戲劇性的割據勢力了,對于所謂的聯盟,雙方該做的事情似乎一件也沒有落下,更是從形式上非常完美----聯合兵力,聯姻,同仇敵忾,互通友使……看起來氣氛是如此的和諧。可是兩家被地裡又什麼陰謀詭計都使---你賴我一塊地,我就想辦法把你家主子賺到我這邊扣起來叫你還我地盤!你賺我家主子?我讓我家主子把你妹騙過來!!相對于這種本質的聯盟,曹操倒是除了赤壁那場大火以外,沒有落下什麼精神上的牽挂。所謂鼎立就根本不存在什麼真正的友好,戰争的定義也不僅僅是那“槍對槍來刀對刀”的兵力較量。相對于政治和計謀來說,孫權和劉備的戰争反而是三國中最為頻繁和慘烈的了。由于曹操勢力過強,他平時隻需要看着孫劉雙方煞有介事地握手,一副不滅自己勢不罷休的樣子。這樣的局勢對于曹魏勢力不但不可怕,反而非常有利!因為兩家的地理位置首先就構不成單獨讓曹操“首尾難顧”的局面,個人認為曹操自從除掉馬騰這個心腹大患之後,也是存在地利這個因素的,即對于孫劉任何一方單獨發動的戰争,曹操都有擊退來犯者的把握。而讓曹操“首尾難顧”疲于奔命的唯一可能就是孫劉同時出兵,這樣以來曹操才受到威脅。但是話說回來,那個時代是沒有真正的聯盟的,什麼都是以利益為基礎。兩方同時出兵,當一方損失的兵力超過将要得到的利益時,該方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放棄,這種聯盟的根本意義就是用一些利益使自己的盟友出手相助.而這一點作為曹操來說,一樣可以辦到,而且可以說做得比孫劉兩家任何一家都得力!最有說服力的就是曹操和孫權非常友好地聯合大破劉備軍殺了關羽。大家可以注意《演義》中的一段描寫---1.“卻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淝,懼孫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遣舌辯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淝,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2.“懿曰: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而又乘間竊取回去;劉備又據占荊州不還:彼此俱有切齒之恨。今可差一舌辯之士,赍書往說孫權,使興兵取荊州;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大王興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為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
這兩段描寫就可見一斑了,劉備割三個城池達到的目的,曹操隻派滿寵開了個空頭支票就辦成了。原因就是,經過一系列的心計較量,孫權對于劉備已經根本沒有了起碼的信任,占自己地盤一拖再拖,基本就是個無賴。而曹操呢?不過是明着攻打自己.在那種戰争的年代,出于一種"時代本能",對于戰争都是相當了解的,也就是說,孫權在和曹操交往中的警惕性甚至要比和劉備的交際還少些。曹操相對于這樣的聯盟對手,又有什麼值得害怕的呢?随着劉備率兵去取西川,孫權就動了荊州的念頭,想趁劉備不在把荊州奪過來。說實話,時機選的不錯。因為孫權暫時不會面對曹操的威脅,錦馬超把丞相爺已經弄得夠戗了.而劉備此時的處境也很尴尬。當時劉備在葭萌關禦敵,和張魯的仗随時都可能打起來。而劉璋這邊已經聽從百官的苦苦勸告,命楊懷高沛緊守白水關。這就意味着劉璋對于劉備的感情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以劉備的眼光看,劉璋是個“遲早要成為敵人的朋友”,張魯是個“絕對不會成為朋友的敵人”,孫權此時出兵,就多了一個“馬上跟自己反目成敵的朋友”。這樣一來。劉備可以說是頭一次面對這麼多不可知的因素。時機雖然不錯,但孫權還真得認真考慮一下,因為自己的小阿妹尚香被諸葛亮很“周瑜”的手段連娶帶押地留在了荊州。對于小阿妹,孫權可真的是用了番心思,最後隻好打出了“親情牌”,說母親病重賺她回來。人選上他選擇了周善。《演義》借孫權之口對周善做了番描述---“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随吾兄。今可差他去。”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周善是那種比較玩陰的将領,有膽量和小算盤,但武功不行(在"多随孫策"這種創業的時代沒有見過他出陣).孫權想是認真地叮囑了一番周善,周善便出發了。成功地混進了荊州,周善如喪考妣般地把事情渲染了一番,結果也一樣簡單,孫夫人被深深打動了,一句:“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就表明了自己回吳已成定局。然而在帶阿鬥的事情上,不谙時局的孫夫人自然也沒有相左的意見,同時也能看出,孫夫人和阿鬥的母子感情相當深厚,國太想見阿鬥,孫夫人毫無任何多心,隻當阿鬥是自己的孩子。沒有作為後母的一點刻薄。可見皇叔和夫人的感情之深。沒有不透風的牆,船隊将開,突然趙雲出現了,也許是宿命的安排,子龍将軍又一次出現在了局勢即将逆轉的時刻。周善傻眼了,除了命人馬上開船以外,他沒有什麼可以做的。趙雲隻能沿岸追趕,這時候趙雲和周善都為自己捏一把汗,趙雲是怕找不到船眼睜睜看着小主任被帶走,而周善是生怕趙雲找到船追上來。也許真的是宿命的安排,江邊偏偏有一隻無人駕駛的小舟。
仗着船小身輕,主母的船離自己越來越近,周善此時無計可施,因為他知道自己和五百軍士面對趙雲這樣的将領根本就無法帶走夫人和阿鬥。而趙雲呢,此時也一樣沖突。因為相對于東吳來說,帶走夫人就算是一種成功,而阿鬥的性命就很難測了。對于救阿鬥需要尺度和方式的恰倒好處。是以趙雲很給周善面子,面對要一心置自己于死地的吳兵,隻是“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槍搠,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而孫夫人此時的心态也早就有了變化,趙雲的行為在他急切的心情下變成了無理取鬧。而且孫夫人的話極端傷人,作為威儀有加的一國之母,竟然可以說出“量汝隻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這樣有侮辱性的語言。這句話确實讓趙雲做事有些對于“情理”的忌憚。此時的另外一方---周善則非常精明,你們盡管吵,多吵才好呢,盡可能地拖延時間,我趕緊把船望對岸劃。是以周善還是頗有心計的,沒有作為第三人卷入這場争執,既避免了地位的尴尬,又能不耽誤每一分鐘讓使命成功的時機,而且離成功是那麼的接近……然而精彩的故事就是一種事件被無數次戲劇化的過程,趙雲面對局勢,此時更多的是無可奈何,雖然救得了阿鬥(實際根本不能說是救,隻是緊緊抱着而已),但實質是沒有變化的,危險一樣在越逼越近,他無奈主母幾何,就像當初夫人随劉備回荊州,丁,徐,陳,潘無法阻攔孫夫人一樣。但是孫夫人也同樣無奈趙雲,她知道趙雲是自己丈夫手下得力的戰将,拿話吓唬吓唬可以,真的要自己和趙雲翻臉恐怕也要自己掂量掂量,自己沒有通知丈夫就私自回家,這本身就是失禮之處,趙雲前來追趕恐怕更大的原因是因為阿鬥。自己和阿鬥再親,這畢竟是劉備前妻的骨肉,從國家角度看,阿鬥就是劉備勢力未來的儲君了。這個孫夫人也知道,一旦因為阿鬥的問題上出現争執,孫夫人即使作為主母,說話恐怕也不那麼硬氣吧?至于周善,哪還有時間做什麼抗争,唯一的期盼就是在趙雲沒有殺自己之前趕緊把船劃到對岸,這就是所謂的僵持……可以做一種假設,如果船漸漸地快到了對岸,趙雲會不會撕破臉皮呢?答案幾乎是肯定,以趙雲這種大局觀極強的人,在真的到了要做出選擇的時候,政治意識絕對會戰勝倫理意識的,阿鬥是劉備的命根子,而自己又是劉備出生入死的死黨,再加上“弟兄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這句劉備最經典的格言撐腰,趙雲是極有可能殺盡兵士侍婢,挾持夫人回荊州的!趙雲不笨,他很清楚劉備當年既然肯為他摔孩子,就不會責怪他在需要抉擇時選擇大局。當年長坂一役,趙雲沒有把活着的糜夫人帶回尚且未見責難,何況今日劉備好容易以荊州為基業,正欲大展鴻圖之際,任何有損自己稱霸的行為都是不可容忍的。是以之于趙雲,一旦真的要下決定,除了夫人和阿鬥,全船的人都要死。至于香夫人,不過是探母心切,面對着視如己出的孩子和久随丈夫出征的手足,天真的孫夫人當然不了解趙雲的過分舉動,因為他跟本就不知道這裡面其實蘊藏着這樣的機關。是以她不會有任何所謂“動機”的成分。也許對于夫人來說,阿鬥你都可以帶走,隻要讓我回家看望母親。而這裡最最危險的就是周善,趙雲趙雲他殺不了,夫人夫人也不能跟他同仇敵忾。而且船越近對岸,自己的死期就越近,他的處境不由讓人想到了甘露寺中的賈華。在這種僵持的局勢中,趙雲占了上風,他雖然局面被動,實際上隻是在等待一個合理的時機去實施行動而已。《演義》中有“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捽,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鬥,抱出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于道理:進退不得。”說明他早就有了這種心思,但僅僅是"礙于道理"而已……
張飛的到來是事件的轉折,三方的地位又有了微妙的變化。張飛是劉備的義弟,和劉備的關系在任何時候都不用論證了。以張飛的身份是可以鎮住孫夫人的。張飛一來,孫夫人就沒有再提阿鬥的事。這是個不容小看的細節,在這種對峙的情況下,任何讓步都意味着氣勢的匮乏。而且張飛雖然是粗人,但是幾句話卻說的孫夫人無言以對.由于封建時代女人的規章是相當苛刻的,沒有向丈夫辭行本是大大失禮,再加上孫夫人見了小叔子,自然就不會像對趙雲那樣趾高氣昂了。由于孫夫人的妥協使這表面很驚險的節奏變得明朗了許多,而張飛之于趙雲,又是一種很好的解脫,為什麼呢?還是那句“礙于道理”,也許危機時刻趙雲的極端選擇不會受到責備,但合了解決更好啊!以趙雲的角度處理這個問題,是臣屬對于主子的政治問題,而張飛出面,恰恰使這緊張到了國于國之間的沖突增加了很多家事的味道,而這三方最倒黴的還是周善,被張飛一劍劈死也沒有什麼奇怪的,于家事來說,蒙哄嫂子和侄兒過江;于國事來說,未經主人點頭把主母和幼主帶往敵國,你周善不死誰死?孫夫人走了,再也沒有回來,而孫夫人的回歸使孫劉雙方在局勢上來了個半斤八兩,友好也變得更加政治化,政治的近乎沒有人情味可言。兩家除了割地利誘以外幾乎沒有了什麼所謂的聯盟。孫權變得更加放松,像鬣狗一樣等待着機會,甚至不惜去聯合曹操;劉備呢?隻有笑眯眯地繼續喊着聯盟給曹操看;而曹操呢?還是笑……面對着孫劉兩家"拆東牆補西牆"一樣的聯盟,他坐得住。因為玩慣了政治手段的他不會不知道,三國鼎立,它就是鼎立。隻是三個實力水準相差無幾的人在玩一局牌,也許兩個稍遜于自己的人會聯合起來“出千”,但是,當冠軍隻能産生一個的時候,那兩方就會很自然地産生"與其單純依靠對手中的任何一個幫助,不如在冷靜中等待對手失誤"的想法。曹操的精明之處在于----當孫劉關系緩和時,他視之為一個對手,當反目時再差別對待。而對于孫劉兩家,眼中的對手始終是兩個,而且對待自己的合作者,尺度和難度遠遠勝過那個名正言順的敵人……阿鬥回來了,趙雲放心了,劉備塌實了,孫權減負了。但這次虎口拔牙的真正勝利者,又是誰呢?
作者: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