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的孩子早早地就家了,孫光賢從小就刻苦學習,最終成為家裡的第一個讀者。成年後,孫光賢和大多數讀者一樣,過着漫遊學習的生活。他本來可能是前者中的小官,但前者去世後,孫光賢目睹了危險的局面,打破了四川人民不願離開家園的思維定勢,從西到景珠地。高繼興切據南平稱南平王。這是一個弱政權,在十國都很口袋,在南唐、姚、堯、楚等分裂政權的包圍下,可以說是"四大戰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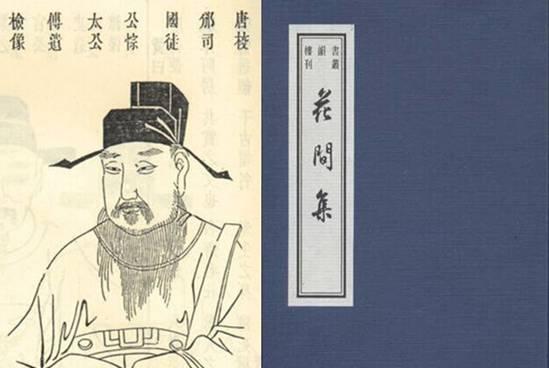
在這裡,孫光賢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四川同胞梁振,梁振推薦他到南平第一代權力吳興王高行下擔任"掌上書記",這個職位一般由知名文人擔任,相當于吳興王高的參謀長。高繼行死後,孫廣賢又輔以高聰、高寶榮等三代統治者,忠心耿耿,高權重,可以說是南平政權的文學勇氣和策劃者。孫光賢是一位頭腦清醒的政治家,他理性務實,這也讓他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與南平統治者相輔相成,為南平政權在四戰局勢中在幾十年的和平發展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天成過年,南平統治者高繼興趁中原亂亂,大軍艦準備進攻楚國,孫廣賢勸阻說,南平剛剛恢複生機,如果善于發動戰争擴大,反而會給周邊國家趁機利用,讓政權有麻煩推翻, 可以看出孫光賢的眼神敏銳,善于檢讨形勢,而這樣的政策也給了老百姓一個休息和療養的機會。
司馬光的《資本管理書》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南平的第二代統治者高聰,非常羨慕楚王馬希凡的奢侈生活,每一句都是眼珠閃耀着哈喇嘛DC,孫廣賢從高霆的眼中看到了前王彥的影子,也看到了死國的迹象, 急忙勸阻說,樊馬希目光短淺,很快就會滅亡,高高從教誨聽孫光賢的勸告,從此"捐好玩,以曆史自娛,省刑瘦,境内安"。後來,孫廣賢的向導梁震自願退休,一切政治事務都托付給他,高霆也非常信任孫廣賢,在孫廣賢的支援下,南平出現了一段穩定繁榮的時期。
其實,回顧孫廣賢的情況,早就看到,北宋建國後,民族團結早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就是所謂的曆史氣勢,被壓迫者之死,孫廣賢敦促南平統治者回歸宋朝,回歸後, 而孫廣賢也受到宋太祖趙薇的贊賞,讓他去黃州做一次刺史。
那麼問題來了,孫光賢是叛徒嗎?不也可以。在統一成為趨勢的情況下,孫光賢的選擇是正确的,可以看出他的頭腦和洞察力确實是非凡的。
孫廣賢在前半生,後半生是一個非常人性化的朝臣,按理說孫光賢應該能夠享受人生,但孫廣賢是一個勤勞的人,應該說他是一個癡迷于書本的人。他癡迷于收集書籍和寫書。在混亂中,高官們經常收集金銀寶,而孫廣賢喜歡收集書籍,每到處,他都會花大價錢買書,這樣家裡就有了藏書,孫廣賢根據這些書,寫進了《北夢瑣事》等書籍,《北夢瑣事》成為研究晚唐社會史的重要參考, 也成為一位著名的曆史學家。
孫光賢是一個三足的花對字人,與溫廷婷和衛莊在一起,但孫廣賢對這個詞的看法與花對花字的人不同。 滿是女聲的《于鑼香澤》。《花套》的《花式》在兩個方面,一是寫關于男女相愛的,如牛所寫的"一定要做一輩子的苦力,做君今天快樂"就能證明。可見,唐末五代十國,是一個充滿荷爾蒙的愛情走向暧昧大爆炸的時代。另一個是yanyan,人們關注粉紅色帳戶中女性的字眼,關注她們的身體部位,他們喜歡寫"眉毛","臉頰","嘴唇","雪胸","纖細腰"等等。總之,花與花之間的字是用花哨的字眼寫出花哨的感情,讓人暧昧止不住。
孫光賢被列為花卉作家,自然也忍不住要寫下這些五彩紛飛的文字,但他也反對追求花哨的語言和熱愛的文字,他希望文字能像詩歌一樣在社會生活中具有教學功能,正如白居所倡導的"歌詩為物而作",文字不僅應該具有積極的教育功能, 但也反映了複雜的社會和悲傷的生活。
孫廣賢其實看不起寫名言的人。他的《北夢瑣事》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金香和凝血,十幾歲時好歌詞,布在雨露。進入階段後,受托人收拾好并燒毀了它。然而,這個國家卻有着沉重的美德,最終為顔言被玷污。車丹進門,号碼是"歌仙"。所謂好事不出去,壞事做千裡之行,就是一位紳士不得不放棄。"繼金的绯香和凝血之後,年輕人喜歡寫豐富多彩的文字,而且很受歡迎。當他和凝血進行屠殺時,他派人到處回收他寫的文字,并把它們帶回去燒掉。但又名氣太大,作品廣為流傳,自然也無法完全恢複,連赤丹人都知道他多姿多彩的話,也給他起了個綽号"宋翔"。孫光賢最後表達了極大的情感,說好事不出去,壞事,很顯然他也看不起那些花哨的字眼,這是當時知識分子比較普遍的看法。"詩意的魅力""言語是道路",紳士的無所作為也是。是以,雖然孫光賢也寫了男女相愛的花話,但他的文字,并不局限于花與花之間的文字,題材有了新的開拓性。
《古史》、《邊疆擁堵》、《鄉村風貌》的花語中很少有字眼,但在孫光賢身上,這些都已成為常态。這些話,相比于寫酒的女人的話,可謂是"花對花",從這個意義上說,孫光賢為花間話主題的拓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喜歡從曆史中學習。作為一個清醒理性的政治家,孫光賢喜歡寫外谷、易史的話。五代十國的混亂與六朝相似,是以六代的興衰可以作為政治參考。孫光賢将着眼于金陵六朝,寫下陳的《後花園花》和張麗華的頭發故事,進而表達他對曆史的深刻思考。幕後花卉:
石城還是空蕩蕩的江國,紫禁城的春天色。七尺綠絲草,世人所不見。
玉英枯萎了,誰知道呢?野草,比如織草,隻是教人加怨恨,絕望。
這個詞的一般思路是,長江下的石頭城是空的,陳後主宮的春色還是一樣的,七尺長的頭發如春草藍張麗華早已是芬芳的玉石,這樣的美在世上是罕見的。繁榮結束後,即使野花燦爛地綻放,也沒人認識她了,就讓人加點吧。六朝的繁榮,早已是一種幻覺。唐代詩人劉維喜也曾這樣哀歎六代文物升天。劉玉玺寫道,"老國山水,潮水打在空曠的城市孤獨地回來了;這個詞應該在劉的詩中使用。
陳後主力窮奢,在國危為難,卻唱着"後花園之花"的大衆之聲;一個是國家最後的紳士,另一個是長得像仙女一樣聰明的漂亮公主,這是中國曆史上死國的标準搭配。在這首歌中,孫光賢沒有明确表達批評,因為中國詩歌是一種微妙的藝術,追求意圖的文字,同時,中國詩歌是一個場景融合的形象藝術,詩人的感受往往是通過場景來表達的。
在這次講話中,孫光賢以金陵春色變成了空洞的傷口,向天下的張麗華緻敬。無論六朝多麼繁榮,而這一切都成了一道痕迹,現在是"更多的人知道,野如織"。表面上是悲傷的貢品美已經過了春天的盡頭,其實是一個荒謬可笑的哀悼時代的結束,一種用暗流的話說,是國家死亡的憂慮。這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從曆史傳統中尋找教訓,也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為國家危機感的擔憂。孫光賢這種深深的曆史苦惱感,在眼中充滿了美麗的風景和想到的花語是極其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