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曾說,你是人間四月天。
艾略特卻說,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
有桃紅柳綠梨花白的美景,也有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懷念。是以,四月是一個感性又感傷、深情又無情的季節。
在古代,文人擅用一首詩、一阙詞抒解心中對亡者的思念。比如元稹的“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陸遊的“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說到悼亡詩,很多人首先想起的總會是蘇轼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還有一阙詞,同樣來自北宋文人,同樣懷念去世的妻子,同樣寫得情意纏綿,哀婉動人。
那便是賀鑄的《鹧鸪天》,它與蘇轼的《江城子》并譽為“北宋悼亡詞當中的雙絕”。
是怎樣的愛情故事,讓堂堂男兒對亡妻寫下如泣如訴的哀思?
又是怎樣的凄美文字,打動人心,繼而成為千古流傳的名篇?
此中的前程往事,還得從故事的主人公——賀鑄,慢慢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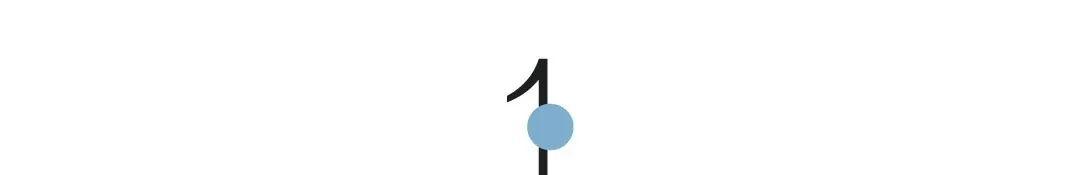
宋太祖的親戚,賀知章的後裔
冬去春來,花開花謝,一年又一年。
有人生離,有人死别,人世自輪回。
宋仁宗皇祐四年,某個秋夜,流星隕落,文宗範仲淹辭世。同年,賀鑄降臨于世。
賀鑄出生在河南衛州,祖籍在浙江山陰。遙想當年,在浙江山陰的四大家族中,賀氏榜上有名。
他還是大詩人賀知章的後裔,或許這是最讓他感到驕傲的榮光吧。
《晉書》上記載,他們的先祖賀純,當過漢安帝時期的大官。朝代更替,人世相傳,賀氏家族出了不少人才,有些當了武将,有些成為文官。
賀鑄的第6代先祖賀景思,當過後唐莊宗李存瑁的侍衛官,他有一位同僚叫趙弘殷。
關于趙弘殷,我們可能不熟悉,可說到趙弘殷另一重身份——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他親爹……
賀鑄的先祖賀景思,與趙弘殷同朝為官,私交甚好。後來,賀景思把女兒嫁給了趙弘殷的兒子趙匡胤。
也就是說,賀鑄的第5代先祖,是宋太祖的結發妻子孝惠皇後。
皇親國戚,王孫貴戚,這般煊赫的家族背景,夠顯擺的。
賀鑄似乎不稀罕這份背景,如遇新友,他更可能這樣介紹自己:遠祖居山陰,吾乃“四明狂客”賀知章餘人也。
賀鑄為人豪爽,俠肝義膽,喜歡談古論今,對于社會上看不慣的事情口無遮攔,一吐為快。
性情使然,他學自家先輩,也自取了個類似的雅号:北宗狂客。
人在年少時,都有英雄夢。賀鑄也曾是俠氣少年,寫下“轟飲酒垆,吸海垂虹”這般豪放的詞句,也懷有戍守邊疆、保家衛國的志向。
可惜,命運不濟,賀鑄一路走來,郁郁不得志。人到中年,更是沉淪下去。
金印錦衣耀闾裡,
少年此心今老矣,
問舍求田從此始。
這三句,或許是他對自己前半生的堪堪回顧。
人生多變,初心易老,年少時做過的夢啊,幾時被遺落于生命的荒原?
不論富貴貧賤,不論今人古人,在這件事上,老天一視同仁。
男人的長相,和才華成反比
男人的長相,往往和他的才華成反比。
此話出自一位企業家之口,這位企業家也用自己的傳奇證明了這一點。
賀鑄似乎也驗證了這句話的正确性。
他長得很醜。
《宋史》中說他長七尺,面色如鐵,眉目聳拔。陸遊在《老學庵筆記》中對這位同時代文人的相貌用了内容豐富的三個字:貌奇醜。
因為其貌不揚,賀鑄還得了“賀鬼頭”的外号。
到底有多醜呢?
大家去想象吧。
年輕時候的他,一邊做着馳馬走狗、刀光劍影的英雄夢,一邊品詩論詞,書無所不讀。據說在宋代讀書人中,就數量而言,排第一的是蘇轼,第二輪到賀鑄。
作為詩禮傳家的貴族後代 ,賀鑄左手持劍,右手握卷。
宋代詞宗李清照眼光挑剔,有些大家入都不了她的法眼。她在《詞論》中平章百家,認為柳永的詞俗不可耐,王安石的文不值一讀,蘇轼的詞作也不過爾爾。
但她贊賞賀鑄,認為他悟得詞中三昧,他的詞才算得上真正的宋詞。
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也對賀鑄的才華稱贊有加:“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嫱、施之袂;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
賀鑄自己呢,也對自己的文學才華充滿信心。
這樣的賀鑄,讓我想到當代詩人餘秀華,老天派給她破敗的皮囊,又賜她寫作的才情。她明白,這是上天給予的補償,給了你這個,就不再給你那個。
有人問,如果用你的作品和才華,換取健康美貌的身體,願意嗎?
她的回答是:不願意,因為不想庸俗過一生。
人生路漫漫,失之東隅,又收之桑榆。上天對每個人終将公平起見,以便才達到生命的平衡性。
芸芸衆生,來來往往,漂亮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靈魂萬裡挑一。
賀鑄同樣如此,長得寒碜,名氣不夠大,可他的才華得到當時和後世的高度贊譽。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
17歲那年,賀鑄仗劍出門,勇闖天下。
小小少年,意氣奮發,那份蓬勃的朝氣、那份江湖兄弟的義氣、那份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正如他自己所寫:
“少年俠氣,交結五都雄。肝膽洞,毛發聳。立談中,死生同。一諾千金重。”
在生死與共的好兄弟當中,有一個人,叫趙克彰。
這個趙克彰來頭不小,他曾祖父是宋太祖的四弟趙廷美。
賀鑄和趙克彰意氣相投,又都有皇族後裔的身份,兩人頗有英雄惜英雄的意味。後來,趙克彰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予賀鑄。
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這句歌詞唱出了一些男人的心聲。比如王小波,她給妻子寫下很多情意綿綿的話語,其中一句是:想起你,我這張醜臉就泛起笑容。
“賀鬼頭”也是如此,他把美妻比作“玉芙蓉”,用詩作記取婚姻裡的甜蜜:
庚伏壓蒸暑,細君弄鹹縷。
烏绨百結裘,茹繭加彌補。
勞問汝何為,經營特先期。
婦工乃我職,一日安敢堕。
……
炎炎夏日,“玉芙蓉”端坐窗下,為丈夫縫補冬天的衣裳。一針一線,她縫得很細緻,汗水不時滴落下來。
賀鑄看在眼裡,疼在心裡,便勸她,我的夫人啊,天氣這麼熱,你好生歇着,這都是冬天的衣物,不急于一時。
趙夫人卻說,這是她的分内事,不敢怠慢。她一邊做手上的針線活,一邊跟賀鑄閑聊家常。
她說,夫君啊,我聽說有一戶人家,眼看着女兒要出嫁了,父母才想起為她治療疾病。
這些雖是冬衣,等到想起要穿時才縫補,那就晚了。現在天氣正好,等天兒冷了,做起針線活,人也縮手縮腳。
詩,寫得質樸無華。
話,說得樸素體貼。
趙夫人的賢惠從中可見一斑。
婚姻中,讓人銘記一生的,除了儀式感很強的重要日期,也包括細水長流的涓滴時光。
除了玫瑰和燭光烘托的紀念日,更值得品味和珍惜的,或許是柴米油鹽的小日子。
生命中多少好時光,當時隻道是尋常。
有一種懷念,叫做物是人非
忽忽幾十年,不過一晃而過。
一眨眼,賀鑄也從朝氣蓬勃的少年成為日暮蒼山的中年。
人到中年的他,客居蘇州,成為故鄉和歲月的浪子。
在此期間,賀鑄的母親病逝了。母親去世的悲痛還未消散,相伴三十年的妻子也離他而去。
接連的打擊将賀鑄推進情緒的低谷。
在最慘淡的境遇裡,賀鑄寫出最凄美的悼亡之作《鹧鸪天·重過阊門萬事非》:
重過阊門萬事非,同來何事不同歸?
梧桐半死清霜後,頭白鴛鴦失伴飛。
原上草,露初晞。舊栖新垅兩依依。
空床卧聽南窗雨,誰複挑燈夜補衣?
那一年,賀鑄已經五十歲了。
這一生,為小小的官職,或者說為了謀生,他輾轉各地,一直走在南來北往的路上。
他從北方歸來,重回江南時途經蘇州阊門,故地重遊,想起當年與妻子在此度過的歲月,往往曆曆,全都于腦海湧現。
姑蘇還是這樣的姑蘇,生活卻已變了模樣。他一邊踽踽獨行,一邊在心裡質問蒼天:既然讓我倆有緣相遇相愛,又為何不能成全我倆相伴終老呢?
梧桐半死,鴛鴦失伴,這在賀鑄眼裡,實屬人世間最悲涼的事情,就和自己的遭遇一樣。
他來到曾經的寓所門前,徘徊着不願離開。他又來前往妻子墳前,一個人久久枯立……
深夜,賀鑄躺在床上,身邊是空出的半張床鋪。他聽着窗外雨聲,腦海裡回放起往日的場景:
燈火下,妻子安靜地坐在那裡,低着頭,她在縫補衣裳。
他和她閑閑絮語,說着白日裡的事情。回想起來,那真是溫暖的燈火、溫柔的側影、溫馨的家常……
這就是“賀鬼頭”賀鑄的愛情故事,平平無奇,溫情脈脈,卻又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就像現實中的很多夫妻一樣。
不知道為何,讀完這首悼念妻子的詞,我突然想起當下流行的歌,忍不住在心裡哼唱起來:
我吹過你吹過的風
這算不算相擁
我走過你走過的路
這算不算相逢
……
人生來來往往,不過是随緣邂逅。
各種冷冷暖暖,卻必須自己承受。
有人說,逝去的人如果被遺忘,那才算真正的死亡。隻要我們為之懷念,離開的人便依然活在我們心中。
生死之間,咫尺天涯,有一份深情的懷念,叫做物是人非,有一種真摯的祭奠,叫作念念不忘。
就像賀鑄的詞,與人生故事。
作者 | 江徐,80後女子,煮字療饑,借筆畫心。
圖檔 | 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