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钰迪丨主播:钰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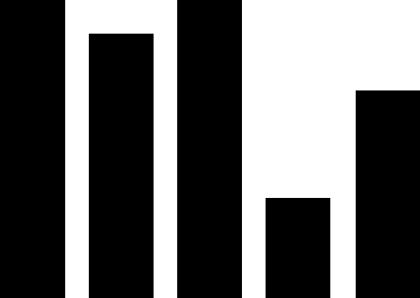
他的文字,因為過分美麗,而讓人戰栗。有人說他是傳奇,有人說他是怪胎。而我說,他是妖。
上世紀是港姐的黃金時代,全亞洲都盯着港娛;而秉承極緻美學絕唱的三島由紀夫,他的頭顱到目前也依然高懸于日本文學的入口,慘烈的死亡方式和暴烈的美學作品共同左右着世界對日本的種種绮念。好像天穹與月魂中傳情的流星,你确切記得那些他來過的時刻,但又永遠無法定義他的存在。
今天讀《春雪》,這本号稱日本版《紅樓夢》的曠世奇作,真的切身體會到三島那種怪戾郁浥又浸滿全身的陰柔魅惑之美。他筆下的人物如高貢的白瓷玩偶,纖塵不染,易碎易逝,但唯有在世俗和污濁之中,可以瞪大雙眼,随時準備玉石俱焚。
/ Part 01
「春雪:曉春的白雪和滾沸的雨珠,生死相依不可方物」
▼
《春雪》講了松枝侯爵和绫倉伯爵兩個世交的大家族後代,松枝清顯與绫倉聰子從春雪到春雪的絕世之戀,充滿了“優雅的犯禁”和“亵渎的快樂”的飽滿對立,也滿含日本古典美學慣有的物哀精神。
他們的愛毀人不倦,又趨之若鹜。彼此的命運包裹在層層疊疊的巨大家族陰謀中,所有的反抗無力也壯烈,最終扯掉牽線木偶的軸線奔湧赴死的一生。他們喚醒了彼此,但也摧毀了彼此。美豔如春光氤氲、時代遺珠的聰子和俊美如珍珠貝内光彩的清顯。
聰子是清顯心裡的一根刺,而清顯是聰子腦海的一枚針:一個讓豔麗悲婉的愛戀像四面八方生長,把金木水火土所有無形之物都含蘊體内;一個把塵世緣起緣滅一針刺破,斬斷情欲手足,徹底遁入空門。
《春雪》是超長篇小說《豐饒之海》的開卷之作,四卷終結後,三島自殺。不同于一味追趕時間的西方小說,他隻想展現東方的輪回思想。停留在一個地方,用時間超越時間,寫著一部足以“解釋世界的小說”。《春雪》中在白茫茫一片裡死去的清顯和剃度的聰子,就是第一個輪回的開始。
三島在文學的世界不遺餘力的造夢,以至于夢溢出到現實,泛濫的夢境反而把現實碾壓,這才是人間清醒。如同每人心尖旁那尊不動聲色的小金佛像,任何情念的漣漪,它都能瞬間剝離皮相和骨相。閱讀他的文字,是當下一地雞毛生活中的賞賜和福利。與其大量地搶購囤物,不如多趁此囤一些光亮的思想,時間奔湧,恒常如新。
漂亮的人一般總能幹漂亮的事,無論是盛大的毀滅還是奪目的璀璨。三島由紀夫是一個從名字就深入我心的人。豆瓣中更是随處可見對其美學理念的膜拜:“美到恨不得整段背誦。”,真是太寵了。在泛着金光的薄脆的糖衣背後,悲傷如瀑布般的錦緞滑落我面前,又頃刻收尾,倏忽絕塵而去。
任憑生命沖撞的本能肆虐在文學的心髒,最後自己在剖腹和三次補刀的斬首中極度痛苦死去的三島,這句話或許是最終極又溫暖的評價:“綠林中,腐爛的屍體開出了黑紅的玫瑰”。
/ Part 02
「燃燒:命運就在他的口袋裡,和那些絕情又違心的信粘在一起」
▼
兩段描寫春雪的文字,是生死最後的唇齒相依。一段是擁吻纏綿的開始,一段是宿命緣盡的結束。
聰子第一次主動約清顯在帷幔包裹的馬車上賞雪:
“布滿灰色微光的帷幔縫隙,忽張忽合,雪花不住地瞅空子鑽進來,在綠色的護膝小毛毯上凝結成水珠兒。大雪撲打着車棚,那聲音猶如躲在芭蕉葉蔭下聽到的巨響。護膝小毯子下面,膝頭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觸,猶如傳遞着雪下一點閃亮的火花。”
漫天飛雪中,清顯身患重病還堅持爬着山路去寺廟為求得和聰子的最後一面:
“這天,大和原野長滿黃茅的土地上,雪片兒随風飛揚。說是春雪吧,又太淡了,猶如無數白粉蟲飄飄降落,天空陰霾,那白色彌漫空中,微弱的陽光照射下來,這才看清楚是細小的雪粉。凜冽的寒氣遠比大雪普降的日子冷得多。”
清顯就好像一場茫茫大雪後的庭院地上闖入的一片櫻花花瓣,冰冷的體溫和熱烈的顔色在體内對峙不熄,最後因為情深夢絕,消逝于最完美的時刻。對他而言脆弱的自尊隻能從拒絕中獲得,而狂熱的愛戀唯有死亡方可成全。
他和聰子從小就形影不離,他被聰子那種大姐姐般總是玩笑對待自己的态度深深地傷害着,也拼命抗拒着。但是他不知道其實内心對聰子的愛意已如草意萌動的初春,在蕭肅凄惶的地下逐漸聲勢浩蕩起來。聰子越是将自己卑微的愛意呈現在清顯眼前,清顯越是甩出既無方向又無歸結的字句。
從出生起,他那哀傷但是俊美的臉上就布滿了一種“孤絕的自我”的迷信,“這種宿疾不存在于肉體,隻寄生于精神。”他的美貌、優雅、優柔、幻象、易傷的皮膚、修長的睫毛,這一切圍簇在他的周圍,似乎都是為了等待那個“宛若六月熟透的杏子,聽起來溫厚又婉轉”的聰子的聲音,把他從沉溺悲傷的夢境中喚醒。而悲傷,曾是清顯體内最精妙的毒素,也是最想去的方向。
清顯被聰子的美麗外表與優雅氣度所吸引,但聰子的性格卻是一股強大的斥力。聰子的成熟,與她不時鋒芒畢露的洞察力與自負心,令青澀任性的清顯自慚形穢。對深愛自己的人報以鄙視甚至冷酷的态度,是清顯最初對聰子的心理設定。但這種毒素是雙向注入的,一方面羸弱的自尊因主動拒絕而多一分韌性,另一方面可以在羞辱冷落聰子的過程中,讓自己墜落的心,被一步步逼着俯沖向前的聰子一點點拉回來。
兩人就在這心靈的跷跷闆上,起起落落,不斷喂養着彼此欲望的胃口。直到那個雪天,馬車的帷幔半推半就地抗拒着輕盈的雪花,而聰子和清顯體内早已集聚了随時噴湧的力量,讓他們在忘我的擁吻中似乎成了那匹頂風冒雪的馬,進而變成一團不斷飛旋向前的冬的倨傲淩冽之氣。
聰子同樣出身貴族,但是男女命運在那個時代是完全不同的。女人多半沒什麼選擇權,她隻能決定是做一顆被利用的棋子還是一具躺平的肉身。是以全篇她的話幾乎很少有什麼言為心聲,全都是在内心被反複洗漱上妝後的話術。
不過有一次例外,當她和殿下有婚姻後還和清顯私通被家人發現,嚴厲斥責,全家慌亂驚悚之際,她淡然又仿佛不是對這個世界說出的那句:“不知女囚犯是穿什麼樣的囚衣,我想穿上它,看看清顯還愛不愛我。”
愛到至深處,女人明知是最終葬身于海的棧橋而不是路,也要走下去,但是男人多半總還是要環顧四周尋一條權宜之路。是以清顯在對聰子愈加濃烈的傾慕和渴望之後,忽然在精神和肉體上都失去了平衡,這種倒行逆施的沖突情緒,源于他矯揉造作的優雅。這份優雅之前在悲傷的底色裡是一種自信,但是現在在澎湃妄為的情欲中卻無處安身,更是在聰子淫靡靈動的自由中,自愧不如。
他在信中,開始和聰子兵戎相見。本以為有抽刀斷水的快意,沒想到是抽絲剝繭的痛苦。離不開,又不敢走近。熱戀本該如色彩斑斓的錦緞一般,可被清顯自己一手打造成家庭作坊的一色純白絲線,一度釋放出的毒絲又重新插進體内。他在“感覺喪失”和“害怕喪失”中毅然選擇了前者。
聰子在多番渴求未果後,在家族絞盡腦汁地鑽營下,被天皇直接敕許給洞院宮三王子。清顯所有的驕傲和自尊原地退下,在喉頭充血的青春氣息中,那頂唯我獨尊的頭顱被頃刻絞殺。對聰子的愛沖鋒陷陣在冬雪消融的第一片酥脆的春日薄冰之上,不過這次沒有如履薄冰隻有一往無前,哪怕是墜入深淵。
/ Part 03
「陰謀:二十年前的詛咒」
▼
所謂優雅就是觸犯禁忌時候的從容,但清顯一開始就觸碰了最高的禁忌。他讓已經和皇室訂婚的聰子有了身孕。
但三島當然不會隻給我們一個愛情故事這麼簡單,他把這個核心的線團外面又精密嵌套了層層線圈,每一個線圈等到指令響起,都會讓我們的心流摧枯拉朽的激蕩一次。人生的思辨和人性的剖析都洞若觀火地纏繞在故事的背後,等待人物牽引起那個線頭。時代不純粹以後,純粹的人必定格格不入,是以這樣看着一手締造的美再被一口口噬蝕為糟粕,故事到這才開始更有意思起來。
這段絕塵之戀的背後,折疊着一段兩大家族曆時二十多年的恩怨情仇。一個肮髒的秘密的尖上開出了一朵妖娆的魅惑之花,人性是養料,時間是催化,這朵花就是聰子,而花的命運在二十年前早就被寫定。越美豔越悲絕。
這裡要提出另一個重要人物的名字:蓼科,绫倉家多年的老管家。她出場不多,但凡出場必是名場面。“蓼”是《詩經》中的一種蓼科植物,它有着極強的生命力和多元的變種。我想三島在此用這個名字按在這個城府極深的管家婆之上也是寓意深厚。
是蓼科一次次幫襯他們掩人耳目完成了所有的偷情幽會。讓他們在偷情的過程中一次次體驗着一種超越幸福巅峰的感覺。聰子曾說,在彼此罪過的行為中,卻在感受着身體被最大限度的淨化。但在一切美的讓人心驚膽戰的時候,這個潛藏多年巨大的醜陋陰謀也逐漸浮出水面。
蓼科在二十年前曾經和聰子的父親绫倉伯爵有染,這是秘密之一。因為這個秘密她暗中接受伯爵旨意,保守了這個家族不見天日的更大的秘密。身為聰子的親生父親,和蓼科極為優雅地說道:“決不能讓聰子以處子之身嫁給松枝介紹的女婿,這樣就能給松枝一個釜底抽薪。”
松枝家畢竟是侯爵,他和绫倉伯爵世交的紛繁關系中,總是有着居高臨下且不可撼動的威嚴。直到有一天松枝侯爵趁着酒興摸着還是娃娃的聰子的頭說:“小姐出落得實在漂亮,長大後真不知會多麼出衆呢!放心吧,叔叔給你找個好女婿,保證是百裡挑一的如意郎君,這事不用你父親操心,我一定讓你穿金戴銀,擺擺绫倉家代代從來沒有過的闊氣。”
绫倉伯爵早已習慣了被當衆無意識的淩辱,他這次依然沒有收起職業性的暧昧微笑,隻不過就是這次,他對蓼科說了上面那句惡毒的施加在女兒身上的咒語。
但造化弄人,當年可能隻是一時怒不可遏的伯爵那麼一說,蓼科卻在心裡紮下了毒根。今時今日聰子經侯爵搭橋,被绫倉家處心積慮又如願以償嫁入皇室家族的時候,蓼科卻依然心懷鬼胎又佯裝忠誠地記挂着當年伯爵的囑托。是以她并不是成人之美,她是早已暗度陳倉。
蓼科這個人物極為複雜,整個禍事的總策劃師可以說就是這個老太婆。她為什麼要策劃這一切呢?她兼有妒忌和愛慕的雙重沖突情感,将年輕的聰子作為老朽的自己肉身的寄托,一邊懷着忠誠的情感來成全這對年輕人的愛情,但卻在中間夾雜着報複性的縱容,多次性消費着這種畸形與變态的快感。
表面上一直忠貞與這個家族的老妖婆,其實一直在等待一個時機出手,用這個秘密毀滅伯爵一家。在時機未到之前,她可以隐忍依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時間,讓濃烈的恨異化成百依百順,等待那黑暗中的箭矢精準射穿暴露于“陽光”下的伯爵。
是以一旦确定聰子懷孕後,一封以蓼科自殺為名的絕筆信就出現在了松枝侯爵的桌上。隐晦又智慧地點明了所有。“這個毫無悔意而服毒自殺的婆子,看她那一臉濃妝,宛若一隻蟋蟀掉到白粉盒裡,裹着紫紅的睡袍,蜷縮着身子。她越是渺小就越使得整個世界都充滿陰郁之氣。”
蓼科想用死來再現自己虛僞的忠誠,把聰子懷孕一事昭告松枝家族,本以為會有兩大家族血雨腥風的兵戎相見。沒想到,處心積慮等待多年的蓼科還是算錯了一步。
/ Part 04
「死亡:我們永世不得相見」
▼
比蓼科的忠誠更虛僞的是,當時日本沒落貴族間對名望聲譽的極力維護。松枝和绫倉家不僅沒有因為清顯使得聰子不光彩的懷孕有所嗔怪,反倒是立刻齊心協力共商如何把日漸隆起的肚子按住,瞞天過海,無論如何都要讓聰子嫁入皇室的肮髒密謀。
大人們太忙了,他們在籌劃秘密堕胎的路上,甚至都來不及回頭看一眼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臉上那僵死般的痛苦早已凝結如霜。女兒的幸福甚至性命,在面子和威望面前,如春雪一般旋即無聲。
聰子被雙方家長安置好所有細節,由母親帶她到大阪做人流手術。在母女二人臨别前去月修寺辭别的過程中,聰子一直如人偶般聽順着母親的所有安排。直到一個月冷如霜岑寂無聲的暗夜,聰子突然叩拜佛祖偷偷剃度為尼。聰子剪掉的青絲供在經案上,她手撚佛珠,眼角輝映着慘淡的銀白曙光,和晨曦中佛珠的冰冷白光交相呼應。
她在塵世間說得最後一句話應該是:“我和他永世不再相見。”
“随着一绺绺頭發掉落下來,聰子的腦袋有生第一次感到如此清凜的寒涼。自己和宇宙之間夾持着的那層燠熱的充滿陰郁煩惱的黑發剃掉了!從此,頭蓋骨周圍展開一片誰也未曾觸摸過的新鮮、寒冷而清淨的世界。剃去的部分逐漸擴大,冰冷的頭皮也随之擴大起來,猶如塗上一層薄荷。
頭上凜冽的寒氣,好比月亮那樣死寂的天體徑直毗連着宇宙浩渺的空氣,其感覺抑或就是如此吧?頭發似乎就是現世本身,漸漸頹落下去,頹落下去,變得無限遙遠。”
人心的冰冷總會給你意外的驚喜。在得知聰子出家的消息後,兩大家族的家長又開始撺掇該給聰子買怎樣的假發,才能繼續扣住這個總是活蹦亂跳,不斷變臉的醜聞。在聰子的頭上蓋更多的假發,也無法為她裸露的頭蓋骨掙得一絲絲的人間暖意吧。
當聰子決意不再走出寺廟的時候,松枝又立刻積極行動起來用萬能的人脈,給聰子開了一個患嚴重腦病的診斷證明。從此蓋棺定論,斷了皇室婚約的心,封了世間閑散的嘴。
清顯知道一切的肮髒最後都被聰子接過去了。他相思成疾,在那個似乎怎麼也走不出的初春,肺病日益嚴重,但孱弱的身體還是沒有赢過随時都會噴湧的想念,他最終離家出走一人踏上去清修寺的路途。奇迹總是在精神先于肉體發生,他覺得從失去聰子的消息後,自己已經很久沒有這麼暢意快活過了,這段路上不再有任何阻礙,什麼優雅什麼悲傷什麼自尊,統統被春雪挾持,他隻要想着最終爬上山能見到聰子最後一面,肉體中就忽然有了那種早已死寂多時的生命迹象的蠕動。
可惜,他反複地哀求都沒能和聰子最後再相見。他想到了當年自己是怎樣用一封封絕情的信把聰子推進了皇室婚約的陷阱。他覺得在這種輪回中,自己跟着這份偉大的愛意也淩空起來。肉體上的折磨會讓精神的刺骨疼痛放緩一些,是以他一遍遍不放棄的拖着垂危的病身攀爬着那座山,總盼望有奇迹發生。假裝最後一場春雪的盡頭就是暖陽。
不過,最後一面始終沒有來。
“回到東京兩天之後,松枝清顯死了,這年他二十歲。”
其實在活着的時候清顯就設想過無數種死亡的方式,最喜歡的還是要優雅的死去。“就像胡亂丢棄在桌子上的繡花和服,不知不覺之間,就滑落到灰暗的地闆上了。”
這個願望,他是實作了。在這場孤絕又浩蕩的豐饒之殇中,遠山、庭院、瀑布、紅葉、春雪、櫻花、大海、寺廟,細膩又磅礴的如畫卷般展開。清顯和聰子就站在畫的旁邊,又或者是裡面,妙不可言。
【本期話題】:你覺得《春雪》中的這種虐戀會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嗎?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本文作者及主播簡介
钰迪:國家級資深電視主持人,一級播音員,進階工程師。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專業大學,廣播電視語言傳播專業研究所學生,北京語言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曾在三聯生活周刊公衆号連載24節氣文章。 當選2021北京青年榜樣。出版書籍《季候電影院》。
音頻制作:上官文露聲音工作室—昊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