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文末分享、點贊、在看三連!
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海上收藏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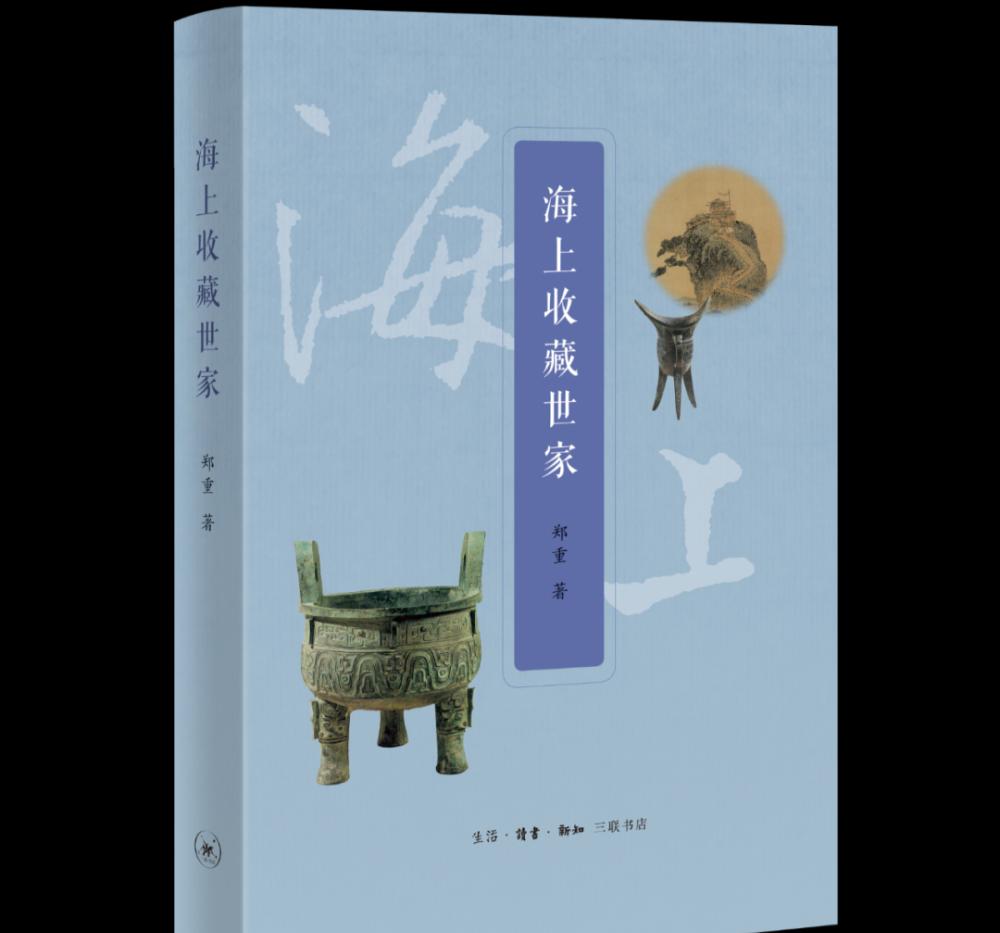
鄭重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2-5
【内容簡介】
這是一部融鑒賞性、知識性與文化性為一體的收藏家傳記。書中共收入20世紀活躍于大上海、曆經半個多世紀的40位收藏大家的逸事。他們有的上承祖蔭,有興趣有資本,走上收藏之路,成為一代大家,如吳湖帆、張珩;有的因家族使命而走上收藏之路,如潘達于;有的創業後有一定資本,漸漸走上這條路,如譚敬;有的出身寒門,但因嗜痂成癖,甘願傾其所有也要收藏,如孫伯淵……無論是何種原因,他們對所愛的收藏都傾盡一生的财富、精力與智慧,更在時代浪潮的變幻跌宕中,與鐘愛的文物一起經曆了坎坷的人生之路。這些人如作者所說,多已成為人間“過客”,但那些沾有他們氣息的珍寶卻得以留存。
【作者簡介】
鄭重先生是《文彙報》資深的名記者,素有援筆成篇,寫情萬裡,精思一隅之譽。為了能留住曆史,我們于新千年初,商請先生執筆編著《海上收藏世家》一書,蒙其慨允,二年來,先生遍訪藏家或其後裔,廣泛收集文獻史料,并對照實物,旁征博引,成此初集,可謂定意于筆,筆內建文,文具情顯。此書之面世,必将洛陽紙貴。
【目錄】
大克鼎:從潘祖蔭到潘達于
半壁江山過雲樓:顧公雄、沈同樾夫婦的書畫收藏
紅頂房老闆:周湘雲和他的收藏
曆盡滄桑的商鞅方升:鑒藏家龔心銘、龔安東父子
珍惜那段情緣:鑒藏家龔心钊、龔安英父女
龐萊臣:虛齋名畫甲東南
從竹山堂到寶山樓:潘博山與潘景鄭的收藏
父子收藏家:丁福保與丁惠康
小校經閣主人劉晦之
錢鏡塘:“我愛雪竹圖”
顧麗江:真、小、精、多的收藏
華笃安:方寸之間天地寬
吳湖帆:梅景書屋,梅花安在
嚴惠宇:收藏以自娛
孫伯淵:碑帖鑒藏家
常熟瞿氏:藏書五世的鐵琴銅劍樓
莊萬裡:兩塗軒“揮淚含笑别家珍”
孫煜峰:有收藏思想體系的收藏家
陳器成:收藏無悔
孫志飛與王亢元:收藏道上兩親家
吳芳生:儒商的收藏精神
張繼英:雲山看去天無盡
袁安圃:将自己“藏”起來
胡惠春:暫得樓主的瓷器收藏
劉靖基:書畫相伴度終生
李蔭軒:青銅淚墜如鉛水
羅伯昭和錢币收藏家群體
李偉先:錢币界的“獨行俠”
施嘉幹和他收藏的現代錢币
吳籌中:紙币收藏五十年
戚叔玉:學者型的收藏家
何東軒與吳王夫差盉
顧恺時:偶然走上收藏之路
王南屏的遺願:送“王安石”回家
薛貴笙:上海古玩界的老資格
譚敬:聚是他,散亦是他
張珩:四海無雙木雁齋
陳萍:功利心太強的人成不了收藏家
杜維善:從“絲綢之路”古錢币上發現曆史
張永珍:收藏我喜歡的東西,再貴也值得
【選摘】
挑起曆史賦予的保護重任
潘祖蔭沒有子女,其弟祖年的兩個兒子過繼給他作為嗣子,不料皆早殇。這樣,潘祖年除了兩個女兒,并無子嗣。長女嫁到吳江同裡徐家,次女潘靜淑嫁給吳湖帆。潘祖蔭在京城逝世,平生遺藏就由其弟祖年用五艘大船運回蘇州。
潘祖年比兄潘祖蔭小40歲。祖蔭逝世後,夫人曾住蘇州,因生活不習慣又回京居住。潘祖蔭夫人去世後,祖年赴京料理後事,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當他到京時,已經耽擱了一個月。潘祖蔭收藏的文物已有部分被盜,有些宋版古籍缺首卷。處理完善後,潘祖年将文物、書籍裝船運回蘇州。銅器中即有著名的大盂鼎和大克鼎。潘祖年對家藏文物定下了“謹守護持,絕不示人”的規矩。潘祖年逝世後,潘達于就挑起保護家藏文物的重擔。
有關潘達于保護克、盂兩鼎的傳說,我久有所聞,可是總感覺那似乎是前朝遺事,離我們相去甚遠。
由于是顯赫家族所藏器物,這些大鼎給人一種高貴而神秘的感覺。1994年的歲尾,我帶着景仰而又激動的心情來到上海高安路口的那座高層建築,走進一個普通家庭。當一位普通的老人出現在我的面前時,傳說中的潘達于一下子變得崇高起來。雖是九旬老人,但步履還穩健,神情開朗,談笑中透露出她那種拿得起、放得下的博大氣度。隻是她那瘦小的身材,和沉重龐大的大克鼎形成鮮明的對比,使我無法相信就是她挑起了曆史賦予的保護克、盂兩鼎的重任。
在這裡,就大克鼎的保藏與捐獻,我對老人進行了長達幾個小時的訪談。
鄭:能否請您談談初到潘家的情況?
潘:我小時候沒上過學,隻是自己留心,粗識一些文字。我18歲出嫁到潘家。我丈夫潘承鏡,表字蓉士,是潘世恩第三個兒子的後代,也叫“老三房”的後代,是祖年公的孫子,過嗣給祖蔭公為孫子,兼祧兩家香火。誰料他和我結婚三個月就去世了,沒有留下子息。這在潘氏家族中也是怪事,嗣進一個就死一個,都是未成年或是沒有子息就亡故。傳統說法都認為這是家中的收藏帶來的陰氣太重,無法承受。祖年公善解人意,很能體諒我的處境,決定不再嗣孫,否則我這寡孫媳今後在家難以做人。當然立嗣是件大事,不能不解決,于是就由我出面,替先夫蓉士立嗣子。可是嗣進不久還是夭折了,決定再嗣,嗣進家懋。家懋又名德齋,日後長成,擔任蘇州中學老師,生兒育女,傳續潘家香火。
丈夫去世時我19歲,家中就隻有祖父、祖母和我三人,冷清得很。不過有祖父在,家裡有主心骨。哪料到第二年剛過新年,祖父也去世了。祖父棺材上的子孫釘,按規矩要子孫來敲,家懋當時才4歲,是讓人把着小手做個樣子盡了禮儀。
祖父去世後,我從此不得不擔起侍奉祖母、撫養幼小子女、掌管門戶、守護家财的責任。我們老小四代四口,在深宅大院裡冷冷清清地過日子。又過了7年,到了我27歲上,祖母也去世了,我身邊隻有家懋、家華一雙子女。家華(老人指指坐在身邊的女兒)是我姐姐丁燮柔、姐夫潘博山的女兒,後過繼給我的。
鄭:家中到底有多少文物,又都放在哪裡,您當時心中有數嗎?您知道這些文物的曆史價值嗎?
潘:當時子女幼小,孤兒寡母守着大量文物财寶,确實讓我心事重重。我知道這些都是幾百年、幾千年來朝朝代代留下來的珍品,一定要想辦法管好,有點閃失就對不起祖宗。至于藏品的總數,我也不大清楚。當時借住在蘇州城裡南石子街“老二房”的舊宅裡,光銅器就放滿了一大間,另有一大間全放古籍和字畫卷軸。這麼多東西,我自己沒有能力去清點整理,但也不許外人來過手。這是祖父立下的規矩。
鄭:那麼多的文物,有沒有被盜與散失?有沒有出售過?
潘:賊偷發生過幾次。有一次在花園圍牆下草叢裡,發現藏着四麻袋青銅古董,這分明是偷賊來不及運出的文物。這裡宅基進深,房間又多,夜裡黑燈瞎火,防不勝防,我稍微經心不到就要出點子事情。究竟幾次被偷,偷去了什麼,我一時也記不清。各式各樣銅綠斑駁的古董,我也認不得叫不出。青銅器最大最重的要數西周克鼎和盂鼎。據祖父說,克鼎是祖蔭公得自天津柯氏,盂鼎原是左宗棠之物,他為了報答祖蔭公營救之恩贈送的。這兩件稀世寶物外國人知道在我家,曾經派人來試探,說是願意用六百兩黃金外加洋房作交換。我想起祖年公曾叮囑這些珍貴文物來之不易,要妥加保護,傳給子孫後代,是以一口回絕。
鄭:傳說日本軍隊占領蘇州時,為了得到大克鼎和大盂鼎,在您家中掘地三尺,由于您周密保護,他們也沒能得到。
潘:抗戰前我曾請可靠的攝影師,将全部青銅器逐個拍照,共得380塊玻璃底片,另外收藏好。抗戰開始,我家也卷進戰亂。家懋、家華随中學撤退去浙江南浔,我随家族到太湖邊上光福山區避難。到了中秋,以為仗打得不那麼急,趁機回趟城裡過節。不料8月16日、17日這兩天,日本飛機大轟炸,蘇州危急,我匆忙收拾好又逃到光福。就在18日、19日這兩天,為了這些珍貴寶藏不被破壞,我立定主意秘密埋藏。先叫家裡的木匠做一個結實的大木箱,底闆用粗粗的圓木直接釘牢。到夜裡,在我住的一進中間背後,搬開了方磚掘個坑,先放入木箱,克鼎、盂鼎成對角慢慢放進箱子,空檔裡塞進一些小件青銅器及金銀物件,随後蓋好箱蓋平整泥土,按原樣鋪好方磚,再細心整理得外表不留挖掘過的痕迹。書畫和部分古董如何隐藏?想來想去放進“三間頭”最為穩當。夾弄裡有三間隔房,我們一向叫它“三間頭”,它隻有一扇小門與弄堂相通,如果小門堆沒,很不容易發現。當時藏書有十幾個大櫥,不好搬動,兒女不在身邊,隻有請我姐夫潘博山将書畫按宋、元、明、清朝代分類,放到書箱裡,裝了30來箱,連同卷軸、銅器等,搬進“三間頭”。小門關嚴,外面用舊家具堆沒,收拾得随随便便。這樣一來,不知底細的人就是走過,也看不出裡面還有隔房。當時家中兩個木匠師傅出力,潘博山和他的八弟具體指點,我始終守在現場,沒有旁人參加。連着兩天幹這樁吃力的事,夜裡點着蠟燭搬運,直到弄好了心才踏實。
日本兵占領蘇州城之後,到處搶劫。我家闖進七批日本軍人,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财物損失就不用提了,萬幸的是大土坑和“三間頭”沒有被發現。據說日軍司令松井都查問潘家的收藏,他到底也沒有搶到手。我家來過那麼多日本軍人,是不是有目的的搜尋也難說。總算躲過了這場災難,文物被儲存下來了。
又是六七年的時間過去了,到了1944年的光景,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爛,泥土帶方磚都塌了,潘博山已經去世。我和兒子家懋及幾個叔伯弟兄和一個木匠,把藏品挖了出來,他們用圓木做架,粗繩結着大鼎,徐徐吊出土坑,箱底還沒有爛掉。兩隻大鼎就此堆在中間背後地方,鼎裡放些破衣雜物,再用舊家具堆沒。這一進的房屋也被釘斷,既不住人也不走人,這樣就一直儲存到新中國成立之後。潘達于講完了和她生命相連的銅鼎以及她個人命運的經曆,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如同完成了保護銅鼎的使命一樣,顯得輕松了許多。
1949年5月,蘇州、上海相繼解放,8月即專門成立了上海市古代文物保管委員會,頒布了一系列保護文物的法令和政策。1951年7月,已經從蘇州移居到上海的潘達于緻函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信雲:
謹啟者,先祖舅伯寅公當遜清光緒間,學尊公羊,啟新民之初轫,網羅金石,創考古之先河。遺箧彜器有盂、克二鼎,為舉世所稱重。公逝世後,儲存迄逾六十年,中間雖滿清兩江總督端方一再威脅利誘,堅拒未為豪奪。達于旅滬日久,所有器物均寄存同族寓廬。迨八一三之役,日寇陷蘇,屢經指名搜尋,幸早複壁妥藏,未罹洪劫,而宅中什物掠奪殆盡矣。竊念盂、克二大鼎為具有全國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貯藏得所,克保永久。近悉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正積極籌備大規模之博物館,儲存民族文化遺産,發揚新愛國主義教育,惟是上海為華東重要地區,全國人民往來輻辏,誠願将兩大鼎呈獻大部,并請撥交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籌備之博物館珍藏展覽,俾全國性之文物得于全國重要區域内,供廣大觀衆之觀瞻及研究,借以彰先人津逮來學之初衷。傥荷鑒同下情,希訂期派員莅蘇辇運,實深盼切,此上
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
潘達于謹啟
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
上海市文管會受捐後,随即派人前往蘇州搬運,由潘達于的女兒陪同前往。當時搬之甚重,今日無法想象,幸好有搬運報告,才使我們可以得知當時的情況,現抄之于後。
—END—
歡迎文末分享、點贊、在看三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