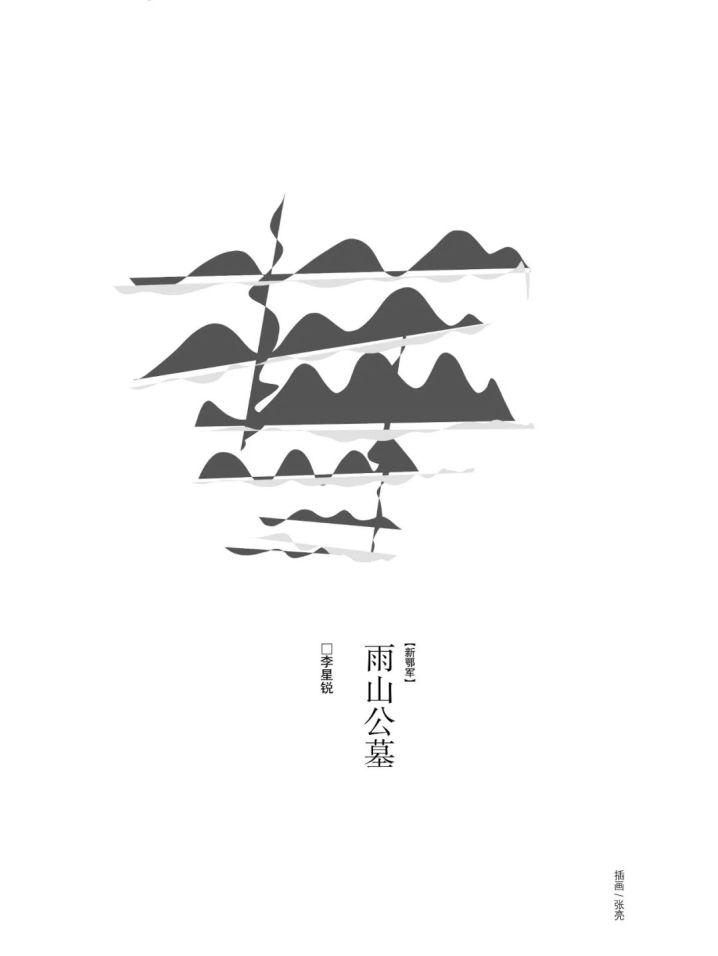
内文摘錄|
我太熟悉他聲音裡的那層水霧。許多年前,當他剛從浴缸裡爬出來,披着浴袍,光着腳,嘴裡叼一支煙,在他空曠的家裡尋找一個打火機時候,就會用那種帶着霧氣的嗓音跟我說話。
雨山公墓
□李星銳
今年夏天,我被辭退以後,就回了老家,打算休息一陣,過幾天清閑的日子。我找來以前的舊手機,把通訊錄從A翻到Z,挨個打過去。除了幾個令我猶豫的名字,和一半左右的空号,其他人悉數寒暄。“你好,打擾了,我是xxx,還記得嗎?”“是我是我,你在家嗎?有空出來玩啊。”熟的不熟的,都約出來吃飯。有時我請客,更多的是對方請。
提到霍明的時候,我正坐在兩個老同學的對面,往碗裡的魚頭上彈煙灰。我們本大可不必提到他的名字,可是這頓飯吃吃停停,已經一個多小時。我們把各自的工作與生活,菜的味道,泡妞的經曆,對學生時代的懷念,對結婚的恐懼,已經聊了個遍,煙也吸了一包半。本來還有個做銷售員的同學坐我旁邊,總想向我們進一步介紹他的工作,未果,想挑起關于國際形勢的話題,也被我們掐滅,終于在兩分鐘前接起一個電話,向我們道歉後,沒有結賬就起身離開了。
“沒意思啊,“坐在裡側做工程的同學說,“上學的時候我就不喜歡他。”外側的律師助理對着手機螢幕傻笑,沒回應他。
做工程的推了推眼鏡,望向我。他戴着遠視眼鏡,從我的角度看過去,他的眼球像是擠在玻璃瓶子裡的香槟,即将從鏡框裡噴射出來。
他說:“我記得你以前和霍明的關系也挺好吧。”
我說,“嗯,以前。”
他咧嘴笑了兩聲,牙齒白得不像是抽煙喝酒的人,“他在我這背過幾萬塊錢的債,我還是上門找了他爸,才把這筆錢給要回來的。”
律師助理擡頭看了他一眼,嘀咕了一句:“你這不厚道啊。”
做工程的說:“你懂什麼,你跟他又不熟。對吧。”
他又轉向我說。“你應該見識過吧,他花起錢來跟公子哥似的,我也是沒轍才找的他爸。不過這都是以前的事了,他現在好像做了警察。要不要叫出來?”
我們都沒有反對的理由。
霍明坐進律師助理的車時,底座嘎吱一響,往下沉了一截,像一艘搖搖欲墜的小艇。上國中時,他是我的同桌,白白嫩嫩,是個還沒長開的小胖子,每天躲在課本壘成的城堡後面呼呼大睡。做不出題的時候,我會隔着衣服,把手指塞進他肚子的褶皺裡,上下三層,起伏如平穩的海浪,手指在裡面,和他沉入到同一場夢裡。如今,褶皺被更多的肉填滿,連成一個光滑完整的球。十多年過去,他已經徹底長開,身型壯碩,吹過的風沙也印入到皮膚裡。隻有手絲毫沒變。中學時代,班上的同學,不論男女,都捏過霍明的手。他的指節修長,手掌柔軟,夾起煙來有一股怪異的陰柔感,讓人聯想起太宰治小說裡的人物。以前我總對他說,你是個天生的音樂家,你應該去學鋼琴。但他并不懂音樂,甚至連撒尿時的口哨也吹不好。
他一見到我,就用胳膊夾住我的脖子,給了我一拳,“多少年沒回來了,啊?連個音訊也沒有。”我把手撐在肮髒的布面座椅上,不知道說些什麼好。
他意識到我的尴尬,迅速抽回手,轉過頭去,從褲兜裡掏出煙來,給我們一人發了一支。
那一晚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四處兜風,開無聊的玩笑。我和霍明被掩埋在嬉鬧之中,繞開了許多本該去談論的話題。臨近午夜時,做工程的把我們挨個送回去,互相承諾有空常聯系,我在家的時候可以多找找他們。我允諾後,很自然地把這事兒抛到了腦後。
第二天上午,我在家門口的早餐店排隊買熱幹面的時候,霍明打來電話,問我今天有沒有空再見一面。他的聲音裡有一層低沉的水霧,不像昨晚四個人一起談天時那麼興緻勃勃。
我太熟悉他聲音裡的那層水霧。許多年前,當他剛從浴缸裡爬出來,披着浴袍,光着腳,嘴裡叼一支煙,在他空曠的家裡尋找一個打火機時候,就會用那種帶着霧氣的嗓音跟我說話。“你莫光站着,快來幫我找。”他嘴裡與皮膚上的水汽會慢慢浸進那支煙裡,讓它變得疲軟下去,逐漸透明。
那時候我們還在讀高中,同在一所半封閉式管理的寄宿學校,但并不同班。所謂半封閉式的意思,就是能辦下走讀證的學生,可以随意出入學校大門,其他人則隻要靠近校門二十米内,就會被門衛警告或驅散。但在我高中三年認識的人裡,沒有一個人拿到過那張神秘的走讀證。
後來回想起這件事情,我覺得另一種解讀方式,更能展現出半封閉式的含義:學校的圍牆上有兩處近似缺口的地方,一處在南端,宿舍樓附近,牆頂的玻璃渣被人用石頭細細磨平了,被我們稱作南門;一處在北端,大門附近,鐵欄杆頂上有一根尖刺被人砸彎,被我們稱作北門。南端的那個靠近網吧,晚上出去通宵的人從這兒走;北端的那個靠近餐館,逃課或加餐的人從那兒出。
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默契,即使是老師或門衛經過這裡,也會扭過頭假裝沒有看見。反正大門是不許走的,交了學費又不想學習的混子們,想要出去玩,就得各憑本事。于是,在我們學校,讀書和翻牆,總得會一樣才行。而且,在我們的觀念裡,隻有那些學不會翻牆的軟蛋,或者沒膽子逃課的慫瓜,才會認命地彎下腰好好讀書,去謀求那條更艱苦的路。
我和霍明都是會翻牆的人。不光會翻牆,而且是身手矯健的佼佼者,是以我們連南門北門都不屑于走,專門找教學樓附近,透過教室窗戶就能看見的牆。助跑幾步,沉住下盤,心裡想着一個讨厭的人,對着牆壁飛蹬一腳,手臂輕飄飄地搭上牆沿。再往側邊伸出條腿,身子就能甩到牆外的世界去。霍明比我高,也比我重,在伸腿的環節,需要我在後面推他一把。也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他幾乎每次逃課都會叫上我。
黃金時間是在下午第一節課後。再早出去的時間太長,比較危險,再晚出去的時間太短,這風險就冒得毫無意義。出了學校,直奔他家,一兩公裡的距離。我想晃悠着去,霍明是個公子哥脾氣,罵我摳門,非要打車。付賬的時候又總在褲兜裡摸來摸去,假裝沒看見後視鏡裡司機的眼神。最後我給了錢,埋怨他兩句,他再罵一次我摳門,“褲兜太深,多摸幾下不就有了。上去請你喝冰水嘛。”
我在他家度過了許多個下午。他的外婆庇護我們,答應替我們保守逃學的秘密。他家是個雙層結構,我們在旋轉樓梯上的房間裡打遊戲,每隔一會兒,外婆就會把他叫到樓下,交給他點兒什麼。兩杯水,或是剛剛洗好的水果。她腿腳不便,無法彎曲得太多,走不了家裡那個狹窄陡峭的樓梯。
樓上的房間對外婆來說,是一個從未踏足過的地方,她隻能永遠地待在樓下,在大廳、廚房和她那間永遠拉上窗簾的暗沉房間裡來回走動,腳步碎得像在發抖。或是在餐桌前的椅子上坐一會兒,起身把放在桌頭的果盤挪到桌尾,把被罩一角的褶皺抖平,喚幾聲霍明,通常十次會有三次得到回應。
相反的,我會盡量減少在他家的一樓逗留。進門和外婆打招呼後,我就溜到二樓不再下去,除非霍明扯着我下樓吃飯。
我讨厭一樓的那片空間。擺在電視牆旁的櫃式鐘擺,像一柄沉悶的大錘,每秒敲擊一次,聲音大得吓人,把整個屋子籠罩其中。隻要待在那裡,就無法不意識到,時間是一個多麼堅硬而危險的東西,它扣擊在四周的牆壁上,仿佛死神的指關節。即使窩在二樓的房間裡,把遊戲聲開到很大,依然能聽到餘音穿門而來。我問過霍明,為什麼不把那個蠢鐘給扔了,這不利于健康。他告訴我說,習慣了。
但我從來沒告訴過他,我還有另一個不喜歡下樓的理由。我有點害怕他外婆。
其實我也無法說清,那是否真的是害怕的感覺。與對蛇、對山谷、對噩夢的那種恐懼當然有所不同——那是一種一旦進入視線,随即就會鑽入腦中,需要用力才能甩開的不适感。
面對他外婆時的恐懼,就像正對着一面歪扭粗糙的鏡子,讓我局促不安,無所适從。面對它時,我無法看清自己的面貌,也不知應該擺出哪種姿态才好。是以,每次進霍明的家門之前,我都要在門口的防滑墊上多蹬幾下鞋底,進門以後趕緊彎腰脫鞋,開始對鞋尖有沒有對齊、擺放是否工整産生莫大的興趣。
“來啦,哎呀,真懂禮貌。”他外婆這麼說道。我哈着腰叫一聲外婆好,轉而捋起襪子上的褶皺來。
“我們要可樂,冰的。”霍明說。
等他外婆用顫抖的手把霍明的兩條胳膊從上到下捏一遍後,她會轉身朝廚房走去。這時,我們上樓,打開電腦,把書包放到飄窗上,霍明會在他外婆的吆喝聲裡下去拿水。
其實,我常會偷偷地觀察他外婆。她太矮小了,而且每次見似乎都比上一次更矮小一點,仿佛正在一點點縮回孩童的狀态。
她患着一種奇怪的病,會一刻不停地打哆嗦。說起話來,語調會被頭部擺得亂飛起來,有時一個音尚未吐完,又被舌頭甩回了口腔裡,聽起來含混不清。手和腿腳也時刻顫動着,仿佛總有一股冷風纏在她的腰上,使她不受控地打起寒戰。我第一次來時,就想問霍明怎麼回事,但他并無向我解釋點什麼的意思,我也就沒有問出口了。
他外婆使我想起我的外婆。但我其實沒有外婆。這對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媽媽說,在她17歲那年,她和她當時的小男朋友在課間的樓道陰影裡接吻,互相撫摸,被準備回辦公室拿書的老師撞個正着。在那個年代,過早萌生的情欲是一頭可怕的怪獸,足以吞沒一個人的命運。媽媽被開除了。每當談論起這件事,她就仿佛又回到了拎着書包離開校園的那個時刻。她說,那天外公穿着沾滿深色油漬的工作服來領她回家的,隻對她說了一句話:“明天來廠裡報到吧。”
外婆則表現得更加痛苦,整晚不停地和媽媽争吵,用最刺耳的話咒罵她。後來的許多天裡,整個屋子都成了她們的戰場。不到一年的時間,外婆被查出乳腺癌,不久就死去了,那時,工廠即将倒閉,媽媽剛剛成年。
盡管我們都說,和她沒有關系,但媽媽總覺得,癌細胞就是在她被開除的那天晚上憑空出現的,并在那些讓人絕望的争吵中得到了滋養。
我沒有見過我的外婆,連照片都沒有見過。聽過媽媽的講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在想象外婆的模樣。我猜想,她應該很瘦,但整個身子往裡扣着,顯得很沉重,乳房無力地吊着,像兩個沒法扔出去的垃圾袋。她應該是充滿憤怒的,但最終還是被生活攪拌成了絕望。
後來,我不再想象了。見到霍明的外婆後,我又開始想了。但霍明的外婆顯然和我外婆——或者說我想象中的外婆——不太一樣。她更矮小,更透明,更像一道漂浮在房屋中的陰影。
有一次我問霍明,外婆叫什麼名字,他那會兒正夾着一支煙,頭從打開的窗戶縫裡伸出去吸着。他愣了一下,說:“你這什麼問題,我不曉得啊。”
我說:“你不曉得你外婆叫什麼名字?”
他說:“我哪曉得,我爸叫她媽媽,我叫她外婆,買菜的叫她吳婆婆。我沒事叫她名字幹什麼。”
他在窗沿上摁滅了煙頭,順手朝外一甩,按下開機鍵,問我:“你今天要玩哪個英雄?”
我們在二樓房間裡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打遊戲。但那裡隻有一台電腦,我們隻能換着玩兒,一人來一局。大部分時候,他都會賴皮,趁着那局快結束的時候,讓我去他書房的抽屜裡找一支煙抽,是從他爸爸那裡翻出來的黃鶴樓1916。或是叫我下樓幫他拿一點吃的,趁此機會偷偷再開一局。
晚飯之前,霍明會在二樓的浴室洗個澡。他一天要洗兩次澡。聽到水聲響起來,他外婆便進了廚房,開始做晚飯。一般隻做我們三個人的飯菜,若是看到餐桌上的菜品更豐盛一些,我就知道,今晚霍明他爸要回來,我便默契地不會留宿。晚飯後,我自己搭公共汽車回學校,從牆外面翻回宿舍裡去。
“不在他爸要回家的晚上留宿”,這成了我們之間一種預設的規矩。我們遵守這個沒有理由的規矩,直到那件事情打破了它。而這種規矩一旦被打破一次,就立刻無效了。
這本是一個無所謂的規矩,打破它的那件事也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的許多時候,我總是反反複複地想起那天的事來。
事情發生在一個星期五,我們本來并沒有打算去他家。按照學校的慣例,星期五下午的最後一節是沒課的,專門用來大掃除。那是周圍網吧最緊俏的一段時間,第二節的下課鈴一響,南北門前排滿了人,有感覺排不上的,甚至大着膽子會去試一試往學校的後門沖,盼着趁門衛給住在學校的老師家屬開門時一起擠出去。
我們和霍明班上的幾個同學說好了,一起去網吧開黑,第二節課下了就走,已經有人提前出去,在網吧占好了位置。
然而,課還沒下,他就開始鬧肚子,用他的話來說,“像有人把擀面杖塞進了他的腸子裡。”放學之後,我讓他的朋友先走,我們随後就到。
等到他一瘸一拐地從廁所走出來的時候,校園裡已經響了薩克斯曲《回家》。掃除結束了,想離校的人已經離開,其他人回到了教室或者宿舍,遠處的操場上偶爾傳來尖銳的哨聲,有人在那邊踢球。
“還去嗎?”我說,“不知道位置有沒有留到現在。”
“去看看再說。肯定是早上的面不衛生,再不到那家吃了。”
“那走呗。”
我們繞去離網吧最近的南門,還有人在排隊,大概是一個宿舍的人,互相推搡着,在牆根的落葉裡撚來撚去。我們站在遠處抽了支煙。霍明往地上吐了口痰,拉着我去教學樓那邊。
“日他媽,沒那個本事還非要占着門不走。”
我撇了撇嘴,踩滅了煙頭。
當我順着記憶的扶梯攀爬回那天下午,我不可避免地一次次想起,從南門走向我們常翻的那道牆的路。我們的心思全放在網吧的座位到底有沒有被搶走這件事上,全然沒有意識到那種奇異的靜谧。
是否有風?路上還有别的行人嗎?我有沒有注意到教學樓的窗子裡飄出的争吵聲?我沒什麼把握。隻有一種仿佛在泳池裡泡久了的困倦感包裹着我。我打了兩個哈欠,用唱歌似的語調喊出來。霍明催促我走快一點。
助跑了兩步以後,霍明蹬着牆向上一跳,大概是剛才把力氣都拉進了廁所裡,他手沒抓穩,掉了下來。“看來今天不适合出校。”我說。
“少廢話。”他松了鞋帶,重新系牢,再蹬一腳,順勢搭上了牆。我正準備推他,聽見背後“咚”的一聲,回頭往教學樓那邊望去。
“操,什麼東西啊?”他一條腿搭在牆沿上說。“抓不住了,快推我撒。”
我沒有回應他。
“别鬧我好不。”他轉頭看我,我正向着教學樓的方向慢慢走去。“你媽……”他摔了下來,一屁股坐進了泥裡,眼睛盯着我步子的方向。
那裡趴着一個人。背着書包,臉貼在水泥砌成的地面上,看上去有點冷。她的另一隻鞋挂在教學樓下方的灌木叢上,像一隻被擊落的麻雀。
霍明起身拍了拍褲子上的泥,喊了一句什麼,我沒有聽清。教學樓的窗戶裡傳出一聲尖叫,像一聲集合的哨響。我擡頭向上望,想辨認出她到底是從幾樓掉下來的。但是辨認不出,所有的樓層都有人探頭,許多人從遠處朝這邊走。霍明又喊叫起來,這次我聽到了,回頭一看,他迅速蹬上了牆,獨自翻了出去。那時我離趴在地上的女生已經很近了。但我轉身跑向霍明的方向,我從未如此害怕過被他抛下。
翻過牆的瞬間,我看見霍明蹲在地上。我朝那個女生的方向看了一眼,人群即将把她包圍起來。從縫隙中,我看見她沒穿鞋的那隻腳上,襪子卷曲起來,腳後跟露在外面。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幫她把襪子拉上去。我這樣想着,人已經落到校外的地面,什麼也看不見了。
誰也沒有再提網吧的事。我們像兩個逃離作案現場的兇手一樣,搭上一輛路過的的士,直奔他家去了。
事實證明,人在面對創傷記憶時會自我保護似的選擇性遺忘,這一理論大約是錯誤的。無論時隔多少年,那個下午所發生的細枝末節,我依然記憶深刻。也或許,對于兩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來說,一個陌生的女孩突兀地出現在學校的水泥地上(簡直就像從地底浮出來一般),和初三某個周日的上午,我在河堤上觀看到的日食屬于同一類事情。那種籠罩住我的謎語般的沉默,不是因為它本身,而是因為它并不屬于我們的生活。
那天晚上,他外婆做了頓豐盛的晚餐,但我們誰也沒有提離開的事情。他外婆在收拾碗筷的時候喊了霍明一聲,沒有回應,她就渾身顫抖着洗碗去了。
我們躲藏進他的房間,沒有人開電腦。霍明去洗澡的時間比平時更早,他從浴室回來時,身上漂浮着溫暖的霧氣,他一言不發地坐在床頭,往腳腕上噴了點兒雲南白藥,嗆人的藥味與煙的氣味混雜在一起。我開了點兒窗。
“操,應該是翻牆的時候扭了。”他說。他的腳踝沒腫,反而蒼白得缺乏血色,就像那個女孩的腳。我轉過臉去不再看他。
午夜,我被樓下叮鈴哐啷的聲音吵醒,應該是他爸爸。沒過一會兒,巨大到不可思議的鼾聲傳了上來,又被節拍器似的鐘擺聲切碎。我背對着霍明,在黑暗中聆聽了一會兒,霍明不打鼾,我沒法判斷他到底是不是醒着。在他家入睡,本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下恐怕得失眠了。我這麼想着,但還是很快就睡着了。
那個周末不放月假,但我們還是在他家多待了一天。他爸在我們起床之前就離開了,沒準連家裡多了我這麼個人都不知道。
霍明早上照例去洗了個澡,等他的時候,我突然感覺有點心慌。他家的鐘擺聲還要響起許多次,才能把這一天耗盡,我不想他走進房間後,出于無聊跟我聊起點什麼,什麼都不可以。于是,在他趿着拖鞋進來找吹風機的時候,我說:“反正今天不去學校,陪外婆買菜去吧。”
他關上櫃門,扯着吹風機的線說:“随便。”
十分鐘之後,我們扶着他外婆出門,我一直在外婆右邊,想把她手裡的菜籃子扯過來,他外婆說:“不用,不用。”我們跟在外婆身邊,順着她的步子行走,從家門口到馬路上的那段小斜坡,就花了四五分鐘。霍明步子大,總想走得快一點,他不知道菜場的位置,走了幾步又折傳回來。
我扶着他外婆,她的小臂細得像一根手指,随着步子輕輕扯動着,仿佛想要掙脫開來。我看她有點喘,幾乎快要被我拖着走了,我說:“您走慢點,我們不急的。”
“孝順哦,孝順哦。”她笑了起來,露出幾顆結石般的牙,“老了就是容易累,步子都邁不開咯。”
霍明說,“要不中午我們做飯吧,你休息下,别累着了。”
“你要是心疼外婆,就少逃點課,免得我擔心。”外婆說,“你們年輕人事情多,做飯還是我來吧。”
“那我們給你打下手。”
但我們沒有打下手。回去之後,我們回霍明的房間打了兩把遊戲,飯就做好了。
那天,我們沒有談起昨天發生的事情,在香煙、遊戲和時斷時續的沉默裡,一個新的規矩悄悄樹立起來。我們從來沒有聊起過那件事情。
晚飯之後,霍明說,還是回學校吧,一天不在,怕老師要告狀了。我說,好。霍明主動去洗碗,我收拾我們的書包,剛走下旋梯,他外婆湊過來,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說:“你是個好伢,帶着點明明,别讓他學壞了。他爸管得少,他又不愛聽人說。”她看了一眼廚房的方向,霍明正在把洗幹淨的碗放回櫥櫃裡。她說:“跟你玩的時候,明明也比平時開心一些。以後多來,想吃什麼跟外婆說,我做給你吃。”
回學校的車上,霍明本來打算睡一會兒,我拍了拍他,說:“你多關心下你外婆。”
他說:“還用你講。”
從那之後,我去他家去得更頻繁了,有時他爸在,我們也過夜。霍明說有題要問我,是以把我扯了過來,他爸便默許了。
我逐漸開始适應他家的鐘聲,和他外婆之間的話也多了起來。
霍明找借口霸占遊戲的時候,我就會溜到樓下,坐在餐桌上慢慢剝一個橘子吃,等着他外婆過來扯着我講她小時候發生的故事。故事斷斷續續的,從她出生的那個荒涼的大院子開始,講到如今已經消失的男人們尚且年輕時淌着酒氣的罵聲,講到女人的腳,冒着濃煙的火焰,鋼鐵,已經忘記面孔的母親。有時候,她會突然岔開,講一講聽說是在同一時段發生的别人的事情。講到興起,我會再剝一個橘子。直到樓上傳來霍明的喊聲,我們把這一頁記憶折個角,等着下次再翻起。
然而,一個多月後,他外婆便去世了。
那天晚上,距離高二的期末考試已經不到一周。具體是星期幾,我記不清了。從聽他外婆講故事開始,我大概去了他家四五次,氣溫爬升得很快,潮濕的熱氣像柳絮一樣,從遠處飄飛而來,我和霍明在學校附近的批發市場買了一大袋雪糕,塞進他家的冰箱裡,準備用以消磨即将到來的酷夏。
“就一把,打完就寫作業。”晚飯以後,霍明嘴裡還嚼着飯,在樓下到處翻找打火機。我從口袋裡掏出來遞給他,他光着腳朝樓上跑去。
“你不去玩嗎?”他外婆說。她圍着餐桌慢走着,忍不住地打嗝,一邊雙手交叉揉着肚子,像是要把胃裡稀少的食物揉碎。
我把盤子裡的剩菜用保鮮膜封好,放進廚房,友善晚上霍明他爸回來加熱着吃。我說,“快考試了,等他休息一會兒,還得寫作業呢。您上次講到您父親走了以後,您就沒去上學了。然後呢。”
“快考試了,等你們考完了我再講吧,暑假多來玩啊。”他外婆說,“夏天我做綠豆湯你們喝。明明說我做的比你們學校裡的好喝,每年夏天都要我弄,還要凍成坨子吃。”外婆擠着嘴笑起來,從她有些歪斜的臉上,我完全沒法看出來任何青春來過的痕迹。
我說,好。
他外婆說:“你去吧,我回房裡把昨天的電視看完。”
那是她說過的最後一句話。之後很多次,我在學校和霍明一起抽煙的時候,他都旁敲側擊地問我,外婆說的最後一句話到底是什麼。我說,就是這句。一次又一次,我重複着這句話,一直到煙吸完,我們都不再開口。我總覺得他隐隐地恨着我,每次我說出這個平常無奇的句子後,他的恨意都會更沉重一分。
我是趴在桌上被霍明搖醒的。打完了那局遊戲,他果然又開了一局,我們一直玩到轉點,霍明他爸早已睡熟過去。
“還有幾天考試了,怎麼辦?”我說。
“明早起個大早,一起寫完再去學校。”他眯着眼睛,鑽到了被子裡。
“我很慌,睡不着。再這樣下去,我們考不上大學了。”
“不是還有一年嗎?我有個考上浙大的哥哥告訴我,考前沖刺比什麼都重要。”他把手機扯進被子裡,細長的手指快速翻動着,有如彈奏鋼琴。“快睡,明天早起學習。”說完,螢幕的光亮熄滅了。
我伫立在黑暗裡,突然感覺到未來的壓力提前朝我壓了過來。我嘀咕了一句:“我又不像你,我沒有退路。”我下樓給自己倒了杯水,擺在煙灰缸的旁邊。拉開椅子,把鍵盤掃到一邊,鋪開作業,打開台燈。
“神經病。”鼓起來的那團被子說,然後靜默了下來。
我被霍明搖醒後,感覺半邊臉都麻木了,脖子像被人折斷後剛剛接起來似的。手邊的作業濕了一片,印出重疊的字影。我看了一眼鐘,兩點半。“幹嗎啊?”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外婆在叫我。”他看上去慌了神,“不對不對,我也不知道是做夢還是真的聽到了。”
“你睡得那麼死,怎麼可能聽得到,外婆聲音那麼小。再說大半夜叫你幹嗎。”我側過耳朵傾聽了一會兒。在寂靜的夜晚,鐘擺聲和鼾聲格外靠近這個房間,簡直就像魔鬼在門口詭異地笑着。我打了個寒戰。
“不行不行,有點怪,我下去看看。”他穿上拖鞋朝樓下跑。
“做夢做傻了吧。你輕一點,别吵着老人了。我先睡了。”我關掉台燈,爬進被子,想趁着迷朦的狀态早點睡着。霍明睡過的地方暖烘烘的,我鑽進這股暖意裡。
還沒有完全睡着,我又被樓下的聲音拽醒。我啧了一聲,翻了個身。鼾聲止住了,我聽見霍明在大聲叫我。
“幹嗎啊?”我用手撐起上半身。
“外婆走了。”霍明喊。
“啊?”我說。
“你莫亂說。”霍明他爸低沉地吼叫了一聲,開始給人打電話。
我從床上爬起來,沒有開燈,準備下樓。我看見樓下的燈全都亮了起來。
“你等下,幫把我外套拿過來。”霍明喊。
我又轉身跑進房間,按下頂燈的開關,還沒等它完全亮起來,透過窗外的燈光,我瞥見霍明的外套堆在床頭櫃上。我拿起它往樓下跑,身旁響起陶瓷破碎的聲音。我碰倒了桌上的煙灰缸和水杯,在剛剛亮起的燈光裡,煙灰如骨灰一樣揚起,又混在清澈的水裡流淌而下,灑落在床單、地闆、霍明的外套上。
“稍等一下。”我喊了一聲,拍打着他的外套,一時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沒有人回應。大門猛地關上了。我跑下樓,沒有人。又跑到樓上,打開窗戶。他們背着外婆上了霍明他爸的車,像背着一塊幹燥的木材。我跑下樓,敞開大門,想跟着一塊兒去。
沒有趕上。車燈在馬路上越來越小,與不遠處閃爍的黃燈融為一體。我在花壇邊站立了一會兒,忽然感覺有點冷。六月初的夜晚,幾乎無風,白天的暖流沉了下去,滲入地裡。我披上霍明的外套,把拉鍊拉到頂,才感覺好一些。他的衣服對我來說太大了,我伸直胳膊,也抓不到袖口。
我順着斜坡往他家走,那是一段漆黑的路,不遠,但黑得徹底。我狠狠地跺了幾腳,感應燈也沒有亮,卻驚擾了不知誰家的狗,它聲嘶力竭地吠了起來。拐進他家樓道的瞬間,我瞥見遠處的一團亮光。附近建立起的高樓裡,誰家的窗戶還亮着燈。剛才我以為那是月亮。眯着眼看過去,有一道人影在燈光裡浮動,應該是在洗澡。不知為何,我覺得那團影子正在唱歌。
收拾完霍明的房間,我無事可做,又晃悠到了樓下。燈光太過耀眼,我關了兩盞,走進他外婆的房間。那是我第一次走進這個房間。暗紅色的窗簾緊緊閉着,一台黑色的等離子電視挂在牆上,像一幅丢失了畫的畫框。我摸了摸,冷冰冰的。床鋪窄小,床單上繡着大朵的雲,肥頭大耳的神仙大笑着在雲上飛。被子掀在角落裡,堆成一條,看上去他外婆像是還睡在裡面。相比之下,床榻的中間幾乎看不出有人睡過的凹痕。
我退出來,坐在餐桌上剝橘子吃。這時,我突然想到,他外婆的故事才剛剛講完童年。
鐘擺的聲音越來越響,像浪頭一樣打來,我覺得自己的骨頭都在随之咔咔作響。片刻後,我站起身,把椅子歸回原位,把橘子皮扔進垃圾簍,走到櫃鐘前,拔掉一節電池,裝進口袋裡。海面歸複平靜。但那聲音還是慣性似的在我腦子裡跳動。
我上樓收拾書包,疊好被子,離開了他家,沿着路邊的花壇往學校的方向走去。
霍明自然沒有參加考試。整個暑假,我們也沒有互相聯系過。開學之後,偶爾在學校碰見,會一起去廁所抽支煙,聊點有的沒的。誰都沒有再提去他家玩的事情。
高中畢業,我去了外地讀書,畢業後留在了那裡。直到這次被辭退回家,我們已經七年沒見了。
是以,在他打來電話,問我今天有沒有空見一面的那個早晨,我是猶豫的。身為少年的霍明已經告一段落了,這個與他同名的青年到底想找我做什麼?我實在容易猜到。無非是填補中間的空白,聊一聊過去的事情。況且,我們大概不可避免會談到他外婆,沒準連那個女孩都得被迫談到才行。
我正在編撰借口,他有所察覺似的,在電話那頭清了清嗓子,“昨天他們說你辭職回來休息,應該都有時間吧。”
我說:“是辭退。”
他像是被絆了一下,頓了頓說,“那我下午兩點去你家門口接你。吹頭發去了。”
霍明開着一輛暗棕色的大衆轎車,樣式老舊,車身有擦痕,我忽然想起來,是那天晚上他爸爸開的那輛。他坐在駕駛座上抽煙,從遠處看過去,愈發像一個勞累的中年人。
我打開副駕駛的門,他說等等,然後解開安全帶,把堆在副座上的商品袋、半包薯片和礦泉水瓶甩到後座去。
“都沒時間收拾。”他說,“坐。”
在駕駛座與副座之間,放着半瓶可樂,半盒抽紙,半包香煙。煙灰缸塞得滿滿的,一些煙灰散落出來,附在變速杆上,像堆積在樹梢上的雪。他座椅下面的地毯上有一塊深色的污漬,大概是可樂揮發之後凝結的糖分。
車裡彌漫着二手煙、沐浴露和打火機油的味道。七八年前,霍明的房間裡也充斥着同樣的氣味,隻是不如這裡的濃郁、暗沉、令人窒息。
我打了個噴嚏,把車窗開到最大,“鼻炎。”
他掐滅煙頭,發動車子,從後視鏡裡迅速掃了我一眼,說:“找個咖啡館坐坐?”
我說:“就車裡吧。”
他說:“行,去個安靜的地方。”
車停在江堤邊,我們去附近的便利店買了兩瓶水,一條西瓜味的口香糖,坐回車裡。
“你怎麼樣啊,小夥子?”他說。
“找我出來就為了說這?”我說,還沒等他回話,我又說,“算了。聽說你當警察了?”
“什麼警察啊。”他說,“就是協警,跑腿的。”
“沒想考個正式編?”我說。
“去年考了一次,沒考上,今年估計也懸。”他打開車門,準備點煙。不遠處的空地上有人在跳廣場舞。他指了指反方向說,“朝那邊走走吧。”
“你現在煙瘾挺大的啊。”我說。
他幹笑了一聲,“沒辦法,同僚們都抽得兇。”
為了躲避太陽,我們下到江堤的那一頭,順着樹的影子慢慢地走。車輪碾過柏油路的聲音與林中樹葉的低語逐漸交彙起來,融合成一種近似于情緒的背景。夏天的江水朝岸邊行走了幾十米,變得寬闊,停止于樹的另一邊。有輛車停在那裡,一個中年男人帶着兩個女孩兒在江邊戲水,旁邊豎着牌子,上面寫着:請勿靠近,預防血吸蟲病。
我們沿着這樣的景色往前走。霍明不停地擦額頭上的汗,一邊傾倒似的對我說了好多他最近遇到的事情。
他找了一個女朋友,是高中時的學妹,後來在家鄉唯一的商場裡再次撞見。他好幾年前一度沉溺于往遊戲裡充錢,為此欠了好多債,直到最近才全部還清。他與那幾個喜歡上網的高中同學還保持着聯系,每周末都有一天的時間一起去當年的網吧。還有一些瑣碎的事情,我沒太認真聽。
我們很快就走到了樹林的盡頭,在那之外,建立起的亭子、輪滑場地、供人跳舞的廣場,共同暴露在烈日裡。我們回頭順着來路往停車的方向走。
“講講你當警察的經曆吧。”我說。
他說,“其實很無聊。帶我的師傅經常有别的事情,我就和另一個協警一起開車出去晃悠,需要巡邏到晚上。為了找點樂子,我倆專找停在人少的拐角裡的車子。你懂的。一看到有車在晃,我們就提着電筒過去敲玻璃,大喝‘幹什麼,警察’,過一會兒車窗就會搖下來,探個腦袋出來道歉。都碰到好多次了。”他哈哈大笑起來,又歎了口氣。
“不過,有一次我倒是印象深刻。”他說。
“因為女的你認識?”我說。
“什麼?”他愣了一下,“不是,我說另一件事。有一次正好是中午,師傅出去了,所裡就我一個人,正在玩電腦呢,一對夫妻帶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進來,探頭探腦的,說有警察同志在嗎。我說有什麼事嗎,正準備給師傅打電話,那個男的說,沒事,就是想讓警察同志教育一下他兒子。”
霍明又掏出一支煙,晃了晃煙盒。最後一支。他看了我一眼,我說,“你抽吧,我不要。”
他繼續說:“我還以為犯了啥事,那個男的把我扯到一邊,說他兒子在學校裡欺負了别的孩子,把同班的男生鎖到了廁所隔間裡。給他說也不聽,蠻橫得很,就想着帶過來讓警察管管他,再不濟吓唬一下也行。”
想到那個場景,我覺得好笑,問他:“那你怎麼教育他的。沒想到你還有教育别人的一天。”
“是啊,我周末去上網的時候,把這事兒跟他們說了,他們都笑翻了。明明我才是那個從小被教育的人。”他說,“我把他帶到會議室呗。本來想吓唬他一下,但是小孩緊張得不行,快哭了似的。我就問他為啥這麼做。他說,其實不認識那個男生。是朋友要他這麼幹的,如果不做,就不跟他玩了。我就随便說了幾句,告訴他,不要交壞朋友,那些人對你好,隻是為了利用你。分辨善惡比友誼重要。然後跟他說了些要好好學習之類的話。”
我本想調侃他兩句,但轉過頭去,發現霍明神情低落,側臉籠罩在剛剛吐出的煙霧裡。我問他,“怎麼了?”
他說:“哦,沒啥,就是當時說完以後,想起來那句話是我外婆之前跟我說的。”
我們回到車裡,他打開空調,又搖了一次空蕩蕩的煙盒,把它扔出窗外。“去接我女朋友。”他說。
陽光開始柔和起來,由白轉黃,冷氣開得太足,我抓住頭上的扶手,有點犯惡心。
“其實還有件事,我印象也蠻深刻的,不過這個沒跟别人說過。”他把音樂聲擰小,“我剛進所裡時聽到的一個案子。有個人死在了我們學校旁邊的湖裡。”
“學生自殺嗎?”我說。
“不是。開車沖進湖裡了。”他清了清嗓子,“是這麼個事兒。有天晚上,我想想,應該還是夏天的時候。某男子開車從市區回郊區的家裡,他每天都要經過那段路。十九歲,我查了查記錄,應該是剛上完大一,蠻好的學校,好像還是個211。開的是他爸的黑色本田。平時他不開車的,總是坐公交回去,但那天開了。我覺得應該是為了泡妞。”
他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聲音開始變得沉穩。那不是我記憶中,他在我高中教室的窗外喊我去網吧時用的那種聲調。他每天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坐在派出所裡與人對話的時候,用的大概就是那種聲調。我突然覺得,霍明長大了,那種聲調,是比他的身材更為顯著的成長。他沒準可以成為一個好警察。
他繼續說。那個十九歲的男孩,在燈火通明的市區裡轉悠了很久,坐在平時父親坐的皮椅上,握着主宰性命的方向盤,一定讓他汗流浃背。
越來越晚了,他在一個燒烤攤旁邊停車,是否吸煙不清楚,在聽什麼音樂也不詳。總之,過了許久,一個女孩上了他的車。我們尚不知曉他們是否認識。也許是女友,也許是情人。普通朋友的機率不大。女孩在步行街裡一個陳舊的男裝店打工,之前還做過奶茶店員、傳單發放員、幼稚園護工和電話銷售員。那晚,她喝了酒,推開幾個鄰桌男人的手臂,上了他的車。沒系安全帶。
他們幾乎沒有什麼談話,或許有,也再無可證明之人。車子駛向沒有燈光的暗路,像是駛向某種命運。路面的漆黑與湖面的漆黑互相侵蝕,鋪作同一個平面,他需要打開刺眼的遠光燈,才能分辨得清。
本來他們倆會一起死去,但是在一個無人的,隻有牙膏廣告牌還亮着的公共汽車站,他把女孩趕下了車,又獨自上路。被人扔在一個蛙鳴纏繞的漆黑站台,女孩想必害怕得發抖,有大聲咒罵男孩去死也說不定。五分鐘後,本田車駛入湖中,濺起黑色的水花,冒出幾個隻有青蛙能見到的泡泡,随即沉入了湖底。
講完以後,我們沉默了下來。霍明把音樂聲擰大,又迅速擰小。
我說:“自殺的嗎?”
他說:“不知道啊,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自殺。屍體是第二天傍晚,被準備夜釣的人發現的。我因為剛去所裡,又沒見過屍體。”他頓了頓,“反正沒看見,隻是聽我師傅說的。我隻是在旁邊維護了一下秩序。我就是老在想這事兒。我覺得他應該是自殺。不然,他為啥中途突然把那個女生放下來。可是,我又覺得他不是自殺,否則為啥要刻意載她一程。後來把那個女生叫到所裡詢問,什麼都不說。因為至少不是他殺,我們就沒好深問下去了。”
他歎了口氣,打開轉向燈,在左邊的一個農村信用合作社門口停下。他說:“到了,女朋友在這上班。”
我說:“無人有意作惡。”
“什麼?”他皺起眉。
“沒什麼。是她嗎?”
我們透過後視鏡,看着他女朋友上車。很腼腆,和我打了個招呼,就埋頭玩起手機了。霍明解釋說:“累着了,在櫃台裡說了一天的話。”
他把女朋友送回家,竟然跟我家是同一個小區。我見她下車,跟霍明說:“不早了,我也回了吧。”
他說:“你等下。”
他女朋友瞥了他一眼,說:“又去網吧。别玩太晚,早點回去。”然後關上了車門。
“不想去網吧。”我說,又補了一句,“也不去你家。”
“沒想叫你去。”他去旁邊的小賣部買了包煙,關上車門說,“你覺得怎樣?可能明年就準備結婚了。”
我說:“挺好的。”又說,“這麼一會兒能看出個啥來。你自己覺得好就行。”
“過日子呗。挺好的。”他啟動車子。
“那幹啥去啊?”
“去了就知道了。”
街邊的店鋪開始準備迎接夜色。列印店、小賣部、五金店關掉了燈,拉下鏽迹斑斑的卷簾門,另一些店鋪開始醒來。燒烤店把鼓風機對準街道,開到最大,讓孜然味的油煙飄到更遠的地方,宵夜店亮起了小龍蝦形狀的霓虹燈,架起桌子,蒙上白色的油布與塑膠紙,撐開巨大的傘,以應對随時可能到來的夏日陣雨。
在這些香氣撲鼻的場所之外,家鄉還是不可避免地困倦了起來。車與人藏進不那麼容易找到的空間裡。由于沒有高樓,夜色不是籠罩,而是淹沒了城市,漫過行人的肩頭。霍明的車越開向郊區的深處,暮色越是稀薄。再過一會兒,仍暴露于空氣中的人,都将溺于黑暗之中。
“你到底要去哪兒?”我說,“要是想學那個男生,把我扔到郊區的車站然後投湖自盡,我會在你死之前把你撈起來殺掉的。”
“你想多了,我隻會載着你一起投湖。”他撕開煙盒的封條,叼出一根點着,把手垂到窗外,煙頭的火星像一面反射着夕陽的鏡子,“帶你去看看我外婆。”
車開了二十多分鐘。中途他走錯了一次岔路,又退回來,用手機搜尋“雨山”,然後乖乖按着導航走才找到。奇怪的是,落日還在目力的盡頭苦苦支撐着,沒有完全消失。
“有一陣我經常一個人過來,最近來得少,路都不記得了。”霍明停在一個凹凸不平的土路上,從旁邊的樹上掰了兩根結實的樹枝,扯掉葉子,遞給我一根,“走,上山。”
他走在前面,用樹枝挑開樹枝,檢視下面小徑的蹤影。我們拐了三道彎,在這座繁茂的土丘上尋找正确的方向。光線越來越冷,屬于青蛙的時間到了,也許還有蛇和黃鼠狼,躲藏在灌木的陰影中。我們靠着手機電筒的光亮,找到了那個稍微開闊一點的平台。幾個低矮的墓碑立在藤蔓之中,仿佛失落的神龛。
“外婆,回來了。”他在其中一個墓碑前盤腿坐下。
“外婆好。”我擦了擦地上的土,把樹枝插進泥裡,也坐下來。
墓碑有點髒了,霍明掏出一包餐巾紙,順着碑上的字用力向下擦,然後把紙捏在手裡,拔掉旁邊的雜枝。借着月光,我看到碑上的名字:吳秀梅。
做完這一切,他再次坐下,在他外婆面前點起一支煙。我說,“你這會兒要是披着浴袍,就更有感覺了。”
他笑了一下,轉頭面對他外婆說:“我又帶我同學來玩了。你應該還記得他吧。他後來去北京了,好多年沒回來。”他看向我。
我極力回憶着他外婆的樣子,但是記不清了,我說:“過陣子我可能又要去那邊找工作了。”我調整了一個更舒服的坐姿,從霍明手裡拿過一支煙來,開始向他外婆講述我是如何被抛到一個巨大的城市裡,如何在那裡尋得一個位置,一個姑娘,又如何失去她們。
講到一半的時候,遠處響起鐘塔報時的聲音。我赫然驚醒,看了一眼手機,八點整。
“對了,你們家那個鐘還在嗎?”我說。
“早扔了,後媽嫌吵。”他說。
我沉默了一會兒,說,“八點了,我們還沒吃晚飯呢。”
“你等我一下。”他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土,消失在樹叢裡,沒了動靜。
天地包裹住我,連眼前他外婆的墓碑也隻剩下一道輪廓。我的胳膊上迅速泛起一層雞皮疙瘩,“霍明。”我打開手機裡的電筒,身邊陡然生長出許多陰影,我又把它關掉。“霍明。”
“來了。”他從樹叢裡冒出來,手裡攥着一些桑葚。“這樹竟然還在,我好多年前就摘過。”
我接過一半,一個個放進嘴裡嚼。我給霍明講了他外婆以前的故事,那些他都沒有聽過,但我隻能講到童年結束。
他說:“外婆果然比較喜歡你。”
我說:“她可是你外婆。”
他說:“你是我的兄弟。”
我們吃完桑葚,在旁邊的樹葉上擦了擦手,又抽了幾根煙。涼意越來越重,困意也随之襲來。可惜我們無法在這裡過夜。
霍明站起來,從煙盒裡倒出剩下的幾根,一一平放在旁邊的墓碑上。有一塊碑斷了半截,他便把煙擺在它的跟前。我們打着電筒看了一圈,有幾個稍遠,走過去實在危險,隻能作罷。
我環視了一圈,附近的碑有七個。七個曾經活過的人躺在這片土丘之下。光照不到的地方還有多少,就不知道了。
“據說這地方風水好,很多人都把墓遷到這邊來,比正規的公墓安靜多了。”他說,“不過,附近在做經濟開發區,可能過兩年又得遷了。”
霍明抽出插在土裡的樹枝遞給我,說:“太晚了,下次再來。”我們互相拍淨褲子上的土,他說:“走,下山。”
于是,我們順着來路摸黑下山,把所有關于死亡的事情都留在了這個夜晚。
創作談
李星銳:踩在欲言又止的邊界上
在寫《雨山公墓》之前,我有兩年左右的時間沒有寫小說。
對朋友的解釋當然是怎麼合理怎麼來:寫小說很窮啦,上班忙沒時間啦。真正的原因解釋起來比較麻煩。就好像是在火車上偶然邂逅了一個對眼的人,在激情的推動下傾訴了一些不過腦的心情,萌生了一點暧昧氛圍。起身上了個廁是以後,再次入座,話頭卻突然滾落得沒了蹤影。
“接下來該說些什麼呢?”想必,這是人與人之間最為尴尬的間隙。
這兩年裡,我有過很多個創意,又始終沒有動筆。還是套用火車邂逅的比喻,再次入座,兩人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話題理應引向更深的地方。可是怎麼引入呢?套路自然是不行的,像個油嘴滑舌的流氓。過度地掏心窩也不好,唐突的真心話一旦說出口,過後隻怕會暗自懊惱,隻好閉嘴不言,靜等這份尴尬自己散去。
回頭看自己最初的小說,有太多的不滿。拘泥于講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上總有些似曾相識的元素,能在這裡或者那裡找到原型。那不是我欣賞的短篇小說。依我的閱讀經驗,好的短篇小說應該沒頭沒尾,像一塊形狀不規則的拼圖碎片,完整的模型已經遺失,隻能憑碎片本身,去想象它的整體性。最好連碎片本身都是模糊的,像是剛好踏進張開嘴巴,卻欲言又止的邊界之中。
談談《雨山公墓》。一句話表述,它起始于一個模糊的念頭:三場死亡,發生在離我們不遠也不近的地方。
事實上,這是我第一次嘗試跳脫出一個完整的故事,鼓起勇氣親近模糊,讓它盡可能靠近“好像啥也沒說”的感覺。不過這也是一個事實,關于死亡,我們能說什麼呢?對于一個和死亡(貌似)相距甚遠的年輕人來說,将“死亡”當作一個命題來探讨時,容易陷入虛幻的概念陷阱,把它認作類似于“人生意義”一樣的存在。過于親近的人的死亡,沖擊又太過強烈,我們隻會陷入情緒,而不會去談論死亡本身。
這都不是死亡與日常的關系。日常中的死亡往往是這樣的:和媽媽閑聊時,得知兒時隔壁家阿姨的丈夫得癌症走了。在計程車上等紅綠燈的時候,司機說這個路口三天前發生了車禍,死了兩個人。聽到諸如此類的話時,總覺得好像應該說點什麼,可是說什麼呢,感慨人生無常?算了吧。仔細想想,還是保持沉默為好。從“好像該說點什麼”到“算了吧”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咀嚼這樣的瞬間,是一件有趣的事,同時也是一件沒有結論的事。
之前讀到雙雪濤的采訪,采訪者問他,“你這篇小說想表達什麼?”他吸了一口煙,出神了幾秒,然後緩慢地回答,“我也不知道。”
這讓我想起和别人談論我以前的小說時,看過的朋友總能輕描淡寫地概括出,“哦,你寫xxx的那一篇。”這使我有一種難言的沮喪感。以後倘若聊起《雨山公墓》,若是被人問到“我想表達什麼”,我總算也可以點一支煙,賤兮兮地回答他,“我也不知道”了。
—END—
《長江文藝》2022年第4期
責任編輯 | 張雙
▲李星銳|
李星銳,1995年生于湖北黃岡,寫小說、影評,作品散見《長江文藝》《特區文學》及「ONE 一個」、騷客文藝等網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