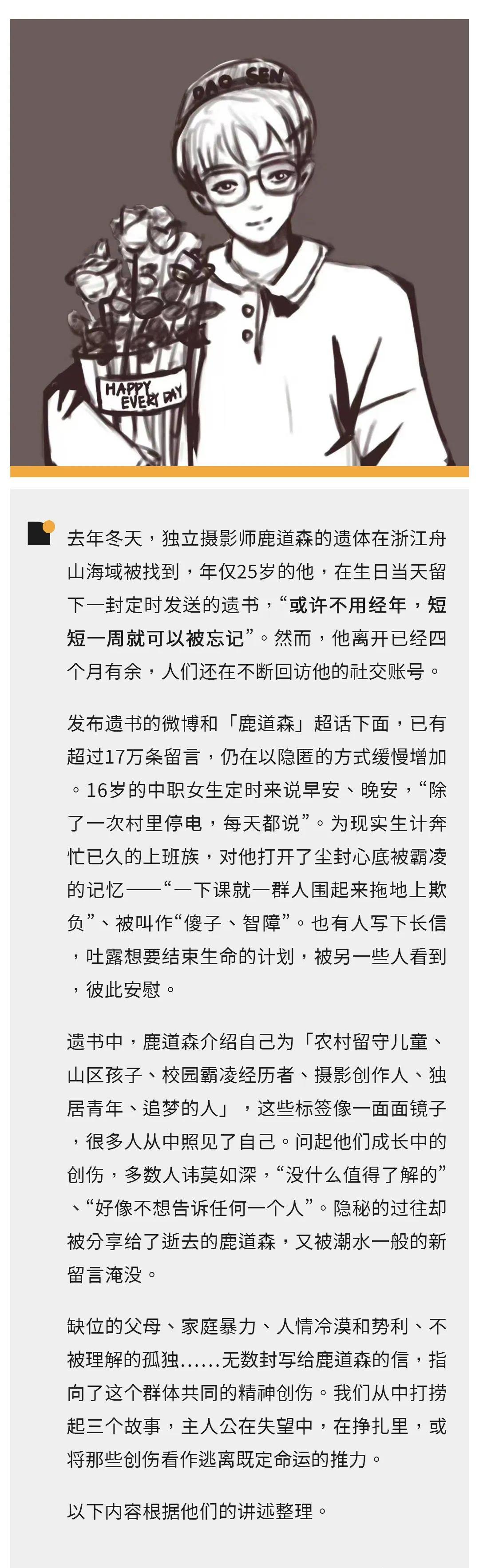
文|姜婉茹
編輯|陶若谷
“他們永遠隻在乎金錢,名利,地位,沒有人關心你是否幸福,快樂,我感覺壓力好大。沒有愛,沒有錢,沒有生活的動力,沒有未來。/
而現在我自己苦苦追求的藝術,現在看來倒是一個笑話,要是我能夠靠作品多賺點錢,或許能夠改變生活吧,但是很抱歉,我沒有,沒能夠改變。”
(節選自鹿道森的遺書)
緻鹿道森:
可是我真的不快樂,死亡對我來說是解脫。
希望這個世界再也沒有原生家庭不幸福的孩子。
—— 黎舒,25歲,做剪輯師的農村姑娘
刷到小鹿新聞的那天,我窩在沙發上看他的遺書,哭了起來。我的貓從沒見過我這樣,它看得呆住了。後來每當我感覺“快要死了”的時候,就會去小鹿的微網誌,“認識”他之前,這些話都憋在心裡,怕被憐憫、怕被安慰、也怕被人說矯情。我不敢把留言同步到自己首頁,不想被正在讀研的表姐看到。有的陌生人會安慰我說什麼“世界美好”,我覺得那些話很空。
我今年25歲,是小鹿離開這個世界的年紀。可能原生家庭的傷害會在這個年齡段凸顯出來,貧窮、缺愛、學曆低、事業不順、被逼婚……都是環環相扣的。但是小鹿上過大學,起點比我高,如果我是他,也許會再堅持一下。
我出生于96年,父親是一名英語老師,母親是國有紡織廠的勞工。媽媽打扮時髦,不甘于一輩子在農村,想要城市戶口。她的工資比我爸還高,脾氣卻很溫和。他倆是經人介紹相親認識的,當時爺爺的農田要被沒收,媽媽嫁過去就能保留,男方催着匆忙把婚結了。我今年還跟外婆感歎,“為了一塊地,就嫁給他了”。
結婚第二年就生下了我。那年工廠大量裁員,媽媽也沒了工作,可能還有産後抑郁的原因,她像變了一個人。爺爺奶奶會用難聽的話罵她,父親也開始對她家暴。小姨跟我說,見過父親把媽媽從三輪車上拽下來,當着全村人狠打。還有一次,小姨透過門縫看見,媽媽躲在堂屋裡面燒婚紗照。
99年,他們離婚了,媽媽什麼都沒要,隻要我。可是她很快又再婚了,我想按她的性格,應該是不願意的,但是在農村,好像女人不能不結婚。她搬去了很遠的地方住,我跟着外婆生活。
我對媽媽隻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一次是在舅舅家,她追着喂我飯吃;一次是放學回家的路上,她突然從藏身的角落出現,送給我一個橘子。我把它吃了,沒什麼特别的感覺。
直到2005年的冬天,那年我9歲,外婆說很久沒見過我媽了,買了東西去探望她,敲了半天門,沒人應聲。找了個鄰居把門撞開,外婆看見我媽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再婚的丈夫出門打工了,沒人知道她經曆了什麼。她對這個世界、對我,都沒有留下一句話。
國小的日子過得還行,我文科成績好,還在一個全國的作文比賽拿過獎。同學們都不知道我家的事,隻是每次申請貧困補助,表格上别人會填爸爸是誰,媽媽是誰,我不知道該填誰,有時填父親陌生的名字,有時填舅舅,盡力糊弄過去。
每天上下學,要經過村裡的“CBD”,總有一群大媽以為我走遠了,就在背後指點比劃,“這個小姑娘沒媽了”,我都聽得清清楚楚。那時覺得很自卑,盡可能繞着那條路走。
●資料圖,源自視覺中國。
真正的噩夢從12歲那年開始。父親偶爾會來學校,送些棉手套之類的小玩意,一天下午,他直接來我班裡,把我抱到面包車上,我很害怕,但是沒有說話,知道無法掙脫。
那天外婆去學校找過我,得知被父親接走了,說“那就跟他吧”。外婆家特别窮,種玉米和小麥,一年差不多賣一千塊錢,三餐隻能吃一些粥,沒有肉。她當年為了吃飽飯才嫁給外公,結果外公經商被騙,跳井死了,後來媽媽又去世了。我不忍心她一個人,總想回到她身邊。
父親後來說,他是不想付每天8塊錢的撫養費了,才把我接回去。他的新妻子是個厲害的女人,嫁之前就說,“我可不像你大媳婦,拿個軟柿子捏”。我父親怕她。那天我哭了整個晚上,心裡始終覺得,不跟我商量就強行“偷走”,很不尊重我,也是以不肯按父親的意願,叫那個女人一聲“媽”。
有天父親讓我背《蔔算子·詠梅》,我不肯,他抓住我的頭發,把頭摁在冰涼的地上打。後來我盡量不跟父親同處一室,躲着他走,不跟他說話。每天三更半夜,我都會看看大門有沒有落鎖,想順着記憶裡的路,逃回外婆家。沒事做的時候,我拿着小刀去劃院子裡的大楊樹,一刀一刀,那棵樹最後死掉了。因為“太過叛逆”,後媽把我攆去了奶奶家。
我的整個人生,都捆綁在親人的利益裡,他們眼裡隻有錢。我的出生跟“一塊地”有關;為了省掉撫養費,被強行拖到父親身邊;又是因為錢不給上學,改變了命運的軌迹。
中考張榜的時候,我考上了高中,跟父親說我要上學,學費3000塊。錢都在後媽手裡,他說“你連媽都不喊一聲,還指望人家給你錢”。我姨跟我姑商量,一家出一半學費,姑姑說,誰讓她上學誰出錢。奶奶也說,女孩子不要上學了。沒人覺得應該幫我這一步。
全班隻有我一個人沒升學。之後父親帶我去辦了一張身份證,為了不被計劃生育政策罰款,家庭住址欄上,填的是一個不存在的地方。
我去了外地打工,在東莞電子廠當倉儲員,後來又去餐館端盤子。打工的日子,我跟周圍喜歡聊家長裡短的阿姨、等着結婚生娃的同齡人格格不入,隐隐覺得有自己的事要做。小時候喜歡一個歌手,因為他和對文字的天然親近感,想要進入傳媒業,接近那道星光。
我用打工賺的錢買了台電腦,先是學設計,又自學了一點剪輯,然後去了鄭州,給新媒體公司剪短視訊,按條計費,沒簽合同。
甲方很挑剔,一組素材大約剪10條1分多的視訊,要求在2-3天内剪完,修改意見多了就意味着重剪,經常熬夜。流量好的片子,也從來沒人誇是剪輯的創意好,彷佛隻是被雇傭的工具人。但我是公司裡剪片最多的,活兒來了就上,多急多累都頂下來了,我沒有生活,隻有工作。
●鹿道森的個人網站,圖源自網絡。
後來公司倒閉,我又換了幾個城市,但一份長久的、簽合同的工作很難找,我的學曆(硬傷)始終擺在眼前,無法逾越。
外婆和舅舅都不支援我做剪輯,覺得學美容美發實在。村裡的姑娘,大多在22歲前就結婚了,為了躲催婚,我過年不敢回家。外婆覺得找個縣裡有車有房的人,對我好就行。但我想攢錢買房子,留在城市裡。
心裡好像有一個很大缺口,想有一些東西是屬于自己的,需要房子、車子、票子帶來的安全感。從小到大,所有親情都離不開錢,感覺以錢為基礎的關系會很結實。别人都是兩個人結婚一起還貸買房,我從沒想過可以依靠别人。
我隻愛傳媒業,視訊釋出的那一刻會有成就感,但是它給不了我要的安全感,也許會有一天,像小鹿跟攝影說再見一樣,我要跟喜歡過的剪輯道别。
前兩年我填了人體器官捐獻的表格,也搜尋過怎樣自殺不痛苦。我很抗拒這樣的命運,總覺得應該能考上一個大學,找到一份好工作,好到像位元組跳動那種。聽說那裡壓力大,但我“想被壓榨還壓榨不了呢”。
已經十多年沒見過父親了,前幾年聯系過一次,他說起正在上大學的女兒學習不好,“當時還不如讓你上學”,這話聽着惡心。但我不再恨他了,希望他注意血壓,早點把房貸還上,這輩子就當沒有緣分吧。
“很抱歉,我的生命,好像就是一直在逃離。/
很多事情文字的表述都顯得蒼白無力,即使你親身體會恐怕也未必知道我是怎樣的感受。冰凍三尺,又豈是一日之寒呢。/
壓垮我的不是一根稻草,是無數的沙粒,我走一步都是像背着大山走。”
(節選自鹿道森的遺書)
緻鹿道森:
如果活着太累太可怕,我不會勸你。
—— 莫非,40歲+,把哥哥埋在蘆葦蕩邊河床上
到了四十幾歲,漸漸過上了曾經向往的生活,很少會再坐下來,揭開傷疤,細數童年的創痛。鹿道森的“遺書”讓我突然又陷入過往,記憶裡已經暗淡的場景,再度被照亮。
年輕的攝影師有條不紊地退租、送出攝影器材、寄送随身物品,安排好身後事,然後冷靜地赴死,這絕不是一時的意氣用事,就像我大哥當年一樣。
那是九幾年的時候,21歲的哥哥策劃了自己的“人生謝幕旅行”。他提前半年開始建立信任,每月幫不當班的工友代領工資。直到最後一次,一次性拿走了10名工友的工資,不辭而别。揣着幾百塊“巨款”,他去了上海、南京、蘇州、杭州,把向往的江南城市走過一遍,然後掐算着端午的時間,回到了最疼愛他的外婆墳前。
舅舅去掃墓時,從哥哥的衣服口袋裡翻出兩毛錢,還有一些火車、景點的票根,拼湊出他人生最後的蹤迹。一張手寫的遺言紙條上,寫着“世上隻有媽媽好”。那是當時熱映的台灣電影插曲,也是一張控訴書,沒有一字提到父親,滿紙卻都在罵他。
我比哥哥小3歲,與他共同生活了12年,睡在一張床上。我們互相分享好玩的東西,他會揍欺負我的孩子,有時也打我。當時我們恥于表露軟弱的情感,哪怕父親的巴掌落下來,都不肯掉一滴眼淚。我和哥哥很少正經地聊一聊成長中的噩夢,沒有彼此安慰過。倔強、敏感、自卑,是我們共同的性格基調,我受過的傷害,哥哥或多或少都遭遇過。
●資料圖,源自視覺中國。
我出生6個月就斷了奶,被寄養在城裡的祖父母家,跟爸媽和3個哥哥姐姐分離。家鄉有一句諺語,叫“甯跟讨飯的娘,也不跟做官的爹”。但是在我3歲的時候,媽媽去世了。
哥哥和兩個姐姐在農村長大,他們常在不通電、沒有燈光的鄉下黑夜裡找父親,大的孩子哭,小的叫嚷着跟在後面跑,而爸爸不知道正在哪家喝酒。
7歲時,爸爸回到城裡住。在外人眼裡,父親是最底層的市民階層出身,沒什麼文化,被配置設定去做重體力勞動,拖着闆車挨家挨戶送蜂窩煤。不喝酒的時候,他是個“老實人”,沉默寡言,沒什麼存在感,在哪裡都沒人在乎他的意見。
父親的人生過得并不如意,也遇到了那個時代的種種問題。隻有面對更為弱勢的小孩時,他才擡得起頭,有機會宣洩壓力和苦悶,也許打小孩,就是他的解壓方式。
打人的時候,他把我們拎進房間,門鎖上,捆住人,用皮帶帶鐵的那頭抽,抽一下身上就紫一道,皮膚腫起來。有時候用皮鞋直接踹背,狠狠踢上一腳,小孩像個木偶,“啪”地就撲在地上。醉酒時下手更沒有輕重,我有時候會想,他要是把我打死了,也就解脫了。
有時鄰居過來敲門,被父親一聲“我打自己的小孩,關你屁事”就吼走了。沒有挨打的哥哥姐姐在旁邊站着,噤若寒蟬,沒人敢阻攔,大姐勸過我“不要忤逆父親”。
好在鄰居家其他小孩也挨揍,雖然沒我家打得狠。當他們嘲笑我身上青一塊、紫一塊,我也有機會嘲笑他們的傷口,有種報仇的快意。
直到高一我竄了個子,比父親更高,可以單手抓住他的拳頭,他知道自己老了,不是我的對手了。
父親對我們的成長不聞不問,養育弟妹的負擔落到了大姐身上。她十三四歲就去服裝廠做縫紉工,維持家裡的開銷,這份工一直做到退休。每學期開學,三個弟妹都要交學費,拿不出錢,就商量誰先交,誰拖一兩個月再交。
少年時我營養不良,體格瘦弱,頭發偏黃,常穿打更新檔的衣服。有個老師用陰陽怪氣的口吻,講我家裡的私事,給我取外号,同學跟着一起叫我“黃毛”,還有人喊“娘娘腔”——實際我沒有柔和的氣質,他們隻是覺得這是個髒詞,攻擊起來有足夠的殺傷力。
校園霸淩未必都是加諸在身上的拳腳,還有不被允許參與集體彙演,體育活動無人互動。交朋友總怕得罪了人,用一種巴結的心态,仿佛同學跟我玩是一種“恩賜”。
哥哥交到了“朋友”,他15歲辍學,還未成年就被父親推進了社會,跟幾個社會上的“弟兄”住在一起,大多是家裡不幸福的孩子。他蹬三輪送貨,去發廊做小工,在醫院做護工,去紡織廠做翻砂工,能做的盡量都做,很少回家。但每次回家,都顯得心事重重,沒有年輕人的朝氣。父親會找他要錢,有錢時哥哥塞一些給他,沒錢時還會偷拿家裡的糧票、布票。無論父親怎麼罵他、打他,他都一聲不吭,安靜地捱着。
我最後一次見到哥哥,是個悶熱的夏天。他坐在床邊喊我過去,好像想說點什麼。等我站過去,他沉默了一會兒,卻什麼都沒說。可能在他眼裡,我還是個孩子。
那時我的心思不在哥哥身上,一心想着最好一夜長大,逃離這個家。哥哥姐姐們可能也這麼想,每個人自顧不暇,都在一灘自己的泥沼中掙紮。
等到我的年齡漸漸超過了哥哥,不斷回想最後的一面,如果那天使勁兒追問,好好勸勸,他可以不走這條極端的路嗎?被社會捶打多年之後,我想,在哥哥萬全而周密的計劃面前,我的勸慰可能蒼白得像一張紙。一個鐵了心告别世界的人,根本不會來抓我伸出的手。
●資料圖,源自視覺中國。
小時候每當父親把我的衣服扔出家門,讓我滾蛋,我想着滾就滾,轉身就去投奔呵護過我的姑媽,總還有個去處。新華書店裡淘到的舊雜志,小說和詩歌,也給過我慰藉,指引了方向。而疼愛哥哥的外婆很早就過世了,他總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在乎他的人。
舅舅發電報給父親,讓他帶哥哥的骨灰回家。父親不願意花幾十塊錢買骨灰盒,直接用一個口袋把哥哥裝了回來,塞到我床底下。過了幾天,一個月光清冷的夜裡,我找了一片蘆葦蕩,把哥哥埋在了河床上,不遠處葬着母親。
父親跟平時一樣,雷打不動地喝得爛醉。什麼事情都不能影響他喝酒,微薄的工資,一直被優先用來抽煙喝酒,從早到晚,一天三頓。他曾經醉酒掉進河裡,也摔過當時珍貴的自行車。醉後出盡洋相,徹夜不息地胡言亂語。是以我一輩子不沾煙酒,仿佛在用一生的時間,清除父親的影響。
15歲高中畢業,我念了技術學校、做過機械勞工、讀過大專夜校、在飯店打過工、報名高自考,最後拿到大學文憑。在地理上,我從長江邊的南方小鎮、那個30多平方米的筒子樓,一路逃到省城、逃到北京,北漂十五年後,又逃出國,被一個聲音驅趕着,“快跑,越遠越好”,就像一個逃犯。
童年幸福的人,可以躲到童年裡去尋找精神上的力量支撐,而我們是無處可退的人。
後來父親因為抽煙酗酒,得病去世了。姐姐買了一塊墓地,想把爸媽和哥哥合葬在一起。但是母親和哥哥的骨灰早已無迹可尋,連哥哥的一件衣服、一張照片也找不到,做不了衣冠冢。隻是在當年埋骨的地方,抓了一把土放進墓中。
「若是我們還能夠擁有時間,若能再次回到血緣的起點,我隻想彼此憐憫,珍視,依偎,諒解。把缺失的感情修複完整,讓心裡的愛簡單如初。但是,時間猶如水滴,不再會回到我們的手中。世間的感情多是如此,無論我們是否甘願,生命裡的遺憾總是和懷念一樣地堅韌。」(莫非紀念親人的文字《縫補》,寫于2012年。)
●網友紀念鹿道森的畫。圖/鹿獅子Lion (已獲授權)
●網友為紀念鹿道森創作的插畫。圖/梁望(已獲授權)
“有人說為啥總感覺你不夠自信,從小就生活在責備的環境裡,我很自卑。我也隻是想要一個溫暖的家,想要被愛,可為什麼就這麼艱難呢。”
我疲憊不堪,重組千萬次,破碎千萬次。
(節選自鹿道森的遺書)
緻鹿道森:
人生不過大夢一場,最終的結局都是一樣。
—— 陳默,28歲,群衆演員
在鹿道森的的超話裡,有很多抑郁的人留言,我會去安慰那些想自殺的人,就像在鼓勵我自己,但其實沒什麼用。很多人還在抑郁焦慮、什麼都不想做的狀态裡,我好像已經到了下一階段,規劃好了一整年要做的事情——練出胸肌腹肌倒三角、一次性考過ACE健身私教證書、學習攝影,強迫自己“變好”,不要死。
這是一個跟自己的負面情緒纏鬥、跟世界拉扯的過程。但可能會因為突然想起了什麼,重新開始消沉。最近得知外婆去世了,疫情原因無法回鄉送終,我拉上窗簾,把自己關在黑暗裡聽歌、發呆、打遊戲、暴飲暴食,拼命吃甜的,胖了5斤。
已經兩年沒喝酒了,這幾天喝了許多。外婆去世了,去年外公也去世了,大前年爺爺也去世了,奶奶30年前就去世了。我又少了一個親人,雖然他們不是很疼我,可我還是很難過。可能兩三個星期後,會再度收拾情緒去健身,撿起“變好”的計劃。
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會有朋友的,翻翻通訊錄,沒有一個可以通話的人。
原生家庭的創傷一直跟随着我。我爺爺之前有一些地,父親是最受寵的小兒子,村裡人叫他“三少爺”。後來家道中落,父親被慣壞了,喜歡在街上跟人喝酒,三天一大場,兩天一小場,從街頭喝到街尾,不肯出去工作。後來他的親哥,我大伯混得不錯,在村裡一大片泥房子中間,給父親蓋了石頭房子。
我媽是十裡八村出名的美女,相親相了一兩百個,她都看不上。相到我爸的時候,看他人長得不錯,整個村又隻有這麼一座醒目的新房子,恰逢家裡當時老給她氣受,賭氣一樣趕緊嫁了。後來我媽被我爸打得受不了,逃回娘家,想要離婚的時候,外公嫌丢人,把母親攆回了家。
當年婦女地位很低,媽媽很難靠勞動獲得收入,家裡一直靠大伯接濟。印象裡有次全班都交了學費,隻有我沒交,媽媽去找外婆借,外婆也沒有錢,現把豆子賣了。但是爸爸很愛他自己,想吃肉就買一份自己吃,我和媽媽、姐姐隻能撿他剩下的。
親戚都瞧不起我家,姑姑來串門,隻帶些賣不出去的爛蘋果,說“反正你們連這也買不起”。姐姐會指使我找爺爺要錢,讓我抱着他的腿打滾兒,爺爺沒辦法了,就給我一毛錢。但是大伯家的孩子來,爺爺會給一塊錢。那時候一毛錢能買一片辣條,或者一袋汽水,一兩塊糖,吃上一次特别奢侈。
小時候轉到縣裡上中學,我一天沒洗頭,兩天沒洗澡,就擔心别人是不是看不起我。甚至于别人看我一眼,都懷疑是瞧不起我。我總是下意識去讨好别人,有次給同學買吃的,怕其他人看見不舒服,就給在場的都買一份,我自己不吃,明明是很想吃的。
●資料圖,源自視覺中國。
因為自卑,我一直不太敢跟别人說話,特别是跟女孩說話會臉紅。雖然我長得比較好看,個頭也高,小時候被選入了校國旗隊。有個姑娘下課總喜歡黏着我,在身後一聲聲地叫,哥。但我沉默寡言,這種自卑被同學解讀為“裝酷”。現在回想起來,我也被人喜歡過。
回到家就隻有無止境的争吵,父親經常打人。姐姐比我大一歲,為了少挨打,有時會嫁禍給我。她摁壞了電視,把遙控器往我身上一扔,就去喊父親:“弟弟把電視弄壞了”。有時她純粹想看我挨打取樂。
有一次我終于忍不住問母親,每次都叫我讓着姐姐,我體諒你,是以不說話,可是誰關心過我呢?母親很意外,她說,你老實,你乖,你姐總是亂嚎,我隻想讓她停下,别打擾他人。
還有一次,二大爺帶了一些火腿腸,我分了幾根給小夥伴吃。第二天父親說,因為這幾根腸他和二大爺打了一架。我在被窩裡哭得好傷心,那天才明白我爸的親哥,也不能算是我的親人。
隻有表姐偏疼我,她隻給我一個人買吃的。有一次看見她,我太激動了,直接從樓上滾了下來,現在鼻子還有一點彎彎的。還有同桌喜歡買鳳梨味的軟糖,會分給我一塊,這件事溫暖了我好多年。
缺愛的人往往得不到愛,不是因為長得帥就能免于受傷。我從來不敢主動開啟一場戀愛,覺得配不上喜歡的人。被人“追到”又想把一切好東西都給對方,沒什麼錢也去買迪奧、香奈兒的口紅。女朋友生氣,我要發幾百條資訊去哄,最後都是她們離開我。
在和抑郁對抗的時候,愛情曾是“武器”,是活着的意義。後來一個女孩教我,戀愛是有套路的,要先噓寒問暖獻殷勤,再忽冷忽熱,欲擒故縱,“讓對方心裡想的都是你”。我認真做了筆記,還沒實踐過。
我想不幸的原生家庭,父母多半不會教孩子人情世故,我還是按照内心的标尺在生活。有時也會想,是不是應該做一個合群的人,按“套路”來的話,就會有錢、有人愛吧?
之前在北京做過一陣兒信用卡推廣,如果在轉化率上作假,一天能掙很多錢,克扣是行業的潛規則。隻有一次交不上房租的時候,我用這種方式賺了幾千塊錢——這錢太好掙了,但後來我再也沒拿過這個錢,過不了心裡的坎兒。
特别痛苦的時候,會選擇逃避。之前逃到部隊當兵,我體能很差,晚睡早起地加練。别人做正常訓練,我會主動跟指導員說,加練負重10公裡跑。實在跑不動也不會停下,一邊跑一邊哭。累到腦子“當機了”,走路都能撞柱子上,就沒時間産生負面情緒了。
現在我又“逃”進了影視城當群演,最多一兩句台詞,角色連名字都沒有。教表演的老師說,演戲就是說謊,人人從小就會。沒人教過我,我是班上的“問題學生”,學得很慢。
最近讀了一些書,找尋活下去的理由,畢竟“來都來了”。我沒勇氣去恨别人,隻當是還了上輩子的債。現在想盡可能去遺忘不好的回憶,去學滑闆,買一輛摩托,去玩,去吃好吃的……還是要努力生活,好好愛自己。
●鹿道森釋出遺書的賬号截圖。
(為保護隐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頭圖為網友為紀念鹿道森創作的插畫,作者難夢星河,已獲授權。)
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權歸屬極晝工作室,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聲明除外。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