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讀書要有敬畏心、謙遜的态度、去功利化的價值追求,克服浮躁、浮華、浮誇之氣,鍛造自己的人格。讀書要有書桌、書櫥、書房,從講台前站到書架上,給自己一個安頓心靈的地方。除了閱讀著作,還要每天讀報紙、讀雜志,确立大閱讀的概念,努力做到海量閱讀。猜想性閱讀讓自己有思想、有創造,可以牽引寫作,而寫作就是深閱讀。教師要從自己的興趣和實際出發,追求自己讀書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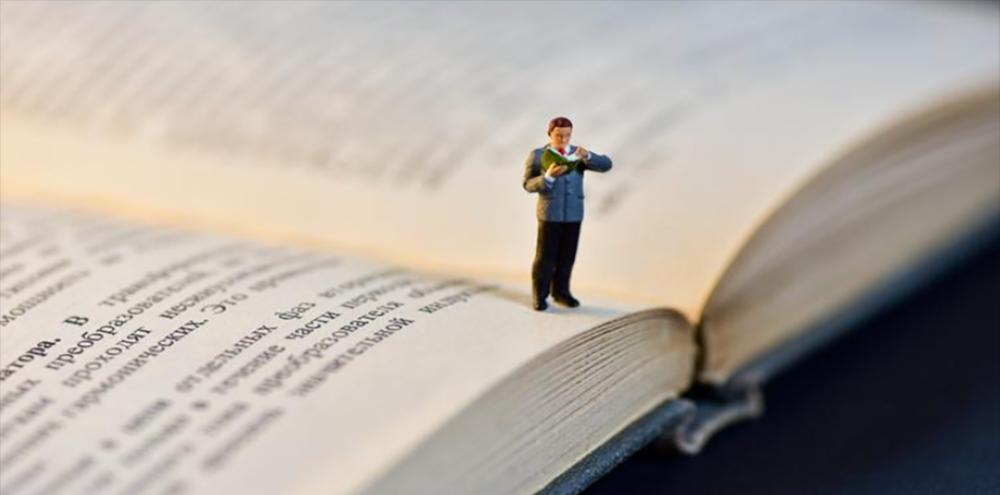
說來非常慚愧,有不少人以為我書讀得多、讀得好,其實,我雖然讀了,但不多也不好;也總有人讓我提供書單,建議讀哪些書,我總是提不出,也不願意随意地提供一份書單。這些絕對不是我的謙虛,隻是客觀地表達我的真誠。讀書,不是把自己的頭腦當作作者思想的跑馬場,而是要把自己帶到思想的遠方。
01
鍛造讀書的品質:
讀書要有敬畏之心、謙遜的美德、去功利化的閱讀價值追求
我始終認為,閱讀要鍛造自己的品質和品位,懷一顆敬畏之心,實事求是,像楊绛先生那樣,做一滴清水,而不做肥皂泡。
這是一種自我警惕,也是對當下閱讀中一些不良現象的批評,因為我發現一些教師讀書比較浮躁,浮躁一定會帶來浮華、浮誇,這“三浮”不是閱讀應有的品質。閱讀是認識自我、提升自我的過程,重要的是内心的體悟與充盈,絕不是做給别人看的,不是用來裝點門面、作秀以至炫耀的。是以,閱讀真正的品質是對讀書的虔誠,把讀書當作對心靈的洗禮。
在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所(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的前身,以下簡稱“省教科所”),我特别崇拜兩個人,他們年齡都比我少,但我視他們為我的楷模和老師。一位是孫孔懿,我稱他是真正的學問家。記得當年他剛調到省教科所工作時,借住在江蘇省幼兒師範學校(已被合并)的宿舍裡,小小的房間裡被一整排大大的書架占滿,書架上層層疊疊地布滿了一列列、一層層的書。孔懿讀書表現為兩個特點:一是廣泛閱讀教育經典,深入思考,在學理上鑽深,又與自己的見解結合起來,開辟教育的新視野,形成教育研究新領域。他專心寫作,先後寫成了《素質教育論》《學校特色論》《教育時間學》《教育失誤論》等。二是專注于教育家研究,寫成了《論教育家》。最近,他告訴我,這本論著幾乎重寫了。他又将教育家研究的重點投射在蘇霍姆林斯基研究上,寫出了兩本煌煌之作:《蘇霍姆林斯基評傳》《蘇霍姆林斯基教育學說》。孔懿研究、寫作有一顆安靜的心,甘坐冷闆凳,如昆曲《班昭》的唱詞:“最難耐的是寂寞,最難抛的是浮華。從來學問欺富貴,真文章在孤燈下。”這是寫作的境界,也是閱讀的境界,閱讀的境界帶來寫作的境界。
另一位是彭鋼,他是哲學家、理論家。他在大學時候學的是中文專業,可非常喜歡哲學。他将閱讀與教育科研結合起來,讓教育科研廣闊起來、深刻起來。前幾年他告訴我,他幾乎把所有海德格爾的中譯本讀完了。他非常認真地讀了海德格爾給海德堡大學哲學系學生上的哲學課的演講錄,又集中精力啃下了1235頁的《尼采》。這本《尼采》至今被稱為“尼采的海德格爾闡釋”,在學術界極有影響。現在他在讀哈佛大學愛德華·威爾遜的著作。威爾遜是生物學家,哈佛大學動物博物館“螞蟻館”的館長,寫成了《螞蟻的故事》,榮獲普利策獎,是普利策獎中唯一的非文學類作品。我問彭鋼為什麼要讀海德格爾的書,他說可以讓自己稍微深刻一些;為什麼讀生物學家的書,他說好玩。“深刻”與“好玩”聯結在一起,就是健康的閱讀心理和目的,而我缺少。
尋找到身邊閱讀的榜樣,心無旁骛,這本身就是一種閱讀。讀人比讀書更重要,在讀書中讀人,讀書為了做人。從這個角度看,人比書長壽,也比書更偉大,因為有了人才有書,書的偉大實則是人的偉大。
02
案頭、書桌、書櫥和書房:
給自己一個安頓心靈的地方
讀書該有個讀書的地方。其實,處處都是可以讀書的地方,也就是說處處皆可為讀書台。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說:“餘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由此,“三上”便成了讀書人津津樂道的話題。“三個地方,三種時間,可謂清靜自如,沒人打擾,能自由自在地讀書、思考;地方看似不雅,時間也零碎,但若能利用此地、此時,久而久之,總能收獲一二。”以上這些文字是葉水濤先生發給我的,因為說得好,我就抄錄了。
我以為以下地方是讀書的地方,也應是讀書必備的物質條件。一是床旁的櫃子。我喜歡在櫃子上放幾本書或雜志,躺在床上,睡前、睡中(半夜醒來,睡不着了)喜歡把所有的報紙翻一遍,看一份往地上扔一份,有重要文章的存放在床上,準備第二天重點看,有的還要剪下來存讀。在床上讀雜志是十分惬意的,随便翻翻,總覺得在床邊的案頭正兒八經地讀書不合适。
二是書桌。我常對自己說,退休前有張辦公桌,退休後把辦公室“搬”回家,改造成一張書桌。辦公桌是臨時的,總歸要“退休”,而書桌永“不退休”。“不退休”的書桌意味着終身閱讀,做個終身學習者。大概當下不少年輕人家裡有化妝台,有牌桌,有酒櫃,有鋼琴,唯獨缺一張書桌,挺遺憾。記得一位來自農村的男教師,一次在我組織的沙龍上講述了家庭晨曲。一天起床後,他看見妻子在梳妝打扮,便說道:“女人應當有張梳妝台,我也應該有張書桌,我倆都要化妝,你是做容顔的美容,我是做精神、思想上的化妝和美容。”全場響起一片笑聲,那是贊賞、認同的回響。
三是書櫥。家裡應當有幾個書櫥,至少應當有書架。江蘇泰州中學前副校長、國文教育家洪宗禮老師在國文教育界作出了很大貢獻,形成了“洪氏國文”教學主張與風格。他說:“我要從講台前站到書架上去。”站到書架上,至少有三層含義:“我每天都要讀書;我要著書立說,讓自己寫的書也出現在書架上;我自己變成一本書。”可以想見,從書架上再回到講台前,教師就似是換了個人,脈管裡的血重新換了一遍。書櫥、書架好啊!
四是書房。有條件的家庭一定要安排一間書房。書房是家庭圖書館,書房是研究、寫作、做學問的地方,書房是自己的精神家園。我就是書房的主人,是圖書館館長,是精神家園的締造者。書房可以很亂,但亂得有秩序、有條理;書房可以有沙發,累了可以平躺;書房可以有零食,随時就着開水吃一兩塊······總之,書房應當舒适、溫馨。“躲進書房成一統”,正是閱讀、寫作的極好感覺。我隻要在家,絕大部分時間都在書房裡。每當早上、中午、晚上夫人喊一聲:“成尚榮,吃飯了!”我可以輕輕地應答一聲,也可以一聲不響,過幾分鐘,打開書房門走到飯桌,那才是讀書人的“譜”,有種說不出的自豪與快樂。
有了床邊的案頭、書桌、書櫥、書房,讀書才有了踏實感、充實感,也有了儀式感和歸屬感。其實,這一切都是在安頓自己的心靈。
03
讀書,還要讀報紙、讀雜志:
建構大閱讀的概念,努力做到海量閱讀
閱讀,抑或說讀書,是個大概念,不隻是讀一本本的書,還應讀報紙、讀雜志。所謂學問,就是要海量閱讀;所謂思想,大部分來自讀書。
在讀書方面,最近一兩年我有了閱讀專題:一讀美學。包括朱立元主編的《西方審美教育經典論著選》,李澤厚的《美的曆程》,丹納的《藝術哲學》(傅雷譯),王長俊、王臻中的《美學基礎》,周清毅的《美的常識》,席勒、普列漢諾夫的《大師談美》(李光榮譯)等一系列的美學著作。這不僅是因為中央發了加強美育工作的檔案,我原本就有一個計劃,專門研究兒童美學。沒有大量的美學著作的閱讀,是不可能搞懂兒童美學的。二讀實踐育人方面的論著。實踐育人是新課改的一條原則。要搞清楚何為實踐育人,首先要弄懂何為實踐。桌上堆了一些書:毛澤東的《實踐論》,金嶽霖哲學三書《知識論》《邏輯》《論道》,袁貴仁的《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韋爾納·耶格爾的《教化:古希臘文化理想》(陳文慶譯),趙汀陽的《四種分叉》,劉曉東的《發現偉大兒童——從童年哲學到兒童主義》,烏特·弗雷弗特的《情感學習:兒童文學如何教我們感受情緒》(黃懷慶譯),王勉三的《知行合一王陽明》,還有《馬克思主義知識辭典》······古今中外都要讀一點。三讀“蘇教名家”(江蘇省教育家培養工程)規定讀的書目:羅伯特·R.拉斯克和詹姆斯·斯科特蘭的《偉大教育家的學說》(朱鏡人、單中惠譯),尤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林俊宏譯),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釋出的幾份國際教育發展的報告。以上這些書都比較難啃,難啃也得啃啊!難啃才有滋味、有嚼頭啊。
我有個深切的體會,不僅要讀書,還要讀刊物。我每年都會訂幾份刊物。第一份是《新華文摘》。這本文摘猶如百科全書,政治、社會、哲學、經濟、曆史、教育、社會科學、新華觀察、文藝作品、文藝評論、科學技術······選取目前學術研究的精華,大大地打開了我的視野,放大了我的格局,豐盈了我的學養,瞭望了世界和未來。此外,我還訂閱了教育科研和課程研究的權威刊物:《教育研究》《課程·教材·教法》《人民教育》。有人曾對《讀者》不屑一顧,認為其文章是心靈雞湯,對這樣的批評,我卻不以為然。我認為《讀者》給了我們另一種視角和表達方式,給人以親近感、新鮮感,還有特殊的美感,閱讀時好像走在春風裡,即使是心靈雞湯又有什麼不好呢?讀書既要向上飛揚,也要向下沉潛;既要有深刻的哲理,也應該有心靈美的滋養;既要有宏大背景,還應回到人自身來,回到當下的生活來。《讀者》往往出現在床旁,可以随時翻看,它更像我家裡的一位成員,可以傾聽,可以對話。
讀報紙是我每日的必修課。近20年了,我訂了以下報紙:《光明日報》,這是一份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報紙,它讓我站在更高的視角看待知識和教育,建構自己的知識圖譜,聽從知識分子良知的呼喚。《文彙報》充滿着開放精神,它紮根中國大地,眺望世界,觸摸未來,在多彩的表達中有另一種感受、另一種啟發。《報刊文摘》的特點是短小精悍,靈活多樣,尤其是第三版,都是極富哲理與穿透力的短文,常讓我感歎“小即美”“小即大”的深義。
讀整本書,幫助我建構一個體系;讀刊物,幫助我在某一主題、某一論點上往深處走;讀報紙,幫助我了解時事,把握走勢。這是我閱讀的圖譜,我稱之為“大閱讀”,但還沒有達到海量閱讀的标準。
04
猜想性閱讀:
閱讀牽引我的寫作,寫作說到底是深閱讀
記得改革開放不久,我讀了報告文學作家徐遲的大作《哥德巴赫猜想》,寫的是數學家陳景潤。讀罷,我心潮逐浪高。當時我就有一個想法:既然哥德巴赫有猜想,陳景潤有猜想而且證明了一半,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有自己的猜想呢?讀書是讀的過程,讀也應該是思的過程,邊讀邊思,邊讀邊猜想。我認為是可以的,是以給這樣的閱讀取了個名字:猜想性閱讀。
猜想性閱讀基于以下理念:不要讓自己的頭腦當作别人的跑馬場,而應讓别人的思想激發自己的思考,讓自己的思想激蕩起來、飛揚起來。猜想性閱讀還有另一個重要使命:培養自己的創新精神、創造能力。我深以為,培養創新精神、創造能力應當是時代的主題,是走向未來的通行證。暫不說,2022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上,總導演張藝謀的創新設計令世人驚呼,他發出一個強烈的信号:中國有自己的文化自信。也暫不說,每年在上海舉辦的世界頂尖級科學家峰會,所設計的每張桌子上鋪着的白色台布,讓所有參會讨論的人,随時在白布上寫下自己的問題、想法、靈感,也許是一個問号,也許是一個圖案,也許是片言隻語······那些轉瞬即逝的猜想都留在桌布上了。現在,我隻想說猜想本身。猜想就是想象,想象是創造的先導,想象是地球上最絢麗的第一朵花。學生的想象力需要教師想象力的呵護與激發,猜想性閱讀正可以激發教師的想象力。
前段時間我讀了《親愛的圖書館》這本書,作者是美國最知名的紀實作家之一蘇珊·奧爾琳。奧爾琳一度宣布封筆,不再寫書,因偶然得知洛杉矶公共圖書館火災事件,重拾起她對圖書館的回憶和情感,這些回憶與情感聚焦一個詞語上——“親愛”。在書的扉頁上,她引用了另一位作家威廉·福克納《八月之光》裡的一句話:“記憶首先是相信,然後才是記住。”我們相信圖書,相信圖書館,相信她們是“親愛”的。由此,我想象到圖書館課程。圖書館應當是課程,圖書館課程應該建構起一個課程體系,于是寫了一篇文章,編輯給它加了一個主标題——“圖書館何以親愛”。同樣,我閱讀德國教育人類學家博爾諾夫的著作《教育人類學》,書中提到學生非連續性發展的觀點,我聯想到教師的連續性發展與非連續性發展,道理是相通的:學生具有可塑性,教師同樣具有可塑性。在一番聯想、猜想後我寫成了《非連續性發展:教師專業發展理論的另一論域》。我讀過一套兒童哲學繪本《哲學鳥飛羅系列》,叢書的主角菲盧是一個六歲半的男孩,恰好處在開始産生社會性困惑的年齡,總是沒完沒了地提問題,全家人為答案吵得不可開交。晚上回到房間,他的好朋友——一隻名叫飛羅的小鳥就會來到窗台,與他交談。周國平認為這個飛羅其實就是菲盧,是他的那個理性的自我。我不斷地猜想、綜合,寫成了關于兒童哲學教育的文章——《當教室裡飛來哲學鳥的時候》······
呵,猜想性閱讀把我帶到了思想的遠方。當讀書建議成為閱讀信條的時候,我們離思想的遠方就不遠了。
— END —
來源 | 本文來源于《中國教師》雜志2022年第4期
作者 | 國家督學,原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 成尚榮
征集|“大國良師的成長故事”
《教育家》發起的第二屆“尋找大國良師”公益活動近日啟幕。活動分為三部曲:
1.征集“大國良師的成長故事”
2.出版《大國良師的樣子》叢書
3.推選“大國良師”
活動截止至2022年底。依據評選标準及參與要求,推選出10位“2022大國良師”,授予“大國良師”稱号,每位“大國良師”将獲得主辦方提供的成長獎勵基金10萬元(稅前)。
2021年11月—2022年6月,開展“大國良師的成長故事”征集活動。
征集要求:參與活動的教師,撰文講述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感觸最深的成長故事。以第一人稱撰文,體裁為叙事散文,字數在1000字左右。要求故事真實感人。文章擇優刊發《教育家》雜志、《教育家》雜志新媒體、學習強國等平台。
參與方式:在“光明教育家”App“尋找大國良師”專題頁面送出申報表及教師自述的“大國良師的成長故事”(申報表及“大國良師的成長故事”需同步送出)。如僅參與“大國良師的成長故事”征集活動(不參與“尋找大國良師”活動),将文章發送至郵箱[email protected],文章中注明學校、姓名、聯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