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市民階層形成與市民文化崛起的時代,是高雅文藝俗化與世俗文藝昌盛的時代,是抒情文學新變與叙事文學漸盛的時代,在中國文化發展史、文藝嬗變史、文學演進史上舉足輕重。宋代小說是市民娛心消遣的經典門類,也是士人淑世資暇的重要文類,可謂觀察文學内部雅俗關系的理想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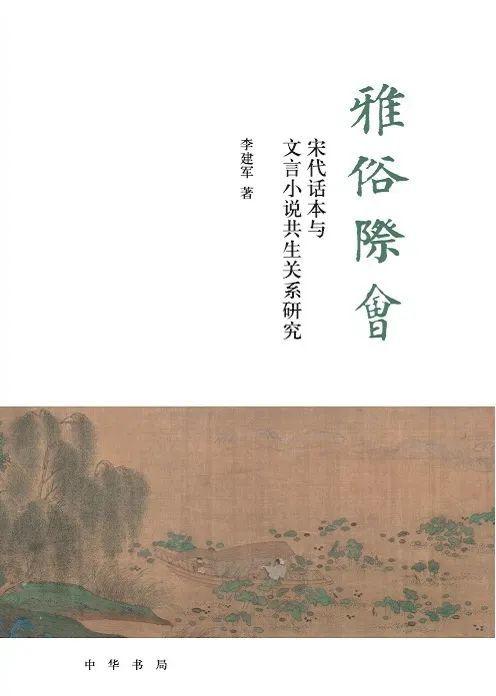
《雅俗際會: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共生關系研究》,李建軍著,中華書局2020年12月版。
具體而言,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既二水分流又局部交彙,既互相倚傍又彼此消長,在中國叙事文學史上形成獨特景觀,并影響到文學的雅俗格局,具有文白互動的典型意義和重要的學術價值。
本文在學界研究基礎上[1],以共生理論的分析架構為骨架,以叙事文學的研究範式為血肉,以雅俗際會的文化視野為魂魄,分析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互動共生(下簡稱“文白共生”)之态勢與動因,并以此為基點追尋宋代以降士人文學與市民文學、高雅文化與世俗文化雙向互動的社會原因、邏輯關聯,揭示近世雅俗文化互滲消長的内在理路及深遠影響。
一、文白共生的叙事語境
宋代小說有話本與文言之分。宋代話本小說的判定,學界有争議,筆者綜合胡士瑩、程毅中、石昌渝、朱一玄、陳桂聲等諸家觀點[2],認為《碾玉觀音》等35種小說話本、《五代史平話》等3種講史話本、另有1種說經話本即《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共39種話本小說的主體内容完成于宋代,雖後世有增删修潤,但仍應判定為宋話本。
宋代文言小說有筆記體(展現為筆記小說集)和傳奇體(多展現為單篇傳奇文)之分。其中筆記小說集據《四庫全書》“小說類”著錄,計91種,包括“雜事之屬”65種、“異聞之屬”14種、“瑣語之屬”12種;單篇傳奇文據李劍國先生《宋代志怪傳奇叙錄》,計85種。上述200餘種話本體、筆記體、傳奇體小說,構成了宋代小說的主體。
共生是不同生物體互利互助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現象,其前提是不同生物體之間的異質互補。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的共生基礎,源于兩者屬于相異又相鄰的叙事類型——士人叙事與市民叙事,源于兩者在叙事話語(用何叙事)、叙事行為(如何叙事)、叙事旨趣(為誰叙事)、人物塑形、叙事倫理等方面的異質互補。
《宋代志怪傳奇叙錄》
宋代文言小說與話本的編創主體、接受主體有士人與市民之别,兩類小說分别反映着不同主體的文化精神和倫理意識,屬于不同類别的叙事。
宋代文言小說的創作和閱讀基本上是在士人圈中,屬于文人叙事中的士人叙事。宋話本的口傳環節是典型的市民叙事,編寫環節雖然經過書會才人等文人的加工潤飾,不可避免地帶有一些文人叙事的情趣和印痕,但主導性的還是市民情趣,是以宋話本的主體應歸入市民叙事。
緣此,就叙事層面而論,宋代文言與話本小說之關系,渾言之可謂文人叙事與民間叙事之互動,析言之則應言士人叙事與市民叙事之共生。
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在叙事話語上存在差異。文言小說(士人叙事)多用書面化的文言,簡潔典雅,含蓄蘊藉,呈現出超語體文的書面加工色彩;話本(市民叙事)則多用口語化的白話,直白俚俗,生動活潑,顯現出語體文的活态口語色彩。
《宋元小說家話本集》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士人叙事所使用的文言與唐代相比,已是吸取較多白話質素的淺俗化文言,而且部分小說已在人物對話等環節直接使用白話以繪聲繪色、畢現聲口;而宋代市民叙事也有大量使用文言的現象,如話本化傳奇、傳奇式話本和白話話本中的文言運用。由此而形成士人與市民叙事在語言運用上既各有側重又互相交叉的現象。
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在叙事行為上差異甚大。一般而言,士人叙事重“事”亦重“叙”,講究結構的謹嚴周密、情節的跌宕有緻和叙述的起承轉合;市民叙事則“事”重于“叙”,更加注重故事本身的生動曲折,而不把“叙”作為重點,在謀篇布局的運思、叙事技法的運用上均不及士人小說精緻。
值得注意的是,市民叙事中大量運用嫁接、捏合、巧合、以物串事等叙事技法,呈現出鮮明的民間性、集體性和質樸性。
尤可一提的是,宋代話本作為典型的市民叙事文本和口傳文學文本,存在較為普遍的程式化傾向,既展現在宏觀層面的情節設計、角色安排,也展現在中觀層面的場景描繪,還展現在微觀層面的語言表達,可謂全方位、多層面的程式化。宋代士人叙事,少量作品如入冥小說也有程式化迹象,但多數作品還是以追求個性化描寫為目标,盡量避免出現重複,程式運用密度較低,程式化程度遠遜于宋話本。
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在叙事旨趣上各有側重。從價值取向而言,宋代文言小說作為士人精神世界的藝術折光,鮮明地展現出他們的心之所向、情之所系。一方面,他們有登第入仕、經世濟民的志趣;另一方面,他們也會有功名浮雲、黃粱夢醒的體悟。兩者交織在一起,呈現出入世與出世、夢想與夢醒互相融會的七彩光譜。相較于宋代文言小說折射出文人士子的登第夢和黃粱夢,宋話本則折射出市井細民的發迹夢和富貴夢。
《宋元平話集》
簡言之,宋話本折射出市井的價值追求,而宋代文言小說則折射出士人的人生體悟,兩者有俗與雅、淺與深、熱鬧與冷靜、直白與含蓄之審美差異,剛好可以異質互補。從旨味追求而言,文人叙事更多追求雅緻的韻味,市民叙事則更為喜好俚俗的趣味,前者含蓄蘊藉,後者淺近直露,前者偏重精神愉悅,後者偏重感官刺激。
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在人物塑形和叙事倫理上各有偏好。就士人形象塑造而言,宋傳奇中的士人形象更多悲情色彩,而話本中的士人形象則更多喜劇情調。[3]這種人物塑形的差異可能與士人與市民的審美心理歧異有關,士人更多以悲為美,而市民更多以喜為美。
宋話本與文言小說的士人塑形的悲、喜格調之别,往往蘊含叙事主體的意圖倫理考量。文言小說通過士人的悲劇故事和顯明的倫理介入,有強烈的勸善懲惡意圖;話本偏重叙述士人的喜劇故事、風流故事,雖也有一定的勸懲意識,但倫理介入并不顯明,叙事的優先考慮是娛樂性。概言之,宋代文言小說是教重于樂,而宋話本則是樂先于教。
《宋代傳奇集》
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共生關系的形成,兩者的異質互補是前提,而宋代整個文化領域的雅俗互滲則是其時代語境。唐宋之際是中國曆史的變革時期。唐宋變革導緻文化轉型,大量平民子弟入仕為官,跻身士紳階層,逐漸改變士人文化的整體面貌和雅俗格局,使得宋代的士人文化較之唐代更具平民色彩和雅俗貫通之習。
另一方面,宋代商品經濟和城市的發展,催生了市民階層的興起,而市民階層的興起,又促成了以瓦市伎藝為代表的市民文化的勃興。市民文化是都市通俗文化,又是介于雅俗之間的文化,連接配接着鄉民文化與士人文化,吮吸着這兩種文化的營養。
士人文化與市民文化雖然有大傳統與小傳統、雅文化與俗文化之差異,但由于唐宋之際社會變革、階層變動、觀念變遷導緻雅俗邊界變化,兩者在宋代的雙向互動非常明顯,一方面市民文化既影響士人文化,又從士人文化汲取養分,另一方面士人文化既輻射市民文化,又從市民文化取精用弘。宋代士人文化與市民文化的雅俗際會,正是話本與文言小說互動共生的時代動因。
二、文白共生的雙向機制
宋代說話及話本與文言小說互動共生,一方面文言小說借鑒說話伎藝出現新變,另一方面說話伎藝倚傍文言小說不斷壯大。
(一)文言小說對說話伎藝的借鑒
宋代文言小說發生了從“淑世”到“資暇”的重心轉移,從“慕史”“傳信”到“幻化”“不必信”的觀念變遷。[]伴随觀念變遷,宋代文言小說的審美趣味,也在向市井伎藝、市人小說的世俗化方向滑動。
明刊本《宋人百家小說》
宋人文言小說尤其是傳奇體小說中,下層文人的的作品大幅增加,這些作品帶着強烈的市井氣息和世俗趣味,逐漸改變着文言小說的雅俗版圖。另外,宋代中上層文人之作,如洪邁《夷堅志》、廉布《清尊錄》、郭彖《睽車志》等,受到話本小說和通俗文言小說的刺激和影響,也在逐漸沾染市井氣息,徐徐褪去稗說雅緻之習。
前者是俗的挺進,後者是雅的萎縮,兩者彙合,使得文言小說的整體風格逐漸由唐之雅緻轉為宋之世俗。宋人文言小說的世俗化,主要表現在小說的焦點逐漸由文人學士、才子佳人轉向市井細民、芸芸衆生,小說的旨趣也逐漸由裨教化、補史阙為主的文人之趣轉向供談笑、廣見聞為主的細民之好。
宋代文言小說不僅在小說觀念、審美趣味上受到市人小說的影響,也在叙事手法上借鑒後者,這最典型地展現在“獨白式”心理描寫手法的運用上。
中國文言小說作為稗史,脫胎于史傳,有較強的慕史傾向和鮮明的史化特征。史傳叙事的“呈現式”模式,雖然是一種全知叙事模式,但撰寫者“全知”領域往往僅限于人物言行,并不包括人物心理。直接描寫旁人無法得知的人物心理,顯然有悖實錄原則,因而此舉被正統史家擯棄。
《新編五代史平話 》
漢魏六朝的文言小說受到史傳叙事的影響,采用“呈現式”叙事模式,盡量秉承實錄原則,客觀再現人物言行,一般不會直接描寫人物心理。這些小說即使描寫人物心理,一般也是通過描寫夢境、幻覺或者人物言行神态等,曲折地呈現人物的内心活動,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會采用人物内心獨白方式直抒胸臆。唐代的志怪小說、轶事小說,也大都不會采用内心獨白之法直接描寫人物心理,傳奇小說則出現了一些新變,如《無雙傳》等晚唐傳奇開始零星出現内心獨白式心理描寫。
傳奇小說至晚唐出現的内心獨白式心理描寫,猶如星星之火,到了宋代,燃成燎原之勢。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具有内心獨白式心理描寫的篇章大量湧現。《唐宋傳奇總集》宋代部分共收錄傳奇184篇,具有内心獨白式心理描寫的篇章共有18篇,占比已達10%左右。[]
第二是大段的心理獨白開始出現,如清虛子《溫婉》叙及溫婉被迫流于娼家的經曆時,多處運用了直接心理描寫之法,且采用了大段的心理獨白。
第三是内心獨白式心理描寫手法的運用漸趨成熟,功能漸趨豐富,或為揭示人物内心、推動情節發展,或為設定懸念伏筆、增加故事波瀾,或為描摹内心隐秘、凸顯人物性格,其中後兩種功能在先宋文言小說中非常罕見。
宋代文言小說中内心獨白式心理描寫的大量湧現和功能漸趨豐富,應與說話藝術的影響頗有關聯。與文言小說“客觀呈現式”的叙事模式不同,白話小說是一種“主觀講述式”的叙事模式。
《宋人小說類編》
宋代說話藝人在講故事之際,常常會直接進入人物内心世界,呈現人物言行的情理基礎,這些直扣心扉之舉在現存宋話本中有清晰的印迹。現存宋代39篇話本中,内心獨白式心理描寫比比皆是,而且類型非常豐富。宋代說話藝人這種直扣心扉的全知視角講述,對宋代文言小說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我們以最能代表文言小說成就的傳奇為例,宋傳奇作者中有大量未入仕的下層文人,這些下層文人與中上層的正統文人相比,叙事時受到傳統規範的束縛更小,更能夠突破傳統文人撰述稗史時效法史傳、不敢直闖人物心扉的叙事慣例,這就為他們寫作傳奇時進行内心獨白式心理描寫提供了可能。
這些下層文人耳濡目染宋代日趨興盛的說話藝術,不斷汲取說話藝人知言知行知心理的講述技法,成功地移植到傳奇寫作上,進而導緻傳奇中内心獨白式心理描寫的大量出現。
(二)說話伎藝對文言小說的倚傍
就宋代說話及其文本對文言小說營養的汲取而言,包括士人叙事文本的借鑒和改編、倫理化傾向影響下的“道學心腸”、文備衆體之法的采借等方面。
士禮居藏本《新刊宣和遺事》
宋代話本小說的素材,很大部分來自于唐宋文言小說。現存35種宋代小說話本中,可以大緻考出本事來源于文言小說者有13種;宋代講史話本中,《五代史平話》乃是對《資治通鑒》所載五代史的敷演發揮,《大宋宣和遺事》則是掇拾故書、文白雜編的早期講史話本,其剽取之書可能有《南燼紀聞》《竊憤錄》《續宋編年資治通鑒》等。
概言之,宋代講史話本主要依賴相關史籍和稗史小說,小說話本則有三分之一篇目是對現成文言小說的捏合、改編與敷演。可以說,宋代的市民叙事(話本小說)是在充分汲取士人叙事(史籍和文言小說)營養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士人叙事從素材上滋養着市民叙事。
宋代文言小說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在主旨方面有強烈的倫理化傾向,這種傾向也傳導至受文言小說滋養的話本小說。本來,話本小說作為說話藝術的文本化産物,其根本屬性是商品性語境下的娛樂性。但由于受到時代風氣和士人叙事的影響,較大部分的話本小說在注重娛樂性的同時也在兼顧教化性,進而呈現出寓教于樂、樂中有教的局面。
宋代的說話藝人,整體而言是重“樂”之際兼及“教”。現存35種小說話本中,有較為明确的教化旨趣者共17種,約占總數的一半。這些話本的教化旨趣非常廣泛,或敦崇風教,或褒贊孝義,或勸人歸善,或引人立身,或宣揚佛道,或針砭時弊,不一而足。
宋代話本小說還學習傳奇的文備衆體之法,篇中有詩、詞、鼓子詞、骈文、辭賦和韻語等多種文體,顯示出市民叙事對士人叙事的借鑒。宋代話本小說的詩詞韻語中,既有民間流傳的俗語、諺語,書會才人、下層文人創作的俚俗詩詞,也有大量的非常典雅的文人詩詞,顯示出民間文藝對精英文學的采借。
《醉翁談錄》
羅烨《醉翁談錄·小說開辟》雲小說藝人“論才詞有歐、蘇、黃、陳佳句,說古詩是李、杜、韓、柳篇章”[],可見民間藝人對精英文學的借鑒化用。詩詞韻語的大量運用,以說唱結合的方式增強了說話的吸引力,同時也以采借精英文學的途徑充實了話本的内容,另外還以文備衆體的形式提升了話本的文化品位,顯示出市民叙事、民間文藝對士人叙事、精英文學的吸納和借鑒。
三、文白共生的典型形态
宋代士人叙事與市井叙事互動共生,催生出世俗化傳奇、準世俗化傳奇、種本式文言小說、話本化傳奇、傳奇式話本等雅俗際會的小說文體新樣式。
(一)世俗化傳奇:《青瑣高議》
宋代的世俗化傳奇,最集中地收錄于劉斧《青瑣高議》(下簡稱《青瑣》)。該書中的傳奇小說,受到說話等世俗文藝的深刻影響,以雅體寫俗情,演變成有别于唐代辭章體傳奇的世俗化傳奇。
誦芬室刻本《青瑣高議》
《青瑣》是一部具有濃厚世俗色彩的雜俎型小說集。《郡齋讀書志》批其“辭意頗鄙淺”[],《四庫全書總目》認為該書乃“裡巷俗書”,指出其序言“不稱名而舉其官”不合常例,所紀又“多乖雅馴”,七字标目“尤近于傳奇”,“間有稱‘議曰’者”“亦多陳腐”[],從書前序言、所紀内容、七字标目、文末議論四個方面揭示該書的淺俗。《青瑣》的“俗”,最重要展現在篇章内容上。
該書所收142篇小說中,雜事小說和志怪小說89篇,大緻可以算作傳奇的有53篇,其中唐人傳奇2篇,宋人傳奇51篇。傳奇作為文備衆體、篇幅曼長、叙事委曲、注重文采的小說文體,本來是小說中最“雅”之體,但《青瑣》中的傳奇作品已出現“雅”體染“俗”情的世俗化傾向。
這種世俗化既展現在故事人物和題材的世俗化,也展現在語言表達的世俗化,更展現在審美趣味和價值觀的世俗化,還展現在藝術手法的世俗化。《青瑣》作為世俗小說集,現存142篇小說中有15篇被說話和戲曲等世俗文藝吸納、改編,被改編的篇目比例超過10%。
(二)準世俗化傳奇:《雲齋廣錄》
宋代的準世俗化傳奇,最集中地收錄于李獻民《雲齋廣錄》(下簡稱《雲齋》)。該書是雜俎型小說集,今本分“士林清話”等六門,共八卷,另附後集一卷,合為九卷,收錄雜事小說12篇、詩話28條、傳奇13篇、傳奇配歌2首,共55篇(首、條),其中最具藝術價值的是13篇傳奇。
這些文本既有叙事委曲、篇幅曼長、富有文采和意想等傳奇文體的一般特征,還有迎合市井細民的豔異化傾向,《四庫全書總目》批評該書“所載皆一時豔異雜事,文既冗沓,語尤猥亵”“純乎誨淫”[]。
清刊本《雲齋廣錄》
《雲齋》的世俗化不僅展現在人物、題材、審美趣味、價值觀念乃至藝術手法方面,也展現在其與市井說話的關系上。
《雲齋》卷四“靈怪新說”,大緻相當于《醉翁談錄》所雲“靈怪”,都是征奇話異的精怪故事;《雲齋》卷五卷六“麗情新說”,大緻相當于《醉翁談錄》所雲“傳奇”,大都是講說人間男女情愛故事;《雲齋》卷七“奇異新說”,大緻相當于《醉翁談錄》所雲“煙粉”,大都是講說煙花粉黛的女鬼與世間男子的人鬼情愛故事;《雲齋》卷八“神仙新說”,大緻相當于《醉翁談錄》所雲“神仙”,都是講說神仙故事。
另外,《雲齋》中的多篇傳奇都曾有相應的宋代小說話本對應。概言之,《雲齋》中的宋傳奇是介于唐代辭章化傳奇與《青瑣》世俗化傳奇之間的一種中間形态,我們不妨将其視為準世俗化傳奇。這種準世俗化傳奇,是雅俗融彙的傳奇新形态。
(三)種本式文言小說:《綠窗新話》
宋代的種本[]式文言小說,即為說話而備的節錄故事梗概的“梁子”式文言小說,集中收錄于皇都風月主人所編《綠窗新話》(下簡稱《綠窗》)。
《綠窗新話》
該書選錄154篇文言小說,大多系節引漢魏六朝小說、唐宋傳奇筆記、詩話詞話、史傳文集而成。每篇都有七言标題,且相鄰兩篇的七言标題大都兩兩相對。從内容傾向而言,該書篇章選擇、文本節錄和文字改動,都有迎合市井的情色化趨勢,可用“風月”加以概括;從編纂體例而言,該書并非類書,而是排列有序、以類相從的故事彙編,可用“類編”加以概括。
合而觀之,《綠窗》可謂“種本式風月類編”。《綠窗》與說話關系非常密切,今本有15篇與《醉翁談錄·小說開辟》所雲說話名目有明顯對應關系。值得注意的是,《綠窗新話》在節錄群書時增飾、捏合等有異于原文的文字改動,既有可能是編者為提升故事的吸引力而主動做出的調整,也有可能是編者采納說話藝人對故事的改編而相應做出的調整,兩者情況可能都存在,而後者尤其值得關注。
總之,《綠窗新話》既選錄改編現成的書面文本為說話藝人提供“梁子”,又将說書場對故事的口頭改編落實為書面文本,再反哺給說話藝人,該書實際上成了“文本”與“話本”、書寫叙事與口傳叙事互相轉化的橋梁紐帶,在話本與文言小說互動關系史上有重要價值。[11]
(四)話本化傳奇:《醉翁談錄》
宋代的話本化傳奇,最集中地收錄于羅烨的《醉翁談錄》(下簡稱《談錄》)。該書是雜俎型小說集,今本以天幹為序分為十集,每集分為兩卷,共二十卷,各卷下又有類目,分舌耕叙引、私情公案、煙粉歡合等21類,類目之下為具體篇目,收錄論小說伎藝文章、傳奇小說、筆記小說、幽默笑話、滑稽判詞等80篇(則),還收錄品評諸妓的七言詩歌55首。
古典文學出版社版《醉翁談錄》
内容雖然龐雜,但基本都是風月題材,目的則應該是為說話藝人提供參考。書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根據文言小說改編而成的23篇話本化傳奇。這些話本化傳奇,大多用淺近文言寫成,一般篇幅較長,叙事委曲,有傳奇之貌。
但其市民情趣的彰顯、市人形象的刻畫、世俗手法的采用、市井言語的充溢,特别是“詩曰”“詞雲”等方式的存在,又使其與唐傳奇等辭章化傳奇、《青瑣》中的世俗化傳奇、《雲齋》中的準世俗化傳奇,頗有差異。
可以說《談錄》中的話本化傳奇是傳奇為表、話本為裡,是滲透着話本精神的傳奇。但這些話本化傳奇,還沒有後來成熟話本的文體标志(入話、散場語、“話說”、“且說”等說書套語),是以還隻能說是準話本。
(五)傳奇式話本:《藍橋記》等
宋代的傳奇式話本,今存者有3種,即《清平山堂話本·藍橋記》《警世通言·宿香亭張浩遇莺莺》《警世通言·錢舍人題詩燕子樓》。這些話本,雖然都用文言化的語體,皆具傳奇體的形貌,但同時都具備入話、散場詩等話本特有的篇章體制,從文體角度考察還是歸入話本為宜。
《清平山堂話本校注》
傳奇式話本基本上隻存在于宋元和明代前中期,到了明代後期,話本體小說完全成熟,白話語體成為話本體小說的标配,從此文言形态的傳奇式話本便銷聲匿迹。于此可見,文言形态的傳奇式話本乃是話本小說發展史上的一種早期形态,是說話藝人、書會才人和拟作文人等借用傳奇文本套上話本體制而生成的一種早期話本,是說話伎藝文本化過程中的階段性文體,呈現了來源于民間的叙事文體(話本體)草創時寄生、依附于文人叙事文體(傳奇體)的曆史圖景。
傳奇式話本與話本化傳奇有同有異。就同而言,兩者都是文言形态的傳奇小說,都是說話伎藝文本化的産物。就異而言,話本化傳奇是滲透着話本精神的傳奇,但沒有話本的文體标志(入話、散場語、“話說”、“且說”等說書套語);傳奇式話本已經具有話本的文體标志,可謂雖未成熟但基本成型的話本。是以,從話本的演進階段而言,傳奇式話本是話本化傳奇的進一步發展。
上述世俗化傳奇、準世俗化傳奇、種本式文言小說、話本化傳奇、傳奇式話本等五種小說文體新樣式,是士人叙事與市井叙事互相滲透的結晶,是雅俗際會的産物,在中國小說文體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四、文白共生的文學史價值
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的共生,推動小說聚焦、叙事觀念、雅俗格局都發生變化,具有重要的文學史價值。[12]
《古體小說鈔》
(一)小說聚焦:“人物”到“故事”、“意蘊”到“趣味”
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的共生,市民叙事與士人叙事的互動,使得宋人小說中雜記體異軍突起,與之相應,小說的聚焦點也逐漸從“人物”移向“故事”,從“意蘊”滑向“趣味”,顯示出邁向近世的世俗化傾向,對後世有深遠影響。
以最有小說性的傳奇體為例,唐宋傳奇中,雜傳體與雜記體的比例大不一樣。唐人所編傳奇集中,晚唐文士陳翰《異聞集》堪稱翹楚,宋人所編傳奇集中,劉斧《青瑣高議》可謂典型,我們可将兩書進行比較。《異聞集》所收唐傳奇40篇中,雜傳體有25篇,占比62.5%,雜記體有15篇,占比37.5%,雜傳體占絕對優勢。
《青瑣高議》所收宋傳奇51篇中,雜傳體有26篇,雜記體有25篇,兩者數量已基本相當,平分秋色。通過比較可以發現,由唐入宋,傳奇體中雜記體所占比例是有大幅提升的。如果說唐傳奇中,雜傳體與雜記體有主從之别,那麼宋傳奇中,雜記體異軍突起,已基本可與雜傳體分庭抗禮。那麼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出現此種情況又意味着什麼呢?
《青瑣高議》
一般而言,雜傳體傳奇以人物價值為焦點,讓讀者在感喟人物命運、感歎人物性格、咀嚼人物形象中獲得豐富複雜的美感,雜記體傳奇則以故事價值為焦點,讓讀者在曲折、離奇、懸念中領略故事趣味,獲得未必豐富但卻非常明快的美感。對閱聽人而言,雜傳體傳奇意蘊較豐,需要閱聽人較強的審美感悟能力方能品出味道,而雜記體傳奇則曉暢明白,閱聽人很容易就獲得趣味。
概言之,在審美品位上,雜傳體傳奇可能略勝于也略雅于雜記體傳奇。宋代傳奇中雜記體的異軍突起,正是傳奇體俗化的一個重要表現。
宋傳奇中雜記體的大量增加,表明傳奇文本的聚焦點正在從唐代的人物價值逐漸轉向故事價值,表明宋人傳奇文本對故事性的追求,正在逐漸超越人物性格的刻畫和形象的塑造。宋傳奇的這個轉向,可能受到說話的某些影響。
宋代說話和話本鮮明強烈的故事性取向,不能不影響到宋代士人的小說寫作。與唐傳奇相比,宋傳奇的作者更為平民化,他們耳濡目染說話伎藝,受其娛樂性基調和故事性取向的影響,更為注重傳奇文本的故事價值,于是出現雜記體傳奇的異軍突起。
宋傳奇中雜記體的大量增加,故事性和娛樂性的不斷增強,使得本來高雅的傳奇體不斷俗化,并與世俗的話本體不斷接近。到了元明,傳奇小說中雜記體已經占據絕對優勢。從唐代雜傳體傳奇占主導到元明雜記體傳奇占主導,宋代是真正的轉捩點。置于這樣一個傳奇體的演變脈絡,宋傳奇承上啟下的轉折意義非常明顯。
(二)叙事觀念:“淑世”到“資暇”、“慕史”到“幻化”
《唐宋傳奇集》日譯本
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的共生,市民叙事與士人叙事的互動,使得宋人在小說“樂”“教”功用與“虛”“實”關系的認知上,逐漸超轶前人。宋代話本小說(市民叙事)的娛樂性、虛構性,沖擊着文言小說(士人叙事)的“補史阙”、“裨教化”,此長彼消,推動了叙事觀念逐漸從“淑世”向“資暇”轉移,從“慕史”向“幻化”邁進。
在中國叙事文學史上,由于受到“史貴于文”以及史傳“實錄”理念的強大影響,小說創作的“慕史”傾向和“史化”特征非常明顯,曆史叙事風靡一時。唐傳奇“始有意為小說”[13]“作意好奇”[14],開啟了“亞叙事”到“叙事”、“史傳叙事”到“虛構叙事”的轉折,但閱聽人僅限于士子文人,缺乏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宋代話本小說的商品性、娛樂性使其“文學叙事”意願更為強烈、特征更為鮮明、影響更為廣泛,并對文言小說産生強大影響,最終推動叙事文類重心從紀實叙事、曆史叙事向虛構叙事、文學叙事的轉移。
(三)雅俗格局:“雅化”到“俗化”、“中古”到“近世”
宋人稗說觀的近世化轉向以及與之相随的稗說的娛樂性增強,再加上傳奇體借鑒市民叙事而呈現俗化趨勢,話本體采借士人叙事而初顯雅化傾向,共同構成話本與文言小說互動共生的完整圖景。這樣的互動共生,整體上是使小說娛樂性更強、幻設意識更濃、故事性更顯、世俗性更切,概言之,使小說從中古邁向近世。
《宋元筆記小說大觀》
從文學史的角度考量,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的互動共生,逐漸改變了中國文學的内部格局,首先是抒情文學與叙事文學比例格局的改變。宋代文言小說受到說話及話本的影響,作為叙事文學文體的屬性更為鮮明。
同時,更多的士人如洪邁、王明清等,願意将講故事、重趣味的小說作為自己舞文弄墨的主要文體之一,傾心于從叙事性文體的寫作中找到樂趣,這就使得叙事文學在士人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
另外,書會才人和下層文人不斷吸納文言小說營養,在整理、改編說話文本的過程中不斷借鑒士人文學的方法、技巧,使得話本小說作為新興的叙事文學文體逐漸從粗率簡陋走向精緻成熟。通俗叙事性文體(話本體)的逐漸成長及其在市井的大受歡迎,高雅叙事性文體(傳奇體和筆記體)在士人中重要性的提升及其在士林的影響擴大,使得叙事文學在雅(士人)、俗(市井)兩個層面都在擴大地盤。
此長彼消,叙事文學的勃興使得文學格局逐漸開始發生變化,即由中古以詩文為主的抒情文學一家獨大格局,逐漸轉向近世抒情文學與叙事文學并駕齊驅格局。此格局到了明清再進一步發展,就演變成了叙事文學更能展現時代風貌進而更勝一籌的文學新圖景。
宋代話本的興起及其與文言小說的互動共生,也改變了士人文學與市民文學的比例格局。宋代之前,中國文學版圖中士人文學一枝獨秀,宮廷文學雖然精緻卻難以成為主流,鄉村文學因為俚俗而難登大雅之堂,市民文學在中唐之後開始萌發也暫未形成氣候。[15]
《宋元小說研究》
到了宋代,随着工商業的發達、城市經濟的繁榮,以及随之而來的戶籍制度變革(單列“坊郭戶”以與“鄉村戶”差別),真正的市民階層開始形成。與之相随,市民文化開始崛起,市民文學開始勃興。
話本小說作為典型的市民文學,深受廣大市民的喜愛,同時也受到不少士人的關注。不少士人借用話本的手法甚至移用話本的情趣寫作文言傳奇,使得這些文言傳奇披着士人文學的外衣,而其核心卻充溢者市民文學的精神。另一方面,在明清時期,也有部分士人在改編宋元話本時不斷灌注士人精神,并不斷改造、雅化話本體,使得話本體這種市民文學文體逐漸變成士人文學文體,又顯示出士人文學對市民文學的汲取。
總之,就小說領域而言,士人文學與市民文學是雙向互動的,但這種互動的大趨勢是市民文學不斷成長壯大,而士人文學則深受市民文學影響而漸趨平民化、世俗化。[16]
文言小說屬于士人文學,灌注着“大傳統”的質素,而話本小說屬于市民文學,奔湧着“小傳統”的血液。宋話本與文言小說的共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觀察大、小傳統互動的範例。
《宋稗類鈔》
宋代之前中國文化中的“大傳統”,其演變發展的主動力有三:一是士人的原始創造,二是吸收外來文化,三是汲取鄉村文化(民間文化)。宋代以降,随着市民階層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昌盛,市民文化已經取代了鄉村文化(民間文化)成為士人創造大傳統的主動力之一。
簡言之,就對主流文學(士人文學)的貢獻和影響而言,宋代之後市民文學可能已經超越了鄉村文學(民間文學)。置于這樣的視域,再來考察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的共生關系,會對探讨士人文學與市民文學、大傳統與小傳統,有更深入的體會。
上下滑動檢視注釋
注釋:
[1]詳參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叙錄》,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魯德才《古代白話小說形态發展史論》,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蕭相恺《宋元小說史》,張兵《宋遼金元小說史》,淩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宋代雅俗文學觀》,李軍均、曾垂超《論宋代小說的雅俗之變及其文化精神》,孟昭連《宋代文白消長與小說語體之變》,紀德君《宋元話本與文言小說的雙向互動》等。
[2]詳參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宋元小說家話本集》,石昌渝等《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朱一玄等《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陳桂聲《話本叙錄》。
[3]李桂奎《傳奇小說與話本小說叙事比較》,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207頁。
[4]李建軍《宋人“稗說觀”的演進趨向與小說學史價值》,《文學評論》2019年第5期。
[5]袁闾琨、薛洪勣主編《唐宋傳奇總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羅烨《醉翁談錄·小說開辟》,第3頁。
[7]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97頁。
[8]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908頁。
[9]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四《雲齋廣錄提要》,第1909頁。
[10]日本學者大塚秀高《從〈綠窗新話〉看宋代小說話本的特征——以“遇”為中心》(《保定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3期)将“小說人将‘話本’的梗概、與原話的差異簡單地用文言記下”的本子稱為“種本”。
[11]李建軍《〈綠窗新話〉文本性質新探》,《文學遺産》2019年第6期。
[12]宋代話本與文言小說的共生,除文學史價值外,還有漢語史價值,詳參孟昭連《宋代文白消長與小說語體之變》(《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
[13]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44頁。
[14]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頁。
[15]袁行霈《中國文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1—78頁)“既着眼于題材内容,又兼顧文學産生發育的環境土壤,以及作者和欣賞者”,将中國文學分成四類,即宮廷文學、士林文學、市井文學和鄉村文學。此處借鑒其分法,而名稱略有不同。
[16]王齊洲《雅俗觀念的演進與文學形态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指出:“中國文學的發展……是不斷地由雅趨俗,即從貴族走向精英,從精英走向大衆,文學主流文體越來越通俗化,文學消費主體越來越大衆化,這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基本趨向。”筆者深以為然,小說領域可謂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