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2003年3月的一天,我調到三聯書店工作還不滿三個月,就請《讀書》的編輯吳彬約揚之水談稿件事。那時我策劃“細節閱讀叢書”,希望通過放大事物的局部,講出背後的道理,引導作者和讀者的趣味,躲過學界的浮躁。我列了幾個假設的名目:《兩座基督教堂》《十二把明代椅子》《二十位人性的見證者》……揚之水所做古代名物考證,也是從細微處入手,甚合此意。不久,三聯書店為這套叢書組織了一次讨論會,與會者有樓慶西、楊泓、尹吉男、鮑昆、孟晖、張琳等,揚之水也參加了。
那時稱呼揚之水的本名趙麗雅,後來知道她還有一個名字是趙永晖。年齡相近的人都知道,“麗雅”這個名字來自蘇聯小說《古麗雅的道路》。“揚之水”來自《詩經》,“趙永晖”有什麼典故就不清楚了。
“細節閱讀叢書”的第一本是孟晖的《花間十六聲》,以散文筆法考證了《花間集》中涉及的十六種古代貴族婦女的用物,很受讀者歡迎,至今還在重印。叢書陸續出版了多種,但沒有揚之水的,因為她的稿子很搶手,不必放在一套叢書裡,比如她的《桑奇三塔》是應我之約給三聯書店的,作為單本書出版了。也許就此結下了緣分。
2011年4月,我調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不久就與揚之水談,想把她二十幾年來關于名物的書稿出一套合集,一套最好的版本。轉眼一年過去,這期間她陸續出版了三卷本《<讀書>十年》,然後騰出時間整理其他書稿。2012年5月23日,我到她家初步談定《棔柿樓合集》十三卷。她列了一個目錄,包括《詩經名物新證》《唐宋家具尋微》《宋代花瓶》《兩宋茶事》《物中看畫》《藏身于物的風俗故事》等。我很興奮,當天就與甯成春老師通了電話,請他做設計師。這套書很适合他設計,很需要他設計。出于一貫對我的支援,甯老師一口答應。告訴揚之水,她也很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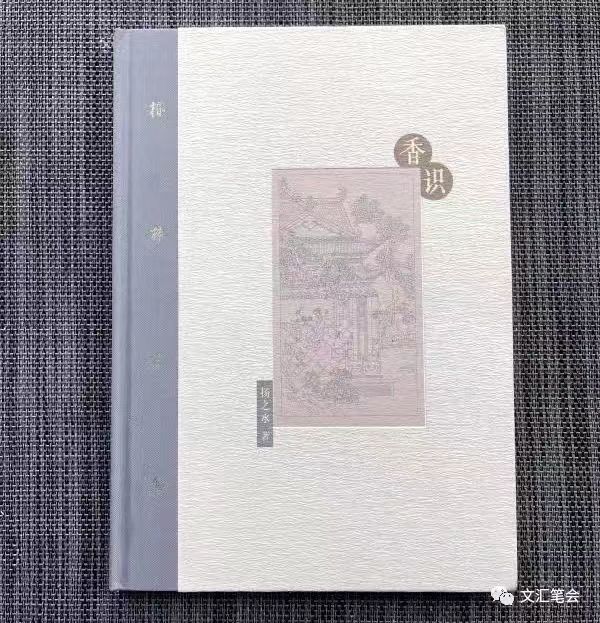
所謂“棔柿樓”,是因為揚之水家的院子裡有一棵柿子樹、一棵合歡樹,合歡樹又名棔樹。揚之水1991年出版《棔柿樓讀書記》時求啟功先生題寫書名,啟先生一并題了“棔柿樓”三個大字橫匾,這三個字正好可以用在叢書名上。商談多次,最後定下出版十二卷,前十卷都有現成稿子(以揚之水做學問的嚴謹,還需要逐篇修改,另外找高畫質的圖檔也非易事);十一、十二卷《中國古代金銀首飾》《中國古代金銀器》她還要下功夫從頭寫過,不過放在最後出也不耽誤。這年8月30日,香港中和出版社的總經理陳翠玲(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和編輯部主任呂愛軍在我辦公室,與揚之水商定,人美版出版的同時,由他們出版繁體字版。12月5日三方簽訂了出版合同。責任編輯由王鐵英擔當,她是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的研究所學生,來人美社多年了。
《香識》内頁
一套皇皇大著的出版就這樣開始了。出書順序并非按卷次排列,而是哪卷完工就先出哪卷。最早出版的是第三卷《香識》和第四卷《宋代花瓶》。《香識》談的是古人焚香、熏香故事,篇目有《蓮花香爐和寶子》《香合(盒)》《兩宋香爐源流》《宋人的沉香》等七篇,文章不過十萬字,圖檔卻有二三百幅,索引足足二十頁。作者認為:“中土香事原有着久遠的傳統,一是禮制中的祭祀之用,二是日常生活中的焚香。魏晉南北朝時期随佛教東傳的香事之種種,不過是融入本土固有的習俗,而非創立新制。至于兩宋香事的興盛發達,卻是與高坐具的成熟密切相關。其時士人的焚香,原是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後世看得是風雅,而在當日,竟可以說風雅處處是平常。”
《宋代花瓶》也由七篇文章組成,内容稍微開放些,除了談花瓶,還談到與花瓶相關相近的《筆筒、詩筒與香筒》《宋人房間的冬和夏》《名刺、拜帖與拜匣》等。
此後的數編,大緻是這兩種體例,或者專門一些,或者敞開一些;圖檔多,注釋繁,索引長。縱觀這套書,最大的特點是見微知著,從細節出發,考證和闡釋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追求,得出前人未曾涉及的結論。揚之水特别喜歡“尋微”這兩個字,幾次用到,大概因為它比較恰當地描繪出她做學問的方法和方向。她的“尋”,表面看比較随意,以能夠吸引她的興趣為前提,實際上正像她自己說的,謹記老師的教誨,“把瑣細的考證結系到曆史發展的主線”,在寫文章之時,“背後也幾乎都有一個大題目的預設”,而另一方面,正因為她對所選擇的課題有興趣,是以能夠耐住性子,一點一滴考證和梳理,并時有意外的發現(比如她從今人所謂“獰厲”的造型與紋飾中發現溫暖、溫柔的東西),這是她堅持自己的研究的底氣。
這套書表面看有點“雜”,有文學(《詩經名物新證》),有藝術(《物中看畫》),有生活(《兩宋茶事》),有宗教(《桑奇三塔》),但雜而不亂,似雜而統,說到底都是通過名物考證還原古人的生活。她說,“一個時代的風氣,多半是嵌在日常生活的細節裡。”她的研究不是古玩欣賞,不是文物鑒定,而是從錯錯落落的精緻中,收拾一個兩個迹近真實的生活場景,拼接一兩頁殘損掉的曆史畫面。正是這個“雜”,撐起了揚之水的學術房廈。從揚之水身上,我清楚地看到王世襄先生從“冷門”課題進入研究領域的傳統,而她比王世襄做得更專,更深入。
因為研究對象比較“冷”,比較“雜”,在論證過程中就比較“險”,為此她特别重視流傳至今或新舊出土的視覺資料的作用,這些古畫、古物是她研究的前提之一。有時候為了一幅圖專程旅行數千公裡,去博物館,去考古現場,而這一幅圖有時就決定一個課題的成敗。除了依據視覺資料進行考證,她還頻繁使用多重考證法,從古文、古詩、鄉諺、俚語等中尋找蛛絲馬迹。這些考證本身也是饒有興味的。她考證《孩兒詩》和《百子圖》時發現,“中國古典文學中,卻是最少表現這一類情感的作品”,“偌大一個古典文學王國,‘童趣’竟是稀有之物。一個成熟的文明,卻沒有為童心和用童心創作出來的童話留出足夠的空間”。于是她的考證就有了空谷足音的意義。
學者羅世平認為,揚之水的名物研究,是“具體而微的近距離觀察,接近微觀的史學方法”,“做好這件事,必定要在文獻和圖像上同時用力,這一點,既是名物學的傳統,又表現出現代學術的性格……除了方法,作者呈現的是鑒識名物的立場,或稱之為‘名物觀’”。揚之水的研究的确既有獨自摸索出來的方法,也有鮮明的個人立場,從來不随大流。
有意思的是,揚之水的讀者群大大越出了名物之辯的專業範圍,得到一般文化人的喜愛——除了有趣的題目,還與她的文筆好有很大關系。她的考據文章其實都是雅緻的散文,比如《宋代花瓶》的開篇:
瓶花的出現,早在魏晉南北朝,不過那時候多是同佛教藝術聯系在一起。鮮花插瓶真正興盛發達起來是在宋代。與此前相比,它的一大特點是日常化和大衆化。其間的差別又不僅在于規模和範圍的不同,且更在于氣象和趣味的不同。影響欣賞趨向的有一個很重要的物質因素,便是家具的變化,亦即房間陳設的以憑幾和坐席為中心而轉變為以桌椅為中心。高坐具的發展和走向成熟,精緻的雅趣是以有了安頓處。瓶花史與家具史适逢其時的碰合,使鮮花插瓶順應後者的需要而成為室内陳設的一部分,并與同時發達起來的文房清玩共同建構起房間布置的新格局……
文字明白曉暢、幹淨平實,而又有書卷氣。
設計版面時,為了不打斷文字的“氣”,同時顧及圖、文和注釋的同頁對應,我建議用一種特殊的格式:每頁文字排在訂口一側固定位置,占三分之二空間,上方三分之一位置留給圖檔,橫向接近切口的三分之一位置留給注釋,如此,打開書頁一路翻閱下去,則書頁上部成為圖檔的展覽帶,下部則是完整成塊的文字;如果有的圖檔需要放大,或者圖檔太多,需要更多空間,則甯願整頁上下全部印圖檔,文字闆塊直接跳到下一頁,讀起來還是連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