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關注“方志四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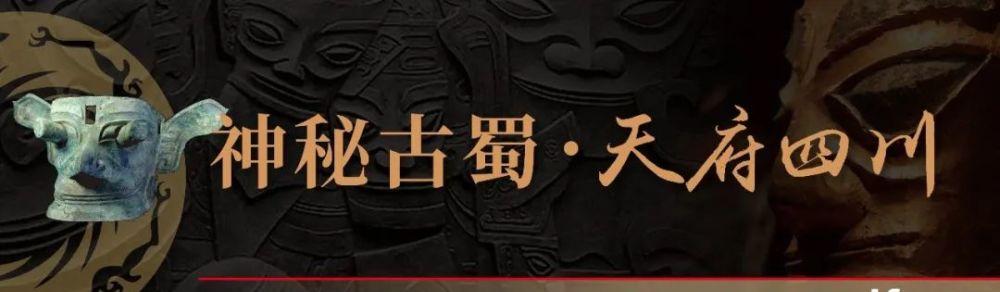
餘 嘉
他拍的神秘文物,讓人夢回古蜀國
巴蜀史志編輯部 方志通
餘嘉,45歲,四川省廣漢市人。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會員,四川省攝影家協會會員,廣漢市攝影家協會主席,《廣漢美食旅遊地理》主編,《影子之城——梁思成與1939/1941年的廣漢》總策劃執行,三星堆遺址祭祀坑新一輪考古發掘特約攝影師。7個多月以來,他在考古發掘現場拍攝8萬多張圖檔,用藝術化手法拍攝文物發掘出土過程中的衆多曆史時刻。
在拍攝之前,餘嘉就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确定了拍攝方式,要用藝術化的手法去呈現三星堆遺址發掘現場的文物。剛進入考古工作艙,餘嘉并沒有太大感觸,作為專業攝影師,在任何一種陌生的場合他都能保持鎮定且高效地完成工作。在下坑之前,餘嘉對坑下場景有過無數次設想,但當雙腳落在幾千年前的土地上時,撲面而來的震撼讓餘嘉真切地感受到坑上坑下完全是兩個世界。半掩于泥土裡的文物,雖然大部分都是殘缺的,但文物特殊的紋飾與精美的造型,讓它們在出土時重獲生命,呈現出别樣的風采。“那一刻帶有沖擊力,你甚至可以想象出3000年前恢弘壯觀的祭祀場面,盛裝出席的古蜀先民跟着國王在悲壯的音樂中完成祭祀前的禮儀。禮成之後,獻祭的官員拿着準備好的海貝、象牙、金器、玉器、青銅面具和跪坐人像等祭品,在千萬先民的注目下敲碎、砸扁,繼而扔向坑裡火焚;通神的巫師帶着面具跳完舞後,祭品被迅速掩埋……”餘嘉回憶起第一次下坑的經曆,還是覺得如夢一場。
多年來與三星堆的緣分
餘嘉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三星堆,是在1997年10月26日,那時三星堆博物館正式建成開放。“當時很熱鬧,來了很多人,裡三層外三層,密密麻麻”,餘嘉說。那時餘嘉剛工作一年,教他播音主持的老師正好受邀擔任三星堆博物館開幕式主持人,是以他也去了。“當時是懵懂的,我對三星堆沒有太多感受,隻覺得稀奇”。餘嘉坦言,年少的他對于這些具象的出土文物還沒有明顯的探索欲望。
但那次機緣,不僅讓餘嘉見證了三星堆博物館曆史的開端,還拉開了他與三星堆長達24年緣分的序幕。
2002年,餘嘉成為一名報刊記者,空餘時間他自學攝影,因拍攝有天賦,他被介紹去三星堆拍攝新聞圖。在工作間隙,餘嘉有大量時間駐足觀察三星堆文物。剛開始,文物隻是作為新聞圖的前景出現,但在一次次接觸中,他逐漸喜歡上三星堆遺址出土面具;也正是這個原因,他開始把目光聚焦在三星堆文物的拍攝上,他想要拍出文物背後的故事。餘嘉認為,文物是獨立的藝術品,攝影師與文物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攝影師扮演的角色從來不是主導者,而是發現者,他們用相機發現文物的美與價值。三星堆文物中神鳥镂空的朝聖形态、權杖上雕刻的魚箭鳥紋飾、黃金面具莊嚴肅穆對稱的結構、青銅神樹神龍盤踞的造型都給予他美的啟發,對他後續的拍攝風格産生深遠影響。
三星堆遺址5 号祭祀坑出土的黃金面具(雲何視覺 供圖)
在三星堆博物館建館10周年舉辦的《重走絲綢之路》活動中,餘嘉受邀擔任特約攝影。活動跨越川、滇兩省,終點在雲南瑞麗,沿途1300多公裡,他們觀察了十幾個地市的地理地貌、民族風情、古物古迹。那次随行,不僅讓餘嘉認識到三星堆作為古代西南文明高地,對西南地區青銅文化的輻射有多廣闊,還讓他認識摯友——三星堆博物館第一任館長肖先進。20世紀90年代,肖先進力主三星堆博物館建設,舉債2000多萬元,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館區修建,其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為三星堆付出的情懷,深深打動餘嘉。
從這件事情中,餘嘉懂得了“情懷”的力量;在這個世上,改變世界的創舉,往往都是“有情懷”的人不求回報推動的。這次活動,讓餘嘉對三星堆的感情得到升華,他的拍攝重點也從關注文物的外形特點轉向聚焦文物的人文内涵。
作為土生土長的廣漢人,餘嘉擁有天然的“故土情懷”,他把對三星堆的記錄看成一種曆史故事的重尋、一種城市文化的延續。2014年,他的作品先被《中國國家地理》采用,随後被其他各大媒體刊登。從那以後,有更多的人通過餘嘉的照片認識三星堆,并喜歡上三星堆。
漸入佳境的拍攝之旅
2019年12月到2020年5月,三星堆新發現6座祭祀坑。2020年9月,三星堆新一輪考古發掘開啟。這次發掘,對完整認識3000年前古蜀國的禮儀文化、宗教思想以及宇宙觀念都提供了重要資料。2021年初,餘嘉接到來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拍攝邀請,那時6座祭祀坑的文物已陸續露出地面,需要一位攝影人在這一重大發掘事件中記錄下出土文物藝術化的一面,餘嘉就成為受邀進入三星堆考古工作艙内拍攝出土文物的唯一一位第三方攝影師。
6座新發現的祭祀坑上,搭建了考古工作艙,餘嘉站在坑上來回踱步,不知道怎樣最好地呈現文物。“我是個完美主義者,我想要拍出最好的作品,但我不知道坑裡面能否打光、能否架三腳架,是以我有畏難情緒。”餘嘉雖然拍過三星堆文物,但那些都是已經出土并被修複好的藝術品,拍攝在安全區裡進行,與文物保持着一定距離。考古人員身着防護服在坑裡精細作業,先用鏟子、刷子清理泥土,再用各種高科技儀器進行檢測分析,“我不知道自己的走動是否會影響考古人員的工作,是以一直放不開手腳”。餘嘉回憶起2021年3月4日第一次下坑的經曆,還能感覺到當時的緊張。
3号祭祀坑坑長徐斐宏看出餘嘉的擔憂,主動告訴餘嘉坑下考古工作的重點,給他理清文物的關系層,教會他在拍攝中如何保護文物,再加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一直鼓勵他放手去拍,餘嘉下坑之後才慢慢拍出自己的特色。
剛開始,餘嘉和其他媒體的幾個記者在一起拍攝,大家都沒有經驗,都在摸索。餘嘉拿出剛開始拍攝的照片給筆者看,坦言那時隻能借助頭上的光源,拍出來的作品扁平、呆闆,沒有質感。在拍攝5号祭祀坑提取一坨揉在一起的金面具融合時,餘嘉找到點感覺,他把現場考古人員和文物結合在一起拍攝。“照片資訊含量很大,把發掘價值的重大、發現新材料的喜悅表現出來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稱贊道。在拍攝3号祭祀坑出土圓口方尊時,餘嘉已融入自己的美學理念,開始突出細節,展現出文物最有價值的一面。“方尊上的獸面紋、鳥紋飾都是三星堆文物獨有的标志,我無論怎麼拍,這件作品都帶有三星堆的印記”,談起這些經曆他總是顯得意猶未盡。
三星堆遺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圓口方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供圖,餘嘉 攝)
借助考古站文物掃描的燈光,拍攝時注重明暗與虛實的對比,餘嘉的拍攝漸入佳境,他拍出了考古界“氛圍感”。一張由3号祭祀坑出土的方口方尊、青銅面具、象牙組合而成的照片,餘嘉拍出了瞬間震撼之美。方口方尊垂直于坑面,青銅面具側頭靠着方口方尊,它們左右各占照片一半的面積,明暗對比間,産生一種立體美。青銅面具的左眼隐藏在陰影下、右眼被泥土遮擋,凸出的眼球若隐若現,拍攝時就凸顯其面部輪廓的流暢。這張照片雖然由方口方尊、青銅面具、象牙組合而成,但觀賞者的目光隻會停留在青銅面具上,即使看不清全部面容,它也彰顯出類似雕塑《沉思者》的氣質,安靜而自洽。這就是跨越時空與文物對話的魅力,在拍出一些類似風格的作品後,餘嘉也确定了拍攝方向——三星堆的神秘。
三星堆遺址3 号祭祀坑中的方口方尊與青銅面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供圖,餘嘉 攝)
在拍攝中,餘嘉也曾經曆心驚膽戰的時刻。拍攝3号祭祀坑的青銅大面具出坑之前,大面具已露出地面3個多月,然而面具上壓着象牙等其他文物,究竟什麼時候能提取,并沒有确切時間。2021年6月23日,餘嘉接到3号祭祀坑坑長徐斐宏電話,告知他大面具即将提取,那時的餘嘉還在離三星堆10公裡外的地方辦事。得知這一消息,他十分緊張,他知道攝影是遺憾的藝術,但他還是害怕錯過這次難得的機會。為不留遺憾,取了相機的他立刻驅車前往三星堆博物館,一路上除了認路,他的腦子裡全是拍攝所需的鏡頭和光圈。一下車,他就立刻穿上防護服進入考古工作艙,所幸趕上了下午3點半的提取拍攝。
2021年6月23日,三星堆遺址3号祭祀坑青銅大面具提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供圖,餘嘉 攝)
一切準備就緒,餘嘉懷着激動的心情躺在青銅大面具旁,臉朝坑下的青銅大面具在升降機的助力下緩緩地露出它的尊容。這時,考古人員擔心青銅大面具若不慎掉落可能會砸到餘嘉。“我相信你們的技術,如果砸到我,那也是我的榮幸,那也值了”,餘嘉打趣地說。“30厘米、50厘米、1米、1.5米……”餘嘉在心裡默默地估計着青銅大面具出坑的高度。就在青銅大面具被提到普通人的身高時,文保人員任俊峰正好擡眼看向青銅大面具正臉,他在觀察大面具上的文物是否會掉下。“咔嚓”一聲,餘嘉把這“跨越3000多年的凝望”定格,就有了這張充滿“未來的曆史感”的照片。提取工作結束後,餘嘉如釋重負,内心卻難掩激動。“要是錯過這個拍攝,我會後悔一輩子”,餘嘉說,他将這組照片視作自己攝影經曆中非常重要的作品。這張照片也因3—8号祭祀坑的發掘出現在各大媒體的新聞裡。
跨越時空的藝術創作
攝影不難,但要拍出光影物的瞬間之美卻最難,這需要天時地
攝影不難,但要拍出光影物的瞬間之美卻最難,這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這不是電影有再來一次的機會;也不是紀錄片,記錄最真實的那一刻;這種美也和自然界裡的景物不同,沒有年年歲歲花相似的重複。想要拍好,不僅需要攝影師與現場考古人員的默契配合,更需要雙方對彼此工作的尊重了解。
攝影不同于電影、音樂、繪畫、書法等其他藝術創作,這些創作基于藝術家自身的經曆,作品帶有其獨特的個性和标簽。而拍攝三星堆文物,靠的全是攝影師對光影的掌控力以及敏銳的觀察力。怎樣還原當時的場景,怎樣給大衆留下想象的空間,怎樣不過多地加入主觀想法,都是他在創作時需要思考的問題。
談到藝術化地拍攝文物,餘嘉有自己的想法。博物館展覽文物的特點,都是一件一件陳列出來,放在玻璃櫃裡;而三星堆文物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出土文物,有可考證的文獻,在欣賞時有代入感。大衆不了解三星堆展陳文物的用途,他們建構的想象是以現有世界作為參考,這會存在文化解讀上的困難,是以他給這次拍攝定位為面向公衆考古,隻發表文物在坑裡的故事,展現與古人零距離接觸的場景。
無論是藝術創作還是藝術革新,都基于一定的時代背景。拍攝文物不是先例,但藝術化地拍攝沒有文獻記載的文物發掘現場,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屬罕見。餘嘉做出的藝術革新,成為跨學科藝術融合的先鋒。
“在坑裡拍攝最接近原始的場景,把文物放在它們特有的文化背景下,有參考物,觀衆解讀時會更加具象;這樣的作品,能最大程度地幫助沒有三星堆知識或缺乏藝術審美的人發現它的美,這也是一個提升大衆審美的機會。此外,攝影可以重構文化語境,藝術化的表達給人充分想象的空間,友善人們二次創作。由于三星堆特殊的斷層文化形态,照片承載着更加重要的文化功能,當曆史無法重制時,我們還能借助照片想象一個時代的文明與繁榮”,餘嘉向記者簡單談到藝術化地拍攝三星堆文物帶來的作用。
餘嘉的作品讓我們拓寬對美的認知,了解美的多元性。三星堆文物,地上是美、地下也是美;完整是美、殘缺也是美;存在是美、消失也是美;事實是美、幻想也是美;曆史是美、當下也是美。埋葬在泥土中的文物或許可以重見天日,但那段高度繁榮的古國文明卻無法再現。雖然三星堆文物鑄造技藝已遺失、文化已落寞、時代已更疊,但藝術創新能打破這一切,于古老塵埃中開出一朵文明絢麗之花,燦爛下一個3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