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時間是大有作用的,少一天都不行。但是,時間又不是平均的,足夠多的時間之後,拐點會猝然出現。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漫長的生長史。即使是一個短篇小說,往往也在心裡放了很久,貌似遺忘了,貌似沒有出路,某一天意外想起來,突然可以寫下去了。起先我以為自己是一個被惰性支配的人,相信自己有嚴重的拖延症,後來意識到,這可能是一部作品産生的正确方式:由時間篩選,被時間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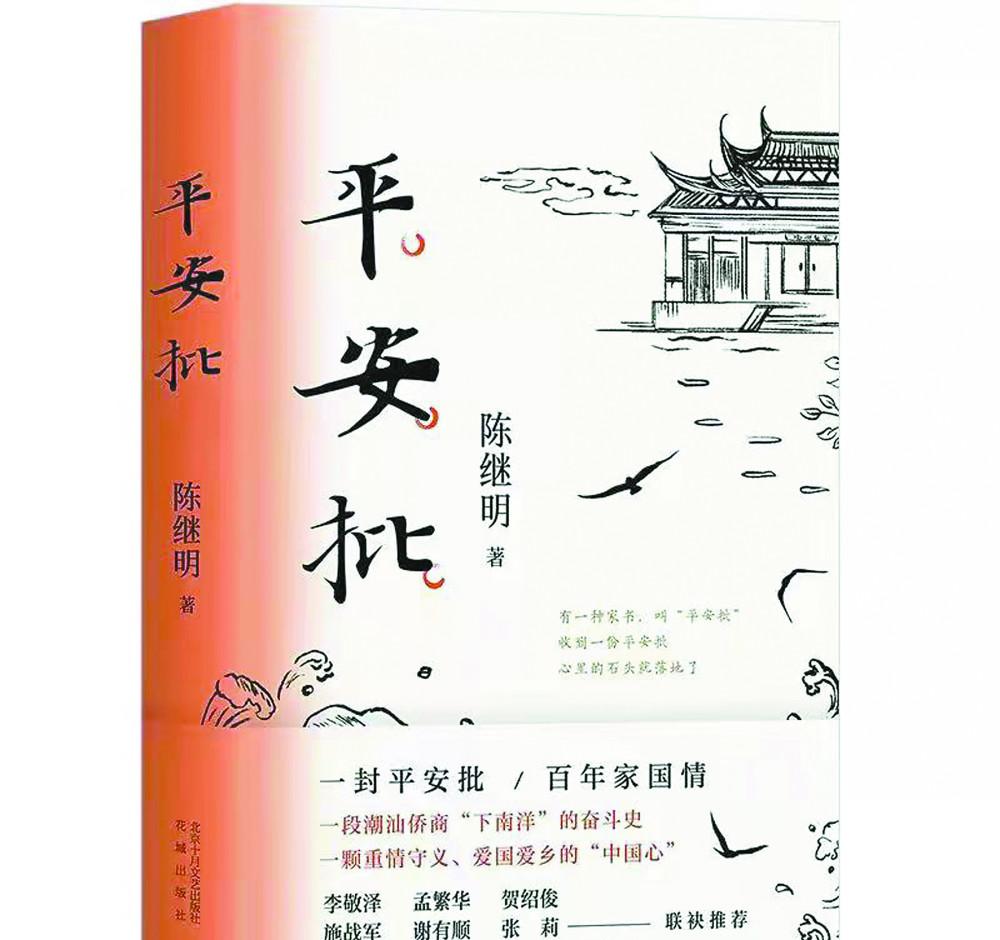
《平安批》 陳繼明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我老家甘肅天水那一帶自古有“走西口”的習慣,目的地是“口外”。口外即新疆。兩者相距數千裡,中間要穿越大沙漠、大戈壁,很多地段沒有人煙和水草,更兼風沙,一半人往往死在路上。終于到了那邊之後,一部分人再也不敢指望有生之年原路傳回,便在遠方重建一個故鄉,把故鄉的山、河、溝、路的名字都帶過去。一小部分人則相反,先是堅定不移的離開,再是更加堅定不移的傳回。當然,又有一些人死在了回來的路上。某人如果是從“口外”回來的,不用聽他多說話,一看就知道是從遠路上回來的,高冷的眼風裡又有曠達和柔情,說話偶爾浮誇,偶爾謙卑。一個天天見面的人突然消失了,原來是“走”了。走,這個字有很确定的含意,一聽就知道,走口外了,可能永遠見不着了。郵差送來的信和彙款單半數來自新疆。人們一直傳說,大地主陳子芬并沒有死,而是金蟬脫殼,走口外了,有人在烏魯木齊的大街上親眼看見過。陳子芬和我家同出一脈。我們的祖先是兩兄弟,分家後依各自住所的方位,分别被稱作前頭、後頭。前頭漸漸敗落,後頭日趨興旺。後頭出過不少人物,有北大畢業生,有省議員,有人死在楊虎城刀下,有一對父子同為縣長,兒子的縣長是花錢買來的,有人當過吉鴻昌秘書,有人參加過戊戌變法。後者名叫陳協華,是甘肅署名響應變法的六舉人中的一個。總之,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想象裡,“口外”這個詞雲蒸霞蔚,天高地廣,是一個我一出生就切實存在的“外部世界”。如果說,我幼年的想象中有兩個外部世界,一個名叫“北京”,另一個名叫“新疆”。新疆與我更痛癢相關。開始學習寫作後,我意識到,對我來說,新疆在我的文學世界,是一本懸在想象中的書。不知從哪天開始,我很想把這本書從空中摘下來,寫在稿紙上,卻一直都未能動筆。有一次偶然看到一個動物世界的紀錄片,知道有些動物也會長途跋涉,曆經千難萬險,執意回歸“故土”。動物們終于踏上故土後,神态立即變了,顯得又舒坦又安心,仿佛重拾丢失的尊嚴。俗話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土窩。大概說的正是尊嚴。自家土窩裡至少有尊嚴。隻是,所謂“故土難離”,顯然并非人所特有,不過是一種生物本能罷了。這個念頭不知不覺消解了我的寫作欲望。之後很多年我不再打算把那本懸在空中的書摘下來。
我四十歲前後,國家有了移民搬遷政策,把貧困地區的農民轉移到水草豐茂的地方。政府已經在新地方蓋好了房子,還有一定經濟補助,仍然難以打動他們,很多人态度堅決,拒絕離開。在外人看來,他們不可理喻,愚不可及,但是,當事人有他們的理由,其中一些說得出的理由是,無法把山山水水和先人遺骨一同帶走。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往往無力置評。如果是我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不會欣然前往。
這令我重新想起那本書,我想,人和故土的複雜關系裡可能暗藏着幽深的人性秘密,不能簡單給他們戴上“低等”“落後”這樣的帽子。另外,文學和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可能也有本質差別,兩者在某個關鍵點上會分道揚镳,南轅北轍,在社會學上落後的東西,在文學上則不一定。比如人對田園生活的向往,對農業文明的依戀,人的故土難離和落葉歸根情結,如果得到文學表達,不能簡單稱之為過時和守舊。文學視角下的人性,是完整的全部的人性,兩者一刻也不能分離。文學最根本的興趣是人性。人性是不能分高下與否的。美國的外來人口和美國的原住民誰更接近文學?開飛機的人和趕驢車的人誰更接近文學?總統和乞丐誰接近文學?這些問題不好回答,也好回答。
又過了幾年,我任教于北方民族大學。有位林濤教授研究東幹文學。東幹人,清代的若幹時期,由于各種原因,流落至今天中亞諸國的陝西人甘肅人新疆人,天長日久,在另外一個國家漸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一百多年後,他們依然說陝西話甘肅話,完整保留了家鄉的風土民情,喜食面食,仍然用筷子吃飯,食物也保留了原來的名稱,如蓮花白、黃瓜、涼粉、鹵面、面片兒、馍馍等。東幹,其中一種解釋是,陝西話“東岸子”的轉音。東岸子,即東邊,黃河東岸。當有人問他們是哪裡人,他們就指着遙遠的東方說:“我們是東岸子人。”東岸的轉音即東幹。前蘇聯進行民族識别時把這部分人稱作“東幹族”。東幹人始終對外強調:“我們的根在中國。”他們也常常自稱“中原人”。在中國,漸漸有了“東幹學”,很多學者研究東幹的曆史、文化、語言、文學。林教授邀我跟随他搞東幹文學研究,我對研究興趣并不大,但是以接觸了很多東幹學資料。
可以想象,在異國他鄉,出于自我維護和家國難忘的天性,東幹人是如何團結一緻,艱苦生存,如何把故土記憶的消亡視作恥辱。幾代之後,他們中總有一些老人,還在談論故國和家鄉的人和事,年輕人、新出生的人,就還知道自己來自中國。對我來說,關于東幹人的全部想象,都是文學,都是一本書的一部分。
又幾年我調往廣東珠海,曾在珠海一個朋友的茶館裡看到了幾十封“僑批”,全是從新加坡寄回來的,寄信人是收藏者的爺爺,收信人是奶奶。當時并不知道“僑批”這個說法。收藏者本人也稱作“信”,而不是批、番批或僑批。我翻了翻,意識到這是口外故事和東幹故事的另一個版本。因為隔着海,可能更典型。
拐點出現在2019年10月,受廣東省委宣傳部和廣東省作家協會委派,我前往汕頭市委宣傳部挂任副部長一年,目的正是寫一部關于僑批的小說。此前關于“走西口”,關于東幹,關于我自己家族的所有遲疑所有準備,都變成了《平安批》的重要資源。經過短短幾個月的廣泛閱讀和艱苦醞釀,我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态度,硬着頭皮提前寫了起來。我告訴自己,不用先把自己變成潮汕通再寫潮汕。
貳
寫作之前,我對自己有幾個要求:
讓語言簡樸、平和、從容,語言裡至少要有兩種氣味,一是漢字和漢語的經典氣味,漢字和漢語裡,有悠久寬廣的中華文化傳統,那麼,這也意味着我要主動迎接一個挑戰,我能否把文化傳統自然地帶進去?能否寫出中華文明的根本特征?二是從潮汕大地上和文獻裡嗅到的那種地方氣味和民間氣息,就像從米缸裡聞到了産自潮汕大地上的好米的氣味。寫作的整個過程裡,我都在試圖抓住上述兩種氣味。
寫一部總體上平實飽滿、有氣質有意蘊的小說。換句話說,盡可能丢掉以往的“習氣”。也正是準備寫《平安批》的那個階段,我意識到作家可能有一種共有的“習氣”。作家們一提筆就習慣于回到“幽深的自我”,習慣于表達“自由”“虛無”“孤獨”“漂泊感”“無根感”等東西,這些東西時髦了很長時間,但它們有可能早就成為文學時尚和文學修辭了。我想,這一次我不要裝高深,甚至不要雄心壯志,隻要平實。平實中的委婉、明麗、深邃,是需要大功夫的,往往也是難以為外人道的。
這部小說發生在漫長的時間和開闊的空間裡,但是,我不打算寫太長,不打算寫成全景式小說,是以結構很重要。我很長時間都找不到結構,後來偶然看見一種工業結構——集散式結構。它的主要特點是,有一個主機和若幹分機,分機可能在遠離主機的地方,用一根線和主機相聯系。于是,我就把它借用過來——這部小說的主機是僑批或是開批局的鄭夢梅,分機是鄭夢梅的家族事務和個人境況,鄭夢梅家裡的女人們,抗戰時期的鄭夢梅父子,老年的鄭夢梅,被董姑娘翻譯到美國再回譯為中文的“依芸家的番批”,等等。我是第一次嘗試用這種結構寫作。結構在小說裡不是一個純物質的僵死的東西,它也在說話。它甚至要說更多的話,代替作家說話。現代小說比傳統小說更需要結構。在傳統小說裡,主要是作家在說話。在現代小說裡結構中不同的結構體是對話關系,或者說是互文關系。任何一個具體的段落都不足為憑,不能單獨成為解讀小說的依據。
回到常識,信任人物,寫好人物。除了寫好男人,更要寫好女人。在潮汕深入生活的幾個月裡,我再三意識到,潮汕女性在相當程度上被忽略或歪曲了。人們以習慣語氣贊美潮汕女性的時候,我覺得任何贊美都是輕浮的。當人們批評她們時,我同樣不能接受。于是,我想把她們寫進書裡,也想看看我為什麼有如此複雜難言的感受。我也堅信,通過女人看一個世界的文明本質,是一個可信賴的角度。在這部小說裡,主人公是男人,表面上也主要寫男人,但在他們背後,他們的奶奶、母親、妻子、女兒們不可或缺,她們甚至是這部小說的秘密心髒。僑批的一端是遠在海外的男人,另一端是家裡的女人,身為持家和等待的一方,她們長期被忽略,長期被簡單化。作為一個群體,她們在全世界絕無僅有,她們身上有顯而易見的文化意義。我的信心和決心促成了書中的一批女性形象。老祖、望枝、乃铿、鄭黃,鄭白這些人物不知不覺從筆下流出,自我成長。
跳出潮汕看潮汕,把潮汕故事當中國故事去寫,甚至當人類故事去寫。遷徙、流落、求生、逃亡、土地、回歸、文化認同,這些命題事實上的确不是中國人特有的,但在中國人身上表現得的确更強烈,更極端,更有意味。梭羅說:“邊緣不是世界結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闡明自己的地方。”這句話始終是我的座右銘。
我還想,這部書要與時代本身形成對話。這是一部以特定階段的曆史為書寫對象的小說,但它是目前這個時代完成的,它和這個時代應該有一種深刻的對話關系。書中的兩個外國人——喬治、董姑娘,是在這種觀念下出現的。
叁
我向來反對小說表達單一主題。我以為,在小說沒有結束之前,主題尚不存在。小說家用小說尋找和探求主題。直到全書即将完成時,我才發現,我找到了主題,不過,我仍然說不清它。小說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令人着迷和好奇。竭盡全力讓一部小說令人着迷和好奇,永遠是一個小說家的艱巨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