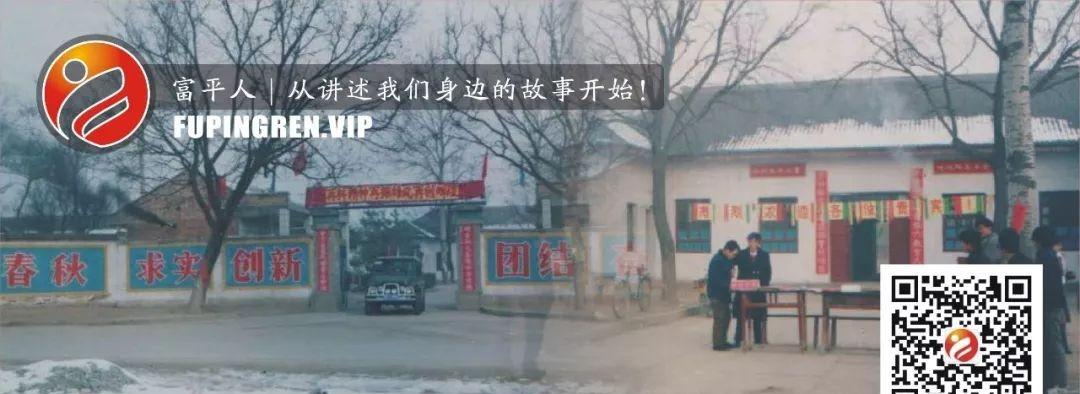
我也想起了我上學時的高中時代
溫/馬啟光
前幾天,伴随着兩位在野外工作和生活40年的高中老人回到母校曹村中學,大家感動不已。是的,以前的母校那"工作"字禮堂,那一排磚砌的學校建築也沒有,隻有門到兩個與母校同齡的鑽石天楊樹依然,比原來的更有活力,高大,高大。大家擁抱着楊樹,擁抱着,親吻着,接着,一滴一滴地流着眼淚。說實話,我們面前的樓宇,一流的教學設施,美麗的校園,沒有什麼能取代我們中學的記憶和那麼多好老師,好學生懷念。
最大的願望是吃飽
我在草村中學度過了我的中學時光。這是一所完整的農村中學,位于金山山脈下,建于20世紀50年代。雖然它隻是一排磚砌的學校建築,土操場,用鵝卵石壓碎的磚塊鋪成的道路,但它是該地區最高的學校,也是她夢寐以求的鄉村聖地。1973年1月,我被馬家坡國小錄取到曹村中學。那時,國中還是"二二制",我的國中是七四,高中是七六。作為一所農村中學,學生基本上都是農家小孩,家庭經濟條件差距不大,貧富不是很明顯,學生之間和諧相處,即使有沖突糾紛也可以自己解決,打架很少,麻煩就是錯的。
但畢竟差距還是客觀的,這種差異首先要從學生身上看出來的差異。學校一日有兩頓飯。當時,學校有一個飯爐。爐子上的學生正在大鍋裡煮玉米繭,沒有蔬菜。爐子上的另一個功能是給全校學生熱,每個班級一個四英尺見方的籠子。每天早上鍛煉後和下午自學後,由兩名值班學生到班上的學生聚集起來,擡到學生爐子上。在兩餐之前,把熱騰騰的飯菜帶回來。籠子是多種多樣的,多樣的,白色,黑色,黃色,綠色,綠色和紅色;除了龍網,還有尼龍網口袋玉米面、紅棗、紅棗等。女孩的蟋蟀通常裝滿網袋,而男孩則使用兩三個帶有筷子繩的鼻涕蟲。很多同學心裡明白,就是這樣品質的雜交,也讓家長們也做了很多苦。
用餐時間是最熱鬧的。先是男生先發制人地從籠子裡出來,女生不容易擠進去找自己的,有錯誤的換貨要求,有别人自己分食,吵吵鬧鬧,前一會兒就散開了。這時一群麻雀哄上來,蛞蝓,抓住籠子裡的殘渣,一點也不怕人。
為了得到贻貝,一些學生買了幾美分一碗煮熟的玉米粥,噴上火。沒有做粥的是一個裝着開水的大瓷碗。兩三個人聚在一起,打開罐裝的白蘿蔔、胡蘿蔔泡菜,或者蘿蔔英式、紅棗葉泡菜,如果有人能吃到噴油的辣肚泡菜,實在是太好吃了。還有一些沒有蔬菜,從胸腔裡拿出一小瓶裝滿辣椒鹽面條,撕下一張作業紙倒上來,吃一口,再喝一口開水,還好好津樂道。後來讀了陸耀的《平凡的世界》,孫少平的學生時代不吃餓,真的是我們這個時代學生的真實生活。不同的是,我班上有一個同學因為長期吃高粱面,經常造成嚴重的便秘,有幾次都拉不下來哭,是同學幫他脫出來的事情。
當時開展工程和農業活動,學校組織學生在繁忙的農業到周邊生産隊伍中拉糞、采棉、包菖、挖紅棗等。每當這個時候,制作組長往往會給學生一點補償,那就是一頓飽餐。它隻是蒸蕃薯或煮熟的玉米棒,這很好。有一次因為校長姬烈賢抄襲了實物資料,誤回家取了,姬老師給我買了一個4個兩白面條,放在老師的爐子上,大肚皮泡菜,太好吃了。我想每天吃兩次小麥面條。
追逐更溫暖
學生分為住宿生和普通學生。普通學生是住在家裡或學校周圍并且有親和力投票的學生,其他人是生活和留在學校的學生。
學校每班有男生、女生宿舍,一班一男生宿舍,少女生或兩班一宿舍。宿舍是南北兩排實心蚯蚓,後來換成了床闆。每個人的寬度為1.5英尺,一根一根地分成一根。一個不同顔色形狀的布袋挂在土牆上。床單種類繁多,色彩缤紛。宿舍有長房,每天安排日常打掃,督促學生鋪床,我們住得和睦。
住宿學生最喜歡的當然是夏天。我們這些守時自律的男生,經班主任特别準許,可以睡在課桌上,前後窗開着,既通風又涼快,沒有蚊蟲叮咬,可以睡個好覺。但醒來後鈴聲響起後一定要迅速起床擺好桌凳,否則會影響到學生早早閱讀。
當然,夏天睡在宿舍裡的學生就沒那麼舒服了。人們太熱而無法變熱,而土堆是跳蚤。尤其是晚上自學後最進階的宿舍學生,應該是高底褲,很快,黑芝麻粒大小的跳蚤就會沿着腿肚争先恐後地爬起來。如果抓捕不及時,隻需跑到外面的空地上,雙手放在一邊硬擦拭下來,同時像兔子一樣跳開。否則,可憎的跳蚤就可以把人帶到飛蛾下,給你一個"紅包"。當然,學校每周安排有人噴灑宿舍,殺死跳蚤。
冬天是最糟糕的。學生必須專注于宿舍。為了防寒,學校會在冬天前買一定數量的生産團隊在草地上,感覺溫暖多了。家庭條件較好,用溫熱水壺,溫水袋,一般學生用葡萄糖瓶裝滿油炸水。晚上自學後,我們一邊坐在被子裡邊吃邊吃冷聊天,更多的是睡覺熱身被子。班上有兩位活動人士,陸姓和盧姓,他們利用這個間隙,表演了一個引體向上的胡,吹奏了長笛。有的學生沒有鑷子,或者被子太薄,經常在兩個自由組合上,一條被子一起蓋住一條被子,通過腿睡覺。有的把被子上綁着一條長長的圍巾,做成睡袋狀的鑽頭。其他人戴着帽子,襪子,被子睡覺,有些人根本不脫下棉褲。總之,我們頭腦風暴,創新思維,防寒的方法已經浮現在腦海中。但很煩人的是造成虱子學生太多,虱子喜歡在被子之間做一系列的小動作,經常有麻煩的人睡不好覺。
不知道為什麼,在這樣一個艱難的環境下,幾乎聽不到怨恨的聲音,同學們互相鼓勵,互相幫助,快樂!這種苦澀與紅軍在草地上攀登雪山相比如何?
如果有自行車就好了
當時,學校規定,寄宿學生在10英裡3天内回家一次,10英裡外每周一次。學生有一對好腳踏闆,遠近兩條腿都用兩條腿來衡量,學生開玩笑地開的是"11号車"。我離家隻有10英裡,星期三我們回家半天後,我用印有"紅軍不怕遠征困難"的黃色袋子一次回來十二、三蛞蝓,當天就回到學校。大家都期待着回家的那一天,媽媽熱騰騰的一餐的香噴自然誘惑着我們,有一個秘密,那就是一路上可以指點。我們的家鄉曹村是著名的柿子鎮,沿山坡地區,到處都是大柿子樹。秋紅甜甜丹柿是我們的最愛,解體卻充滿了饑餓感。空采收隊的嫩度,玉米地裡的甜棒(玉米的空杆),采摘場裡的豌豆角,刨地裡的紅棗,等等。總之,隻要是果子肚皮和救濟工作,即使冒一些險,群體也願意做。在我的印象中,制作團隊的管家似乎從不把學生太當回事。
我們班上還有幾名學生在白廟山,最遠的是在瑤州區附近的銅河小原市,杜家,要走40多英裡的山路。我周六回家吃早餐,冬天天黑的時候我不能回家。星期天早上離開回到學校,肩上背着兩個大布袋前後,翻過群山,快黑的時候趕到學校。想想現在的中學生,一隻天空手走30英裡的平路,可能走不下去。此外,這些學生心中有理想,腳下有力量。在白廟山中還有一個叫城路的地方,有一位校友天亮後,每次去上學、上學、爬月洞山,他不走羊腸山路,偏從最陡峭的地方爬山,平時練上非凡的登山技藝,被國家登山隊選中後, 成為著名的登山家和登山隊長。老師們也經常用這個典型的例子來教育我們。
但在家鄉這半山半平的地方,當時理想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學校的老師基本上都有自行車,這在農村是罕見的。如果有人有一隻璀璨的飛鴿,永久的,鳳凰,哪怕是一輛紅旗自行車,也相當于現在你開奔馳、寶馬一般的樣子,拉風。我們班林前坡有一個老家夥叫黨高旺,瘦高,半妖。他主宰着一輛舊自行車。老到什麼程度,有一個光滑的嘴:前面有夾子,後面皮帶沒有花,騎得快脫鍊條,騎着慢慢磨溝蛋。就是這樣一輛破車,在他的腋下,卻像一輛好寶馬聽着叫聲,上坡不下車,下坡不抓把手,平平路一陣風,窩讓我走。在上學的路上,那是一幅風景。那時候,我總是幻想着,有錢的時候,先買一輛自行車。
什麼時候可以穿棉質外套?
人們常說:過去的歲月一直很好。不知何故,我總是覺得學生時代的冬天是最艱難的。那時候,冬天似乎特别寒冷,北風斬臉,雪蓋屋,屋檐、麥子上的冰棍經常長着長着挂着,小夥伴呼出一口熱氣,頭發,劉海會立刻打結一層薄薄的白冰,冷肆虐,主宰着北方的土地。
學生的冬裝簡單富足,種類繁多。男孩的主要顔色是黑色和藍色,可能有黃色。棉質褲子是家織的土布,棉絮是多年的老式,有些驚慌失措的家庭連舊的套都不夠,棉質衣服薄,保暖性能較差。裡面大部分學生不穿襯衫,不穿無蓋衣服,空心穿着棉質衣服,寒風會肆無忌憚地鑽進去,凍僵的人發抖。還好當時棉質褲子都是大褲子,前後不管穿什麼,褲子腰部高度和胸圍,再放棉絮兩件開襟衫,用大腰帶裹在幾圈外面,箍緊,冷風不會從中間沖破,也堵住了寒風的通道。如果您沒有大腰帶,請使用長圍巾。後來大人,才知道我們家鄉有個習俗,娶女人的時候一定要有一條9英尺長的腰帶,意思是長長,不知道它的用途多幾裡!男孩一般戴帽子,得戴棉帽,得戴機車帽,還有不戴長圍巾的帽子,頭上和耳朵上繞着一個袋子繞着脖子再圍一圈打結,有要求媽媽暫時把一頂帽子換成棉帽。在腳下,你通常會穿巢(棉鞋)或線襪,或由家居面料制成的布襪。
女孩們穿得更仔細一些。棉絮一般是洋薊表面,或紅或綠或花,不花棉絮外面也會有遮蓋物,棉袖。棉質褲子的顔色比較随意,但一般都會有頭巾在棉窩的腳上。
由于教室沒有爐子,是以幹燥而寒冷。等老師上課前會唱歌,我們常常凍得麻木的腳不會幫助他們,不僅随着節拍,不僅響亮,還使教室塵土飛揚,咳嗽。此時受到老師的批評是不可避免的,但學生往往帶着笑聲真誠地接受批評。
除了課前"腳部運動"加熱外,還有課間打乒乓球、踢鑷子、跳繩、鬥雞加熱等。男生更熱衷于"擁擠的熱巢取暖",即一個人側身靠近牆磚柱,其他學生一個個向一個方向擠,擠出隊列跑到隊伍盡頭向前擠,來回循環,嘻哈、熱鬧,感覺不暖和。這項運動似乎隻是在最初幾天才開始玩,然後随着年齡的增長而沒有。
但是冷,冷,真的很冷,真的很冷。學生在凍瘡的臉上,凍傷耳朵,凍傷手,凍傷腳比比皆是。即便如此,也很少有請假。唉,村莊是真實的東西。
那醒目的黃色棉布,是一個很不錯的階級路的一個男孩,父親是一個皈依的士兵,給他一件軍裝,白天穿,晚上蓋上蓋子,看起來很結實。我很羨慕,當我們還穿一件棉質外套時。
一個好老師就是一個好老師
在這樣一個苦澀的環境中,熱愛校園生活的主要原因是,我們遇到了一群熱愛學生的好老師。這些高素質的學生畢業于名校,每所學校都技藝精湛,不僅無私地傳授給我們知識,更是我們人生的導師。老師的跟進和教導深深地影響了我學生的時間,貫穿了我的一生。
教學作風嚴謹,愛學生 劉旺平老師,幽默風趣,一句好話的王宇老師,知識淵博,出口成一章支援燕老師,舉止優雅,教學技巧高,被譽為"張化學"的張天琦老師,班上隻有幾支彩色粉筆就能把各國、各省、地區的地圖掀起波瀾, 人文地理知識口上的王傳進老師,實體課畫聲畫彩色,一位圓畫姬铉老師,一套黑色西裝,鼻框金眼鏡,以蘇聯專家為進階翻譯的高伯沖老師,一位毛茸茸的,會唱歌跳舞的老師吳鳳英,遊戲老虎,運動員陳紅秀老師, 吃苦耐勞,血脈淋漓的吳成茂老師,等等。40多年過去了,這些優秀的老師大多已經去世了,但他們的笑容,班級的形象,經常浮現在我的夢中,活在學生的心中。即使在那批批"有尊嚴的教師",鼓吹"白卷英雄""反潮流鬥士"的特殊時期,這些教師依然不忘使命和責任,認真做到每一堂課都做到好。我的進階班主任吳成茂悄悄地鼓勵我們這些愛學的學生:"國家建設還需要高端人才啊。"這句話還在我耳邊,已經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
當然,提到老師是繞開張永新校長的。1973年1月在草村中學就職前,曾在土村中學、廬山中學任校長數年。當時,30多歲的張校長,灑了一身,齊宇玄昂,走到胸前,說話的聲音像洪忠,把手放在雙腳之間會表現出英俊的作風,全校上百名學生都不是不無禮,也不怕不怕不學。張校長在曹村中學工作了12年,管理學校,在一所偏遠的農村中學中組織良好,教育品質不斷攀升,跻身南方地區名校行列。他自己的許多轶事在茶後都很受歡迎。在草村中學學習的四年裡,我想到了兩件事:一是學校沒有開除一個學生;二是學校沒有開除一個學生。
1977年,國家恢複了聯考制度,社會各界歡呼雀躍。那一年,曹村中學校友就考了一個數字。和七、三年級的學生白騰石一樣,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後來成為中國航空工業寶成航空儀表廠的進階工程師和研究員,榮獲中國航空工業突出貢獻獎。七四級學生陳繼陽,冷門學生,從西安某大學畢業後被派往瑞士學習,獲得博士學位,成為國内同行業頂尖人才。七五年級學生趙鵬敏,出身貧寒,愛學,曾被軍校選拔為戰鬥機飛行員,現為空軍副參謀長,少将軍銜。郭豔林,七六年級學生,從西安某大學畢業後,在德國留學,現為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博士生導師。我這七六班同學,從小到大喪母,窮困潦倒的家庭,愛學習,當一些學生絞盡腦汁寫批判性草稿時,他正在研究分析幾何。
上面的名單隻是我認識的幾位高中生校友,他們沒有辜負老師的教育和教育訓練,跳出了農場的大門,成就了事業。後來,母校的教學品質一路高歌猛進,2014年第二本書上線了576本,先後進入清華大學也有幾所,學校被評為陝西省标準化高中、閩南市模範高中,成為全市農村高中的一顆閃亮之星。
四十年來,子彈指揮舞着。回憶高中時代,甘苦鹹味,豐富的生活經曆;
我懷念高中生活,忘不了曾經背着、裝書、印在"紅軍不怕遠征難"的紅色字母黃色袋子上。
2019.12.16
簡介:阜平縣曹村馬啟光,老教育家,喜歡和學生打交道和言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