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論或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強調西方文化優越性的觀念,這種觀念本來是西方人的曆史錯覺。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優勢地位,進一步強化了西方人的這種錯覺。目前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已成為十分迫切的任務,超越西方中心主義不是簡單地推翻現有的學科基礎,也不是回歸傳統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孫曉春認為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的唯一可靠的理由隻能是現代化。當代中國處于現代化的曆史程序中,超越西方中心主義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系統工程,應該有現代的眼光和國際的視野,在改變以往食洋不化狀況的同時,避免盲目複古、崇古傾向,加強基礎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同時進一步加強對西方思想文化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這是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必由之路。
重要觀點:
1
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要有現代的眼光和國際的視野。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學術體系,避免陷入自話自說的困局,使中國特色話語能夠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所了解和接受,使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成為整個世界能夠了解的知識,才是我們努力的目标。
2
在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過程中,在改變以往食洋不化的狀況的同時,也應該避免盲目複古、崇古的傾向。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需要現時代的人們憑借自己的理性去認識和解決,建構當代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隻能依賴當代中國人的理性而不是曆史傳統。
3
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基礎理論研究是重中之重。應用研究固然重要,理論研究卻更為重要,因為應用研究的前提是理論,在應用研究中應用的是理論而不是其他。離開了基礎理論研究,應用研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4
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應該進一步加強對西方思想文化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
更多精彩觀點
随着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推進,在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之時,“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成為擺在我們面前十分迫切的任務。于是,超越西方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主義便成為學界讨論的話題。讨論中,在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這一點上,人們已經達成了基本共識。但是,怎樣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本文試圖就以下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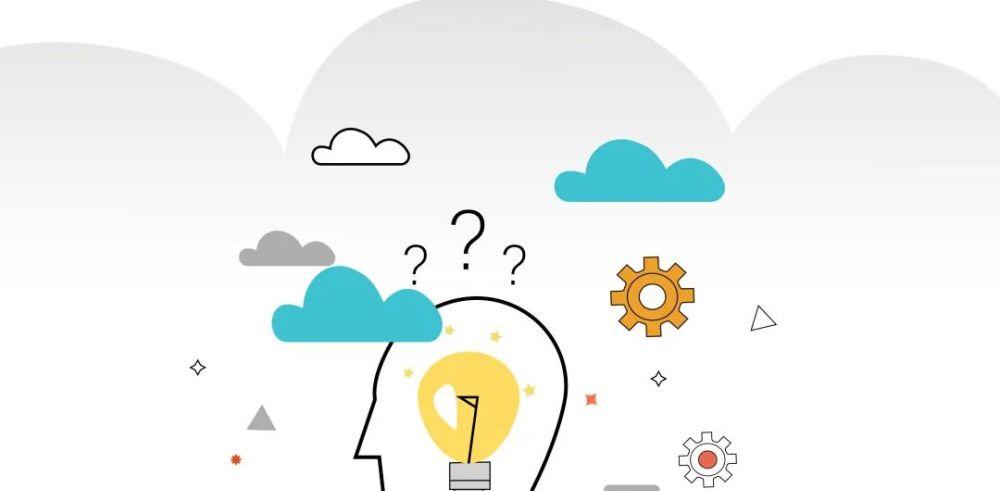
西方中心主義:一種曆史的錯覺
西方中心論或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強調西方文化優越性的觀念,在西方人那裡,這一詞語表達的是一種自我優越感,這種優越感是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内形成的。是以,認識西方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主義,首先要有曆史的眼光。
現代考古學與曆史學的研究成果表明,人類文明是多元的。文明的多元特征是在人類文明最初發生的那一刻就決定下來的。對于生活在現時代的我們來說,人類文明産生之初的許多細節以及人們的生活狀況,我們無法得知詳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人類文明是在許多地方發生的,在亞洲、非洲、歐洲這幾片大陸上都能找到遠古文明的痕迹。文明源頭的多元性,決定了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一些民族在文化上的自我優越意識,也是在文明多元的環境下形成的。
許多民族都曾有過文化上的自我優越感,這與一定曆史時期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有關。在遠古時代,文明是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下各自發展的,這在客觀上導緻了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叙述的就是這個事實。
封閉的地理環境與文化的差異,在客觀上影響了以往時代的人們對于人的了解。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也是生活在不同曆史環境下的人們了解人的過程,這一過程最先是從認識自我開始的。德國學者米夏埃爾·蘭德曼說,早期的人們自我解釋的特征之一,就是根據一個人是不是自己民族的成員來判斷其是不是人,“他們還遠遠沒有非常全面地辨認他們自己的類,甚至像埃及那樣發達的文化中,也隻有埃及人才保留着做一個人的特權。所有的異鄉人都不是‘人’,這種現象叫做民族中心主義”。蘭德曼所說的“民族中心主義”,與文化中心主義或者文化中心論是相近的概念,民族中心主義或文化中心主義産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對人的全面了解。
當生活在不同地理區域的人們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後,是否與自己共享一種文化,往往被當作判斷一個人或者一個族群是否為人的依據。這種情形在東西方的曆史上都曾有過。據米夏埃爾·蘭德曼的說法,幾個世紀之前,歐洲人還在讨論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是否為人的問題。在他們看來,“隻有‘基督教的人’(這是自馬丁·路德以來仍為人熟知的一種表達)才真正是一個人。”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及近代史上販賣黑奴的貿易,其真實原因就是西方人并沒有把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人當作人來對待。曆史地看,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排異性,每一個民族在文化方面都有自我優越感,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華夏族稱周邊少數民族為蠻、夷、戎、狄。秦漢以後,華夷之别一直為曆代中國人所重視,到了明清時期,來到中國的西方殖民者也被稱為“紅毛夷”“西夷”。正是文化的排異特征和自我優越感,才使得一個民族的文化在長期的曆史過程中得以保持下來。
民族文化的自我優越感,也與曆史上各民族之間文化發展的不均衡有關。曆史上,由于錯綜複雜的原因,在一定的地理區域内,往往是某一個民族的文化率先發展起來,進而在特定的地理空間内具有了優勢地位,發源于黃河流域的中國文化和發源于希臘羅馬的西方文化都屬于這種情形。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内,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都在它們所能影響的區域内推動着人類文明的進步,這是無可否認的曆史事實。然而,也正是這一事實使人們産生了某種錯覺,他們并不知道,在他們感覺到的地理邊界以外,存在着許多類型的文明和文化,每一種文明和文化都有其價值和意義。
戰國思想家孟子在談到華夷問題時曾經說過:“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孟子道出了黃河流域中心地帶的華夏族文化較之周邊地區的文化更為先進這一事實,但在另一方面,這句話也展現了某種文化優越感,在孟子看來,夷狄是需要由華夏文化來改變的,在孟子身後,這種文化優越感是被不斷放大的。直到18世紀末葉,英國公使馬嘎爾尼來到中國的時候,清王朝的統治者還以為大清王朝是世界的中心,“天朝所管地方至為廣遠”,“外藩使臣到京”無非是“傾心向化”。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更多地是由于對外部世界缺少了解。
鴉片戰争以後,當中國人對世界有了更多了解的時候,便逐漸從自我優越的錯覺中走了出來。相反,由于近代以來整個世界的曆史程序,西方人卻在自我優越的錯覺中越走越遠。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暫時領先,客觀上強化了西方人固有的自我優越感。他們以為,人類社會的曆史是以西方文明為中心展開的,西方文明就是人類文明的标杆,他們的責任就是拯救西方文明以外的所有人類。近代史上,歐洲人在世界各地瘋狂的殖民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觀念在作祟。不過,很多西方人不太願意提起的是,在把他們的文化向整個世界推銷的同時,西方人也在歐洲以外的地方犯下了種種罪惡。
總之,西方中心論或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曆史錯覺,如果說這種錯覺根源于西方人自古就有的自我優越感,那麼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率先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曆史事實,又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這種錯覺。
現代化: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理由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學術界曾有過一次關于“政治發展”的讨論,這場讨論的核心議題是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發展問題,最初讨論這一問題的主要是政治學者,後來,社會學、經濟學、曆史學以及人類學等學科的學者也參與了進來。根據二戰以後許多非西方國家都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的情形,一些持有西方中心論觀念的學者,對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前景産生了濃厚興趣。在他們看來,西方國家的政治現狀就是非西方國家的未來,這些國家政治發展的目标就是建立與當代西方國家相同的政治結構。不過,這種觀點也受到了曆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者的質疑:非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并不必然重複歐洲的曆史經驗,西方國家也不是所有非西方國家政治發展的理想模型。問題的關鍵是要弄清什麼是西方的,什麼是現代的。對于西方中心論者來說,這一觀點不啻是一味清醒劑。其實,這一觀點對着意超越西方中心論的我們來說,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立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和學術體系,也同樣要厘清什麼是西方的,什麼是現代的。是以,讨論超越西方中心主義這一問題,應具備現代的視角。
按照社會學的了解,現代化是涉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全球性的、迅速的社會變遷過程,其中主要包括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經濟現代化、以民主和效率為标志的政治現代化、人們的生活從以農村為中心轉向以城市為中心的城市化以及以科層制為起點的組織管理的現代化。這一曆史過程的起點是近代英國革命,後來漸次擴充到整個世界。
随着現代化曆史程序在全球範圍内的展開,西方人把他們的科學技術、知識、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也帶到了世界各地,于是,一些原本是西方的東西,變成了現代的。以至于在當今國際社會,許多通行的規則和标準都是由西方人建立起來的。現代化在改變着每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活的同時,也把這些标準和規則推給了每一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國家。事實證明,現代化是不可以也無法另起爐竈的,一個國家想要成為現代國家,它就必須接受西方所認同、推行的現代的知識和國際通行規則、标準。例如計量機關,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克、千克(噸)、米、千米(公裡)、公升以及在石油交易中所使用的“桶”,這些最初都是西方人使用的計量機關,但是,當這些計量機關為整個世界所接受以後,便成了國際标準。在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接受這些計量機關,就無法參與國際社會的經濟活動。再如競技體育,除太極拳、圍棋、中國象棋之類的項目以外,大多數運動項目都源自西方,競賽規則也是依據西方國家的标準建立起來的。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接受這些規則,就無法成為當今國際體育大家庭的一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中國駛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快車道。短短幾十年裡,我們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迅速縮小了與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領域的差距。改革開放政策不僅激發了經濟活力,而且也促進了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發展。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方面,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斷完善的同時,黨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目标,1999年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将依法治國的原則寫入憲法,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又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在公德心建設方面,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的十九大報告又指出:“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國民教育、公德心建立、精神文化産品創作生産傳播的引領作用,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與此同時,國家治理現代化也進入了當代中國政治建設的議程。現代化建設在根本上提高了我們國家社會生活的品質。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曆史證明,“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唯一正确的選擇,我們國家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的成就,都是通過這條道路獲得的。筆者認為,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同樣要有完整、準确的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立足中國國情、迅速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這意味着,一方面,我們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的經驗,簡單地模仿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另一方面,以現代化為目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有别于傳統、僵硬的以計劃體制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當我們堅定不移地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的時候,我們不應拒絕現代國家所應具備的基本要素。是以,我們才要弄清什麼是西方的,什麼是現代的。
按筆者了解,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也應該基于現代化視角來了解。我們之是以着力于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主要理由就是通過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建設,進一步推進我們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曆史程序。
為什麼要把超越西方中心主義與現代化聯系起來,說到這裡,有必要提及近年來關于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讨論。有學者認為,現代化的範式不僅無助于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反而是大陸社會科學發展的障礙。例如,鄧正來在論及中國法學應該向何處去時便說:“中國法學之是以無力引領中國法制發展,實是因為它們都受一種‘現代化範式’的支配,而這種‘範式’不僅間接地為中國法制發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而且還使中國法學論者意識不到他們所提供的不是中國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同時,這種占支配地位的‘現代化範式’因無力解釋和解決因其自身的作用而産生的各種問題,最終導緻了所謂的‘範式’危機。”是以,他認為,中國法學的出路就是結束這個受“西方現代性範式”支配的法學舊時代,開啟一個自覺研究“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法學新時代。筆者并不同意這一說法。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本土化,肯定是正确的發展方向。然而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實作本土化,如何建構屬于我們國家、我們時代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确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在改革開放以後的幾十年間,我們經曆了一個大量引入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階段。必須承認,在許多研究領域,這些年來被引入的基礎性知識和研究方法是被我們接受了的。這構成了目前大陸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基礎。我們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之是以能在短短幾十年裡拉近與國際學界的距離,具備參與國際社會的學術對話的能力,成為國際學術共同體的一員,完全仰賴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如今,我們國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之中,當我們明确了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立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這一目标時,現有的學術基礎恰恰是我們實作超越的起點。
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與我們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方向是一緻的。這在客觀上決定了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不可能是回歸傳統。在前些年曾經一度流行的國學熱和重建儒學的思潮中,曾有人主張放棄現有的學科分類方法,回歸傳統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學科分類,也有人主張用“王道”之類的傳統術語替換現有的學術話語,進而重建傳統的知識體系。這些想法其實是不可行的。
目前,人們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使用的許多概念、術語都是外來的。例如,經濟學界人們常用的GDP(國内生産總值)、CPI(消費者價格指數)、PPI(生産者價格指數)、M1(狹義貨币)、M2(廣義貨币)等,這些術語及相關的分析方法,對于描述和分析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貨币政策是十分有效的工具,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能夠替代它們的術語和分析方法。如果不顧這一社會科學發展現實,盲目追求本土化或回歸傳統,其後果将是災難性的。
筆者較為熟悉的政治學也是如此。在當下的政治學研究中,我們所使用的許多概念,如民主、專制,等等,雖在中國古典文獻中都可以找得到,但我們對這些概念的了解與古代人卻有很大不同。“民主”,在傳統的中國話語中是“群眾的主人”的意思,而到了近代,作為democracy的意譯,所指的卻是以人民主權為基本原則的政治體制。“專制”,在中國古代文獻中的本意是權臣專斷,禍亂朝政,《韓非子·亡徵》中“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羁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是其證。但是,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戰争以後,當鄭觀應、嚴複、康有為等人思考中國之是以貧弱的原因,将中國傳統的君主政體與近代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政體進行比較時,“專制”逐漸成為用于描述中國傳統社會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概念。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期間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便說:“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有人說,把傳統的中國社會稱為專制國家,孟德斯鸠是始作俑者,這種說法有違曆史事實。康有為使用“專制”概念的時候是1898年,而孟德斯鸠的《論法的精神》為中國思想界所了解是晚些年的事情。在傳統話語中諸多概念的内涵已經發生本質改變、學界同仁對這些概念已經形成基本共識的今天,回歸傳統話語是不可能的事情。
綜合來講,筆者認為,超越西方中心主義不是簡單地推翻現有的學科基礎,也不是回歸傳統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我們努力的方向應該是建構一個比現有的學術體系更為合理、更有解釋力、對于人類社會生活更有指導意義和規範意義的知識體系。從這一意義上說,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的唯一可靠的理由隻能是現代化。
建設中國特色的知識體系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系統工程
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當我們緻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時,也必須認識到,這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能否高品質地完成這項任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對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了解,以及我們在怎樣的程度上作出行之有效的努力。
首先,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要有現代的眼光和國際的視野。我們所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不僅是有中國特色的,更重要的是,它也應該是現代的,相較于前者,後者更為重要。在人類曆史上,思想學術的發展總是與知識的增長、學理的精進分不開,思想學術演進的總體趨勢是陳舊的知識被先進知識所替代,而區域、國别的因素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從表面上看,近代以來在整個世界流行的思想文化和知識體系是西方的,但實際上,這些東西之是以能夠在整個世界流行開來,并且為西方以外的許多地方的人們所接受,其根本原因并不僅在于它們是西方的,而是因為西方近代文化較之非西方的文化和知識體系更為先進,其中包含更多現代元素。在整個世界日益成為一個整體、高度資訊化的今天,僅靠本土化是不可能實作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超越的。
近年來,在有關社會科學本土化、建構中國話語的讨論中,有的學者就政治學的研究現狀發表議論說:“我們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架構、研究方法大都來自于西方,甚至我們讨論的熱門話題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學則不屑讨論我們提出的問題,更不會運用我們發展的概念、基本假設、分析架構和研究方法”,是以,建構政治學中國話語的目的就是改變長期以來中國學者扮演“概念、理論、方法的消費者和進口者”的角色的現狀。這一說法的要義就是中國學者應該用本土概念、本土理論和本土方法來研究和解釋中國問題,或者說,就是“用中國特色話語體系解讀中國道路、中國實踐和中國經驗”,這一說法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道理的,中國特色的政治學首先應該面對中國問題。如果不是這樣,政治學在中國就失去了存在意義。
但是,當本土化的概念、理論、方法成為我們的學術願景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忽略問題的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的政治學話語體系,以至于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建設中國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目的,不僅僅是用中國的概念、理論、方法解釋中國問題,更重要的是超越現有的以西方近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為基準的知識體系。這是因為,在全球化程序日益加速的資訊時代,僅能解釋一個國家現實問題的學術體系是難以獨立存在的。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純粹的本土性知識無法形成對話,也無法産生認同”,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學術體系,避免陷入自話自說的困局,使我們的特色話語能夠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所了解和接受,使我們想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成為整個世界能夠了解的知識,才是我們努力的目标。
其次,在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過程中,在改變以往食洋不化的狀況的同時,也應該避免盲目複古、崇古的傾向。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确實有過一段大量引進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時期。不過,如果追根溯源,這一過程早在19世紀末葉,嚴複、梁啟超那個時代就已經開始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傳入中國,固然與西方國家在近代曆史上的強勢地位有關,但在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遠遠不能滿足中國近代化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對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大量引進,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引進現代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實作了具有曆史意義的進步。不過我們也應看到,在這一過程中,确實出現了一些偏差。一些學者在把西方學界的某些理論與方法,特别是近幾十年較為流行的理論和方法引入國内的時候,往往不審其義,不究是以,囫囵吞棗式地拿來就用,甚至錯用。例如,在西方學術界,博弈論本是現代數學的一個分支,後來,博弈論的觀點和方法被引入經濟學界,成為一種有效的分析方法。此後,博弈論又進入了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領域。雖然不同學科對博弈論的了解和運用有所不同,但在最根本的一點上卻是一緻的,即參與博弈的雙方或各方是平等的主體,這些主體之間在各自表達意見的基礎上,有可能在某一點上達成契約。可是,有些學者卻忽略了這至關重要的一點,用博弈的觀點來解釋我們國家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把人們通常所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解釋為“博弈”。筆者不止一次在博士論文評審和答辯中遇到這種情形。事實上,用博弈的觀點解釋央地關系,是對我們國家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扭曲認識。
近年來,食洋不化的情形曾在許多學科領域裡都不同程度地發生。可以說,改變這種食洋不化的狀況,也是我們是以要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重要理由。不過,與此同時,筆者也不贊同當下較為流行的複古傾向。如前文所說,一些學者以為,建設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就是回歸傳統,應該到曆史中去尋找現實問題的答案。然而,古代人所生活的社會環境與我們這個時代存在本質上的差異,以往時代的社會主題也全然不同于我們的時代。在經驗性曆史過程中發生的事情,隻是我們認識的對象,并沒有為我們提供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需要現時代的人們憑借自己的理性去認識和解決,建構當代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隻能依賴當代中國人的理性而不是曆史傳統。
再次,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基礎理論研究是重中之重。與自然科學一樣,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在根本上取決于理論與方法的進步。在社會科學的每一個學科分支,基本概念的定義與内涵都是通過理論研究明晰和确定下來的,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學科的基本規範也是通過理論研究建立起來的,規範和引領社會生活的價值也是通過理論研究建構的。如果說一個學科是一座金字塔,理論研究就是金字塔的基石,它決定着一個學科可能達到的高度。同樣,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理論修養如何,也在根本上決定着他所從事的研究能夠達到什麼境界。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我們隻能從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做起,此外再無他途。
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一直有重視應用的傾向,這一傾向在政治學、管理學等應用學科中尤為明顯。不能否認,重視應用的研究導向對于推進和繁榮我們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使我們的學術研究更加貼近現實的社會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應用研究固然重要,理論研究卻更為重要,因為應用研究的前提是理論,在應用研究中應用的是理論而不是其他。離開了基礎理論研究,應用研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在更多強調應用研究時,理論研究便有意無意間被忽略了,于是,理論研究日漸薄弱便成為不争的事實。僅就筆者熟悉的政治學領域而言,近年來,高屋建瓴的理論研究成果雖然也有,但絕不多見,最常見的是大資料、績效評估、基層治理之類的成果。筆者并不是貶低這些研究成果的價值,隻是認為,離開了基礎理論研究,不可能形成高品質的應用研究。我們常常看到,洋洋灑灑幾萬字,羅列了一堆資料、表格,最後得出了一個簡單至極的結論,證明了一個無需證明的問題。可以斷言,如果基礎理論研究得不到加強,技術主義的路線将是一條不歸路。
最後,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應該進一步加強對西方思想文化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哲學社會科學本土化,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老話題,最近三十餘年來人們一直在讨論這一話題。不過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這方面說得最多的是原本不怎麼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人,從事西方哲學史、西方現代哲學、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卻較少參與這個問題的讨論。筆者認為,這些學者一定是贊同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實作哲學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他們也同樣在努力建構社會科學的中國話語,而之是以較少參與這個問題的讨論,是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超越不易。
有一個常識,如果我們想要在公路上超車,我們首先得知道我們要超的車在哪裡,前車的駕駛習慣、速度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義也是如此。我們要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超越西方中心主義,我們更應該知道,近代以來的西方思想家究竟說了些什麼,他們所倡導的價值觀念在本來意義上是什麼,他們的思想學說在什麼意義上是合理的。我們也應該知道,當代西方那些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有影響力的學者,他們的學術見解如何,他們是通過怎樣的邏輯展開論證的,他們的分析架構在什麼意義上是合理的,他們的研究成果展現了什麼樣的價值觀念,對于人類社會政治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他們給出了怎樣的答案,如果他們給出的答案不符合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又應該作出怎樣的應對。
總之,正是因為我們要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我們才需要對西方思想文化、當代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更為準确的了解。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志2022年1月下(微信有删節)
作者: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孫曉春
原文責編:陳璐穎
新媒體責編:單甯
視覺:劉潔
(圖檔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