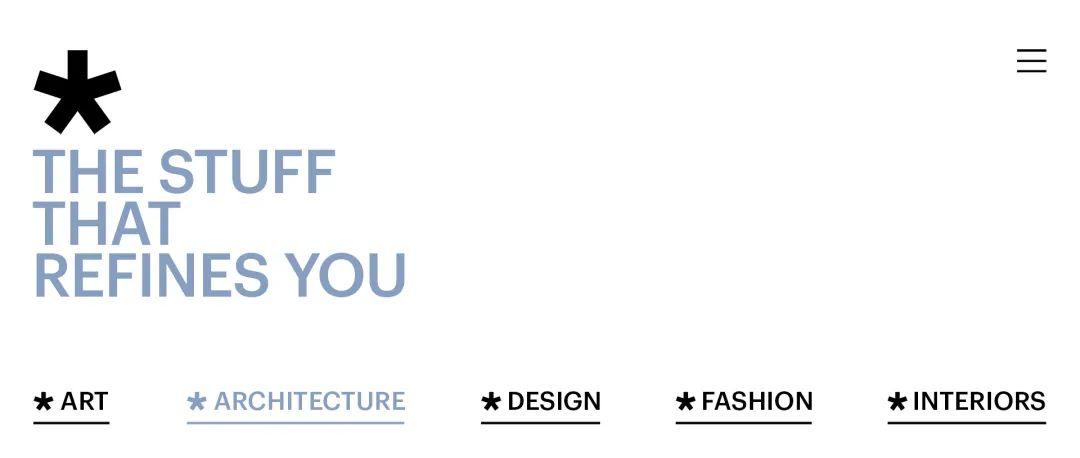
風景是藝術家永恒的話題。從意大利建築師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曾說過的那句名言“我想用我的建築剪裁出一片天空之藍”(Volevo ritagliare l’azzurro del Cielo.),到大地藝術家克裡斯托(Christo and Jeanne-Claude)的一系列用大地藝術與風景建立對話的作品,藝術家面對地景時的想象力是無窮的。當一件作品離開高密度的都市環境進入自然,如何營造它與地景的關系,是一個相當吸引但又棘手的難題。
裝置是一種現代藝術的發明。當現代藝術與現代建築結合得越來越緊密時,先鋒建築師往往也使用裝置作為介入空間實踐的媒介。另一方面,裝置潛在的可移動性也令它具備了比傳統意義的建築物更為靈活的設計模式。青年建築師郭廖輝目前處于獨立實踐剛展開的階段,他在成立事務所後的第一年裡完成的幾件裝置與建築作品都與山水和風景有關。它們從幾個不同的次元嘗試回答建築學的核心思維如何與地景對話。
2020年下半年,郭廖輝應OCAT上海館“空間的規訓”展覽的邀請,以一件裝置參展。策展人提出的命題是需要參展人以童年回憶為出發點,出生于荊楚之地的郭廖輝聯想到了與當地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長江大堤。在宜昌一段,每年長江的豐水期與枯水期之間形成的巨大水位差帶來了一種日常的奇觀,即枯水期能供人散步的堤岸在豐水期将完全被淹沒。
“空間的規訓”展覽現場。
現代堤岸的修築其實以一種工程的思維來考慮構件的尺度與人及地景的關系。建築師從小對堤岸的記憶是人走在上面時雙腳的感覺,同時他發現江邊鋪設的都是六角形的地磚。用六角形來拼圖案,特别适合略顯凹凸的地形,能比較好地達到滿鋪的效果。六角形元素被提取出來作為裝置的原型,為表達堤岸的斜面,在六角形地磚底下用纖細的木杆件将其支撐為一列往上擡升的斜線。
六角形地磚下纖細的木杆件。
該裝置占據了整個展廳裡的一處線性空間,地磚整齊相接,形成一道斜向序列。鋪地向來都是被人踩到腳下的,但是這一次,這個裝置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手法賦予了這件作品特别的含義。即便建築元素比起抽象藝術元素終究更為直白,但這一列斜向地磚卻甚少讓觀者立馬意識到這是來自長江邊的鋪地。而且實際上,這些地磚是以混凝土預制塊模拟了江邊鋪地,并非直接将地磚運過來使用。
“空間的規訓”展覽現場,六角形的混凝土預制子產品模拟堤岸的鋪地,并在下方用木杆件撐起逐一擡升。
從正面看,六角形構成的整齊序列提示了這可能是有别于一般裝置的建築構成;從背面看,細長的木構件恍如細腿,讓人不禁聯想到了郭廖輝曾經跟随學習并實習過的建築大師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曾在挪威海邊建造的女巫審判案受害者紀念館(Steilneset Memorial)。木頭溫暖的材質,以及在兩個坐标軸體系裡互相交接,令整件裝置作品顯示出一種樸素的精緻(austere elegance)。
滑動檢視“江邊漫步”圖紙。
這種樸素的精緻是建築師郭廖輝作品身上流淌着的歐羅巴血液。在瑞士門德裡西奧學院求學以及在歐洲遍地旅行的經曆讓他習得了如何有節制地來表現精緻。現代瑞士建築無疑是以精準度和精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建築門派,而對這種精緻的追求首先表達在材料和建造上。雖然處于正式開業的最早期,郭廖輝仍在目前有限的小型項目裡不斷探究如何通過材料和建造來表達精緻,其實木頭對他而言是很重要的材料。他在卒姆托事務所實習時曾見證了與卒姆托本人做配合的木匠是如何雕琢木工的,是以在回國後開業的項目裡,木頭也成為了他力圖做出作品性的一種選擇。
同年底,在廣西陽朔糖舍,建築師獲得委托要建造一處輕質的火塘。在桂北的村子裡旅行時,郭廖輝看到了侗寨的鼓樓及其中央的火塘,還有侗族人家在民居中烤火以及煙熏肉類的場景,這些旅行記憶激發了他創作“入木火塘”的靈感。嚴格意義來講,“入木火塘”也是一件裝置,還不能算是一件建築作品。但建築師完全是以一種對待建築節點和構造做法的态度來推進設計的。入木火塘的木構交接方式比前一個被命名為“江邊漫步”的裝置更為複雜。入木火塘的平面投影為正方形,依靠木杆件、布幔、拉索三種構件即可組裝完成。
裝置“入木火塘”與陽朔山水格局的地景構成了對話。
裝置一共有三層,每一層都依靠四根木杆件搭成,頗有一種現代簡化版的原始棚屋(primitive hut)的味道,同時又以其木杆件之間繃緊的深色布幔模拟了西南民居的批檐形态而讓人自然聯想到鼓樓造型。火盆被懸吊起來,不接觸地面,一方面它為整座火塘提供了作為阻尼器的結構作用,另一方面它頂上的拉索一旦繃緊之後,會反過來令底下的木杆件咬合得更加緊密。通過從造型到細部的多處嘗試,“入木火塘”與陽朔山水格局的地景構成了對話。
“入木火塘”僅靠杆件、布幔、拉索三種構件組裝而成。
從結構角度來看,這件裝置作品頗有創新。木構件的結構選型為互承式結構(reciprocal structure),四根木杆件通過精确的開榫而拼接在一起。如何對木材構件進行三維切割是決定了這件裝置作品在藝術性、經濟性、快速建造之間取得平衡的關鍵。
“入木火塘”中的火盆懸吊在中間而不接觸地面,與陽朔山水格局的地景構成了對話。
郭廖輝控制木構件節點開槽的方式其實是一種在有限的條件之下進行參數化的模組化和施工圖轉換。在這些項目的實施過程中,都是由建築師團隊直接對接木匠,不涉及工廠裡的機床加工。由于這件裝置作品使用互承式結構,其節點在四根相接的木杆件上是一緻的,而且在上下三層的杆件上都可以通用。如此一來為建築師的工作帶來很大便利。
搭建過程中,對木杆件的開槽和拼接。
雖然木榫的開槽面是斜的,給工匠帶來了一些不同于正常節點的操作難度,但由于建築師以單一節點控制所有開榫,整個建造過程的成本與耗時也就得到了控制。從這個項目開始,郭廖輝的實踐開始跟自然與地景産生了更多的聯系,而他的作品也開始逐漸走向構架與建築。
滑動檢視“入木火塘”圖紙。
2021年,在昆明滇池畔的一次建造實驗裡,裝置的規模擴大為一個已經可以容納人體在内部行走的體量,同時建築師面對的是滇池及周邊山脈更為開闊的地景。假如說“入木火塘”的縱向收分的體量更能契合陽朔一帶的喀斯特地貌,那麼,湖畔平亭(roof pavilion)則以橫向展開的體量回應了滇池與遠山。
湖畔平亭(roof pavilion)以橫向展開的體量回應滇池與遠山。
木頭依舊是這個項目的結構選材,建築師将其排列成連續的韻律。通過引入60度線,正三角形單元成為了控制整座建築的基本模度。除了位于兩端和中間的開口,這座作為展廊的建築通體在木杆件外側釘了陽光闆為覆層,在陽光照耀之下仿佛一隻白色蝴蝶。
陽光闆覆層下的湖畔平亭在光照下呈現出精緻的光澤。
除了“湖畔平亭”輕盈的外觀造型之外,其精确的木構件節點加工以及與陽光闆、鋼片的連接配接處的設計,都讓這座作品在細節上增色不少。
上圖:湖畔平亭剖面圖。
下圖:遊人可進入平亭内部行走與休憩,并透過剛好留出的菱形窗洞向外眺望。
炎熱之時,遊人可以進入平亭内部行走與休憩,并透過剛好留出的菱形窗洞向外眺望。三角狀的室内空間與陽光闆形成了人通過視野欣賞地景的獨特方式。
滑動檢視“湖畔平亭”圖紙。
假如說湖畔平亭依舊有些像是一件尺度近似建築的構架作品,那麼,同期完成的桂海生活體驗館那肯定是一件真正的建築作品了。場地位于桂林郊區,在喀斯特地貌隆起的奇山之間,該建築一道潔白的橫向體量以一條有力的水準線對地景做出了别有意思的回應。這條水準線并非羁直,而是微微順應了地形的緩坡,并且以極其纖細的豎向支杆輕輕托起了遊廊部分的屋頂。
桂海生活體驗館以一條有力的水準線對地景做出回應。
在遊廊内行走能體驗到它形态的擺動與接合,而纖細的杆件又讓人聯想起德國建築師埃貢·艾爾曼(Egon Eiermann)與塞珀·魯夫(Sep Ruf)共同設計的1958年布魯塞爾博覽會上的德國館。同樣是立面上極為纖細的豎向杆件,它令整座建築的精緻程度得以提升。而建築自身的鋼結構主體與遊廊之間微妙的交接關系,賦予了人在當中走動時輕松欣賞兩側地景的自由。
滑動檢視“桂海生活體驗館”圖紙。
這些作品從最小尺度的室内裝置開始,在各種機緣巧合之下,一步步擴大為立于地景之中的構架及建築。青年建築師郭廖輝目前的實踐就像他當年在瑞士提契諾與格勞賓登山區裡師長前輩們的實踐那樣,追求一件小作品自身樸素的精緻的同時,将作品納入到地景尺度進行考慮。這些作品深刻帶有了他留學瑞士的烙印,沒有誇張的造型,沒有喧嚣的詞彙,隻有強調建構感覺的節點設計和力求簡化的材料選型。或許在不久的将來,這些直面地景的裝置和構架,會演進為更複雜的地景建築。
上圖:桂海生活體驗館剖面圖。
中、下圖:在遊廊内行走時,可輕松欣賞周圍的自然景觀。
本次卷宗邀請到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助理教授江嘉玮與郭廖輝展開對談,分享其工作方法與學習經曆帶來的影響,探讨設計背後的思考。
江嘉玮
請郭老師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目前做設計的工作模式,比如草圖、草模、電腦模型、1:1的mock-up,您都有哪些設計常用工具?
我從兩個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一種是“指向可能性”的工具,在設計的初期我仍然在使用比較傳統的工具——草圖和草模,這樣的工具具備一種開放性,使我往往不會看到答案而是看到可能性。通過這些工具可以探索設計的政策、氣質、邏輯和形式。另一種是“指向精确性”的工具,它可能是電腦模型、技術圖紙甚至是1 : 1的mock-up。這個過程往往會更關注到功能、尺度、建造、材料、細節,也可以更有針對性地對不确定的問題進行嘗試,尋找平衡各種條件的答案。這兩種工具的界限是模糊的,在設計過程中一定會交織和反複。在有條件的項目裡,我們會比較強調一以貫之的工作模型。
郭廖輝
我觀察到您目前建成的三四個小作品都處于某種具體的自然環境裡。您結合經曆,談談自然景觀與人造構築物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在瑞士求學期間,了解到提契諾派建築師高度參與了提挈諾州的快速路的路線和隧道出入口等基礎設施的設計,這拓寬了我對于建築或者構築物存在于自然景觀中的認知。建築形式和姿态對于地形、風景的回報,成為進入提契諾學派理性而有力的建築的路徑之一。提契諾學派建築師奧雷裡歐·加爾費梯在貝林佐納設計的公共遊泳池就具備這種力量。
Aurelio Galfetti設計的貝林佐納公共泳池
在進入卒姆托工作室之前,仍然更多關注他作品中的建構、材料、氛圍的讨論。參與到第一視角看待設計之後,景觀和文脈在設計中的位置更加清晰了。即使是尺度極小的教堂,也能夠回報大尺度的地景并且點亮風景。克勞斯兄弟田野教堂(Bruder Klaus Field Chapel)在剖面上梳理出了作為背景的樹林、坡向村落的田野和低處的村落的關系,精确地放置了教堂。
左圖:克勞斯兄弟田野教堂
右圖:聖本笃教堂
聖本笃教堂(Saint Benedict Chapel)的兩條軸線提示了建築和景觀的關系:主體幾何的東西向軸線反應了抽象的自然,區分了教堂受光面與背光面,在教堂幾何的幫助下材料得以演繹陽光。入口的軸線揭示了具體的風景,連接配接聖像指向山谷,讓人想起入職初期卒姆托帶領我們在恩加丁山谷登山時他對山谷縱深的眺望。這些經曆加強和喚醒了對人造建築與自然景觀關系的思考。從設計的政策、空間到建造,這些優秀的先例都值得反複琢磨和學習。
在OCAT上海館的“空間的規訓”展覽中,十幾位建築師對家鄉的空間進行重制。我并沒有選擇一個建築空間,而是跟随直覺從景觀尺度對這個命題進行了解讀。借此機會回望了大約二十年的被動體驗和觀察,在這個過程中我對人和景觀、城市和景觀關系的認知已經在積累了。在長江這樣與我密切相關的文化和地理尺度面前,自然的能級是高于城市的,并且影響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江邊漫步模型
在實踐初期我們接觸到了一些尺度豐富的項目大部分都處在自然環境之中。這也提供了重新審視某一個具體風景的機會。我們在建築設計的各個層面尋找機會,使建築能夠揭示人們視而不見的景觀,這個景觀不僅僅是具體的自然風景,也包括長期積累而形成的人文景觀。
您在瑞士門德裡西奧學院學習過建築學,您認為您目前實踐中的哪些地方受到了門校的影響?
一是對建築學的整體認知,在門校的學習的确補充了一些缺項。比較完善的教育能讓學生們對建築學形成一個整體的認知,這包括了建築學的各個方面以及如何互相作用。二是認識到一種樸素有力的品質,在一部分教授的課題上,我們很多時候會強調将不同設計條件聯合起來形成一個簡單但又回應了很多問題的形式,進而導向一種理性而緊緻的品質。這似乎在瑞士的建築教學中比較普及。它培養了一種審視設計操作的機制。如果它沒有讓學生在設計方法和設計語言上變得更加教條,就能讓學生在堅固的基礎上尋找自己的路徑。三是工作方式的影響,在門校的求學經曆以及在歐洲的實踐中,通過有連續性的訓練,我逐漸獲得了一種有效的工作方式。這種工作方式正在實踐過程中根據具體的條件進行調整和進步。
您的作品目前呈現出很明顯地表現結構的傾向,比如使用纖細的杆件、強調節點的精确交接并表現之。您是怎麼考慮的?這會成為日後您進一步實踐時的首要選擇嗎?
我支援“建造是建築學的最終形式”的理念。是以會在意将結構和空間、材料和構造的關系納入到建築的表達。我認為建築需要展現出建築師的智慧,是以會強調建築設計中各種層面的編織和整合。基于這兩點,杆件、節點的精确性在杆件語言的建築設計中一定非常重要。
目前項目的自然環境和地區傳統建築有着明顯的木構基因,形成了構件化的潛台詞。根據項目的條件,有時候是比較臨時的,也導緻更傾向于以構架的形式出現。或許在更深層面上作為東方文化語境中建築師有着對木構的天然感情和構架形式的敏感度。是以意大利建築師Franco Albini在帕爾馬設計的建築立面對木構的演繹讓我印象深刻。
對我而言建築的形式和語言并不是一個預先設定的内容,而是設計的結果。是以我們願意像經曆一個完整的旅途一樣去從頭思考每一個項目,在設計沒有成型之前形式是未知的,而希望每一個建築最終都能獲得一個得體的形式。
若建築以裝飾來凸顯其特征,純粹追求視覺的愉悅或者某些文化的意義,卻并非真實的表現結構,您對此是怎樣考慮的?您能夠接受建築使用裝飾嗎?
結構的真實對我來說不是絕對不可動搖的,結構作為建築表達一部分,可以更偏向于和體驗者的交流的資訊傳達。我所觀察到的對建構的演繹而形成的有“結構感”的一些建築都很有意思。在我們的項目中,也會考慮在結構真實表達的基礎上的“二次演繹”,這種操作可以協調很多設計問題,比如對尺度、體驗、表情的控制。他們也不必要是純粹的裝飾,也可能有其他因素來支援其合理性,而它帶來的富于變化的品質會為設計增彩,甚至能加強核心的理念。在重視結構、重視設計邏輯的前提下,或許服務于整體設計的裝飾有可能幫助建築師走得更遠。
您與拾柴小組曾經研究過意大利現代建築師
Luigi Caccia Dominioni、Ignazio Gardella、Franco Albini等人,那麼您從學生時代到開業之後的建築設計裡究竟受到了這些意大利建築師哪方面的影響?
在12年夏天,通過去好友Logan Amont家裡看書,這樣一批建築師進入了我的視野。我在門校學習期間也通過對建築師作品的學習和踏訪加深了了解。拾柴的研究是一個大家把積累已久的興趣轉化成行動的工作。我比較大的收獲是深度閱讀方案的經驗。研究者背景帶來了研究的視角,文獻收集、背景挖掘的工作得以将設計放在一個立體語境中還原,也會對所處的設計條件有一定的認識。同時作為一個多背景聯合的集體工作,各種觀察和讨論也豐富了所有人的觀察角度。
能否和我們分享您在歐洲旅行時最打動您的建築作品,并簡要講講為什麼?
我逐漸發現最打動我的建築和空間都是非建築師的。那些景觀中的城市和基礎設施往往令人感動。人們對景觀的不斷改造(rework)成為了新的建造的基礎,在設計的時候我們需要保持這樣的耐心和敏感度去繼承和轉譯。如果一定要有一個大寫的建築作品,那可能是由荷蘭的修道士建築師Hans van der Laan加建設計的St. Benedict's Abbey。除了plastic number的比例系統,在其他設計方面,我們很難認為這位建築師在設計上有多麼技藝精湛。這也不斷引發我們去思考我們所做的一切與技藝相關的表達和演繹的背後是否還有什麼?
St Benedict’s Abbey, Vaals
撰文、采訪:江嘉玮
編輯:Kim、Ruihan
編排:穆越彪
攝影:朱清言,李銀銀,王海懿,吳清山,部分圖檔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