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愛動武的名将,聽起來很扯,但理論上完全行得通。畢竟《孫子兵法》追求“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人們也常把“不戰而屈人之兵”挂在嘴邊,是以史上還真的有這樣的奇人,比如唐朝的這位。
說起淩煙閣功臣,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除了唐太宗最初設立的24位外,後世的唐朝皇帝也陸續往裡面增添畫像,其中有這麼一位:
郭元振,他是武周朝、唐睿宗、唐中宗、唐玄宗四朝元老,前半生基本上活躍在西北軍事第一線,擔任過檢校安西都護、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等軍職,統帥過數以十萬計的大軍,由于經營邊疆有方,他被視為唐代名将,畫像被懸挂于淩煙閣。
但神奇的是,你在史書中幾乎看不到他帶兵打仗的記載。他的軍旅生涯,完美地展現了何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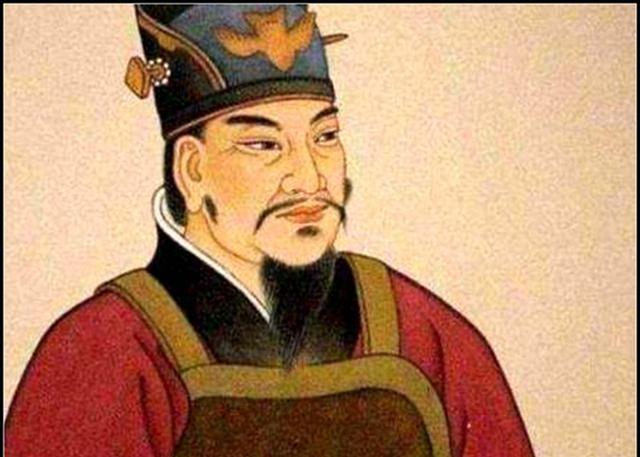
郭元振本名郭震,字元振,本是讀書人。在這一領域,他站在了當時的金字塔頂尖。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他18歲就高中進士,同年被任命為通泉尉。這是什麼概念?唐朝的科舉的難度是公認的地獄級:每年隻一次進士,每次大概就隻錄取一二十人而已;
更坑的是,進士及第後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從政,若想當官,還要經過吏部的再次考試,但錄取率卻是坑上加坑:“吏部之選,十不及一”,據說許多進士終生都沒法當官。
是以,科舉制在唐朝時也催生了許多“怨男”,最知名的當然就是屢試不第、憤而造反的黃巢。
其次,郭元振的文采過人,被譽為“文章有逸氣,為時所重”,《全唐詩》收有他的詩作十八篇,《全唐文》收其奏疏五篇,還另著有文集二十二卷。這種成果,即使放在整個唐朝也相當出彩。
但在人才輩出的唐朝,如果隻有上述特點,那也太“普通”了。郭元振還有以下異于常人之處:
外型優越——雖然唐朝帥哥很多,但被史書專門描寫外貌的挺少見。郭元振就是個例外,他“長七尺,美須髯”,像關羽那樣身材高大、美髯飄飄,一表人才、氣質過人。
俠氣過人——“俠”,原本是先秦時期極具影響力的特殊群體,他們待人大方、視金錢如糞土,不惜為朋友兩肋插刀,但也難免是以觸犯法律。當初經過西漢幾任帝王的打擊後,這一群體已經逐漸銷聲匿迹。但在郭元振身上,再度展現了這一氣質:
他在年僅16歲時進京就讀太學,随身帶去了家裡給的40萬錢盤纏費。但在一天,當一個身穿喪服的人登門拜訪、聲稱自己沒錢安葬親人後,郭元振二話不說、把自己的盤纏全部相贈,甚至都不問問對方叫啥名字。
更離譜的是,後來他剛剛進入仕途、擔任通泉尉期間,由于大手大腳地揮金如土、廣交朋友,導緻經濟出現了問題,竟然腦洞大開,悍然私自鑄币、倒賣人口......
如此看來,郭元振就像個充滿了黑社會氣息的讀書人。但随着他離開地方、進入朝廷,被安排到對口的崗位上,卻變成了護國安邦、利國利民的名臣。
鑄私錢、倒賣人口一事,讓一直默默無聞的郭元振引起了當時最高統治者的注意,那就是我們熟知的武則天。
一開始,聽說堂堂大唐帝國的官員竟然幹出這種缺德事,武則天是很憤怒的,她召來郭元振,計劃自己當面進行嚴加處理。
但聊了幾句後,發現對方竟然談吐不凡;為了全面了解,她讓郭元振交一份自己寫的文章,後者呈上了《寶劍篇》。
看完後,武則天贊歎不已,并且傳閱給以才學知名的學士李峤等人,随後更是大手一揮:越級任命郭元振為右武衛铠曹參軍、進奉宸監丞。
像這樣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對于武則天而言并不稀罕,狄仁傑、姚崇、宋璟、婁師德等名臣,都是被她慧眼識才、一眼相中。而郭元振也不例外,但許多人沒料到的是,這位文人,竟然因在西部邊疆建功立業而揚名立萬。
高宗、武後時期,大唐對外仍舊積極進取,并且取得了覆滅高句麗的成就。但在當時,各民族、文化間的交流、碰撞日益頻繁,周邊諸多族群都具備了自立門戶的實力,導緻當時的具備一定力量的政權多如牛毛,複雜程度史上少有;而在唐朝内部,由于長期政局不穩、政治鬥争錯綜複雜,人事關系頻繁變動,朝廷未能像貞觀年間那樣保持穩定的民族政策,導緻西北方向的邊疆問題越來越嚴重,強悍的吐蕃、西突厥各部讓人大為頭疼。
最牛的自然是吐蕃,它在當時被稱為中國古代最強“西戎”,其攻擊力、對中原帝國的威脅,甚至可與匈奴相提并論。公元670年的大非川之戰,吐蕃名臣論欽陵率40萬人過招大唐名将薛仁貴,10萬唐軍灰飛煙滅、幾乎全軍覆沒。随後雙方長期你來我往、邊打邊談,誰也拿對方沒轍。
在這種複雜的曆史局面下,往往會湧現出操作神奇的牛人,就像隋朝時巧妙肢解突厥的長孫晟那樣。在武周一朝,首先具備這種風采的就是郭元振。
公元696年,吐蕃示意請和,武則天委托郭元振出使。
會談中,論欽陵提出了“唐軍退出安西四鎮(當時是碎葉、龜茲、于阗、疏勒)、交出十姓突厥之地”的要求。這相當于赤裸裸地要求唐朝交出西域、自斷羽翼,進而逼近河西,郭元振當然不會接招;但為了避免直接撕破臉,他提出讓吐蕃派人跟着自己去朝廷當面商量。
但在實際上,郭元振早已胸有成竹。回到洛陽後,在他的建議下,朝廷這麼回複吐蕃:
既然你們對大唐的甘、涼二州沒興趣,那我們可以滿足你們的核心訴求——将遠離中原、形同雞肋的四鎮、十姓拱手相讓;
隻不過,青海、吐谷渾也是大唐的戰略核心區域,早年被你們搶去了,現在應當歸還以示置換。
對付敵人過分要求的最好辦法,莫過于對等提出一個同樣過分的要求。郭元振可謂掌握了人性的真谛,他吃準了論欽陵本意是想空手套白狼、不可能答應土地置換;但對方一旦拒絕,就會陷入理虧的處境。在實際上,唐朝壓根不可能置換西域,抛開絲綢之路的戰略地位不談,“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萬國來朝的大唐帝國,怎可能抛棄真心歸順自己的藩屬國、用來當成談判的籌碼?
但這隻是第一步,郭元振随後提出了更絕的後招。據他分析,吐蕃之是以提出求和,隻因其百姓對長年累月的戰事苦不堪言;朝野輿論壓力過大,讓挾兵自重的論欽陵也不得不做做樣子。但說到底,他是不可能化幹戈為玉帛的(畢竟兔死狗烹的規則到處都适用)。
是以,郭元振針對吐蕃的這一沖突,建議故意每年都派人去吐蕃示好求和,論欽陵越拒絕,就越應該派,以此激化吐蕃君臣、朝野間的沖突。
就這樣,當論欽陵連續幾次忤逆了唐朝的“好意”之後,吐蕃果然爆發内讧。公元699年,論欽陵在内亂中被殺殺,他的弟弟率領餘部投降唐朝。
這就是典型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郭元振的雙面計策更像是外交層面的勝利,但随後,他親自前往西線、鎮守一方。
公元700年,吐蕃軍隊入寇涼州,但被涼州都督唐休璟輕易擊退。據史書記載,當時的郭元振也參與軍機,這也許是他距離親自打仗最近的一次。
下一年,吐蕃與後突厥(東突厥的繼承者)聯合進犯涼州,武則天立即任命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帶領五萬人兵馬奔赴河西。因為吃過大虧的吐蕃贊普(相當于王)一向忌憚郭元振,聽說他親自前來,吐蕃人立即聞風而退。
随後在涼州主政的五年間,郭元振在咽喉要道修建軍事要塞,極大擴充了唐軍的控制區域,史稱“拓境千五百裡”。同時,他派人因地制宜、屯田耕作,涼州年年獲得大豐收、牛羊遍野,糧草可支十年隻用;此外,由于他手腕過人、善于撫禦,西陲多年未發生戰事,社會安定,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各族軍民甚至修建生祠歌頌其功德。
在郭元振的經營下,涼州成功地威懾了吐蕃和突厥,并且成為北庭/安西兩大都護府的後方基地、連接配接中原的堅實樞紐。也正是這個原因,他被視為一代名将。神龍年間,他更是被升為左骁衛将軍、安西大都護。
但作為軍事統帥,郭元振并不怎麼喜歡打仗,他最愛幹的可以歸結為:能動嘴就絕不動手,能攻心的就絕不付諸武力,擺平西突厥就是最好例證。
作為一個政權,西突厥雖然在公元657年被蘇定方剿滅,但餘部仍長期生活在舊地,上文所謂“十部突厥”就是其代稱,他們對唐朝時和時反,着實讓人頭疼。
郭元振擔任安西大都護時,當時頗為強盛的烏質勒所部願意向大唐歸順,于是倆人便在帳内議事。也許是相談甚歡的原因,二人一談就是好幾個時辰,當時大雪紛飛,郭元振年富力強也凍得夠嗆,而上了年紀的烏質勒卻沒頂住,傳回後沒多久就去世了。
這下烏質勒的兒子娑葛不幹了,他認為是郭元振故意害死了自己父親,于是率兵進攻。唐軍倒不怕打仗,隻不過這事确實說不清,一旦交手的話,今後更沒法招攬各部。于是郭元振既不躲避、也不迎戰,而是親自趕到突厥大營、在靈前吊唁烏質勒,哭聲震天動地,随後還留下幫忙處理喪事。
這種姿态,讓娑葛的憤怒化為烏有,他摒棄猜疑、盛情款待郭元振一行,并向大唐進獻五千匹馬、二百頭駱駝、十餘萬牛羊以示歸順,大唐與西突厥關系日益密切,郭元振因功加封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後來,這事曾再生波折,而郭元振再次力挽狂瀾、成功避免了不必要的戰事滋生。
公元708年,唐中宗李顯在位。這一年,由于并不服氣娑葛的節制,烏質勒的老部下名叫阙啜忠節起兵,雙方互相攻打、幾經較量,攪得突厥各部苦不堪言。為了消除沖突,郭元振建議朝廷征召阙啜入朝,他的部衆則分散遷移至内地。
但在手下的煽動下,阙啜忠節滋生了更大的野心,他賄賂了當朝宰相宗楚客後,成功讓朝廷指令安西兵聯合吐蕃軍共同攻打娑葛、扶持自己。
郭元振對西域的情況了如指掌,他明白阙啜不可靠、娑葛更值得信任,于是立即立刻上書朝廷加以阻止,但在宗楚客的操縱下,他的意見被擱置。随後,當唐軍還沒行動時,探知消息的娑葛立即先下手為強,攻陷安西都護府、生擒了阙啜忠節,大唐幾乎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
但即使如此,宗楚客等人仍在遮掩真相、驅逐郭元振,并且計劃調集大軍攻打娑葛。一旦到了這個地步,将是雙輸的局面。在獲得娑葛的表态後,郭元振派兒子抄小路赴京彙報實情。最終,朝廷審時度勢,恢複了郭元振的職務,并且冊封娑葛為西突厥十四姓可汗,賜名守忠。此後,娑葛不再與大唐作對,忠心耿耿的守衛邊境。
唐睿宗李旦即位後,郭元振回朝任職,西域各族首領苦苦挽留、百姓聞風迎送。唐睿宗對其也贊不絕口:“元振正直齊于宋璟,政理逾于姚崇,其英謀宏亮過之矣!”其後數年中,郭元振官至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遷吏部尚書,還擔任過朔方軍大總管、兵部尚書等職務。
但這位國之柱石,最終還是逃不過政治的殘酷。公元713年,郭元振參與了誅殺太平公主事件,被進封代國公;沒多久,他被李隆基任命朔方大總管,防備突厥。
但就在緊随其後的骊山講武事件中,他被冠以“軍容不整”之罪,差點被斬首,在劉幽求、張說的勸谏下才改為流放新州。不久後,李隆基感念他的功勞,特赦其為饒州司馬,但此時的郭元振早已身心俱疲,在上任途中病死,終年五十八歲。
大唐帝國的四朝功勳,竟落得如此下場,不是郭元振不忠心、不優秀,隻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李隆基想必隻是為了騰籠換鳥、不允許如此德高望重的軍政元老待在高位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