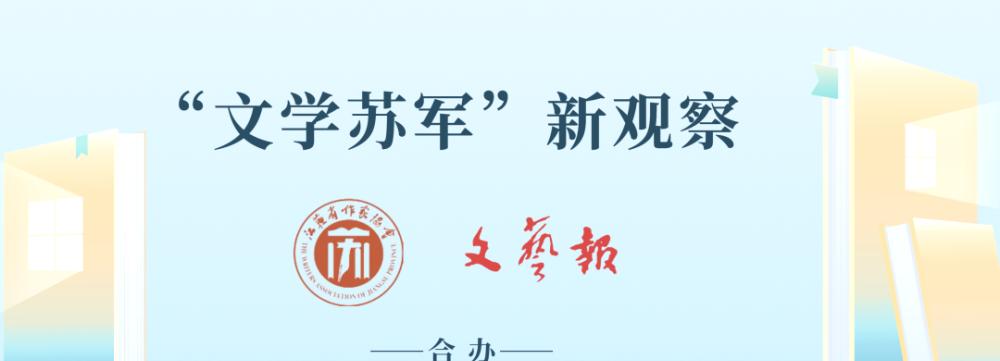
散文是一種包容性很大、富有彈性的文體。我們這裡給出“江蘇大散文”的指稱,自然不是對賈平凹先生當年首次提出“大散文”觀的簡單呼應,而是基于江蘇散文生成機理及其格局氣象的觀察。
江蘇大散文是種有根的文學創造,它的“大”成,從文化的根系上,與江蘇文化構成的豐富性有關。“江蘇文化”是總體性區域文化概念,由吳文化、金陵文化(甯鎮文化)、徐淮文化(楚漢文化)、維揚文化和蘇東海洋文化等構成,這些交融互補的“文化個體”,影響着作家的個人經驗、寫作心态、文化态度等,促生了江蘇大散文的多樣多質。從創作主體上,與作家身份的變動不居有關。江蘇散文作家身份多容兼備者居多,我們說的學者散文、評論家散文、小說家散文、詩人散文、官員散文、報人散文等,基本是作者職業身份與散文的疊加或是化學反應,不同身份帶來價值訴求、内化體驗、情緒載體、審美形态的多樣化,如學者散文偏智識性、評論家散文偏批判、小說家散文偏虛構叙述、詩人散文偏内傾詩性、報人散文多取事新聞等。從文體觀念上,與有“大體”無“定體”的美學趨向有關。江蘇大散文跨文體寫作突出,它與非虛構、紀實文學相連結,與小說、詩歌、戲劇等體裁越界合流,與文學批評、學術研究融為一體。江蘇散文越界走向開闊,漫溢成江河叢林。“散文蘇軍”也由此成“軍”。
當然,從更廣泛的主題題材上,江蘇大散文的“大”,與寫作對象及寫作内涵的拓殖程度有關。在文本意義上,“江蘇大散文”固然包括展現江蘇文化基因的散文,其實還應包括江蘇籍作家與“新江蘇人”寫的并非囿于地域元素的散文,這些散文不是“地方幻覺”的祭品,更多的存在,與中國散文文化有關。一般來說,中國散文沿着兩條文化路徑在走:一條是“文以載道”,這是中國古典散文的主流,确認了社會功用在中國散文中的精神價值;另一條是追求個性言志的“抒情傳統”,指向散文内在的審美感覺。江蘇大散文的寫作生産,立意為宗、憂患意識、家國情懷等構成了“文以載道”的文化要義,個人言志的多向度促生了散文“抒情”風格的多形态。前者主張散文理性價值,曆史散文為主要樣本;後者傾向散文的情感性,以個人化散文為主導。
曆史寫作是江蘇大散文中的一大亮點。書寫曆史散文者,首先不是“思垂空文以自見”,更多時候,是想弄清中國曆史中的一些問題以及對現實的投射情況,也包括對曆史暗處人性意義的探尋。主要有兩種姿态:一種是直面曆史,即經由某些重要的文人或事件、人文山水進入曆史,将曆史還原于曆史人物事件的“在場”中、複現在文化遺迹的客觀中,由此追問曆史的種種;一種是“非曆史的方式”,即在被忽略或被遮蔽的“曆史的背面”發現民間價值的所在。“直面曆史”的散文,以丁帆、王堯、王彬彬為代表,他們的散文凸顯着求真審慎、自由意志、獨立精神的風骨。丁帆的散文是一種思想的寫作,他認為價值取向的定位是散文的靈魂與最核心的問題,人性的聚焦是散文的最終追求。散文集《江南悲歌》《枕石觀雲》《尋覓知識分子的良知》《知識分子的幽靈》等都是在追尋、拷問知識分子命運沉浮以及人格品性,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永遠的言說者和批判者的爽言快語。王彬彬從2002年在《鐘山》開設專欄“文壇舊事”,一路寫到“欄杆拍遍”的政壇舊事,綿延寫來20年,表以學術文章以外的“後學術”,這種曆史還原和考證的寫作,内融着作者學術以外的種種感受和問詢,後結集為《往事何堪哀》《并未遠去的背影》《大道與歧途》《顧左右而言史》《費城的鐘聲》。王堯的行文走墨透着“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他的曆史散文起自《東方文化周刊》,之後陸續在《南方周末》《收獲》《鐘山》《雨花》等開設專欄,傳遞他對曆史真相的追溯、對時代的憂心、對知識人的關切,展現知識分子所持有的文化良知與反思精神等,後結集為《脫去文化的外套》《紙上的知識分子》《滄海文心:戰時重慶的文人》《日常的弦歌:西南聯大的回響》《時代與肖像》等。當然,也有以曆史知識為文本依托“回訪”曆史故現場的散文,如賈夢玮在《南都》中回味六朝古都的人文曆史,夏堅勇在《紹興二十年》《慶曆四年秋》中探訪南宋北宋時期的社會生活及政治風雲等,氣息相對平和,在他們的筆下,“曆史就不再是那些筋絡性的年号和事件,人物也不再是一些符号和類型,一切都日常化,細節化,心理化了”。
江蘇大散文的“非曆史的方式”,指向民間性和文化詩性,這種書寫不追求曆史宏大叙事,着重在日常的瑣碎中展示“真人間”,直接拓展了自古“詩意”江南的新内涵。作家們或徜徉在文明的廢墟上,或輾轉在江南的園林古鎮中,主要以文化散文和江南散文為支撐。徐風用《一壺乾坤》打開中國紫砂藝術史,用《風生水岸》《江南繁荒錄》記錄江南文化形态;山谷在古都風雨中《回眸江南》;費振鐘在《黑白江南》中反複書寫江南細碎而極具生活的場景;車前子流連在蘇州園林裡記下《品園》,他的《中國後花園》《江南話本》拉拉雜雜地記着風俗土物;黑陶在《夜晚灼燙》《漆藍書簡》《泥與焰》中雕刻着“父性”江南……這些“民間曆史”的散文,将“江南”豐富在民間文化的“雜質”中了。
某種角度上,散文是一種更個人化的書寫方式。這既意指作品的價值判斷和語言方式要有作者的“我”在,也表示作者的個人經驗成為散文寫作的基本資源。這樣的寫作,從個體的角度是“小”的,但集“小”成“大”,成為江蘇大散文的重要構成要素。這種個人經驗及其關聯内容的寫作,基本以非虛構式叙述和絮語式抒情兩種方式展開。
所謂非虛構式叙述,傾向于亞裡士多德所說的“叙述已發生的事”,作家主要以“在場”方式進行書寫,也可以演化為一種“創造性非虛構”,在緻力于叙述真實時,運用适度的想象等補充對細節的模糊記憶及體驗。大緻有以下多種情況:一是個人與時代的叙述,如王堯的《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畢飛宇的《蘇北少年“堂吉诃德”》,前者以作者生活的農村為線索,書寫時代轉型中的人和事;後者回望興化街頭的童年生活,錄下“一個時代的童年‘老照片’”。二是個人與他人的叙述,如丁帆的著作《先生素描》,王堯的《記莫言》等文章,前者叙議互生,具有知識分子精神史的意義,後者給當代作家畫臉譜。三是個人與故土的叙述,其中多有返鄉、鄉土淪陷、民間信仰、新農村發展等随記雜談,透着濃郁的地方氣,如胡弦的《永遠無法返鄉的人》、周榮池的《一個人的平原》、韓麗晴的《意思》、劉旭東的《吾鄉風物》、劉仁前的《楚水風物》、嚴蘇的《大地萬物》等。四是個人與家族的叙述,如劉劍波的《姥娘》、龐餘亮的《半個父親在疼》、向迅的《與父親書》等,兼以紀實、詩歌、意識流、書信、日記等雜糅的親情叙述。
絮語式抒情散文,既有胡夢華式的“零碎感想文章”,也有根據抒情角色不同拓展出的心靈性。一是即景式抒情,以遊記散文為主,如黃蓓佳的《地圖上的行走者》、趙本夫的《西部流浪記》、葛芳的《南極之南,遠方之遠》等。二是叙寫生命感悟,包括日常經驗與文字閱讀的感悟,如丁帆的《人間風景》《天下美食》、汪政的《悲憫與憐愛》、葉兆言的《無用的美好》、畢飛宇的《小說課》等。三是抒寫女性經驗,如範小青的《一個人的車站》、朱文穎的《必須原諒南方》以及魯敏的《就花生米下酒》《而今人們擠擠挨挨站滿你的書房》等單篇散文,于瑣屑處逸出生存的意義。
在“江蘇大散文”中,報告文學的創作情況也值得關注。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報告文學界,江蘇作家的創作頗有聞聲,其中楊守松及其《昆山之路》等的影響更大。雖然現在的地位不能企及當年,但近年江蘇報告文學創作整體态勢的穩健活躍卻有目共睹,令人欣喜。現實題材的集體主題寫作,這兩年湧現了《向時代報告——中國小康江蘇樣本》《向人民報告——江蘇優秀共産黨員時代風采》《觀遍地英雄——江蘇抗疫故事》《茉莉花開——脫貧攻堅江蘇故事》等佳作。章劍華的“長江大橋建設三部曲”“小康三部曲”、丁捷的《追問》、周桐淦的《智造常州》、傅甯軍的《大學生“村官”》《長江星辰》、龐瑞垠的《大道無垠》《一個人與一座城市》、王成章的《國家責任》、張文寶的《萬國互聯》、姚正安的《不屈的脊梁》、陳恒禮的《蘇北花開》、蔣琏的《支教:在小涼山的28年》、王向明的《永不打烊的警務室》等,基本是傳統意義上的報告文學寫法。
另一種非虛構方式的寫作,既有底層鄉村的田野調查,如錢兆南的《跪向土地》、杜懷超的《大地無疆》《大地冊頁》、費振鐘的《興化八鎮》、程慶昌的《鄉村匠人》、懷念的《年輕手藝人》、韓修存的“大地三部曲”,也有黑陶的《二泉映月:十六位親見者回憶阿炳》、高保國的《尋找張思德:一位作家的采訪手記》等回憶錄及口述實錄,還有徐風的《布衣壺宗》、楊守松的《昆曲之路》《大美昆曲》、張嵩山的《解密上甘嶺》、張曉惠的《北上海,這片飛地上的愛恨情愁》等傳記或紀實,鄉土、城市、戰争、公安、文化等題材多向拓展,現實與曆史、國家叙事與小微叙事等多樣并存。
當然,我并不想把江蘇散文隻是擱置在江蘇“地方”中讨論,更願意把“江蘇”作為系統的“人本主義地理學”概念,從“人地關系”中讨論作家關于地理存在的美學反應。如此,人的理念、人的體驗、人與他的文化、人與地“合一”的有機度,共同構成了“江蘇大散文”的重要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