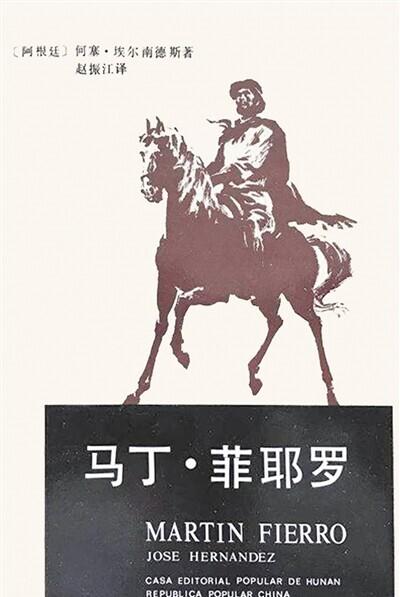
開欄的話
譯者與書相遇,在心靈共振中融以智慧、學識和情感,語言轉換的同時,打開不同文化間互望之窗,成為文明程序中重要一環。經典重譯,新作新譯,字裡行間,滿是凝結的知識、無聲的故事與文化溝通的印記。本版自本期起推出“譯者·書”欄目,在譯者的講述中,品讀翻譯背後的故事,追尋文明交流的共鳴。
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在《論〈馬丁· 菲耶羅〉》中說:“在歐美的一些文學聚會上,常常有人問我關于阿根廷文學的事情。我總免不了這樣說:阿根廷文學(總是有人不把它當回事)是存在的,至少有一本書,它就是《馬丁·菲耶羅》”。
反複推敲,力求譯文中西近似
大學三年級時,我們有一名阿根廷外教,選了《馬丁·菲耶羅》作泛讀教材。這部高喬史詩的内容和藝術風格吸引了我,于是便試着将一些詩句譯成中文。時斷時續,日積月累,到1979年,我總算譯完了史詩的上卷——《高喬人馬丁·菲耶羅》。同年,我有機會去墨西哥學院進修,就想在那裡把它譯完。恰好那裡有幾位阿根廷老師和學生,可以向他們讨教翻譯中遇到的問題。兩年後回國,基本譯完了,隻剩幾個零星的難題未解決。幸運的是,我認識了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任教的卡洛斯·阿爾伯托·雷吉薩蒙教授,他曾擔任阿根廷國立科爾多瓦大學文學系主任,是研究高喬史詩的專家。在他的幫助下,我終于完成了《馬丁·菲耶羅》的翻譯,譯完之後便束之高閣,從未奢望出版。
1984年,是史詩作者何塞·埃爾南德斯150周年誕辰,阿根廷政府要展覽各種文本的《馬丁·菲耶羅》。我駐阿使館與國内聯系,希望盡快出版此書,送去參展。時間緊迫,隻剩3個月了,在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援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精裝的《馬丁·菲耶羅》(見右上圖,資料圖檔)。這位用中文吟唱的高喬歌手在家鄉受到熱烈歡迎,阿根廷《馬丁·菲耶羅》譯者協會委托中國駐阿使館文化參贊給我帶來了譯者證書和紀念銀币。
1988年5月,時任阿根廷總統阿方辛訪華時參觀北京大學,時任校長丁石孫将《馬丁·菲耶羅》作為禮物送給他,總統立即說:“我邀請譯者通路阿根廷。”遺憾的是,我當時正在西班牙主持翻譯西班牙語版《紅樓夢》。
《馬丁· 菲耶羅》是我個人獨立完成的第一部譯作,其難度可想而知。所幸在翻譯過程中,我從不自覺到自覺地追求譯作與原作的最佳近似,既不生吞活剝,又不脫離原文,盡量求得“異化”與“歸化”的和諧共存。首先是詩歌形式的近似。史詩作者是在模仿行吟詩人(流浪歌手)的即席演唱,采用的是西班牙語中最常見的每行八音節的民歌體,而且一以貫之,7200行都是八音節。但是漢語中極少有“八言詩”,而七言詩則非常流行,是以我決定用七言民歌體來翻譯。原詩押韻,譯詩自然也要押韻。既然是漢譯,當然要遵循漢語詩歌的格律,否則會“水土不服”。僅以史詩開篇的6行為例:
我在此放聲歌唱,
伴随着琴聲悠揚。
一個人夜不能寐,
因為有莫大悲傷。
像一隻離群孤鳥,
借歌聲以慰凄涼。
這基本是直譯。有一位學長曾建議我改為:
此時此地歌一曲,
吉他聲聲伴我語。
一生一世唱不盡,
苦難深深埋心底。
好似孤飛鳥一隻,
我以此歌慰自己。
感謝學長的好意,但我還是堅持了自己的原譯。首先,原詩押“阿”(a)的韻,是開口音,适合吟唱;而譯詩中的“曲、語、底、己”是閉口音,不适合吟唱。再者,就内容而言也和原詩有較大差異:如第一行,原詩中是“開始歌唱”,而不是“歌一曲”,且全書上下卷共46章,7200行,何止“一曲”。尤其是第三行和第四行,完全是譯者自己的創作。我還是覺得自己的譯文略好些,或許是“瞎媽抱個秃娃娃——别人不誇自己誇”吧。
跨越國界,詩歌翻譯拉近人心
上世紀90年代,阿根廷新任駐華大使剛到任,他知道我是《馬丁·菲耶羅》譯者,便請我到使館一叙。我将拙譯送給他。大使很高興,請我喝馬黛茶,然後說:“趙先生,可否請你讀一段,讓我聽聽馬丁·菲耶羅如何用漢語吟唱。”我說當然可以,便朗讀了開篇這一段。他聽了,興奮不已,先是站起身,給我一個擁抱,然後想找一件禮物送給我,可事先又沒準備,就從客廳櫥窗的展品裡,取出一把高喬人用的Facón(長匕首)送給我。我和他開玩笑說:“我們中國人送禮不送刀,一刀兩斷!”他笑着說:“諾,諾,我不僅不和你一刀兩斷,還要申請,叫我們的總統為你授勳呢!”
他果不食言。1999年,譯林出版社将《馬丁·菲耶羅》收入世界英雄史詩譯叢。阿根廷駐華使館為新版中譯本《馬丁·菲耶羅》舉行了首發式,并借此機會為我頒發了由總統簽發的騎士級“五月勳章”。
2008年12月,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家出版社采用我的譯本,出版了西班牙語、英語、漢語三語版的《馬丁·菲耶羅》,不僅受到讀者的歡迎,也引起了阿根廷外交部的重視。他們立即購買了1000冊,并願意支援出版羊皮燙金封面的豪華三語版《馬丁·菲耶羅》,作為饋贈各國貴賓的禮品。
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馬丁·菲耶羅》譯者協會主席戈麥斯·法利亞斯先生編了一本《孔子和馬丁·菲耶羅》,将史詩中的格言與《論語》中的孔子語錄進行對比,雖然有些牽強,卻可以看出作者對史詩的熱愛和對中華文明的崇敬之情。
2009年,因翻譯《馬丁·菲耶羅》,我有幸認識了阿根廷著名詩人胡安·赫爾曼,并推薦他參評獲得首屆金藏羚羊國際詩歌獎。赫爾曼不僅是塞萬提斯文學獎得主,還是令人尊敬的革命鬥士。他曾任新華社特聘記者,兩次應邀訪華。當周恩來總理問他有什麼要求時,他說“想走長征路”,并真的沿着紅軍足迹完成了自己的“長征”。在第二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期間,我們成了好朋友。臨别前,他為我寫了一首題為《青海湖》的詩。
2011年,我邀請阿根廷作家協會副主席、詩人羅貝托·阿利法諾參加第三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自1974至1985年,羅貝托作為博爾赫斯的助手,和他一起從事翻譯工作。回國後,他在阿根廷《民族報》上撰寫題為《偉大的詩歌節》的文章,借用秘魯作家略薩的話贊美中國:“這是一個現代化的、信心百倍、繁榮昌盛、真正的21世紀的國家,其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舉世矚目。當今世界依然掙紮于貧困、被邊緣化和缺乏安全感之中,而中國所發生的這一切堪稱全世界的榜樣。”
從青海回到北京後,我陪同羅貝托遊覽了長城和故宮。當他知道秘魯裡卡多·帕爾瑪大學邀請我于當年10月去做關于巴略霍詩歌翻譯的講座,并授予我名譽博士學位時,一定要我順訪布宜諾斯艾利斯,同樣做一個關于翻譯《馬丁·菲耶羅》的講座。我欣然接受,這正好彌補了我當年未能通路阿根廷的缺憾。在阿根廷作家協會大廳,上百位阿根廷詩人、作家和文化界人士濟濟一堂、聚精會神,聽我講漢西兩種語言的對比以及我在翻譯中遇到的問題。在聽講座的人中,有一位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師告訴我,第二天,他在課堂上說起此事,一位學生對他說:“老師,我外公有一位中國朋友,也翻譯了《馬丁·菲耶羅》。”原來,這位學生的外公就是雷吉薩蒙教授。我很快就和教授的女兒莫妮卡聯系上。2012年,莫妮卡和姐姐以及一名同僚來華旅遊,我請她們到家裡做客并參觀北京大學。無論對她們還是對我,這都是終生難忘的驚喜。
通過翻譯《馬丁·菲耶羅》,我深深體會到,語言是使人心相通的橋梁,而翻譯就是在搭建溝通心靈的彩虹橋,能為其添磚加瓦,譯者一生都會感到幸福和欣慰。
趙振江,1940年生。曾任北京大學西語系主任、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會長,曾獲西班牙伊莎貝爾女王騎士勳章和智者阿方索十世勳章、智利聶魯達百年誕辰勳章等。2004年被評為全國模範教師。曾獲中坤國際詩歌獎、魯迅文學翻譯獎等。主要著作有《西班牙與西班牙語美洲詩歌導論》,譯著有西班牙語版《紅樓夢》與西班牙語詩選20餘部。
版式設計:蔡華偉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