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左宗棠得到格外重視不同,郭嵩焘在他的老家湘陰汨羅,幾乎找不到“遺迹”。我跟當地的朋友講,五十年之後,郭嵩焘的名望會高于左宗棠,朋友不敢置信。我為什麼這麼說?我當然也喜歡左宗棠,多有能耐的一個人,英雄。但是,我想告訴諸位,這種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别是在中國文化水土裡,而類似郭嵩焘這種能夠提供新的世界觀,新的文化視界的人,卻不多見。
——孟澤
文丨孟澤(中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郭嵩焘一生也有應對人際關系非常裕如的一面。
視其為兄弟的不僅有曾國藩、曾國荃、劉蓉等,更有李鴻章這樣被梁啟超指為“不學無術”而實際上“不學有術”的人。他也深知“古人成一名,立一事,艱難挫折,遲久而後成,氣挫而志愈堅,道诎而心愈隐,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他同時懂得“君子之道,必協人情,未有非人情而可強行者也”。郭嵩焘也可以辦事,譬如為曾國藩籌饷,處理兩淮鹽務,治理蘇松錢糧,包括整頓山東厘務,巡撫廣東,這多少可以否定,郭嵩焘沒有與人共事的性格,隻有不能辦事的書生意氣等說法。
除了苛刻地打量士大夫,特别是那些為官作宦的士大夫們的德性、器識與作為,他當然也為那種能“殷殷然求為深遠之計”的官員叫好,為那種真正學有優長的士子争取位置和空間,譬如陳右銘(寶箴)、陳澧。而對那些出現在他身邊,充滿才情、銳氣、見識而胸懷遠大的晚輩,如陳伯嚴(三立)、曾重伯(廣鈞)、郭慶藩,更是推崇備至,獎掖有加。他更毫不隐晦地贊美如曾國荃那樣有膽有識的英雄,謂“其學問見識,倍增磨砺,超出一時,生平功業良為有本,政府諸公無知之者”。這真是舉世罕見的判斷。
但是,由于他的思想,以及伴随這種思想的個性和先知先覺,他的誠實與認真,讓他的生涯确實充滿梗阻,以至于一挫于僧格林沁,再挫于李湘棻,三挫于左宗棠,四挫于劉錫鴻……其實,真正挫折他的是他為之俯仰終生的朝廷,是鹹豐,是讓他為國家任艱苦的慈禧(唐德剛所說的李鴻章當年對俾斯麥感歎與之共事的“婦人孺子”),是那個時代的士大夫階層普遍的因循和因襲。他在晚年有詩說“今日朝廷真有道,古來事變渺無方”。證明他并不是沒有認識到,他生死以之的朝廷究競是怎麼回事。但這屬于理智,而非情感所向。他對總歸有一天要親政的光緒,實是有所指望和期待,至少在與洋人言及國務時,就希望别人看到這一點,還曾勸告洋人,暫時不要太逼迫清朝當軸。
事實上,對于郭嵩焘本人的才具和他面臨的處境,連被稱為莽夫粗人的曾國荃都知道∶“居今日而圖治安,舍洋務無可講者。僅得一賈生(指郭嵩焘),又不能用,此真可以為太息流涕者也。”賈誼(前200—前168),西漢政論家,值漢文帝劉恒時,曾為長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賦》,有《新書》十卷,作《陳政事疏》《過秦論》,對漢代政治多所主張。但是,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誼不能不“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 。
事情也正像曾國荃所看到的那樣,與當時整個士大夫群體在西方文明面前所表現出來的人格分裂相差別,郭嵩焘的文化人格幾乎稱得上健康;與當時土大夫群體常常隻有道德激情而缺少求真求知勇氣相差別,郭嵩焘擁有着不止于道德勇氣的求真務實的熱情與對于知識的熱情。
正是在這裡,郭嵩焘與他同時代的“精英”愈行愈遠。
而且,他對于國務、洋務洞悉之明、執着之深、信心之堅,實遠在李鴻章輩之上。他對于中西文明的某些方面的認知和了解,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而有着某種普遍的意義,屬于任何文明都必須遵循和踐行的公義和道義。
也同樣基于此,郭嵩焘對于國家處境與前途的基本判斷常常更加真确,在數十年甚至一百數十年後,不能不讓人們重述。
民國學者柳定生說∶“處清季頑固笃舊風氣之中,吾輩猶得見郭公不偏不倚之論,衡量中外得失之宜,無不淖極緻理,力排浮議,謀解天下困厄,矯正南宋以來,士大夫空言激世之痼弊,是何異于中流之砥柱,冀挽狂瀾于既倒耶!”
1901年,李鴻章在臨死前以空前屈辱的條件,代表清廷再一次簽署城下之盟——《辛醜條約》,然後上書朝廷說:“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内,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猝,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内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譬諸多病之人,善自醫調,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矣!”這樣的話,郭嵩焘在差不多半個世紀前的鹹同之際,就大聲說過,當着慈禧的面說過,中法戰争時又說過,無人響應。
當代著名曆史學家黃仁宇、唐德剛在他們的著作中說,大曆史中的中華民族,一個多世紀以來,置身風雨如晦之中,如鳳凰之涅槃,正穿過如同三峽一樣漫長的坎坷和險阻,在可以設想的未來,終将踏上康莊。而差不多一百五十年前,郭嵩焘認為,中國需要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漢以來累積深厚、流極敗壞的政教,造就新的行之有效的“禮儀風俗”,非這樣漫長不能指望成功。他說,武器、裝備、制造,有賢者擔當,也許三五十年就能夠有所改變,可以得其大概,這同時有待于教育,百年樹人,百年之力或許可以蕩滌舊染,又以百年之力或許可以磨砺出合适合格的人與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積成人心風俗,真正的改變在于人心風俗,需要有大視野、大氣魄的“聖人”接踵而起。
自然,也離不開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們一點一點的努力,所謂“毫末”之功。
這樣的使命,确實至今伴随着華夏子民。而且,前路漫漫,任重道遠。
他還說,“俯仰今昔,慨然傷懷,能知此義者誰哉?”他意識到,所謂曙光,并不就在他的身邊、他的身後,并不就在觸手可及的地方。
于是,我們無法不同情郭嵩焘曾經的郁悶,他在題寫自己的詩中說∶“世人欲殺定為才,遷拙頻遭反噬來。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世人欲殺,不複以人數,他什麼時候舒展過自己的懷抱呢?
同時,我們也無法不驚訝郭嵩焘曾經有的自信:“傲慢疏慵不失真,惟餘老态托傳神。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這是一種天才的自信,郭氏自然也有一種作為天才的情緒和心理特征:在生活中,特别是在官場上,對于有些人、有些事,求之過深,對有些人、有些事,又失之大概。但如果不是如此,又如何構成郭嵩焘不同尋常的遭遇,如何擁有他不同常人的發現與洞見,如何成就他在近代曆史的特殊意義?
對此,我們自然不必做類似醫學一樣的解剖。通過這種解剖,來完成對曆史人物的打量,未必高明。何況,郭嵩焘對于自己的處境、自己的所作所為,又是何等了然于心,又有着何等恰當的自我認識。
郭嵩焘曾經在曾國荃六十歲生日時,比較了自己和曾國荃晚年的遭遇,戲言:沅浦在山西履艱巨之任,自己在泰西作清逸之遊;沅浦惠澤披億萬生靈,自己罵名遍九州四海;沅浦讓山西人民俎豆敬奉而秉德做人越來越謙抑,自己讓湖南人民視為糞土而說話越來越高亢;沅浦建功社稷忙不過來,自己身兼衰病正好退休。
一個自我感覺如此清明而不乏自嘲能力的人,一個明知深受傷害而不退避後悔的人,一個在自嘲中如此充滿驕傲的人,我們幾曾得見?
是的,确實如此,他留給我們的是一個芬芳俳恻的靈魂,一種超越了時代的有關中西文明的見識和思想,而不是令人回腸蕩氣的不朽功業。他沒有隻手定乾坤、安社稷,他想安也安不了,他甚至是一個失敗者。但是,當我們深入中國的曆史,特别是近代史,當我們意識到中國社會及其文化的現代轉型,至今為止,如何反反複複,如何步履艱難,而中國的發展依然處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也就是說,中西文化與文明的交通融合,至今并未完成。那麼,你一定會覺得,郭嵩焘在思想和行動上所跨出的那一步,是多麼偉大的一步,是隻有偉大者才可能跨出的一步,是需要我們馨香禮拜的一步。
他的挫折,遠不是個人的挫折,而是這個民族有個性的出類拔萃者的挫折,同時是整個民族的挫折。
政邦藏書架
本書主角郭嵩焘是一個觀念領先時代不止一步的人,以至于他的某些言行連他的莫逆之交曾國藩、李鴻章都難以了解和認同。作為晚清亂局中的一個清醒客,郭嵩焘背負了太多的誤解與罵名。
本書以郭嵩焘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曆為主線,串聯起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晚清軍政重要人物;通過描寫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不同人物的抉擇與命運,反映内外沖突交織的晚清政局。
從今日之視角回望那段曆史,郭嵩焘仿佛一個從現代穿越過去的另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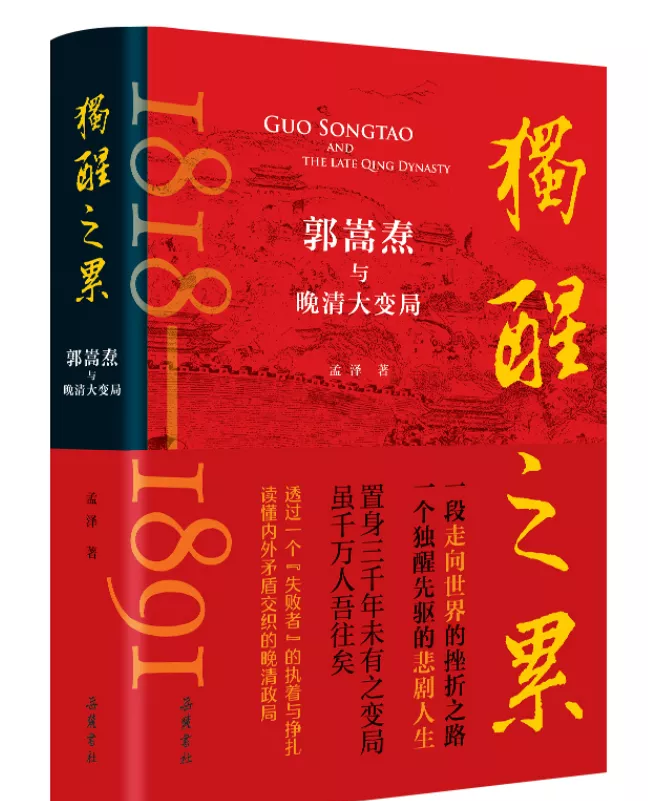
【書名】《獨醒之累:郭松焘與晚清大變局》
【作者】孟澤
【出版社】嶽麓書社
【出版時間】2021年11月